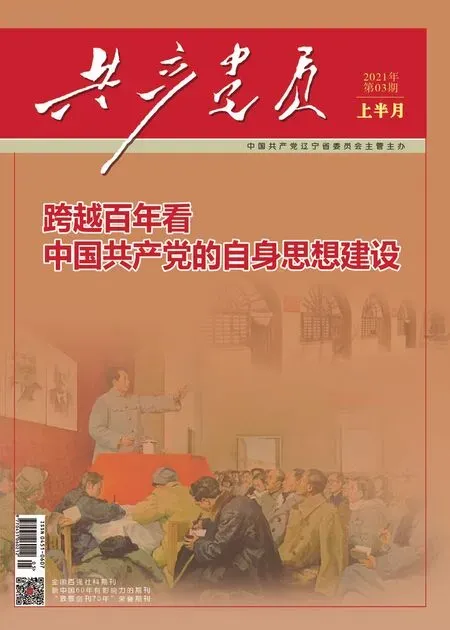樂于薦才的歐陽修
文/江舟
歐陽修是人們所熟知的北宋著名文學家,他在政治上屬于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良派,性情剛直耿介,直言敢諫,在官場上幾經沉浮,先后做過滁州、揚州、潁州的地方官,后來調回京城,在朝廷中歷任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要職。歐陽修在仕途上幾起幾落,歷經坎坷,深知成才之不易,所以特別注重擢用人才,提拔后學。凡是有才華者,不管相識與否、個人政見恩怨如何,歐陽修都會大力扶持薦舉。
王安石自幼喜歡讀書,據說能過目不忘。經弟子曾鞏引薦,歐陽修讀了王安石的詩文,非常賞識,到處為王安石揚名。他寫了一首《贈王介甫》,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把王安石比作李白和韓愈。可惜王安石因為學術觀點原因,并沒有把歐陽修視為知己,不以為然地酬答說:“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他在這里自比孟子,以經術為己任,而不接受歐陽修的贊譽。“熱臉貼了個冷屁股”,歐陽修卻毫不介意,后來他在奏折上推舉三人可以為相,其中便有王安石。
歐陽修推舉為相的還有另外兩人,分別是呂公著和司馬光。呂公著當年極其排斥范仲淹,也是把歐陽修貶謫到滁州的主要參與者;司馬光曾經在一場政治爭論中視歐陽修為異黨,與歐陽修關系并不融洽。然而歐陽修卻能做到唯才是舉,不計個人恩怨。所以宋代詞人葉夢得稱頌歐陽修:“公于晦叔(呂公著)則忘其嫌,于溫公(司馬光) 則忘其議論,于荊公(王安石) 則忘其學術,世服其能知人。”
宋代詞人葉夢得稱頌歐陽修:“公于晦叔(呂公著)則忘其嫌,于溫公(司馬光)則忘其議論,于荊公(王安石) 則忘其學術,世服其能知人。”
歐陽修樂于薦才,給了王安石、蘇氏三父子等一批文壇新人脫穎而出的機會,成就了北宋的文章盛世,對當時乃至后世的文壇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蘇洵27 歲發憤為學,然而卻屢試不中,便燒毀所有文稿,閉門苦讀,很快就精通了六經和諸子百家,下筆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絕,片刻千言。蘇洵與當時的成都太守張安道相熟,在他和兒子蘇軾、蘇轍同赴京城趕考之前,曾經從家鄉眉州去成都求太守張安道為之斡旋。張安道說:“我能力不夠,歐陽修是當今文壇領袖,應該能夠幫上你們。”歐陽修和張安道曾因政見不同而交怨,這時候,歐陽修擔任翰林學士,他很清楚蘇洵父子和張安道的關系,但在見到蘇洵父子三人后,并沒有給他們以冷遇。特別是當歐陽修讀了蘇氏父子的著作之后,極力贊譽說:“后來文章當在此。”并且把蘇洵的文章呈送給皇帝審閱,曾經默默無聞的蘇洵頓時聲名大噪,京城士大夫爭相傳閱并效法他的文章。歐陽修看到蘇軾的應試文章后,贊許地說:“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為了擴大蘇軾在當時文壇的地位和聲譽,歐陽修在嘉祐五年親自保舉他參加殿試,這種滿腔熱情獎掖后學的精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成語“出人頭地”,正是出自歐陽修對蘇軾的評價。歐陽修對老友梅堯臣說:“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意思是說,自己應給這位有才華的青年讓路,讓他有出頭的機會。
不別于親疏、不囿于政見、不執于恩怨,唯才是舉、唯才樂舉,體現了歐陽修坦白的襟懷。襟懷是一種氣度,是一種雅量,也是一種品格。歐陽修樂于薦才,給了王安石、蘇氏三父子等一批文壇新人脫穎而出的機會,成就了北宋的文章盛世,對當時乃至后世的文壇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斯人已去,風范猶存。歐陽修樂于薦才的襟懷,確實值得后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