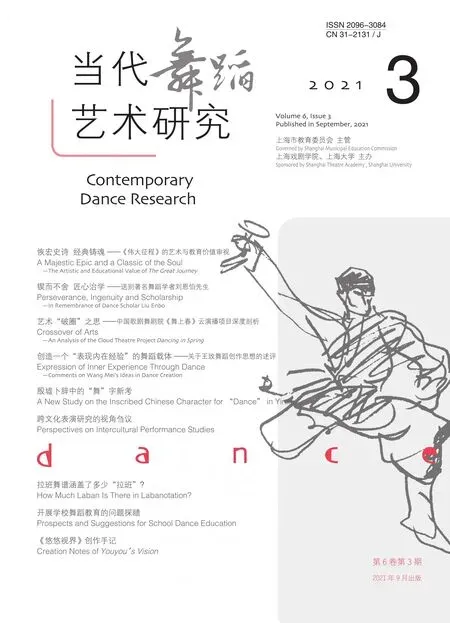跨文化表演研究的視角芻議
孫惠柱
一、跨文化的巴厘舞蹈與梅蘭芳
“跨文化表演/戲劇”(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Theatre)是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流行起來的概念,跨文化表演研究,主要研究西方表演藝術家對各類東方表演形式和故事的借鑒及交流,代表人物從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到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尤金尼奧·巴爾巴(Eugenio Barba)、鈴木忠志(Tadashi Suzuki)等。1991年2月,紐約大學教授理查·謝克納在意大利的貝拉吉奧國際會議中心主持這一領域的首次專題研討會“跨文化表演”(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邀請各國研究這一課題的19位學者、藝術家進行為期一周的深入探討,我亦有幸參加。謝克納在會議的總結論文中這樣概括跨文化表演的多種形態:
一個表演可以在內容上跨文化,如戴維·亨利·黃(黃哲倫)的《蝴蝶君》,或者孫惠柱和費春放從一個中國演員的視角來審視中美文化的《中國夢》;也可以是通過融合不同的形式、文本及表演者來跨文化,如彼得·布魯克的《摩訶婆羅多》和鈴木忠志的《特洛伊婦女》《酒神的伴侶》;也可以因其對“能量”和“在場感”的實驗而跨文化,就像尤金尼奧·巴爾巴的戲劇人類學所做的……[1]
國際上的跨文化表演隨著20世紀跨國交通及大規模移民的發展而興盛起來。20世紀最后二三十年民用航空業的飛速發展使得表演藝術的國際交流日益增多,跨文化表演的研究也越來越多。這意味著研究者要跨越文化或國家的界限,去研究本不屬于自己文化范圍內的“他者”的表演,或者把對自己文化中表演的研究展示給文化“他者”看。早期此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到西方展示的東方表演藝術引起西方人的興趣,例如阿爾托1931年在巴黎世博會上看到印尼巴厘島的舞蹈(本來巴厘島的表演藝術舞、戲不分,阿爾托稱之為“巴厘戲劇”,因為他喜歡不用語言的戲劇)和布萊希特1935年在莫斯科看到的梅蘭芳表演的京劇。梅蘭芳早在1919年就訪問了日本,1930年訪美巡演,讓日本人和美國人更早看到了他的表演,還有一些外國人則是在北京看了梅劇。和現在相比,20世紀前期的跨文化表演交流畢竟少得多,像巴厘島的舞蹈和梅蘭芳的京劇那樣的跨國演出都有很強的民族文化代表性,研究者選題也就相對容易。其實阿爾托和布萊希特的感想式解讀都存在著先入為主的誤讀,因為他們不懂研究對象的語言,缺乏對東方文化的深入了解,也沒機會和藝術家直接交流,所以他們的研究只字不提表演中的故事情節,只聚焦于演員的肢體動作,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阿爾托認為:巴厘島的演員們“勝利地、絕對地展示了導演事先設計好的一切——他的創造力完全不需要文字。主題是含蓄、抽象、極其籠統的,但它們在舞臺上栩栩如生,是因為對姿勢和聲音的全新的運用”[2]。連布萊希特這位劇作家也喜歡分析梅蘭芳舞蹈般的手部動作,他的解讀竟是:“藝術家的目標是在觀眾面前顯得奇特和令人吃驚,而他的手段是用奇怪的眼光看著他自己和他的作品。”[3]
然而,他們“為我所用”的“創造性誤讀”,對歐洲表演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藝術家對跨文化表演藝術形式上的誤讀常常難以避免,但對表演的肢體動作來說往往無傷大雅,甚至還有可能歪打正著,產生有益的效果;可是如果作為戲劇,誤讀了劇情內容就會出現比較大的問題——尤其對于學者來說。所以阿爾托和布萊希特都巧妙地只講表演,避開了以語言為主要媒介的劇情。
阿爾托寫巴厘戲劇①、布萊希特寫梅蘭芳②是兩個跨文化表演研究史上的經典案例,剛好代表了兩種很不一樣的藝術。梅蘭芳憑借高度專業化又經過不斷創新的獨特藝術在大都市競爭激烈的戲曲演出市場中脫穎而出,成為既是票房冠軍又能代表“國劇”的耀眼明星;而巴厘舞蹈是在前現代體制中,社會宗教一體的背景下自然演化而來的社群藝術,那里無所謂專業演員,也無須專門劇場,并不演給買票的觀眾看。據曾去巴厘島學過舞蹈的秦子然博士介紹,直到現在,那里的村民男女老少幾乎都會跳舞,村里有宗教性活動時,常會看到大家一起跳舞,有時在室內,有時在露天的場子上。在比較重要的場合,大家就聚集起來看水平高的人的表演。因為大家都會跳,所以水平只是量的差別,并沒有質的鴻溝③。在印度尼西亞,巴厘舞蹈也和位于政治中心的爪哇舞蹈很不一樣:“在巴厘,舞蹈仍是一種活躍的大眾藝術。……而在爪哇,優秀舞蹈家是從屬于宮廷的專家,通常是王孫本人。而在巴厘,他只是個有天資和有特長的普通村民。他為他社區的聲譽,為他鄰里的娛樂而表演。……爪哇人認為巴厘音樂嘈雜不堪,并把他們的舞蹈貶低為粗俗原始的鄉巴佬的產物。巴厘人在他們的戲劇中,不斷注入新的生命。”[4]以研究印尼社會民俗著稱的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尼加拉:19世紀巴厘劇場國家》一書中指出:“劇場之于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巴厘人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劇場中上演的更多的不是政治的某種集中展演,而是巴厘人日常生活的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講,‘劇場國家’這個意象所指涉的就不僅僅是政治,還是社會。”[5]
梅蘭芳是公認的大師、國寶,我們比較容易理解他的國際影響,但巴厘島上人人會跳的業余舞蹈也能算達到國際水平?這就涉及跨文化藝術的選擇標準問題。巴厘舞蹈并不是阿爾托選擇研究的題目,他只是碰巧看到后喜歡,就寫文章贊揚。選巴厘舞蹈去巴黎演出的是世博會的組織者,可能也有印尼的推薦者參與。1931年的世博會的主題是“殖民地展覽”,按現在的標準肯定屬于“政治不正確”。但歷史無法重來,如果放在現在,我們又會怎么選擇?我國已經在上海開過世博會,各國的展覽基本上都是自己選的。但除此之外,我們也會經常性地挑選國外的藝術來表演,也挑選自己的藝術送出去。當今世界上,跨文化表演的量越來越大,這也給研究者的選題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研究什么?為誰研究?研究成果寫出來給誰看?
關于文章的選題,西方新聞界有個簡單的標準: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也就是要怪異才值得寫。這條出自美國的新聞選題標準早已被引進國內,可以說眾所周知。中國學術界還沒有這樣明說的標準,但近年來流行一些十分相像的說法,求新奇、求前沿,也就是說,必須選最新的題目。求新本來應該是編輯部、出版社歷來的標準,尤其是理工科的標準——不過我國出版界把關不嚴,低水平重復的“論文”“專著”還是太多——尤其是那些付費就能發表和出版的;然而另一方面,在文科領域里,不看研究的真實內涵,把求新僅僅理解為題目本身越新奇越好,也會導致選題的偏頗。
巴厘舞蹈、梅蘭芳的戲曲舞蹈被兩個歐洲人發現的案例,在20世紀30年代都是極新的課題案例,更重要的是,在當時,這兩種表演藝術對印尼和中國來說確實是最有代表性的。八九十年過去后,情況復雜得多。現在,跨文化表演的量這么大,出國學習和考察的機會也很多,出去后很可能覺得“五色令人目盲”,什么都是新的,應該選哪些來學習研究呢?同樣地,對外國人,我們又應該介紹些什么樣的中國表演藝術?如果還要選最有代表性的中國表演藝術樣式來研究,應該找什么?很多人習慣找梅蘭芳那樣的名人作為研究對象,但現在還有公認演技超群又每天登臺表演的表演藝術大師嗎?對于國外藝術,我們還會有興趣去研究阿爾托癡迷的巴厘舞蹈嗎?阿爾托并不怎么理解巴厘舞蹈的內容,但從中看到了他自己苦苦尋找的東西。馬丁·艾思林(Martin Esslin)說:阿爾托被巴厘舞蹈“深深地打動了,他一直想做一種用光、色和肢體動作構成的非語言的神奇戲劇,他這方面的所有想法好像都實現了”[6]。布萊希特看梅蘭芳也差不多④。巴厘舞蹈對我們有什么意義嗎?如今在中國很難看到像巴厘舞蹈那樣普及的社群藝術,最接近的同類項好像就是廣場舞。廣場舞值得研究嗎?
二、跨文化的“廣場舞”
廣場舞的研究價值取決于我們的觀察視角。既是跨文化,自然就有來自不同文化的表演者和研究者,不僅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有不同的視角,在同一個國家,也往往存在不同語言和文化傳統的民族之間視角的差別——有些文化差別根深蒂固,很難逾越,也有些在不斷加速的民族交融中逐漸縮小。不久前的西藏之旅讓我更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
2021年8月2日,我們從林芝坐大巴來到拉薩,我問導游在哪里方便看到街頭的鍋莊舞。導游略帶驚訝地回答我,鍋莊就是廣場舞。他不知道我就是想看藏族的廣場舞——比在上海、北京出現得早得多的廣場舞。導游大概是想,上海戲劇學院的舞蹈教授非常專業,怎么會要看街頭老百姓跳舞?同行的二十多人里只有我和沈亮教授對此有特別的興趣。6日上午,我倆按導游指的路去宗角祿康公園,很遠就聽到了大喇叭放出的藏族音樂,進門看到一大群人——也可以說有好幾群人,在那里跳鍋莊。廣場位于中間,地勢稍低一點,有點像露天的圓形劇場。從里到外有三圈舞者在跳——中間的圓心堆著他們各式各樣的包,整個廣場幾乎沒有一點多余的空間。“劇場”的一邊是帶點坡度的看臺,有幾排簡易的長條凳子供舞者休息、觀者觀看——二者可以隨時轉換身份。另外三邊的平地上各有兩三排人,跟著同樣的音樂、學著“劇場”里的三圈舞者一起舞動。舞者中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的都有,有些穿著完全正規的藏族服裝,氈帽、藏袍、長靴;也有些穿西裝戴墨鏡或者T恤、牛仔褲裝束。但服裝未必能說明他們的民族身份,也看不清藏族人與漢族人的區別。舞者們體型、服裝差別很大,但樂曲相同,大家的舞姿也大同小異。我拍照的時候,沈亮放下背包,找空檔下場插進了舞者的行列,經過短短的模仿適應,很快就融入了內場第三圈的舞隊。后來他告訴我,在融入的過程中,他發現在所有同時跳的舞者中,內場最里邊第一圈的舞蹈最權威最正宗,應該是全場舞者的核心范本,初學者都會學他們的跳法。
想起5年前去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第一次看到街頭的鍋莊舞,那里相對地廣人稀,一個廣場只有一個大圓圈,男女老少都有。我最大的驚喜是看到了青少年——中小學里也有鍋莊,但變了點形式。2009年我曾在報上撰文倡議重編廣播體操,最好男女分開,以便在孩子們每天都要重復練習的動作中融入點戲曲和民族舞的風格,讓他們從小就培養中國特色的肢體美感,而不只是做一套機器人似的活動筋骨的健身操⑤。有些學校做了各種嘗試,但男女分開是個難點,一直沒有大范圍地實施。在玉樹的學校里,我意外地看到了鍋莊風格的民族特色廣播操,無須區分男女風格,超越了性別這一讓很多人糾結的難題。這次在拉薩,我又看到鍋莊這個極具代表性的藏族原生態舞蹈形式,很容易就被并非舞者的漢族教授學會了。跨文化舞蹈無須語言,是不是要比跨文化戲劇容易很多?除了藏族的鍋莊舞,很多民族都有在“廣場”上跳舞的悠久歷史傳統,例如黎力博士論文中研究的湖北土家族從“跳喪”到“巴山舞”“巴山操”的舞蹈⑥、張蔚博士論文中研究的山東的秧歌舞⑦,都是在露天的公共空間,由社群成員經常性地表演。不同民族的“舞種”各有各的具體傳統和規范,這些既可以做分門別類的研究,也可以結合起來做一個全國各民族、甚至世界各國“廣場舞”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沈亮很快學會鍋莊,除了其難度不大,也可能因為藏漢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的緣故。如果要學的是源自歐洲的芭蕾舞、踢踏舞、西班牙舞,就未必會這么容易了。此外,即便模仿其他文化的舞蹈動作不是特別難,但要研究跨文化舞蹈,還是離不開語言文字的詮釋,也不會這么容易。宗角祿康公園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廣場舞研究的個案,這里的鍋莊舞不同于多數大城市的廣場舞,有極其鮮明的藏族特色,又常常會吸引各民族的觀眾參與進來,因而是跨文化的,也應該屬于跨文化研究的范圍。從宗教背景及社群傳統的角度來看,鍋莊舞與印尼巴厘舞蹈的相似程度還超過了與中國其他廣場舞的相似度。要是當年阿爾托在巴黎看到的是中國送去的鍋莊舞,他也會那么癡迷嗎?事實上西藏文化也是不少西方學者很感興趣的研究領域,那么,最早開辟跨文化表演研究這個領域的西方人會用什么樣的視角來看鍋莊舞呢?
三、研究視角的矛盾
我曾和一位歐洲知名教授有過一場歷時數月的爭論,導火線就是研究選題——在對我倆來說都是“他者”的新加坡,什么樣的表演更有代表性、更值得關注和研究?我經常去新加坡開會、教課、導戲,最久的一次,參與了為期3個月的暑期學校教學。在我眼里,文化接近、人口密集的新加坡和中國比較相似,近年來也有不少社區居民自發組織廣場舞之類的草根式表演,大多是對所選理想范本的集體模仿,其學習的過程和經常性地當眾呈現都反映了“和為貴”等中華文化中的傳統價值觀。當地政府也對社群的表演活動給予支持,因為公園、廣場上日常的業余文娛體育活動以相當低的成本就能明顯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這和西方社會有很大的不同。幾年前,我在準備為紐約的英文學刊《TDR戲劇評論》主編一期題為“社會表演學”的專輯時14,寫了一個解釋專輯主題的“征稿啟事”,發給計劃約稿的一些作者。荷蘭烏德勒支大學的尤金·范·厄文(Eugene van Erven)教授在郵件中表示不同意我對社群表演的看法:
孫惠柱的“征稿啟事”區分了中國的“諸如廣場舞、街道演藝社團、校外學生活動等集體的、社群建設性的表演活動”與主要發生在西方或受西方影響的地方的反體制的反叛性示威行動。他認為研究非西方世界的社群建設性表演活動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有助于建設有合理規范的、健康的和諧社會”。但是西方和非西方怎么劃分呢?比方說,2015年4月16日,我目睹了新加坡人(東方還是西方?)Brian Tan Yeo Hui的一個藝術性很高的多媒體表演,其內涵具有激進主義的反叛性,盡管表面上好像不是。表演是在烏德勒支大學的一個名為“游戲、表演、參與”的研討會上,他的現場表演借助幾個月前在新加坡拍的視頻,重現了一個本來很難引人注目的動作。那個作品微妙、詩意、親密,但向人們揭示,新加坡有關公共場所的規則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行動及表達的自由,作品也告訴人們如何創造性地“打擦邊球”。對一般的新加坡路人來說,這個作品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會受到注意的,但對一個新加坡之外的先鋒藝術鑒賞者來說,這個藝術表演就可能很有意思。而對一個開了竅的當地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既激進又藝術的社會表演作品。[7]
顯然,范·厄文這位喜歡先鋒表演的西方學者對廣場舞這類有明顯中國特色的表演不感興趣,他只關注新加坡一個激進主義者去他所在的荷蘭大學的研討會上呈現的多媒體反叛性表演。他沒說這個表演在新加坡有多大代表性,跟那里的社會有多少關系,但承認“對一般的新加坡路人來說,這個作品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會受到注意的”。巧得很,就在同一年,我又去新加坡開會,到那里的頭一天晚上,晚餐后步行去劇場看戲的路上,不經意地看到了很多大媽們在跳廣場舞,她們隨著伴奏音樂,做著盡可能整齊劃一的舞蹈動作——跟中國隨處可見的廣場舞幾乎一模一樣。4天里我沒見到任何激進主義者的“行為藝術”表演,但廣場舞卻每天都看到了。當然,范·厄文就是去了新加坡也很可能看不到廣場舞,或者看到了也視而不見,因為他的眼睛只注意尋找模仿西方范本的反叛性“行為藝術”。可以說他和我都能看到真實的新加坡社群表演,但各自都無意中用不同的“理想社群表演”的標準篩選了我們的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即便如此,我還是要說,根據普通人的常識,社會上廣場舞之類的表演遠比范·厄文所欣賞的那種“微妙、詩意”的反叛性“行為藝術”多太多,因為它們關系到更多人群的日常生活,當然更有代表性。為什么西方人就是對前者毫無興趣,只關心很少有人會注意的后者呢?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他們就像記者一樣,一心想找新和怪的題目來寫;另一方面,人的眼睛習慣于尋找熟悉的同類,他們在非西方文化中偶然看到西方范本的拷貝,更容易眼前一亮。西方教授的學術興趣自然完全是他們的自由選擇,但問題是現在國內不少學生乃至學者也習慣了跟著西方人的學術指揮棒來選題做文章,這就影響到了中國的學術界,因此我這里特別要強調不同于范·厄文們的研究重點。
范·厄文的選題習慣在不少來中國學習的留學生中也十分常見,其原因不僅是文化習慣,還有語言障礙,不愿多下功夫。上海戲劇學院自2013年以來每年招收“跨文化交流學”的國際碩士研究生,他們中不少人在碩士論文選題時,都希望找一些懂英語的中國藝術家,采訪一下他們正在學習的西方先鋒藝術,很容易就能寫出論文來。他們用英文寫論文,如果過多這樣的論文拿到國際上發表,會誤導外國人,以為中國只有拷貝西方的假先鋒派而沒有自己的東西。我常常會勸阻這樣的選題,甚至直言那是“偷懶”的做法。有位來自東歐的學生想寫肢體戲劇,但她只知道歐洲的肢體劇大師如雅克·勒考克(Jacques Lecoq)和艾蒂安·德克魯斯(Etienne Decroux)等人,還有那位已經完全不新但仍有很多人在炒冷飯寫論文的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她想找些正在學西方大師的中國人,寫一篇“歐洲某大師的方法在中國”之類的論文。
我完全理解她的想法,國際交流中難免遇到語言障礙,戲劇工作者常想要繞開語言,肢體戲劇就會成為首選;但表演能繞開語言,而教學研究還是繞不開的。我曾邀請美國布朗大學肢體戲劇專家丹尼爾·斯特恩(Daniel Stern)教授前來授課,他恰好是德克魯斯的學生,但他在中國的教學卻因理念不同而效果不佳。他的課人數上限為16人,可是第一天來了六七十個人。我希望他考試擇優,他卻用抓鬮決定人選,不肯承擔老師的責任——認真觀察每個人再做出選擇。第一天課上完后,旁觀的學生要他第二天再次抓鬮重新選人,他不顧我的反對意見又抓了鬮。我們請他來給學生進行專業技能的提高,他卻只是讓所有人都伸伸腿、彎彎腰、開開心。這樣顯然不可能創作出好作品。第二年我還是請他來,我知道他教學還是有一套的。例如上課先來個“大忽悠”:這堂課沒有任何規則;事實上隨著課的進程一點點提出要求(也就是規則),而且越收越緊——這就是他的“技巧”。但第二年我要求他提前一周來以日奈的劇本《女仆》為基礎,做一個有人物、有情節的肢體劇。他雖然接受了,卻要每個學生輪換扮演劇中的三個角色,讓大家都“嘗嘗味道”,直到最后還是一人多角、一角多人。這雖然算是表演“民主”,但誰也認不清誰在演誰,觀眾也看得莫名其妙。他只是在游戲式的課上讓學生用肢體表達一點意思,就沒想做出藝術品來,玩玩就夠了,沒讓學生學到實在的本領,以后再沒請他來上課。我也沒讓學生們(都是碩士生、博士生)去寫“斯特恩方法在中國”之類的論文,這樣的題目雖然新,卻并無實際的用處,對我們的表演藝術教學沒什么幫助。
這位美國教授的例子在表演領域并不是孤例。當然我也沒有因此就小看了肢體戲劇,肢體戲劇是我們需要學習的一種重要戲劇形態,但要和我們自己的創作結合起來才好。我看好《短打契訶夫》系列的加拿大肢體劇編導迪安·吉爾莫(Dean Gilmour)——也是德克魯斯的傳人,想請他來我們學校,以魯迅為原型做個類似的肢體劇。但還沒來得及落實,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先請他去合作了,做出了《魯鎮往事》,非常出色。上海師范大學的唐劍威老師看了吉爾莫的戲后,借鑒其方法自創中國故事的肢體劇,把莫言的《蛙》等小說改編成以肢體為主、含少量臺詞的新型戲劇,也很精彩。我把他推薦給想研究肢體戲劇的那位留學生,她去唐老師的劇組做了幾個月“田調”,果然發現不少好材料,寫出了研究中國肢體劇的好論文,這就比僅僅介紹中國人如何恭敬地拷貝外國方法有價值得多。
四、我們更需要什么樣的研究
中國人去國外留學、考察,會遇到更多選擇的問題。如美國的大學絕大多數是綜合性的,學生選課的自由度比國內多許多倍,翻開一厚本課程介紹,有“選擇焦慮癥”的留學生往往不知所措。有時候外國教授按他們的思路要求學生必須修某一門課,也不一定都合適。挪威一個大學有門課名曰“創造性舞蹈”(Creative Dance),竟是讓大家在音樂中隨心所欲地擺動肢體,怎么做都算舞蹈。有個去交流一年的碩士生問我怎么辦,我說最好修別的課,這種沒有標準放任自流的課也許有類似“人咬狗”的新聞價值,但并沒有藝術或學術的價值,也不值得就此寫論文。歐洲的高校體制不同于美國,專業訓練在獨立戲劇院校里進行,但很難考進。綜合性大學的戲劇課大多是通識性課程,學生多多益善,并不以培養戲劇人才為目標。挪威人可以在那樣的課上隨便玩,而對中國學生來說,一年時間很寶貴,要選擇學習符合各自目標、更有價值的東西。
什么樣的外國表演更有價值、更值得學習研究呢?要看其在所在國家的文化中是否有代表性,還要看對我國表演藝術的發展是否有幫助,當然也要看是否新——避免重復別人已經做過的工作,做無效勞動。這幾個標準時常會相互沖突,特別是“新”這個新聞界的標準常常有太大的誘惑力,導致一些研究者忽略代表性和為我所用這兩個更重要的標準,唯“新”為上,一窩蜂地就一些貌似新奇的題目做大同小異的表面文章,其實多半是照搬西方話語,拾人牙慧,并沒有什么新的發現,而真正對我國的文藝事業發展有幫助的好東西卻很少有人研究。我最熟悉的領域是戲劇,但也看了紐約、倫敦舞臺上大量的舞蹈表演——大多不是在純粹的“舞蹈會”(Dance Concert)上,而是在數量大得多的音樂劇中。音樂劇是當前國內演藝業中發展最快的藝術形式,編舞極其重要,然而很少看到有人對音樂劇的舞蹈進行深入研究。這個位于兩種藝術樣式之間的題目有點尷尬,舞蹈人認為是戲劇界的事,不懂戲劇不好研究;戲劇人又認為它屬于舞蹈,不懂舞蹈也難以置喙。這確是實際的困難,但還有一個原因更值得引起學界注意。且不說音樂劇中的舞蹈,就連音樂劇本身,研究的人也很少,其原因在于世界上掌握戲劇話語權的著名西方教授多半只喜歡找新奇怪異、曲高和寡的先鋒派新東西來研究發表論文,基本上瞧不起音樂劇這種太通俗、太大眾、成功得太久的藝術樣式——占了紐約劇壇的大半壁江山,還不斷地佳作迭出。我們的學者多半并不知道那些著名西方教授選擇先鋒派的語境,不顧中國戲劇人有學習音樂劇成功經驗的急切需要,很多人盲目地瞧不起音樂劇,只想拷貝那些無須食人間煙火的西方教授的思路。
近幾年來有很多人發表大同小異的論文,吹捧某部把莎劇切得支離破碎的“沉浸式戲劇”,誰也說不清那個所謂的“戲”到底講些什么,但怎么寫都不會錯,因為那本來就是在玩一個便于媒體炒作的花招,談不上有什么意思,連文盲語盲也可以任意評論而不會有人來挑錯。與此同時,倫敦西區、百老匯、外百老匯這些年來上演的那么多有深刻社會意義的好戲,包括連演四五年仍然火爆的《漢密爾頓》那樣的現象級音樂劇則很少有人去認真研究。因為要研究首先必須能聽懂、看懂舞臺上呈現的內容,能理解劇中的音樂和舞蹈,還要研究其社會歷史背景,了解觀眾的反應,這都是不肯下苦功只想短平快發論文的研究者絕不會去碰的題目。
如果說集音樂、舞蹈、戲劇之大成的百老匯音樂劇是有代表性的美國表演藝術,值得我們認真研究;那么廣場舞可以說是中國有代表性的表演藝術嗎?難道我們的專業藝術不如業余的?藝術為人民服務,表演藝術更要為當下的民眾服務;看一種藝術是否有代表性,要看從業人員和服務對象兩方面的人數。美國音樂劇不但演職人員多,更重要的是觀眾面特別廣,很多戲駐演數月、數年,演職人員還去世界各國巡演;此外各地中學業余劇社也常常學演音樂劇,很多百老匯音樂劇專門做了簡化的青少年版。而當下我國專業團體普遍的演出模式卻是“新戲短演”,一個戲在一個劇場演出一兩場就結束是常態,能有多少觀眾看?談何服務大眾?談何影響力、代表性?有些人還喜歡自詡精英,沾沾自喜于曲高和寡的“小眾藝術”,其實連小“眾”都談不上。不過,老百姓不愿買票進劇場,并不意味著中國的表演藝術就衰亡了,因為有社群集體娛樂的文化基因,眾多業余愛好者自己組織起來跳廣場舞、唱歌唱戲,因此我國的社群文藝倒比西方發達國家熱鬧得多。
鄒昊平博士2010年的博士論文《城市社區群眾文娛社團研究》⑧聚焦于上海地區各式各樣的社群表演,其中最大的一塊兒就是各色舞蹈隊的活動。那時候“廣場舞”這個說法還未流行,但她已經在論文中預測了社群業余舞蹈活動的遠大前景,幾年后果然廣場舞蔚為大觀,成為全國城鄉最重要的群眾文藝活動。如果有外星人像《三體》所寫的那樣從星際空間窺探地球,一定會首先注意到這一驚人的人類活動——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中國人幾乎同時、又分成一群群地整齊地跳舞。在我主編的紐約《戲劇評論》專輯中,鄒昊平和司徒嘉怡博士合寫了專門研究中國廣場舞的長篇論文,得到了學刊總主編謝克納教授以及眾多讀者的好評14。廣場舞反映了什么樣的中華文化特點?它對其他國家會有什么意義嗎?它下一步將會如何發展?5年前“廣場舞研究”已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之一,但它的意義絕不是一個政府課題所能窮盡的。一個涉及這么大人口基數的文藝活動,從各個角度做深入的研究絕對必要。
其實,百老匯那部全劇無聲不歌、無動不舞的《漢密爾頓》的最大特色“嘻哈”(hip-hop)本來也是一種極草根的業余愛好者的“廣場歌舞”——中文“廣場舞”譯成英文為dancing in public square——公共空間的舞蹈。誰說我們各民族的廣場舞就不可能變成中國音樂劇舞臺上的特色舞蹈?當年我們是怎么一步步創造出民族歌劇和芭蕾舞劇的經典《白毛女》的?今天,我國的音樂劇要做到像百老匯那樣既極專業又極大眾,也絕離不開草根藝術的滋養。但草根藝術未必會自動地轉化升級,這就是研究者和藝術家的用武之地了。
【注釋】
①參見:ARTAUD A.On the Balinese Theatre[M]//ARTAUD A.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New York:Grove Press,1958:53—73.
②參見:BRECHT B.Verfremdung effects in Chinese acting[M]//Brecht on theatre: the development of an aesthetic.New York:Hill and Wang,1964:91—99.
③參見:2021年8月20日對秦子然的采訪,2021年夏她作為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碩士生赴巴厘島修課三周。訪談人:孫惠柱;訪談地點:上海。
④參見:孫惠柱.從“間離效果”到“連接效果”:布萊希特理論與中國戲曲的跨文化實驗[J].戲劇藝術,2010(6):100—106.
⑤參見:孫惠柱.廣播體操能否更具“中國儀態”:兼談文化遺產如何進入日常生活[N].文匯報,2009—06—16(5).
⑥參見:黎力.湖北長陽土家族“跳喪”儀式戲劇的表演研究[J].劇作家,2007(6):73—75.
⑦參見:張蔚.鬧節:山東三大秧歌的儀式性與反儀式性[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⑧參見:鄒昊平.城市社區群眾文娛社團研究[D].上海:上海戲劇學院,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