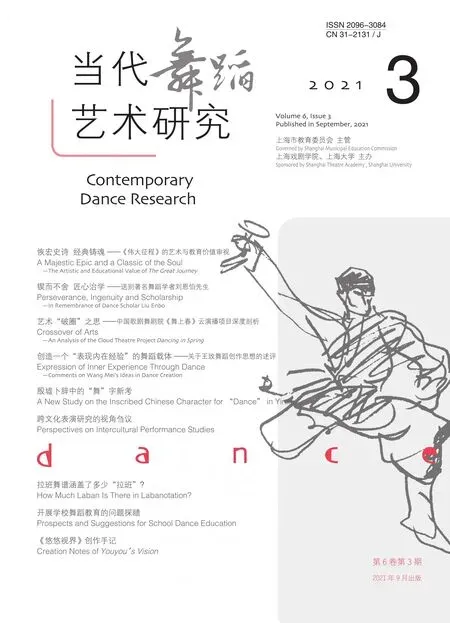現代性·審美·主體:當代中國舞蹈發展的文化關鍵詞
——兼評仝妍《時代嬗變的身體言說:當代中國舞蹈 發展的文化思考》
閆楨楨
“當代中國舞蹈的發展”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研究視閾。在這樣一個研究范圍內想要確立某種思考的線索,并以此勾連起百年間的中國舞蹈實踐,確實充滿了挑戰。一方面,搭建這樣的線索需要深厚的舞蹈史學基礎,要能夠宏觀地把握近百年來舞蹈藝術在中國的發展脈絡;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經歷的變遷涵蓋從民族國家的初建到極端政治話語的鉗制,從改革開放到全球化的信息時代,短短百年,滄海桑田。這也令當代中國舞蹈無論在形態、媒介還是觀念和技術上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想要把這些復雜的變遷統合到一條相對穩定的學術思路上來,實在困難重重。
仝妍教授在《時代嬗變的身體言說:當代中國舞蹈發展的文化思考》(以下簡稱《文化思考》)一書中顯然已經對上述的問題有了長時間的思考和權衡。既然無法從一個視角來“限制”百年間林林總總的舞蹈藝術現象,那么將不同的視角并置于研究成果中,讓它們彼此應和、激蕩、補足,也許是更加明智的選擇。所以,《文化思考》為當代中國舞蹈的研究設立了三個坐標:文化、審美與主體。這三個坐標的設置頗具深意:如果缺乏宏觀的文化視野,多樣的審美形態迭變就會亂象紛呈;而僅僅考慮文化語境的整體變遷,就難免將豐富的審美形態化約為缺乏活力的被動“反映”。要在二者之間達成溝通,就不能脫離具體的舞蹈藝術實踐,而藝術實踐的主體——舞蹈家,乃是對“作品——時代”或者說“審美——文化”感受最敏銳的群體。他們通過個體化的經驗敏銳地感受著時代的文化脈動,用審美形式將其凝結在舞蹈作品中。這也是全書第三個坐標的意義所在——“人”作為藝術實踐的主體,在歷史、文化與審美過程中的選擇與能動性。
于是,“現代性”“審美特征”與“藝術家主體”這三條線索交織構成了《文化思考》的觀察視野,也勾勒出當代中國舞蹈發展進程中“身體言說”的宏觀脈絡。
一、現代性:當代中國舞蹈的文化語境
“現代性”這一概念對于當代中國文藝的研究來說,可謂已經具有了某種“背景”意味。在各門類藝術的當代發展中,“現代性”無疑已經成為繞不開的理論預設。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①曾經嘗試為“現代性”(或者說主要是“現代性”的“后果”)給出一個簡潔的描述。
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17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在外延和內涵兩方面,現代性卷入的變革比過往時代的絕大多數變遷特性都更加意義深遠。在外延方面,它們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系方式;在內涵方面,它們正在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1]1—4
在吉登斯看來,“現代性”在社會秩序上完全不同于過往的社會,這些社會秩序塑造了現代社會的生活形態,從最廣闊的世界圖景到最個性化的私人體驗,無不產生了深刻的變遷。
這也就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舞蹈身處的最為宏觀的文化語境提供了基本的參照和理論前提:當代中國舞蹈的建構是與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緊密關聯的,換句話說,當代中國舞蹈的建構乃是當代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的文化表征之一。
在我看來,《文化思考》為探索當代中國舞蹈發展所尋覓的這一理論基點是非常準確的。舞蹈作為一種人類的文化行為,古已有之。然而,當我們談論“當代中國舞蹈”時,這個概念所指向的藝術觀念及其實踐早已超越了簡單的舞蹈行為,而是一種高度審美化的身體動態的組織形態,它不僅具有可觀測的、相對穩定的作品形態,還指向特定的審美與文化內涵。
這也是《文化思考》選擇《民國時期(1912—1949)舞蹈發展的歷史意義》一文作為全書第一篇文章的原因。文章認為:
從總體上看,民國時期的舞蹈主要有四大類型:藝術啟蒙舞蹈、社會娛樂舞蹈、學堂美育舞蹈和民主革命舞蹈,這些舞蹈體現了民國時期社會文化發展的激變,民國時期的舞蹈從啟蒙到革命的本質性轉變,積淀了新中國舞蹈藝術的傳統“基因”。[2]3
作者看到,新中國舞蹈藝術的傳統雖然在理論上包含著全部的過往,但在藝術實踐與觀念基礎上,則更加直接地源于“中西文化雜處以及傳統與現代觀念的交織性沖撞”[2]3。這種獨屬當代的“交織性沖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舞蹈的專業化。社會生產組織的高度專業化分工,本就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近代以前,中國傳統舞蹈藝術就當代對于“舞蹈”的形式界定來看,尚不足以被視為“專業化”的“舞蹈”分工類型。當代中國舞蹈的起步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歐美舞蹈進入國民、特別是知識階層的視野。隨著清末民初外交活動的開展,一些出使外國的官員與留學海外的學生通過各種形式的出版物記述了國外正在盛行的舞蹈形式(其中包括芭蕾舞、交際舞、民間舞等)。這些關于舞蹈形式的描寫,使得國人對現代意義上的舞蹈有了最初的了解。吳曉邦、戴愛蓮、賈作光等中國當代舞蹈的奠基者和先驅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舞蹈的觀念,并通過自己的舞蹈藝術實踐,奠定了中國當代舞蹈的發展基礎。
當然,完善的專業化體系尚需更多時間才能構建起來,從吳曉邦、戴愛蓮等人的舞蹈實踐來看,當代中國舞蹈的專業化啟蒙,最初主要體現為舞蹈形式的獨立和舞蹈觀念的建立。戴愛蓮、賈作光以中國傳統的民俗舞蹈為資源,將其中的舞蹈進行提煉和加工,按照當代劇場化舞蹈藝術的形式創作了大量具有民俗氣息,同時又具有審美性和傳播性的藝術作品。吳曉邦則更加強調舞蹈藝術的時代性,他接受了歐洲現代舞的觀念,認為舞蹈應該更多地表達現實生活,主張創作“能與社會發生直接關系的舞蹈作品”[3]。舞蹈形式的獨立要求舞蹈在創作與表演方面的“專業化”,也就是要求從事舞蹈創作與表演的人群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舞蹈不再是一種人們可以信手拈來的自娛行為,而是要求建立某種吉登斯意義上的“專家系統”。對這種“專家系統”的信賴則是現代舞蹈觀念的重要基礎。隨著“專家系統”的建立,當代舞蹈的存在方式(舞臺作品)、表現形式(審美化)、文化價值(意義表達)與古代舞蹈產生了根本性的差異。
第二,舞蹈的大眾化。“大眾”概念的內涵就其發展來說,可謂異常復雜。具體到學術研究領域,“大眾”的概念往往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聯系在一起,正如“Mass Culture”與“Culture Industry”的內在聯系一樣。②具體到中國當代的“大眾”概念,至少需要從兩個層面來考慮:1942年以來以工農兵為核心的“大眾”與改革開放40年間逐漸形成的、受市場化經濟影響的“大眾”。
對當代舞蹈之“大眾化”的理解亦當涵蓋上述兩個層面。中國當代舞蹈的發展與作為社會主導力量的工農兵“大眾”的確立有著緊密聯系,特別是當代中國獨具特色的舞蹈類別——“中國民族民間舞”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工農兵“大眾”作為文化主體力量的藝術成果。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大眾”的內涵逐漸從“工農兵”式的政治身份轉向以“消費者”為代表的經濟身份。與之相應,來自受眾群體文化需求的壓力與國際舞蹈視野的開闊,共同推動當代中國舞蹈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展開了“舞蹈觀念更新大討論”③。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社會文化消費的形式與范圍不斷豐富、擴大,“大眾”的內涵已經越來越接近“Culture Industry”。從旅游文化與舞蹈產業的結合,到時尚品牌與舞蹈創意的聯合;從楊麗萍的《云南映象》到張藝謀的《對話·寓言2047》……當代中國舞蹈的產業化、市場化趨勢已經成為發展的主流。正是在“大眾”內涵的變遷中,我們得以窺見當代中國舞蹈變遷的又一內在驅動力量。
第三,舞蹈的民族化。在《民國時期(1912—1949)舞蹈發展的歷史意義》一文中,作者以戲曲舞蹈和“邊疆舞蹈”為例,指出民國時期舞蹈發展的民族化取向。在作者看來,“民族化的理論取向是擺脫現代化的‘世界性’,簡單地說,民族化就是以特定的傳統風格展示共性的時代風貌”[2]15。事實上,對于當代中國舞蹈而言,傳統風格的構建本身就是民族化的主要任務。當代中國舞蹈的民族化過程不僅包含對外來舞蹈形態的吸收、對中國古代舞蹈資源的提煉,同時也必須要應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多種舞蹈形態共存的狀況。
自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古典舞”“中國民族民間舞”的形態構建,可以說是當代中國舞蹈“民族化”的核心成果。構建過程的曲折自不待言,直至今天,以“中國古典舞”“中國民族民間舞”為名的舞蹈形態及其觀念理路依舊面臨種種質詢與考驗。這些質詢和考驗自有其價值,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代中國舞蹈的“民族化”正是在“中國古典舞”“中國民族民間舞”的建構過程中完成的。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中國舞蹈的訴求由“民族化”日益轉向“本土化”。如果說“民族化”的核心任務在于構建屬于中國的舞蹈形態,那么“本土化”的主要目標則更傾向于凸顯一種不同于西方歐美文化的美學與倫理取向。前者重在構建“對象”,而后者意在提供“價值”。在我看來,當代中國舞蹈構建民族化舞蹈形態的歷史任務雖不能說已經完成,但頗有建樹:在國際化的語境中,我們已經擁有“中國古典舞”“中國民族民間舞”這樣的民族舞蹈形態。然而對今天的中國舞蹈來說,已經到來的本土化挑戰似乎更加嚴峻。如果說中國舞蹈的“民族化”構建完成了“身體言說”的符號,那么“本土化”就是要進行“身體言說”的表達。這也正是全球化語境中,當代中國舞蹈不得不面對的時代課題。
二、審美特征:當代中國舞蹈的價值取向
“現代性”作為一種文化語境,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舞蹈的從業和接受群體、發展趨勢提供了宏觀的視野。該書也沒有忽略那些趣味橫生的細節。正是豐富多樣的細節,構成了當代中國舞蹈中那些值得研究的審美特性,為我們理解藝術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聯提供了最為生動的案例。
仝妍在《文化思考》一書的“中編”分析了那些在她看來能夠代表當代中國舞蹈的審美形態,這些看似各自獨立的文章集結在一起,呈現出了當代中國舞蹈獨特的審美發展路徑。作者在《論中國當代舞蹈的價值取向》一文中從審美價值、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三個角度來把握當代中國舞蹈的價值取向。這當然是為了在單篇論文的有限篇幅內盡可能地把握論題而采取的操作方式。
事實上,當代中國舞蹈的價值取向正是通過其審美特征而呈現的。從戴愛蓮、吳曉邦的舞蹈實踐開始,當代中國舞蹈的審美建構就沒有走一條“為藝術而藝術”的形式主義道路。戴愛蓮廣泛挖掘與整理中國各民族的民俗舞蹈并按現代舞臺藝術的審美原則和審美形態加以呈現,目的在于“為建立中國舞蹈成為獨立的劇場藝術”邁出“堅定的第一步”。④
舞蹈的歷史,開始先有原始舞發展為土風舞,以后進展到美化的舞蹈,如果我們要發展中國舞蹈,第一步需要收集國內各民族的舞蹈素材,然后廣泛地綜合起來加以發展。……這些舞蹈介紹到舞臺上來本來太簡單,為了編制形式上的考慮,多多少少有些經過改變了的。有幾個節目照原本演出,有些是僅直接或間接的素材加以發展改編的。……將來希望能夠給予一些對于舞蹈工作有興趣的人以可能的便利,對中國一切舞蹈做一次完整的學習,以這些材料,為舞臺建立起新的中國現代舞;同時,還得開展土風舞運動,使之遠而且廣,要每個人為娛樂自己而舞,從日常生活的煩惱得到解放。[4]
可見,戴愛蓮不是要創造一種能夠凸顯舞蹈之形式魅力的舞蹈形態,而是要構建獨屬“中國”的現代舞蹈藝術。這種舞蹈形態未必要在形式上達到至高的審美境界,卻必須是屬于“中國”的。這不正是當代中國舞蹈實踐從其發生伊始,就將民族性作為首要價值的證明嗎?而對于吳曉邦來說,“新舞蹈”的意義更重要的是用舞蹈應和與表達時代的精神。“1935年后,我把這種現代舞蹈引進中國,我是想通過這種新型的舞蹈形式去揭露反動統治的罪惡。新舞蹈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形象的語言,它能夠起到組織群眾和鼓舞群眾的作用,它會像暴風一樣煽動人民群眾的陣陣怒火,席卷阻礙中國走向科學和民主道路上的舊思想、舊信仰、舊風俗、舊習慣勢力。”[5]正是吳曉邦灌注在“新舞蹈”中的革命熱情,使得當代中國舞蹈在其發軔之時就將自身系于歷史與現實,努力貢獻自身的社會價值。
1949年之后,中國舞蹈的發展延續“民族化”“革命化”“現實化”的道路。在審美方面,“大眾化”(這里主要是工農兵大眾)和“政治化”成為舞蹈發展的主導原則。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舞蹈的審美意識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我們完全可以把20世紀80年代的“舞蹈觀念大討論”看作是當代中國舞蹈審美意識的自覺時期。仔細回顧這一時期的舞蹈作品,那些昂揚的時代氣質、自由的人文精神無不滲透在作品的審美訴求中:《黃土黃》中向外放射的躍動,《殘春》中向生命深處尋覓的顫動,《黃河》中與音樂織體對位應合的動作組織……正是舞蹈作品中蓬勃高漲的審美意識,蘊含著國家高速發展時期的時代精神,同時也在承擔著新的時代所賦予舞蹈的價值取向——一個融入世界的、開放的、快速發展的中國,在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型中,努力去尋覓民族文化之根,去構建屬于新的歷史時期的精神家園。
21世紀的今天,曾經在舞蹈審美表達中著意強調的那些超越性的宏大“價值”日趨消散。這似乎是一個經歷了“后現代”洗禮之后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疲憊不堪而又花團錦簇的,是嘈雜喧嘩而又內在沉寂的。“審美”迅速被消費和市場攫取,只有那些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的藝術產品才是值得被“生產”的,“價值”只在消費和市場的意義上才能夠得到認同。當代中國舞蹈逐漸進入所謂的“大制作”時代——舞臺技術與視覺奇觀成為最受市場與消費認可的審美形態。以“先鋒”“實驗”“極簡”種種概念為依托的審美建構,不正是“大制作”“奇觀化”的一種辯證性“癥候”嗎?而這種攜帶著某種“反抗”意味的審美特征同樣只能以消費、市場作為其立身的基礎——無論創作者賦予作品怎樣的精神性、思想性,“吸引”受眾的方式已經被市場所浸染:或者出奇出新,提供文化符號;或者拼貼雜燴,提供感官愉悅。當下中國舞蹈創作在審美上的豐富、多元與在價值取向上的單一、匱乏,并非藝術家之過。當一種社會結構中的“價值”只能被貨幣、資本來加以衡量時,我們又怎能期望藝術家們赤手空拳地營造審美“烏托邦”呢?
對于當代中國舞蹈而言,審美從來都是與價值緊密聯結的,甚至可以說二者是內在統一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無法剝離一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而去抽象地談論審美本身。審美從來都是價值的組成部分,是價值的表征形式,當然,也可能是對價值的反思。
三、藝術家主體:當代中國舞蹈的個體表達
當我們論及“文化語境”與“價值取向”時,研究的核心更多地集中在整體地把握特定歷史時期的藝術趨勢方面。在這樣的研究視野中,盡管構成時代特征的藝術作品林林總總,卻常常被歸于特定的“趨勢”或“特征”的總體性判斷。說到底,雖然特定時代的藝術作品的確會呈現出相似或相近的形式特性,不過忽略作為藝術家的個體性和創造性,也會極大地減損研究的敏銳度。
這也是《文化思考》在第三部分選擇聚焦于特定藝術家的原因。從賈作光、胡果剛到萬素,再到王亞彬,這些藝術家分處于當代中國舞蹈發展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成長背景。在他們的藝術創作中,一方面是時代賦予個體藝術家的“任務”,其間銘刻著難以避免的歷史印記;另一方面是他們自身蓬勃的創造之力,這些創造之力在與歷史責任的碰撞中迸發出獨特的藝術光芒。
作為當代中國舞蹈的早期從業者,賈作光這一代舞蹈人普遍受到國外(歐美、日本、蘇聯為主)舞蹈藝術的影響,形成了與中國古代禮樂、女樂傳統不同的舞蹈觀念。20世紀30—40年代的國家境遇,使得像賈作光一樣的舞蹈家對現實生活報以極大的藝術熱情。不同于吳曉邦的“新舞蹈”,賈作光選擇了一條與區域化、地方化民俗舞蹈緊密相連的創作之路。“蒙古族牧民套馬、馴馬式的雙肩動作,以及婦女擠奶時雙手與雙肩的動作……要將這些生活動作舞蹈化,就必須掌握它的全部特點和標準。賈作光將這個轉化過程視為一種‘規范化’。所謂舞蹈語匯的‘規范化’,就是要求舞蹈的民族風格、特點及其表現形式的準確性,也即舞蹈語匯的標準普及;是將生活中產生、又在生活中經過無數民族藝術家長期發展形成的、能鮮明體現本民族生活和性格的舞蹈特點固定下來。”[2]205這樣的“規范化”處理,在當代中國舞蹈的發展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當代中國舞蹈對少數民族舞蹈最具代表性的舞臺化提煉方式,進而生成“改造、重塑中華民族這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核心力量”[2]206。
可以說,以賈作光、胡果剛為代表的藝術家們構成了當代中國舞蹈的“形塑”力量。這一代舞蹈先驅們奠定了當代中國舞蹈最初的主流形態、分類格局與創作觀念。他們所創造的成果,一方面為當代中國舞蹈的創作提供了基礎的規范與框架,另一方面也為后來的藝術家們劃出了界限。
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提出了“影響的焦慮”,來形容存在于后輩詩人與前驅詩人之間的“誤釋”(misprision)與“逆反”(antithetic)。在他看來,“一部詩的歷史就是詩人中的強者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間而相互‘誤讀’對方的詩的歷史”[6]。這種“影響的焦慮”并不僅限于詩人,幾乎所有的藝術家都會在尋求創造性突破的過程中,感知到這種來自傳統的影響的焦慮。舞蹈家們也概莫能外。
當一種藝術形式已經產生了廣為認同的規范與框架,逾越規范或“溢出”框架就難免攜帶著危險。作為當代中國舞蹈頗具個人特色的中、青年編導,萬素和王亞彬選擇了不同的“逾越”與“溢出”方式。
萬素的創作走的是一條“破壞”與“融通”之路:民族民間舞、古典舞、芭蕾舞,都在她的現代舞創作中匯為一體,同時破壞任何先在的規則。在她的創作中,不僅被視為壁壘的舞種界限消弭無形,就連舞蹈的界限也頻頻遭遇挑釁(例如她在作品中使用沙畫、裝置、多媒體、說唱、戲劇等多種舞臺形式)。這種創作觀念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方式:一種是從作品的訴求出發,去評價多種舞蹈形式是否在同一個意義框架內扮演了合理的角色;另一種則是從舞蹈的約定性或風格出發,去判斷作品是否與主題契合。不同的評價方式自然會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這也是萬素作品總是在兩極口碑之間跳躍的原因。仝妍用“審美自律性”與“審美主體性”來把握萬素的作品,這為我們提供了頗具借鑒意義的參考。事實上,對于萬素這樣的創作者來說,期待她符合“規矩”恐怕注定是要落空的。在她的創作之路上,已經有來自前人建構得足夠強大的傳統之影響,只有不斷沖破,才能消解焦慮,即使這種“沖破”不得不攜帶著某種“回歸”的內涵,也依舊趨于一種具有“新質”的“重復”。
作為青年一代編導的代表人物之一,王亞彬的身上有著不同于前輩編導(如萬素等)的特質。如果說在萬素的作品中,“自我”是執拗地存在于每一個形式細節背后隱匿而堅定的“硬核”,那么在王亞彬的作品中,“自我”則飄忽在每一次尋覓“自我”的沖動間,帶著三分欲望七分迷茫。
在王亞彬的作品中,對“自我”的尋覓涉及“生長”“朋友”“守望”等多個主題。正如仝妍所說:“作為一名青年女性舞者、編導,臺前幕后的王亞彬始終處于‘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中:‘自我’是個人的職業、年齡、性別身份與當代中國的時代、民族、文化身份等;‘他者’是身體、時間、空間等劇場內外的表演場域……因此,王亞彬的舞蹈創作中有著各種或隱或顯的對話性”[2]229。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筱燕秋”(舞劇《青衣》中的角色)看作王亞彬的舞臺鏡像:一個始終在各類象征性坐標(女性、母親、妻子、戲癡……)的縫隙間游走,努力尋求自我的個體。對于內(尋求主體位置)、外(符合象征秩序)交困的個體來說,對話是一條尋覓之路,而這條路通往何處?也許并不重要。這條路本身,似乎已經是個體對抗焦慮的竭力一搏。
如何理解當代中國舞蹈的精神?這些以“爆破者”形式出現的、永恒復歸的硬核自我,以及徘徊在“理性者”形象中的、精疲力竭的迷茫自我,不正是當代中國舞蹈最具身化的隱喻嗎?
結語
“當代中國舞蹈”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實在顯得過于繁雜龐大。然而,把握自身所處的“當下”幾乎是任何一個研究者都無法抵擋的誘惑。
舞蹈藝術的特性使其顯得過于鮮活,以至于我們總是習慣性地依賴經驗、直覺、情緒去接近、感知、把握它。仝妍教授強調“文化思考”,其深意也正在于此——聆聽“時代嬗變的身體言說”,當然離不開經驗、直覺與情緒,離不開那些新鮮可感的藝術形態,離不開那些撥動心弦的瞬間感動。但是,將這些活生生的肉身體驗置入“文化思考”的框架,也許才是“研究”的題中之義。當代中國舞蹈作為一種“現代性的后果”之表征,一方面用豐富鮮活的審美表達承擔著時代賦予其的文化使命,另一方面也在用自身獨特的方式記錄與折射出中國社會的現代性進程。
人們常常用“提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來嘲笑一種超越客觀限定性的妄想。可是,那些對自己所處時代既敏感又充滿疑問的“妄想者”們,也正是人類百折不撓的求知精神的繼承者吧。
【注釋】
①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將現代性的動力機制問題闡述為三個基礎,即時空的分離、抽離化機制(脫域機制)與制度反思性。其中,“抽離化機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專家系統”。吉登斯認為:“專家系統,指的是由技術成就和專業隊伍所組成的體系,正是這些體系編織著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物質與社會環境的博大范圍。……融專業知識于其中的這些體系卻以連續不斷的方式影響著我們行動的方方面面。……我不得不信賴他們的能力,但是與其說是信賴他們,還不如說是更信賴他們所使用的專門知識的可靠性,這是某種通常我自己不可能詳盡地驗證的專業知識。”參見: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24.
②參見:趙勇.大眾文化的概念之旅、演變軌跡和研究走向[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312—320。該文對西方“大眾文化”的概念流變與理論資源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
③“舞蹈觀念更新大討論”是指在1985年的“八五思潮”中,舞蹈界開展的一系列以傳統與現代為論爭焦點的討論。參見:任文惠.轉型與重構:審美現代性視野中的“舞蹈觀念更新大討論”[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9(3):14—20。
④參見:戴愛蓮.發展中國舞蹈第一步:1946年在邊疆音樂舞蹈大會上的講話[M]//仝妍.時代嬗變的身體語言:當代中國舞蹈發展的文化思考.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