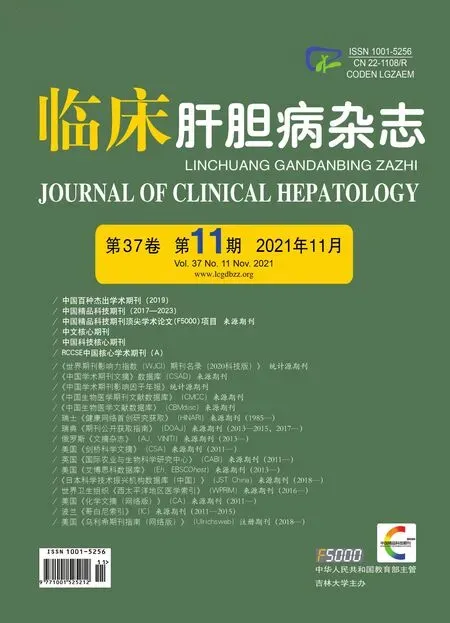藥物性肝損傷病理學(xué)的特征及鑒別診斷
楊永峰
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附屬南京醫(yī)院(南京市第二醫(yī)院),南京大學(xué)教學(xué)醫(yī)院 肝病科,南京 210003
藥物性肝損傷(DILI)是常見(jiàn)的肝臟疾病之一,組織病理學(xué)診斷對(duì)確立診斷、病情評(píng)估、預(yù)后判斷均起重要作用。然而DILI的組織病理學(xué)表現(xiàn)多種多樣,不同致肝損傷藥物、不同肝損傷類型的DILI病理特征不同,同樣的病理特征既可以見(jiàn)于DILI也可以見(jiàn)于其他疾病,部分藥物可引起多種組織類型DILI。因此DILI的病理診斷需要緊密結(jié)合臨床。本文對(duì)DILI病理特征和鑒別診斷作一綜述。
1.DILI組織病理學(xué)模式分類
DILI按發(fā)病機(jī)制分為劑量依賴型和特異體質(zhì)型,按病程急緩分為急性和慢性,按臨床特征分為肝細(xì)胞損傷型、膽汁淤積型、混合型、肝血管損傷型,按照組織病理學(xué)改變分為炎癥壞死型、膽汁淤積型、脂肪肝和脂肪肝炎型、血管損傷型和輕微病變型[1]。
1.1 炎癥壞死型 炎癥壞死型是最常見(jiàn)的DILI病理模式,表現(xiàn)炎癥和/或肝細(xì)胞壞死。DILIN(DILI Network)中超過(guò)1/3病例表現(xiàn)為不伴膽汁淤積的炎癥壞死,如果計(jì)入伴輕度淤膽病例,則接近1/2[2]。根據(jù)炎癥壞死的分布特征可分為急性肝炎型和慢性肝炎型,根據(jù)病變程度可分為輕微和顯著。需要注意的是組織學(xué)特征分類的急性和慢性,和臨床病程分類的急性和慢性并不是同一概念。
急性肝炎型以小葉內(nèi)肝細(xì)胞損傷、炎癥、壞死為主,肝實(shí)質(zhì)損傷重于匯管區(qū)損傷,多伴有肝細(xì)胞凋亡、灶性分布淋巴細(xì)胞和吞噬細(xì)胞浸潤(rùn),正常肝竇結(jié)構(gòu)排列紊亂(小葉排列紊亂)。DILIN中1/4病例表現(xiàn)不同程度的3區(qū)(靠近中央靜脈的區(qū)域)融合性壞死[2]。急性肝炎型也可伴匯管區(qū)和界面炎、匯管區(qū)漿細(xì)胞和嗜酸性粒細(xì)胞浸潤(rùn),其程度和肝實(shí)質(zhì)損傷成正比,需要和自身免疫性肝炎(AIH)鑒別[3]。急性肝炎型嚴(yán)重時(shí)可伴輕度淤膽,損傷模式上多歸類為淤膽型肝炎或急性肝炎伴淤膽。多種藥物可引起急性肝炎型DILI,包括免疫檢查點(diǎn)抑制劑[4]、英夫利昔單抗和其他腫瘤壞死因子α拮抗劑、異煙肼、非甾體抗炎藥、精神治療藥物等。3區(qū)凝固性壞死是對(duì)乙酰氨基酚所致DILI的經(jīng)典病理模式,壞死組織中可見(jiàn)輕微炎癥、吞噬細(xì)胞和少量中性粒細(xì)胞浸潤(rùn)[5]。不伴明顯炎癥的單純性3區(qū)壞死較少見(jiàn)于藥物性損傷,此種病理類型需注意排除血管病變引起的缺血性損傷。急性肝炎型DILI的重癥病例表現(xiàn)氨基轉(zhuǎn)移酶10~30倍增高,常伴黃疸。
慢性肝炎型組織學(xué)表現(xiàn)和慢性病毒性肝炎類似,以匯管區(qū)炎癥為主,肝實(shí)質(zhì)損傷較輕,通常不伴淤膽,炎癥明顯時(shí)可伴肝細(xì)胞玫瑰花結(jié)。某些藥物,如呋喃妥因引起的慢性DILI可能出現(xiàn)纖維增生,甚至匯管-匯管間的橋接纖維化。部分引起急性DILI的藥物也可致慢性DILI,如呋喃妥因、米諾環(huán)素、異煙肼、阿托伐他汀等[6]。慢性DILI臨床上常表現(xiàn)氨基轉(zhuǎn)移酶中等程度增高,膽紅素多正常,需要和AIH、病毒性肝炎等鑒別。
炎癥壞死型DILI的特殊類型還包括肉芽腫型肝炎和肝竇內(nèi)淋巴細(xì)胞浸潤(rùn)型肝炎。肉芽腫型DILI伴有顯著的肉芽腫性炎癥,肉芽腫通常較大,不伴中心壞死。肉芽腫形態(tài)可類似結(jié)節(jié)病而易于辨認(rèn),也可邊界不清而難以辨認(rèn),或呈微肉芽腫表現(xiàn)。肉芽腫型DILI需要和結(jié)節(jié)病、真菌或分枝桿菌感染等其他肉芽腫性肝損傷鑒別。肝竇內(nèi)淋巴細(xì)胞浸潤(rùn)型指肝竇內(nèi)串珠樣排列的淋巴細(xì)胞和Kupffer細(xì)胞浸潤(rùn),但是不浸潤(rùn)肝細(xì)胞板,不伴明顯的肝細(xì)胞損傷,是EB病毒感染的常見(jiàn)組織學(xué)模式,也可見(jiàn)于部分DILI,如苯妥因鈉,通過(guò)EB病毒原位雜交可以鑒別。
1.2 膽汁淤積型 肝組織膽汁淤積機(jī)制有兩種基本形式,即膽汁積聚和膽汁酸積聚。膽汁積聚時(shí)肝細(xì)胞、毛細(xì)膽管、細(xì)膽管、小葉間膽管內(nèi)可見(jiàn)到膽汁,也可在吞噬細(xì)胞(尤其3區(qū))內(nèi)發(fā)現(xiàn)膽汁顆粒;細(xì)胞內(nèi)膽汁顆粒易和含鐵血黃素、脂褐素等其他色素顆粒混淆,特殊染色有助于鑒別。膽汁積聚的位置有助于病因鑒別,DILI時(shí)通常以毛細(xì)膽管和肝細(xì)胞膽汁淤積為主,不會(huì)出現(xiàn)細(xì)膽管和膽管膽汁積聚。慢性膽汁淤積可導(dǎo)致匯管區(qū)周圍肝細(xì)胞內(nèi)膽鹽積聚,引起細(xì)胞漿淡染和空泡改變,稱為“羽毛樣變性”;這些肝細(xì)胞內(nèi)還可出現(xiàn)銅積聚,通過(guò)直接或間接銅染色有助于識(shí)別;膽鹽積聚的肝細(xì)胞還可出現(xiàn)CK7免疫組化陽(yáng)性。
DILI膽汁淤積包括3種基本組織病理模學(xué)模式,即混合性淤膽型肝炎、膽管損傷和單純性淤膽。混合性淤膽型肝炎表現(xiàn)為匯管區(qū)和/或肝實(shí)質(zhì)炎癥伴毛細(xì)膽管及肝細(xì)胞淤膽,可見(jiàn)于30%病例,是最常見(jiàn)的模式。膽管損傷嚴(yán)重時(shí)可致膽管消失綜合征[7]。單純性淤膽表現(xiàn)為肝細(xì)胞和毛細(xì)膽管膽汁淤積而炎癥壞死輕微。部分淤膽型肝炎可呈慢性過(guò)程,組織學(xué)可出現(xiàn)纖維增多和細(xì)膽管增生反應(yīng),多伴有不同程度膽管損傷,需要和原發(fā)性膽汁性膽管炎、原發(fā)性膽汁性肝硬化等慢性肝內(nèi)淤膽性肝病鑒別[8]。
1.3 脂肪變性和脂肪肝炎型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LFD)、酒精性肝病(ALD)組織學(xué)表現(xiàn)為肝細(xì)胞大泡脂肪變性,是最常見(jiàn)的肝臟疾病。臨床診斷DILI的患者如發(fā)現(xiàn)大泡脂肪變性病理改變,要首先排除NAFLD、ALD等基礎(chǔ)疾病。部分藥物也可引起類似NAFLD的病變,如他莫昔芬、甲氨喋呤,脂肪變性于停藥后可緩解[9]。疑診DILI的患者如組織學(xué)表現(xiàn)大泡脂肪變性,還要再仔細(xì)尋找提示DILI的其他證據(jù),如淤膽、顯著炎癥、血管損傷、大量凋亡肝細(xì)胞等。
部分藥物可干擾脂代謝或改變外周胰島素抵抗,這也解釋了藥物引起肝細(xì)胞脂肪變性的機(jī)制。尤其導(dǎo)致線粒體損傷的藥物易致脂肪變性,形態(tài)特征以小泡脂肪變性為主。彌漫的肝細(xì)胞小泡脂肪變性大多和藥物或毒素相關(guān)。引起小泡脂肪變性的藥物如水楊酸鹽、胺碘酮、利奈唑胺、丙戊酸;非藥物性原因如環(huán)境毒素、酒精、妊娠脂肪肝。
1.4 血管損傷型 藥物可引起從門靜脈小分支到肝靜脈大分支的任何水平肝血管損傷,臨床表現(xiàn)閉塞性門靜脈病(obliterative portal venopathy,OPV)、Budd-Charis綜合征、肝竇阻塞綜合征(sinusoidalobstruction syndrome,SOS)、結(jié)節(jié)性增生性再生(nodular regenerative hyperplasia,NRH)。口服避孕藥等可引起凝血異常的藥物可導(dǎo)致肝靜脈血栓,受累肝組織可出現(xiàn)大范圍的出血和不伴炎癥的肝細(xì)胞壞死。含有吡咯環(huán)結(jié)構(gòu)的中藥(如土三七和千里光)、抗腫瘤藥物等可引起SOS,組織學(xué)表現(xiàn)肝竇擴(kuò)張、充血、肝細(xì)胞板萎縮[10]。包括DILI在內(nèi)的急性肝炎可引起不伴出血的中央靜脈炎,已有文獻(xiàn)[4]報(bào)道免疫檢查點(diǎn)抑制劑可引起中央靜脈炎。DILIN病例中靜脈血管內(nèi)皮炎較內(nèi)皮損傷和SOS更為常見(jiàn)[2]。
除門靜脈、肝竇、肝靜脈系統(tǒng)的明顯損傷外,部分藥物還可表現(xiàn)肝竇和門靜脈的輕微損傷。奧沙利鉑、嘌呤類似物和NRH相關(guān);奧沙利鉑還可引起門靜脈損傷,嚴(yán)重可致OPV;NRH和OPV均可出現(xiàn)肝竇擴(kuò)張。
1.5 輕微病變型 部分DILI組織病理學(xué)表現(xiàn)輕微而易被忽略,如前文所述的NRH和OPV,由于形態(tài)學(xué)改變不顯著,難以辨認(rèn)而易被忽略。其他輕微組織病理學(xué)包括肝輕微匯管區(qū)或小葉炎癥,少量凋亡小體,輕度脂肪變性,肝細(xì)胞類毛玻璃樣改變,肝細(xì)胞內(nèi)的包涵體、脂褐素沉積、糖原沉積等,需要在閱片時(shí)仔細(xì)辨認(rèn)。輕微型肝損傷除可見(jiàn)于DILI外,也可見(jiàn)于各種急性肝病的恢復(fù)期、慢性肝病的緩解期、其他系統(tǒng)和全身疾病影響等多種情況,需結(jié)合臨床資料以助鑒別[11]。
2 肝組織病理學(xué)對(duì)DILI的診斷價(jià)值
肝損傷性疾病表現(xiàn)“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一因多果”是指同一病因可引起不同病理?yè)p傷模式[12],如HBV感染可引起急性肝炎、慢性肝炎、淤膽型肝炎、亞大塊壞死、肝硬化等多種病理?yè)p傷模式;即使是同一藥物,也可能引起不同病理模式肝損傷。“多因一果”是指同一組織病理學(xué)改變可見(jiàn)于多種病因,如以匯管區(qū)炎和界面炎為主要特征的慢性肝炎病理模式可見(jiàn)于慢性病毒性肝炎、AIH、Wilson病、AIH樣DILI等多種病因[13]。因此,對(duì)大多數(shù)肝損傷性疾病的病因診斷來(lái)說(shuō),組織病理學(xué)并非“金標(biāo)準(zhǔn)”,病理和臨床緊密結(jié)合才能使其“金標(biāo)準(zhǔn)”的含金量接近百分之百。
對(duì)DILI診斷來(lái)說(shuō),目前各個(gè)學(xué)會(huì)的指南推薦仍然是臨床診斷,RUCAM評(píng)分是最常用的DILI診斷工具,組織病理學(xué)檢查并非必須。筆者的工作經(jīng)驗(yàn),臨床懷疑DILI,但存在如下情況時(shí)需肝穿刺病理檢查:(1)DILI診斷不肯定;(2)DILI可能不是唯一致肝損傷原因,不能用一元論解釋的肝損傷;(3)多藥物接觸史,不能確定具體致肝損傷藥物;(4)治療效果不符合預(yù)期;(5)慢性DILI;(6)預(yù)后評(píng)估需要。
組織病理學(xué)檢查對(duì)DILI診斷可起到以下作用。
2.1 明確診斷 肝毒性藥物接觸史是診斷DILI的前提條件,然而并非所有病例都能清晰的問(wèn)出藥物接觸史,尤其一些臨床常用且常規(guī)認(rèn)為安全性高的藥物,在尋問(wèn)病史時(shí)可能被醫(yī)生和患者忽略,此時(shí)組織學(xué)可提供重要的診斷線索。如筆者2017年曾診斷1例反復(fù)轉(zhuǎn)氨酶增高1年余的中年男性,肝穿刺病理表現(xiàn)肝竇擴(kuò)張,影像不支持肝血管疾病,反復(fù)追問(wèn)后患者近1年有胃復(fù)安使用史,且胃復(fù)安可引起肝竇擴(kuò)張模式的DILI,停用胃復(fù)安1個(gè)月,患者肝功能持續(xù)正常,證實(shí)為胃復(fù)安引起的DILI;另有1例中年女性,表現(xiàn)為膽汁淤積型肝損傷,肝穿刺顯示膽管消失,追問(wèn)病史患者述過(guò)去常于牙痛時(shí)自服阿莫西林,而該藥可引起膽管缺失綜合征[14]。其他類似情況包括保健品、化妝品、食物添加劑、環(huán)境因素等所致的廣義概念上的DILI,患者和醫(yī)生都有可能忽略這方面病史,很多病例都是在組織學(xué)提示DILI可能后,再深挖病史而確診。筆者2019年發(fā)表的一組不明原因肝病病理最終診斷中,DILI占25.1%(118/470),其中大部分是用藥史比較隱匿而難以診斷[15]。
DILI既可以單獨(dú)發(fā)病,也可以和其他的病因同時(shí)致病,還可以發(fā)生在慢性肝病基礎(chǔ)上。當(dāng)基礎(chǔ)病過(guò)程隱匿且診斷困難時(shí),容易被DILI的“一元論”解釋掩蓋基礎(chǔ)病,如AIH基礎(chǔ)上的DILI等。當(dāng)臨床遇到反復(fù)發(fā)作的“DILI”,或肝細(xì)胞損傷型DILI停用可疑藥物后肝功能仍反復(fù)異常,此時(shí)要想到AIH基礎(chǔ)上DILI可能,及時(shí)的肝穿刺組織學(xué)檢查可避免延誤診斷。
此外,對(duì)于慢性DILI有必要肝穿刺病理檢查。DILI肝損傷多為急性過(guò)程,尤其是肝細(xì)胞損傷型DILI,多在3~6個(gè)月內(nèi)恢復(fù)。然而部分DILI在停用致?lián)p傷藥物后,肝功能仍然持續(xù)異常6個(gè)月以上,表現(xiàn)慢性肝損傷,甚至可能向肝硬化進(jìn)展,難以和其他慢性肝病鑒別。慢性DILI多有其特定病理類型,包括AIH樣DILI、肉芽腫性肝炎,OPV、SOS、NRH、肝紫癜、藥物性脂肪肝(炎)、肝細(xì)胞內(nèi)沉積物、單純性淤膽、膽管消失綜合征、藥物誘導(dǎo)的肝臟腫瘤等,且每種模式都有其常見(jiàn)的致?lián)p傷藥物,組織學(xué)檢查有助于明確診斷[6]。實(shí)際上對(duì)所有原因不明確的慢性肝損傷都有組織病理學(xué)檢查的必要。
2.2 明確疾病預(yù)后 組織病理學(xué)有助于評(píng)估預(yù)后和幫助臨床決策。除炎癥壞死程度和DILI預(yù)后直接相關(guān)外,有研究[16]顯示纖維增生、小泡脂肪變性、細(xì)膽管淤膽、膽管反應(yīng)、中性粒細(xì)胞浸潤(rùn)、閉塞性門靜脈改變和預(yù)后不良相關(guān),而嗜酸性粒細(xì)胞浸潤(rùn)多出現(xiàn)于輕癥病例。此外,如組織學(xué)表現(xiàn)前述的慢性DILI特征,多提示疾病遷延不愈。
3 病理醫(yī)生對(duì)臨床醫(yī)生的要求
3.1 對(duì)肝穿刺樣本的要求 肝損傷性疾病病變分布不均一,組織學(xué)檢查時(shí)要有充足的組織樣本量才能減少取樣誤差。有研究[17]證實(shí),小于10個(gè)匯管區(qū)的肝穿刺組織會(huì)導(dǎo)致炎癥程度和纖維化分期的低估。對(duì)不明原因肝病病因診斷也是如此,充足的樣本量才能獲取足夠的診斷信息。肝組織匯管區(qū)到中央靜脈之間的平均距離約0.8 mm,穿刺組織的直徑達(dá)到0.8~1 mm才可能獲得完整的小葉結(jié)構(gòu),使用16G穿刺針可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大多數(shù)指南推薦肝穿刺要使用16G穿刺針,取出肝組織長(zhǎng)度不小于20 mm,這樣才能保證完整匯管區(qū)在10個(gè)以上;如果穿出肝組織長(zhǎng)度小于20 mm,建議繼續(xù)穿第二條組織[18]。經(jīng)頸靜脈肝穿刺在國(guó)內(nèi)已逐漸開(kāi)展,該技術(shù)拓寬了肝穿刺的適應(yīng)證,使部分有嚴(yán)重凝血障礙的患者也能穿刺,然而頸靜脈肝穿刺所用的針比較細(xì),通常是18~19G,通常建議穿4條組織才能滿足樣本量需求[19];此外頸靜脈肝穿刺組織在拉出過(guò)程中極易碎裂,操作時(shí)要盡可能輕柔。
樣本處理方面,常規(guī)的組織學(xué)檢查包括HE染色,膠原纖維、銅、鐵、糖原等的特殊染色,免疫組化等,這些檢查常規(guī)福爾馬林固定即可。對(duì)于懷疑線粒體功能障礙,或需鑒別遺傳代謝性疾病時(shí),需另取0.3~0.5 mm肝組織2.5%戊二醛固定液固定,以備電鏡檢查。
3.2 臨床病理溝通的重要性 肝損傷性疾病組織病理學(xué)表現(xiàn)“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病理密切結(jié)合臨床才能最大可能得出最終診斷。從病理診斷角度,如果組織學(xué)模式考慮DILI,臨床資料也支持DILI,且和文獻(xiàn)報(bào)道的可疑藥物所致DILI的組織學(xué)模式一致時(shí),可以確立DILI的診斷。反之,如果僅僅組織學(xué)考慮DILI而臨床不支持DILI,或組織學(xué)模式既見(jiàn)于DILI又見(jiàn)于其他疾病,或組織學(xué)模式不能用可疑藥物一元論解釋時(shí),均需要結(jié)合臨床資料進(jìn)一步甄別,具體鑒別診斷的步驟見(jiàn)圖1[20]。準(zhǔn)確的病史、充分的臨床資料不僅對(duì)DILI的病理診斷,對(duì)所有肝損傷性疾病的病理診斷都至關(guān)重要,臨床醫(yī)生一定要提供充足的臨床資料。當(dāng)病理診斷和臨床不符時(shí)臨床醫(yī)生要及時(shí)質(zhì)疑,并和病理醫(yī)生充分討論;有條件的單位可選派經(jīng)驗(yàn)豐富的臨床醫(yī)生學(xué)習(xí)肝臟病理并直接參與臨床病理討論和病理診斷,使病理和臨床能夠密切結(jié)合[21]。

圖1 疑診DILI時(shí)的組織病理學(xué)鑒別路徑[20]
利益沖突聲明: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