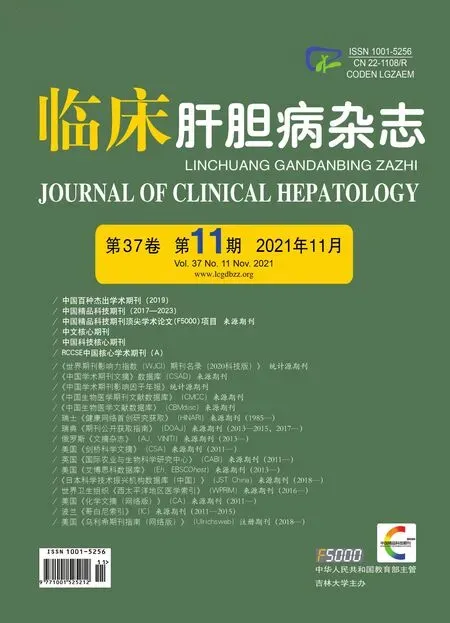正常免疫小鼠新型人源肝癌異種移植模型的構建
唐慧昕,李珊珊,洪 豐,畢研貞,王全義,張小蓓,程姝敏,段鐘平,舒振鋒,陳 煜,6
1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 肝病中心四科,北京 100069;2上海美峰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上海201203;3 青島市立醫院 感染科,山東 青島 266011;4 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 肝病研究所,山東 濟寧 272000;5 濟寧醫學院臨床學院,山東 濟寧 272000;6 肝衰竭與人工肝治療研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69
原發性肝癌是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被列為全球人類腫瘤相關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嚴重威脅人類健康[1]。肝癌早期診斷仍較困難,確診時多為晚期,術后5年生存率僅約14%[2]。盡管某些治療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仍在迅速增加[3]。因此建立能夠模擬臨床特征的肝癌動物模型對于肝癌的診治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人源腫瘤組織異種移植(patient-derived xenograft,PDX)模型是指將患者的新鮮腫瘤組織或腫瘤細胞通過原位或異位等方式移植到小鼠體內,依靠小鼠體內環境生長的一種異種移植模型[4-6]。PDX模型目前被認為是最接近臨床患者的腫瘤動物模型,基于臨床新鮮肝癌腫瘤標本建立的PDX模型,可以準確地反映肝癌患者的腫瘤特性。但PDX模型的構建通常選用高度免疫缺陷的小鼠,以排除機體免疫反應,但基于此模型進行腫瘤發生機制以及抗腫瘤藥物的研究必然存在局限性,尤其是研究通過免疫系統來發揮作用的藥物。因此,如果能在正常免疫小鼠體內成功構建人肝癌PDX模型,將對肝癌的精準醫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microcarrier 6[7-9]是一種新型微載體,由可正電化有機復合多聚物組成,呈多層孔狀條索樣,相互交聯卷曲形成有足夠空間的“迷宮”樣不規則結構。孔徑大小、表面正電荷密度、載體顆粒大小可通過化學合成調節,是純有機化合物,不易污染,不含雜質,具有低免疫原性、生物兼融性及可代謝性等特點,可為細胞生長提供穩定的三維微環境。microcarrier 6內部足夠的空間解決了細胞生長營養和代謝廢物濃度不均的問題,同時,由于microcarrier 6“迷宮”樣不規則結構可以短時間內起到屏障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擋免疫細胞對腫瘤細胞的直接殺傷。另外,使用基質細胞衍生因子-1α(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α, SDF-1α)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對微載體進行修飾后,可加速血管形成,誘導血管長入,為腫瘤的快速生長提供血供營養[7]。
本研究從新鮮肝癌組織中分離提取出原代肝癌細胞,與mocrocarrier 6共培養后,將肝癌細胞-微載體復合體植入小鼠體內,在正常免疫小鼠體內成功構建了新型人肝癌PDX模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主要制劑 膠原酶B購于美國Sigma公司,RPMI 1640培養基、胰酶、胎牛血清、紅細胞裂解液、青鏈霉素均購于美國Gibco公司,兔抗人CK8/18、GPC-3、Hep單克隆抗體均購于英國Abcam公司,異氟烷購于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microcarrier 6由美國ELYON BIOTECHNOLOGIES LLC公司提供。
1.2 實驗動物 C57BL/6小鼠75只,雄性,6~8周齡,體質量22~25 g,購于濟南朋悅實驗動物繁育有限公司(實驗動物生產許可證編號:SCXK 20140007、實驗動物使用許可證編號:SCXK 20180002),飼養于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SPF級實驗動物中心。
1.3 標本信息 5例新鮮肝癌組織標本均來自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肝膽外科,腫瘤標本的獲取經過了患者本人及家屬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僅供實驗研究。患者詳細信息見表1。

表1 肝癌相關PDX模型的病例信息
1.4 人原代肝癌細胞的獲取 以RPMI 1640為溶劑配制濃度為0.05%的膠原酶B溶液,用孔徑0.22 μm的濾器濾過除菌,置入37 ℃恒溫水浴鍋水浴30 min。將新鮮肝癌組織標本放入RPMI 1640培養基中沖洗3次,用剪刀將標本剪為體積約為1 mm×1 mm×1 mm的碎組織塊,加入0.05%膠原酶B溶液,置入37 ℃恒溫箱內消化1 h后取出,加入RPMI 1640稀釋后反復吹打混勻,提取上清液,用孔徑70 μm的濾網過濾后,以1000 r/min離心8 min。裂解紅細胞后即可得人原代肝癌細胞。殘余組織塊中加入0.05%膠原酶B繼續消化,按上述方法依次提取膠原酶B消化2、3、4 h的人原代肝癌細胞。
1.5 人原代肝癌細胞與microcarrier 6共培養 將microcarrier 6浸泡于75%酒精24 h,1×PBS緩沖液清洗3遍,加入含10%胎牛血清的RPMI 1640培養基,調整微載體懸液濃度為300 μg/mL,于37 ℃恒溫箱中孵育24 h備用;用SDF-1α和VEGF對微載體進行修飾,濃度均為100 ng/mL,孵育時間為12 h。收集所有時間點提取的人原代肝癌細胞,取臺盼藍計數活細胞數>95%,取含10%胎牛血清的RPMI 1640培養基重懸細胞,調整細胞濃度為2×107/mL。1/2肝癌細胞懸液與修飾好的microcarrier 6懸液混合(體積比為1∶1)放于15 mL離心管中,另1/2肝癌細胞懸液加入等體積的含10%胎牛血清的RPMI 1640培養基放于15 mL離心管中,另取等體積的microcarrier 6懸液加入等量的含10%胎牛血清的RPMI 1640培養基放于15 mL離心管中,三管樣本均置于37 ℃、5% CO2培養箱中培養24 h。
1.6 正常免疫小鼠肝癌PDX模型的建立 5例標本共用75只C57BL/6雄鼠,每例15只。實驗分為3組,細胞對照組、微載體對照組和實驗組,每組5只小鼠。細胞對照組小鼠單純接種肝癌細胞懸液,細胞數為2×106個/只(按共培養前肝癌細胞懸液的計數);微載體對照組小鼠單純接種空載體懸液,微載體量為30 μg/只;實驗組小鼠接種肝癌細胞-微載體復合體懸液,每只小鼠接種2×106個細胞、30 μg的微載體(按共培養前肝癌細胞懸液的計數)。共培養24 h后,用1×PBS緩沖液清洗肝癌細胞、空載體和肝癌細胞-微載體復合體3遍,加入1×PBS緩沖液輕輕混勻,使最終體積跟清洗前體積一致,放于冰上備用。異氟烷麻醉小鼠,用套管針在小鼠右腋下皮下接種移植,按分組依次進行接種,200 μl/只。
1.7 觀察指標及病理學檢查 皮下接種移植的腫瘤,每周測量腫瘤最長直徑(a)和最短直徑(b),計算腫瘤體積,腫瘤體積(V)= 1/2×a×b2,繪制腫瘤生長曲線。待腫瘤最長直徑達1 cm,頸椎脫臼處死小鼠,完整剝離腫瘤組織,用4%中性甲醛固定,石蠟包埋切片,常規HE染色。按試劑盒說明采用EnVision二步法進行免疫組化染色。染色結果判定:陽性顆粒定位于腫瘤細胞質內,陽性細胞數<5%為陰性,陽性細胞數≥5%為陽性。
1.8 倫理學審查 本研究方案經由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2021B029,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同時經由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動物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2021B029,符合實驗室動物管理與使用準則。
1.9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22.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兩組間比較采用Fisher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于microcarrier 6體外構建人原代肝癌細胞三維培養體系 剛分離出的原代肝癌細胞呈球形,幾乎全為單個細胞,折光性強(圖1a);microcarrier 6為不規則團狀或長梭狀,質地疏松,內部有大量孔隙(圖1b);原代肝癌細胞與修飾過的microcarrier 6共培養24 h后光鏡下可看到肝癌細胞可以很好的貼附在microcarrier 6上,達到飽和狀態,外周可看到不規則細胞團(圖1c)。

注:a,原代肝癌細胞;b,微載體microcarrier 6;c,原代肝癌細胞與微載體microcarrier 6共培養。
2.2 基于microcarrier 6在正常免疫小鼠體內建立肝癌PDX模型 75只雄性C57BL/6小鼠均采用皮下接種法將肝癌細胞-微載體復合體植入小鼠體內,5例患者的肝癌細胞接種小鼠后有3例對應的小鼠出現了成瘤,此3例實驗過程中,各組小鼠食欲、毛發、體質量無明顯變化,僅實驗組小鼠1周后活動度稍減少,各組沒有小鼠死亡;細胞對照組和微載體對照組小鼠從實驗開始到實驗結束均無小鼠長出腫瘤,成瘤率均為0;實驗組小鼠在接種移植后5~7 d即可觸及皮下包塊,實驗組共有12只小鼠可觸到皮下包塊,總成瘤率為80%,與細胞對照組和微載體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2)。移植瘤生長迅速,1~2周是生長高峰期,移植瘤體積迅速增大,2周左右肉眼即可觀察到皮下有隆起包塊,2~3周時移植瘤體積變化不大,達到穩定期,20 d左右體積可達到0.5~1 cm3(圖2、3)。移植瘤組織易與周圍組織分離,形態不規整,多為圓形或橢圓形,周圍血供豐富,顏色灰白色或灰紅色為主(圖3)。

表2 3例成功成瘤實驗中小鼠成瘤時間和成瘤率

圖2 移植瘤生長曲線

圖3 肉眼觀察荷瘤小鼠體內移植瘤
2.3 移植瘤組織病理學結果 原代肝癌組織石蠟切片在光鏡下可見核大深染、異形性明顯、雜亂排列的腫瘤細胞(圖4a);移植瘤組織在光鏡下可見大量雜亂排列、異形性明顯的細胞,細胞呈圓形或橢圓形,排列呈巢狀或片狀,核大且大小不一,染色質粗,核仁明顯,可見病理性核分裂象。間質中可見大量淋巴細胞以及尚未被清除的microcarrier 6周圍的異物反應。肝癌細胞向周圍浸潤生長,伴有明顯壞死,主要位于腫瘤中央,移植瘤組織中新生毛細血管豐富,多位于腫瘤邊緣(圖4b)。

注:a,原代腫瘤;b,移植瘤。黑色箭頭,異形細胞;紅色箭頭,未被清除的微載體;藍色箭頭,血管。
CK8/18、Hep、Gpc-3主要表達于癌細胞膜和胞質中,是肝癌細胞特異的標志物。對移植瘤組織進行免疫組化染色發現CK8/18、Hep、Gpc-3均為陽性表達(圖5),進一步證實異形性細胞為人源肝癌細胞。

注:a,CK8/18;b,Hep;c,Gpc-3。
3 討論
原發性肝癌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常見惡性腫瘤之一,目前肝癌的治療方式如肝切除術或肝移植術等僅適用于早期患者,隨著分子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的進展, 中晚期肝癌患者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治療選擇[10-13],但目前仍缺乏能完全治愈肝癌的有效方法。研發針對肝癌的新型有效治療手段均需要動物實驗來進行模擬,所以建立一個模擬人肝癌的動物模型顯得尤為重要。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肝癌模型的研究不斷深入,目前已逐步建立小鼠肝原位移植性動物肝癌模型、誘發性肝癌模型、轉基因動物及人類肝癌異種移植模型的肝癌模型[14-15]。
現有的動物模型在研究人類癌癥的發生和發展上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和工具,但目前尚缺乏理想的小鼠肝癌模型,理想的肝癌模型應能準確反映肝癌的生物特性,充分模擬人類腫瘤微環境,并且容易操作,重復性高且價廉。肝癌PDX模型是目前為止最接近臨床研究的相關腫瘤模型[16-17],這種模擬人腫瘤特異性的模型對腫瘤臨床前評估、治療和預后具有重要的轉化意義,有望為腫瘤患者個體化治療帶來新突破。構建PDX模型通常需要用免疫缺陷的小鼠,這些小鼠缺乏免疫系統才能避免對移植瘤的排異,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PDX 模型不能用來評價免疫相關的藥物,如疫苗及免疫調節藥物PD-1抗體或通過免疫激活實現的藥物如CD40單抗等。此外,免疫缺陷小鼠還具有飼養費用昂貴和壽命短的缺點。
本研究選取具有正常免疫功能的C57BL/6小鼠,可以很好的解決以上問題。另外本實驗選取的4例臨床樣本病理類型均為肝細胞癌,是最常見的原發性肝癌類型,具有臨床代表性。移植部位和途徑選擇小鼠腋下皮下異位移植,主要考慮該部位血供豐富和組織疏松有利于腫瘤的生長[18]。
本研究采用microcarrier 6是一類新型微載體,人原代肝癌細胞與之共培養可以成功構建三維生長模型。microcarrier 6具有低免疫源性、質地疏松的特點,中間有大量孔隙可供腫瘤細胞在其中生長,可以(短時間內)起到屏障作用,阻擋免疫細胞直接殺傷腫瘤細胞,并且經過修飾后有利于血管生成,為腫瘤細胞快速生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7-9]。腫瘤細胞與microcarrier 6共同培養24 h后形成的3D細胞團,既能避免單個腫瘤細胞進入小鼠體內后被小鼠的免疫系統迅速清除,也能克服移植原代組織塊后細胞由于缺乏血供而死亡的缺陷。本課題組前期不僅使用MKN45細胞系成功構建胃癌小鼠移植瘤模型,并利用人原代卵巢細胞構建了正常免疫小鼠的人原代卵巢癌細胞模型[7-9]。
借助于本研究構建的人原代肝癌細胞的三維生長模型,實驗組在正常免疫小鼠體內成功構建了人肝癌PDX模型,而細胞對照組和微載體對照組均未成瘤。該模型特點是腫瘤生長迅速,在5~7 d時可以觸摸到瘤塊,1~2周為腫瘤生長高峰期,20 d左右體積即可達到0.5~1.0 cm3。病理HE染色可見大量核異型性細胞,并向肌肉、脂肪等浸潤;殘存的microcarrier 6被淋巴細胞包繞形成肉芽腫;中央有大片壞死,考慮生長過快,血供不足所致,符合人體肝癌的發展規律;毛細血管豐富,主要位于腫瘤周邊。肝癌特異性標志物CK8/18、Gpc-3、Hep的免疫組化染色均為陽性,進一步證實異形性細胞為人肝癌細胞。
本實驗成功基于microcarrier 6復合人原代肝癌細胞在正常免疫小鼠體內建立了人肝癌PDX模型,該模型可用于體現機體免疫系統和腫瘤的相互作用,在未來實現腫瘤轉化研究及精準治療等方面勢必有著廣泛的前景。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倫理委員會成員、受試者監護人以及與公開研究成果有關的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唐慧昕、李珊珊負責課題設計,收集數據,資料分析,撰寫論文;畢研貞、王全義、張小蓓、程姝敏負責數據收集和分析;洪豐、舒振鋒、段鐘平負責擬定寫作思路;陳煜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