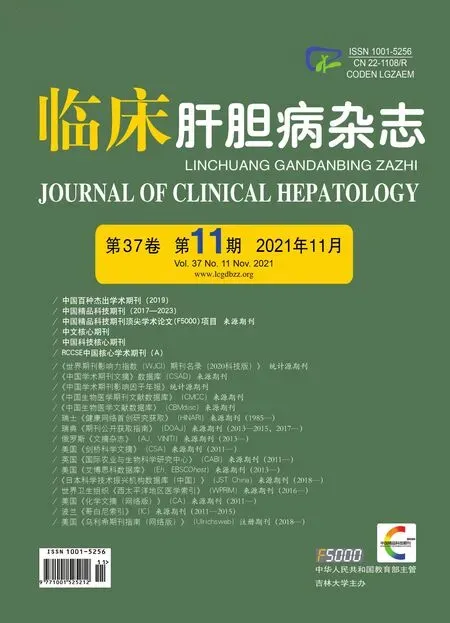預測兩型肝包蟲病肝切除術后并發癥列線圖的建立及評價
郭 兵,龐明泉,許曉磊,韓軍偉,王海久
青海大學附屬醫院 肝膽胰外科,青海省包蟲病研究重點實驗室,西寧 810001
肝包蟲病有較高的發病率及死亡率,肝切除是其主要治療方式。雖然術后死亡率比之前有所降低,但肝切除術后并發癥(post-hepatectomy complications,PHC)發生率卻未見顯著下降[1-2]。目前肝包蟲病PHC的臨床研究比較局限,所納入病例混雜且例數相對較少、PHC相關內容欠缺,并且尚無相關列線圖風險預測模型的構建及驗證[3]。本研究旨在探索兩型肝包蟲病(囊性和泡型)PHC的獨立危險因素,構建列線圖風險預測模型,以更好的指導圍手術期臨床決策,減少PHC的發生。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青海大學附屬醫院2015年1月—2020年8月收治的263例兩型肝包蟲病行肝切除手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入組標準:(1)術前影像學和術后病理學診斷為肝包蟲病的患者;(2)行肝切除手術治療;(3)久居青海。排除標準:(1)影像學及病理學診斷不明確;(2)合并肝囊腫、肝癌、肝血管瘤等其他肝臟良惡性疾病;(3)無術前、術中、術后所需指標;(4)術前已有術后相關PHC;(5)行肝移植、病灶微波消融、病灶穿刺引流、合并其他疾病行化療等治療方法;(6)已行多次肝臟手術治療患者;(7)包蟲病灶剔除患者。
1.2 手術方式 取上腹部反“L”字形切口(腹腔鏡根據需要采用不同數目的腔鏡孔洞),分離韌帶、游離肝臟,離斷病側肝短靜脈。Pringle法一次性阻斷入肝血流不超過15 min,如需繼續操作解除阻斷5~10 min或精準阻斷病側血流(區域阻斷)。標記肝臟離斷面,縫針牽引肝臟,CUSA刀切斷肝組織,沿斷面依次處理管道,5-0 proline線縫扎脈管系統斷端,較細的脈管系統用“連發鈦夾”夾閉,病灶與肝靜脈密切處使用“切割吻合器”處理。膽腸吻合:自腸系膜上血管后方上提空腸,距離盲端15 cm離斷,4-0可吸收縫線依次連續縫合。無菌紗布法檢查創面有無膽漏,若發現則使用4-0 proline線縫合。肝創面電凝止血并使用“速即紗”覆蓋。腹腔注入透明質酸鈉、膈下及創面常規放置引流管。
1.3 臨床資料搜集 收集患者資料:(1)年齡、身高、體質量等基本信息;(2)術前ALBI、TBil、AST、PLT等實驗室指標;(3)包蟲直徑(病灶最長直徑)、數量等影像學資料;(4)是否合并乙型肝炎;(5)手術時間、輸血量、切除段數、切除部位、血流阻斷方式、有無膽道介入手術等術中資料;(6)術后血紅蛋白、INR、TBil、PT、血清肌酐(Scr)、引流液或其他部位體液細菌培養等實驗室指標;(7)術后胸部腹部CT及彩超等影像學資料;(8)術后引流液量、顏色、化驗結果;(9)術后腹腔穿刺是否引流出膽汁、血液、腹水;(10)PHC的治療措施。
1.4 相關定義 (1)中央型肝切除包括肝Ⅳ、Ⅴ、Ⅷ段,并留有兩個創面。(2)肝切除術后膽漏(post-hepatectomy bile leakage,PHBL)即術后引流液膽紅素濃度為血清濃度的3倍;肝切除術后肝衰竭(post-hepatectomy liver failur, PHLF)即術后第5天或之后INR增高伴隨高膽紅素血癥;肝切除術后出血即血紅蛋白水平較術后基線水平下降>3 g/dl或需要介入或重新開腹止血,上述定義遵循國際肝膽胰小組標準[4-6]。(3)胸腔積液:術后經胸部CT證實并采取胸腔閉式引流治療。(4)肝切除術后感染的診斷符合《醫院感染診斷標準》[7],即體液或引流液培養出相關細菌并進行抗感染治療。(5)急性腎衰竭診斷符合2004年國際專家共識[8],即術后Scr升高3倍或Scr≥354 μmoI/L伴Scr急劇上升>44 μmoI/L。(6)切除3個以上的肝段稱為大肝切除。(7)膽道介入是指術中行膽腸吻合、肝腸吻合、膽道重建、T管引流等膽道的有創性操作。(8)死亡定義為住院手術期間死亡病例。(9)PHC包括PHLF、PHBL、出血、胸腔積液、感染、急性腎衰竭、死亡。
1.5 倫理學審查 本研究方案經由青海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PSL2018006,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PHC發生情況 入組263例患者中PHC組93例,對照組170例。PHC組包括PHLF 78例、PHBL 19例、出血9例;胸腔積液31例、死亡3例、急性腎衰竭4例、切口感染1例、肺部感染3例、腹腔感染17例。
2.2 一般資料 PHC組及對照組間的包蟲直徑、術中出血量、ALBI、手術時間、切除段數、是否膽道介入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1)。

表1 兩型肝包蟲病PHC組和對照組資料比較
2.3 單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分析前將APRI、包蟲直徑、術中出血量、ALBI、手術時間等計量資料取最佳截斷值,然后轉化成二分類變量并進行賦值:APRI<0.47為0,APRI≥0.47為1;包蟲直徑<10 cm為0,包蟲直徑≥10 cm為1;術中出血量<1000 mL為0,術中出血量≥1000 mL為1;ALBI<-2.45分為0,ALBI≥-2.45分為1;手術時間<280 min為0,手術時間≥280 min為1。單因素回歸分析篩選出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為包蟲直徑、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ALBI、切除段數、膽道介入(P值均<0.05)(表2)。進一步多因素logistic回歸結果顯示包蟲直徑、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ALBI是PHC的獨立危險因素(P值均<0.05)(表3)。

表2 兩型肝包蟲病PHC的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表3 兩型肝包蟲病PHC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2.4 共線性診斷 將篩選出的危險因素行共線性診斷,方差膨脹因子分別為1.337(包蟲直徑)、1.402(手術時間)、1.504(術中出血量)、1.284(ALBI)均<10,表明4個獨立危險因素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2.5 列線圖及驗證模型的構建 根據獨立危險素構建可視化列線圖(圖1)。ROC曲線結果顯示AUC為0.877(95%CI:0.831~0.923),最佳截斷值為0.356(圖2)。設置種子數為300,Bootstrap1000重采樣結果顯示:C-index為0.871。ROC曲線及重采樣法均表明列線圖預測模型有較好的區分度。Bootstrap1000重采樣構建校準曲線(圖3)顯示:擬合直線(Apparent)、校準曲線(Bias-corrected)與實際觀測直線(ideal)緊密貼合。Hosmer-Lemeshow檢驗結果顯示:P=0.905。校準曲線和Hosmer-Lemeshow檢驗均表明模型一致性良好且無過渡擬合情況出現。DCA(圖4)結果顯示:閾值在8%~89%區間內,患者受益曲線(黑色虛線)高于兩條異常曲線(黑色橫線和灰色斜線),并且ROC曲線所得結果的最佳截斷值0.356在閾值區間內。假如把35.6%當做診斷PHC且給予治療的閾概率值,帶入DCA,可以發現,100例患者中,在不損傷剩余人利益的情況下有22例患者從DCA中獲益。

圖1 預測兩型肝包蟲病PHC發生風險的列線圖

圖2 預測模型的ROC曲線

圖3 預測模型的校準圖

注:黑色橫線表示患者術后均無并發癥且無治療措施,灰色斜線表示患者術后均有并發癥且給予治療。閾值在8%~89%區間內,患者受益曲線(黑色虛線)高于兩條異常曲線(黑色橫線和灰色斜線)。
3 討論
包蟲病隨著流行范圍逐漸擴大,越來越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肝泡型包蟲病的生物學特性決定了其主要治療方式為肝切除術;而對于肝囊性包蟲病,雖然治療方式多樣,但是復發率及并發癥較高,嚴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質量。隨著外科條件及手術工具的不斷進步,肝切除術已經逐漸成為一種常規的手術,也成為其主要的治療手段[9]。雖然肝切除手術方式多樣,但是PHC一直是困擾臨床醫師的難題,不僅使術后護理難度加大,還延長了住院時限,使住院費用增加。
包蟲直徑較大引起PHC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1)更容易對周圍肝臟造成壓迫,形成術中難以發現的隱匿性膽漏;(2)需要離斷更多的血管、膽管、淋巴管及其附屬組織;(3)切除范圍大,剩余肝體積相對較少,嚴重影響肝功能;(4)手術時間、術中輸液量、出血量更多,手術創傷大和大量凝血因子被消耗。既往研究[3,10]表明腫瘤直徑>10.5 cm或>12 cm是PHBL的獨立危險因素。以往大多數PHBL的研究[3,5,11-13]中均排除了術中膽道介入的因素,只有極少數的研究表明膽道介入與PHBL有關,提示隨著醫療科研及手術的進步,膽道介入已經不是影響PHBL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有Meta分析表明,病灶直徑>10 cm是PHLF的獨立危險因素[14]。常磊等[15]Meta分析表明:Pringle法與半肝血流阻斷法在PHC發生率方面無差異,但是Pringle法較半肝血流阻斷法術后肝功能恢復時間較長。在本研究中Pringle法與半肝血流阻斷法的PHC無明顯差異。在本研究中病灶直徑≥10 cm是最佳截斷值,與既往PHBL、PHLF的研究結果一致。
術中出血量多和手術時間較長引起PHC原因有以下幾方面:(1)血流重新分布,不重要血管收縮,血流量減少;(2)間接影響術中輸血量;(3)消耗大量凝血因子;(4)加重肝功能損傷。相關綜述及Meta分析表明,術中出血量≥1000 mL是PHLF的重要影響因素[14,16-17]。也有研究[12,18]表明手術時間≥300 min是PHBL、術后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有學者[19]依據Clavien-Dindo分級系統對PHC分析,結果表明術中失血量是PHC的獨立危險因素,但是未給出術中出血量的最佳截斷值。本研究術中出血量和手術時間的最佳截斷值分別為≥1000 mL、≥280 min,與既往相關研究大致相同。
肝功能狀態是影響PHC的主要因素。ALBI由于其簡單、便捷、無創等優點被廣泛用于肝功能的評估。Zou等[20]對行肝切除的 229例肝癌患者進行分析,ALBI評分較Child-Pugh評分更適合用于PHC或PHLF預測模型的構建。同時多中心研究[21]表明:ALBI評分比終末期肝病模型更能有效的預測PHBL和PHLF的發生風險,但該研究雖然證實了ALBI在預測PHBL和PHLF的價值,但是沒有對其截斷值進行確定,僅僅停留在分級系統上。本研究中ALBI的截斷值是-2.45分,分屬B級范圍,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21]。Tian等[22]從細胞因子水平證實了轉化生長因子β在肝囊性包蟲病患者中表達上調,與肝纖維化密切相關。同時Zhang等[23]在基因水平上闡述了肝囊性包蟲病囊液通過抑制miR-19的表達促進囊型包蟲病囊周纖維化。有學者[24]認為APRI是肝癌患者PHC發生的關鍵評估因素。但在本研究中,APRI在PHC組和對照組間無明顯差異。目前尚無肝包蟲病與纖維化程度、進程、范圍的相關研究,其原因可能與包蟲所致纖維進程較慢,所致范圍較窄,根治性手術期間已經將肝纖維化部分病灶切除有關。
綜上所述,以4個獨立危險因素為基礎構建的預測模型具有良好的臨床應用前景,未來可以在多中心驗證的基礎上尋求進一步的臨床應用。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倫理委員會成員、受試者監護人以及與公開研究成果有關的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郭兵、龐明泉負責課題設計,資料分析及撰寫論文; 郭兵、龐明泉參與收集數據及修改論文;許曉磊、韓軍偉負責擬定寫作思路;王海久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