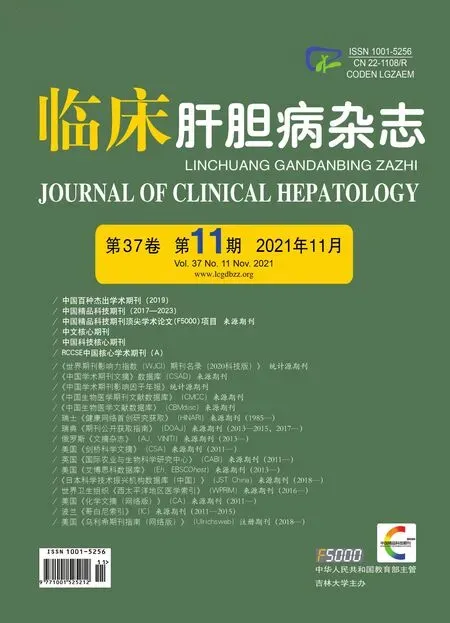原發(fā)性脾血管肉瘤1例報告
王慧君,牛劍祥,徐曉艷,鄭衛(wèi)華,李朋飛,劉一博,張俊晶
1.內(nèi)蒙古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醫(yī)院 肝膽胰脾外科,呼和浩特 010050;2.內(nèi)蒙古醫(yī)科大學(xué) 病理學(xué)教研室,呼和浩特 010030;3.呼和浩特市第一醫(yī)院 肝膽胰脾外科,呼和浩特 010030
原發(fā)性脾血管肉瘤(primary splenic angiosarcoma,PSA)是1種起源于脾竇血管內(nèi)皮的惡性腫瘤,臨床罕見,自Langhans于1879年報道了第1例PSA以來,截至2019年全世界僅報道300例左右[1]。張智旸等[2]回顧性分析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收治的68例病理確診為血管肉瘤患者的臨床、手術(shù)病理資料和治療情況,其中脾血管肉瘤僅有3例。PSA因其發(fā)病率低且臨床表現(xiàn)無明顯特征性,臨床易誤診,一般發(fā)現(xiàn)時已屬晚期。筆者所在醫(yī)院近來收治1例PSA患者,術(shù)前曾考慮為血液系統(tǒng)疾病,同時伴有肝臟、骨髓形態(tài)異常,診療期間因自發(fā)破裂行急診手術(shù)。本病例近乎出現(xiàn)所有嚴(yán)重的并發(fā)癥,現(xiàn)結(jié)合國內(nèi)外文獻(xiàn),報道如下。
1 病例資料
患者女性,65歲,因“瘀斑8個月,進(jìn)行性加重伴乏力2個月”于2020年6月17日入院。查體:貧血征陽性,出血征陽性,腹平軟,無壓痛、反跳痛,肝臟未及,脾大,約左肋緣下6 cm,質(zhì)硬,無壓痛。血常規(guī)示:血紅蛋白 79 g/L;白細(xì)胞計數(shù) 2.92×109/L;血小板計數(shù) 26×109/L;凝血四項(xiàng)示:纖維蛋白原 1.45 g/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 30.80 s;凝血酶原時間 13.20 s。腫瘤標(biāo)志物正常;抗核抗體正常;免疫球蛋白A、G、M正常。初步診斷為:(1)三系減少待查;(2)脾大待查。入院后患者出現(xiàn)左上腹痛、腹脹、發(fā)熱,給予抗感染、補(bǔ)液、補(bǔ)血,止痛、穩(wěn)定內(nèi)環(huán)境等相關(guān)治療。實(shí)驗(yàn)室檢查結(jié)果顯示輸血制品不能糾正的低血小板和紅細(xì)胞減少趨勢,同時存在凝血功能障礙。全腹增強(qiáng)CT示(圖1):肝脾多發(fā)乏血供結(jié)節(jié),肝右葉血管瘤,肝多發(fā)囊腫;脾大;腹盆腔積液;子宮肌瘤;雙側(cè)胸腔積液。骨髓穿刺結(jié)果示(圖2):骨髓見梭形細(xì)胞,稍有異型,可見血管腔隙,CD34(+)。2020年6月30日,患者脾區(qū)疼痛突然加劇,診斷性腹腔穿刺抽出不凝血,考慮臟器破裂出血,行急診腹腔鏡下巨脾切除術(shù),術(shù)中視及腹腔內(nèi)大量積血,脾臟明顯增大,表面尚平整,可見被膜下血腫,被膜破損處有活動性出血(圖3)。術(shù)后病理示:脾臟血管肉瘤(中-低分化);免疫組化示(圖4):Ki-67熱點(diǎn)區(qū)(15%+),CD31(+),CD34(+),F(xiàn)Li1(+),F(xiàn)Ⅷ(+),CK-pan(-),CD3(-),CD20(-)。患者術(shù)后無并發(fā)癥,切口恢復(fù)良好(圖5),10 d出院,最終診斷:(1)PSA伴脾自發(fā)破裂出血、肝轉(zhuǎn)移、骨髓轉(zhuǎn)移;(2)失血性休克;(3)肝囊腫;(4)肝血管瘤。門診隨訪患者于出院40 d后死亡。

注:門靜脈期見肝脾內(nèi)彌漫分布小結(jié)節(jié)狀低強(qiáng)化影,周圍見液體密度影。

注:a,HE染色(×400);b,骨髓見梭形細(xì)胞,稍有異型,可見血管腔隙,CD34(+)(免疫組化,×400)。

圖3 術(shù)中腔鏡視野

注:a,脾內(nèi)未見皮質(zhì)、髓質(zhì)結(jié)構(gòu),可見殘存脾小梁(藍(lán)色箭頭),視野中見大量增生的腫瘤細(xì)胞,多排列為裂隙樣,部分見壞死(紅色箭頭)(HE染色,×100);b,分化較好部位,腫瘤細(xì)胞有一定異型性,部分呈鞋釘樣,可見血管腔隙(HE染色,×400);c:分化較差部位腫瘤細(xì)胞呈梭形,有一定異型性,呈束狀、片狀排列,可見裂隙,其內(nèi)可見一脾小動脈(紅色箭頭)(HE染色,×400);d:Ki-67熱點(diǎn)區(qū)域(15%+)(免疫組化,×400);e:腫瘤細(xì)胞彌漫CD31(+)(免疫組化,×400);f:腫瘤細(xì)胞彌漫FLi1(+)(免疫組化,×400)。
2 討論
PSA是一種罕見的間葉組織惡性腫瘤,發(fā)病率0.14~0.23/百萬,發(fā)病年齡多在50~79歲,有輕微的男性優(yōu)勢,男女比例約為4∶3[1-4]。該病惡性程度極高,腫瘤轉(zhuǎn)移率69%~100%,平均生存時間4.4~14個月,只有約20%的患者能存活超過6個月[1]。不同于其他肉瘤的致病因素,PSA與氯乙烯、砷暴露和二氧化釷等化學(xué)暴露之間沒有相關(guān)報道,有一種理論認(rèn)為,PSA可能是其他良性脾臟腫瘤惡性轉(zhuǎn)化的結(jié)果,如血管瘤、淋巴管瘤和血管內(nèi)皮瘤[5]。本例患者否認(rèn)既往化學(xué)暴露及良性脾臟腫瘤病史。
PSA的臨床表現(xiàn)多樣而無特異性,最常見的癥狀是腹痛,其他可能的癥狀包括疲勞、厭食、體質(zhì)量減輕以及高溫等[6-7],此外30%的患者會出現(xiàn)自發(fā)性脾破裂,并由此導(dǎo)致急腹癥和腹腔積血甚至危及生命[8]。查體發(fā)現(xiàn)脾腫大是較為一致的體征。貧血是PSA實(shí)驗(yàn)室檢查的主要表現(xiàn),其他包括血小板減少、白細(xì)胞減少、紅細(xì)胞沉降率增高等[9]。本例患者比較典型,入院前2個月開始出現(xiàn)乏力,入院時查體捫及脾臟明顯腫大,入院后主訴左上腹反復(fù)疼痛、腹脹同時出現(xiàn)發(fā)熱,實(shí)驗(yàn)室檢查顯示三系減少。但這些癥狀同樣很貼近血液系統(tǒng)疾病的表現(xiàn),所以術(shù)前診斷偏向于考慮更為常見的白血病、淋巴瘤等,直至患者急性脾破裂后手術(shù)治療,才明確為PSA。這種沒有特征性表現(xiàn)的疾病加之罕見,臨床上很容易被誤診。
影像學(xué)在本病的術(shù)前診斷具有重要意義,彩超的典型表現(xiàn)是脾臟腫大,并伴有一個或多個不均勻的回聲腫塊,可能存在無回聲區(qū)域,反映腫瘤內(nèi)壞死[3,10]。CT最常見的是脾臟增大,病灶一般為境界不清晰的稍低密度影,典型強(qiáng)化方式是動脈期腫塊邊緣和中央斑片狀或不規(guī)則明顯強(qiáng)化,靜脈期和延遲期持續(xù)向心性或離心性充填。PSA的MRI在T1和T2獲得的圖像上可以同時看到信號強(qiáng)度增強(qiáng)和降低的區(qū)域,低信號多對應(yīng)脾臟慢性失血或腫瘤纖維化,高信號則主要由于脾臟亞急性出血或腫瘤壞死[11]。
PSA的最終確診依賴于病理學(xué)檢查。該病患者脾臟往往明顯腫大,切開后顯示邊界不清的紫色或紅色結(jié)節(jié)狀腫塊,彌漫性脾臟受累較常見,孤立性腫塊內(nèi)多有明顯的出血和壞死區(qū)域[12]。鏡下可見腫瘤由排列紊亂的吻合血管通道組成,內(nèi)有豐滿、不典型的內(nèi)皮細(xì)胞,細(xì)胞核大、不規(guī)則、深染,有絲分裂率高,一些腫瘤細(xì)胞突入腔內(nèi)呈大頭針樣或堆積在一起成簇狀、乳頭狀、實(shí)性片狀[13]。除外形態(tài)特征,既往研究[1]表明診斷該腫瘤尚需結(jié)合免疫組化結(jié)果,提示血管分化的有CD34、CD31、FⅧRAg或VEGFR3等指標(biāo)中至少2項(xiàng)結(jié)果陽性,提示細(xì)胞分化的有CD68或溶菌酶等指標(biāo)中至少1項(xiàng)結(jié)果陽性,即可明確診斷。本例患者脾臟明顯增大,總體積14 cm×13 cm×5 cm,切開后部分區(qū)域似出血,其余切面實(shí)質(zhì)易碎,顏色暗紅,部分區(qū)域呈灰白色。鏡下表現(xiàn)為較常見的彌漫性脾臟受累,鏡下未見皮質(zhì)及髓質(zhì)結(jié)構(gòu),僅可見殘存脾小梁,部分可見壞死;腫瘤細(xì)胞呈梭形,有一定異型性,分化好的部位可見血管腔隙,分化差的部位腫瘤細(xì)胞呈束狀、片狀排列,免疫組化提示CD31、CD34、Fil1均陽性,與既往報道相符。
PSA的主要治療手段是脾切除術(shù),因該病罕見,其他治療方式尚不明確。對于惡性腫瘤,大部分醫(yī)師往往并不首選腔鏡下手術(shù),考慮脾腫大會增加出血、包膜破裂和中轉(zhuǎn)為開腹脾切除術(shù)的風(fēng)險。但Silecchia等[14]對76例連續(xù)行腹腔鏡手術(shù)的未經(jīng)選擇患者的分析證實(shí),腹腔鏡手術(shù)在惡性和良性血液疾病中都是安全可行的,且腔鏡下具有創(chuàng)傷小、恢復(fù)快、住院時間短的優(yōu)勢。本例患者術(shù)前破裂出血,已存在擴(kuò)散可能,因此選擇腹腔鏡下探查加脾臟切除,術(shù)后未出現(xiàn)并發(fā)癥且10 d后出院。除手術(shù)外,以放化療為主的輔助治療也有報道,de Azevedo等[15]和Hara等[16]均報道過患者使用輔助治療后生存期延長;Vakkalanka等[17]報道了第1例紫杉醇作為新輔助化療方法促進(jìn)局部晚期PSA手術(shù)切除的情況,這些病例可能提示輔助治療是有效的。PSA起源于內(nèi)皮細(xì)胞,所以具有抗血管生成的紫杉醇、減少VEGF的沙利度胺以及抗VEGF的貝伐珠單抗等都可能是未來更好的選擇方向[18-22]。
前已述及,PSA預(yù)后極差,Naka等[23]對55例血管肉瘤病例進(jìn)行多因素分析后發(fā)現(xiàn)腫瘤大小、治療方式和有絲分裂數(shù)是影響預(yù)后的獨(dú)立因素,目前存活最長的是一名7歲患兒,僅接受脾切除術(shù)后無病生存16年,該患者長期存活的原因可能正是由于其腫瘤有厚厚的包膜以及較低的有絲分裂數(shù)[24]。有研究[1]指出,在疾病破裂和擴(kuò)散之前切除脾是最重要的,可以使生存期從4.4個月延長到14.4個月。這些影響預(yù)后的因素,提示在面對PSA時需要早診斷、早干預(yù),在腫瘤尚小或者至少在脾破裂之前進(jìn)行手術(shù)切除一定程度上能夠延長患者生存期。本例患者術(shù)后不足2個月即死亡,筆者認(rèn)為一部分是因?yàn)椴∏檠诱`時間久,8個月前出現(xiàn)瘀斑時沒有及時就診,腫瘤在肝臟、骨髓均有轉(zhuǎn)移;其次本次入院前期誤診為血液系統(tǒng)疾病,沒有在脾破裂之前及時進(jìn)行手術(shù)切除。
總之,PSA作為一種罕見、惡性程度高但缺乏臨床特征的疾病,臨床醫(yī)師一方面要提高對該病的認(rèn)識,在遇到脾大、貧血、血小板減少的患者時能夠提高警惕,充分利用各種手段進(jìn)一步鑒別診斷。另一方面需要探索新的更具代表性的血清標(biāo)志物、探索更好的治療方案。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xiàn)聲明:王慧君負(fù)責(zé)撰寫論文;牛劍祥、鄭衛(wèi)華、李朋飛、劉一博負(fù)責(zé)收集數(shù)據(jù),修改論文;徐曉艷負(fù)責(zé)提供病理學(xué)方面支持;張俊晶負(fù)責(zé)指導(dǎo)撰寫文章及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