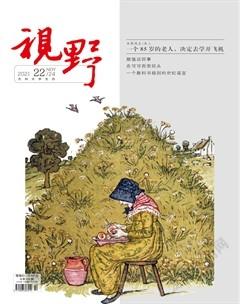鏌铘島人
馬未都

我的老家在膠東半島的頂端,有一狹長的間歇半島,名叫鏌铘島,取自寶劍之名。間歇半島是非常奇異罕見的地貌現象,每天退潮后形成半島,有一條路與大陸相連;鏌铘島海底沙子硬朗,退潮后可以開車出入,全世界都不多見,如開發為旅游地,肯定是個聚寶盆。可惜在三十多年前被無知的人修了一條水泥馬路,把這個間歇半島徹底毀了。
父親十幾歲的時候就從鏌铘島中走出來當兵,參加了革命。因為有點兒文化,一直做思想工作,從指導員、教導員干到政委。父親曾經對我說,他們一同出來當兵的有39人,到解放那年就剩一個半了:他一個全活人,還有一個負傷致殘。抗日戰爭期間,山東戰斗激烈,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大部分都是在山東境內實施的。解放戰爭時,山東戰場打得慘烈,父親打完孟良崮戰役,打濟南戰役,接著打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最后打完上海戰役進駐上海,五年后奉命晉京。
父親開朗,小時候我印象中的他永遠是笑呵呵的,連戰爭的殘酷都以輕松的口吻敘述,從不渲染。他告訴我,他和日本人拼過刺刀。一瞬間要和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決以生死,其殘酷可想而知。他臉上有疤,你問他,他就會說,掛花誰都掛過,軍人嘛,活下來就是幸運了。
我15歲那年,父親帶我第一次回老家。山東人鄉土觀念重,但他參軍后很少回家,因為要打報告獲準。他在路上對我說,十多年沒回老家了,很想親人,想看看爹和娘,你弟妹不能都帶上,帶上你就夠了。那次讓我感到做長子的不同。
那時路上火車很慢,他按規定可以報銷臥鋪票,我得自費。那年月沒人會自費買臥鋪,都在硬座上忍忍就過去了。我和父親就一張臥鋪,他讓我先睡,他在我身邊湊合坐著。我15歲已長到成人的個兒,睡覺也不老實,結果躺下一覺到天亮,醒來看見父親一人坐在鋪邊上,瞧樣子就知他一宿沒睡。我有些內疚,父親安慰我說,小時候他的祖父還每天背著他渡海去讀書呢!
1968年的隆冬,父親只身帶著我們兄妹三人,拎著兩件全家的行李,登上了北去的列車,到了黑龍江省寧安縣的空軍“五七干校”。直至1971年初我才又回到北京,所以我一個老北京,戶口本上卻奇怪地寫著由黑龍江省寧安縣遷入。如不說這段歷史,戶口本是沒法證明我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的。我生于北京,長于北京,只有那兩年不在北京,連戶口都遷了出去,按老話說算是闖了關東。
剛去東北的時候特苦,吃食堂,沒油水,而我們都是長身體的時候。空軍干校是由廢棄機場臨時改建的,空曠的視野中凈是些沒用的大房子。東北的冷那才叫真正的冷,一直可以凍得人意志崩潰。那時的人覺得做無產階級光榮,所以家里什么都沒有;從北京啟程的時候,父親在行李中只塞了一口單柄炒菜鍋,木柄已卸掉,避免太占地。剛到干校的一天,父親叫上我們兄妹三人,隨他走到很遠的一座大房子里,這座房子估計以前是個庫房,四處漏風,中間有一個高高的油桶改裝的大爐子。父親攏上柴,點上火,支上鍋,安上鍋柄,變戲法地從軍大衣兜里掏出幾把黃豆,在鍋中翻炒起來。我們兄妹就滿屋子撿碎木頭細樹枝,幫助父親添柴。父親被火光映紅的臉露出了笑容,他高高地舉著胳膊欲將鍋從火爐上端下來,一瞬間,事故發生了,由于鍋柄安得不牢,炒菜鍋一下傾翻,一鍋黃豆一粒不落地扣入火中,火苗子躥起一人多高。那天,我的難過我還可以描述,可父親的難過恐怕無法說清。
父親晚年罹患癌癥,病重的日子,曾把我單獨叫到床前,他告訴我,不想治療了。他說,人總要走完一生,看著你們都成家了,我就放心了。再治療下去,我也不會好起來,還會連累所有人。他認真地說,拔掉所有的管子吧。我咨詢了主治醫生,治療下去是否會有奇跡發生?醫生給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12月19日晚上,在拔掉維持生命的輸液管四天后,父親與世長辭。過去老話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深刻而富于哲理。
(閻蕊森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