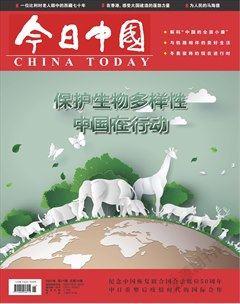完全統一是民族復興的偉大政治事業
田飛龍

2021年10月9日上午,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歷史判斷和政治宣示。作為歷史判斷,臺灣問題確實由于近代殖民主義、國共內戰及美國的帝國霸權前后作用、交疊影響而造成,今日之兩岸出現“冷對抗”甚至臺獨化的現象,這是國家完全統一的最后課題。作為政治宣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也是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因而成為中國人民強大政治意志的聚焦對象。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為民主進步、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作出了具有歷史開創性的貢獻,而臺灣問題之解決也必然在這些先行者的理想規劃之中并成為后繼者的接力使命。
具有豐富的歷史哲學內涵和現代性意義
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是在革命歷史和民族復興的大敘事中呈現臺灣問題之性質與出路的。這一講話的主題是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辛亥革命是中國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民主革命,同時也是重塑中華民族政治格局與團結秩序的民族革命。習總書記將這一革命界定為:“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探索。”
這一定位有著豐富的歷史哲學內涵和現代性意義:其一,革命的主體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其中“中國人民”是歷史的完整主體和革命的主力軍,是客觀的、固有的和一經組織化即發揮強大的歷史建構力量的,而“中國先進分子”屬于革命的啟蒙者和領導者,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會有不同的擔綱力量和組織形式,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驅的政治貢獻。其二,革命的目標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動員人民參與革命,推翻帝制和外來壓迫,重造統一的國家和自由的民族,這一革命目標顯然包括了對國家完全統一的強烈而堅定的規范性訴求。習總書記在講話中也正式援引了孫中山先生的“‘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加以確認,從而伸張國家完全統一追求的政治正當性和歷史延續性。其三,革命的意義是“偉大”的,但過程是“艱辛”的,且具有“探索”性質。這是符合歷史的客觀理性的判斷,因為辛亥革命開民主與民族革命之先河,奠定了基本的民主價值和民族復興目標,但習總書記講話中也正確指出“由于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其歷史開創性和歷史局限性并存,并給后繼者以重要的歷史基礎和方向指引。其四,作為“艱辛探索”的延續,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這不僅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初心和使命同樣包含民主追求和民族復興,而且國共兩黨曾在孫中山革命后期實現過真正的聯合與進步,共同對大革命做出過歷史性貢獻。中國共產黨從中獲取了“繼續革命”的豐富經驗、政治教訓、社會基礎和民心力量,實現了初步的價值奠基、政治成熟和路線定型。
正確指出臺灣問題的解題迷津
在民主追求與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人走得更加深入、持久、堅韌,也付出了更大犧牲,并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國家建構與現代化進步成就,為中國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民族尊嚴的維護及國家統一的促進展開了全方位的奮斗,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道路。而臺灣問題正是這一宏闊歷史進程的“遺留問題”,是殖民主義、內戰及美國霸權干預復雜作用的歷史結果,是民族“弱亂”造成的。習總書記正確指出了臺灣問題的解題迷津:民族復興。既然臺灣問題是因“弱亂”而起,殖民主義、內戰及美國霸權干預也乘機利用了民族“弱亂”之機攫取其自身利益而嚴重損害了辛亥革命指向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主要目標,那么民族“復興”就必然要求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完全統一,且民族“復興”之進程和不斷凝聚的團結力量更是實現完全統一的強大、可依賴的歷史條件。
在論及臺灣問題必然解決時,習總書記明確提出“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其中“一定要”是強大的民族整體意志,是主觀性條件,而“一定能夠”則是綜合各方面的條件和要素作出的理性判斷,是客觀性條件。隨著中華民族復興進入新時代,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展現出全球制造強國的不可逆發展趨勢,隨著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對全球治理的建設性參與,隨著“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化發展,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與民族自信心的提升,習總書記提及的關于祖國完全統一的主客觀條件正在系統成就和緊密扣合。
在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命題上,中國共產黨人和辛亥革命先賢們的政治思考與責任倫理是高度一致的。完全統一是民族復興的政治事業。習總書記在講話中發出歷史性邀請,號召兩岸同胞“都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共同創造祖國完全統一、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偉業。”通過追憶和肯定辛亥革命的過程與功績,在臺灣問題與國家統一層面,什么是“歷史正確”,什么是“歷史錯誤”,在兩岸同胞之間是能夠達成前所未有之強大共識并轉化為促成和平統一之集體行動的。

2021年9月24日, 由香港各界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會主辦的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談會在香港中銀大廈舉行
追求完全統一的三個層次
在涉及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路徑和方法時,習總書記精準凝練地提出了邏輯上相互關聯的三個層次的核心論述:
一是統一心理層次,即兩岸完全統一是民族整體的心理追求,是民族文明心理與制度建設的大勢所趨。習總書記引述了孫中山先生關于“統一”作為全體國民希望以及統一與否的利弊分析,并將國家統一類比為孫中山先生所稱的“世界潮流”。這就確立了“統一”作為兩岸關系政治定位和歷史目標的最高價值地位,并在兩岸同胞的政治與歷史心理層面激發出強大且不可逆的民意共識,構成兩岸完全統一的歷史命運共同體基礎與契約合意。
二是憲制法理層次,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方案與主導性法理。這再次回應了1980年代鄧小平一代領導人構想“一國兩制”的初衷,也再次確認了習總書記2019年1月2日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大會講話中的政策主旨。“一國兩制”是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建設相協調的重大政策構想和制度創新,在共和國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戰略布局中已有基本思考和雛形,在改革開放時段通過鄧小平的創造性實踐而首先在港澳落地并對臺灣產生一定程度的示范意義。今日之兩岸關系,仍有著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運籌“一國兩制”時的基本要素和適用空間,故“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仍然是兩岸關系的最優解。“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的方案,而和平統一是民族復興的高級證明:一方面完成祖國統一的歷史任務,作為民族復興的關鍵標志;另一方面則顯示中國共產黨的高超治理能力及兩岸中國人的團結與合作的政治智慧,構成一種讓所有中國人自豪的“光榮偉業”。和平統一之路需要兩岸相向而行,攜手突破,而回到“九二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始終是根本的法理底線和出發點。
三是制裁行動層次,即兩岸和平統一遭遇到臺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的嚴重干擾和破壞,國家必須加以制裁和反制,為最終統一創造全方位的有利條件。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臺獨”勢力是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因此,反臺獨的全方位斗爭,包括軍機繞臺、適當的經濟制裁、臺獨分子制裁清單甚至《反分裂國家法》的細則解釋或修訂,都是必要而正當的國家行動。習總書記論及了中華民族的“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光榮傳統,這是中華文明及其政治秩序延續數千年而實現“超穩定”的歷史優勢所在。也是“大一統”的智慧和歷史韌性所在。臺獨挑戰中華民族的這一根本利益和“大傳統”,其結果只能是所謂的“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兩岸統一的阻撓力量當然不限于“臺獨”,還包括外部干預勢力。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專門提及了臺灣問題的內政屬性及反對一切外部干預的國家意志和國家能力。考慮到美國“臺灣牌”的極限利用以及日本等國的地緣政治投機性,反干預的戰略統籌和制度安排是切中要害的,而精準性的反制行動也需要果斷而行,堅決斬斷外部干預之手。
總之,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遺產和民族復興目標,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財富和共同任務。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既正確而深刻地解讀和界定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和進步價值,又權威而堅定地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與行動意義。涉臺論述是這篇講話的重要內容和落腳點之一,而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正是辛亥革命未竟事業、中國共產黨歷史任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交匯點。站在這個交匯點上,兩岸中國人就有了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感和集體行動意義,從而能夠凝聚起全面的民族力量和全部的有利條件“反獨促統”,共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世紀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