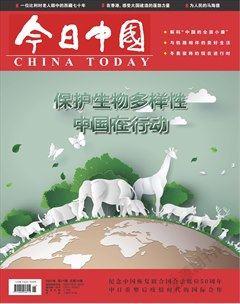一位比利時老人眼中的西藏七十年
劉婷
“西藏和平解放70年來,社會進步迅速且巨大,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西藏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比利時藏學家安德烈·拉克魯瓦如是說。
拉克魯瓦曾是比利時的一名中學教師,退休后的20多年里致力于研究藏學,曾多次到西藏實地考察。2019年,他的著作《達蘭薩拉:當面具被揭開》由法國Amalthée出版社出版發行。在書中,他列舉了達賴喇嘛炮制的涉藏謊言,以犀利的筆觸揭露了達賴喇嘛隱藏在表象背后的真面目。
被一個與西方宣傳完全不同的真實西藏所感動
和大多數歐洲人一樣,在未到訪中國之前,拉克魯瓦對西藏的了解主要來源于西方媒體的報道,他甚至曾經認為所有藏族人都是所謂的“文化滅絕”的受害者。然而,一次在中國的長途旅行打破了拉克魯瓦的固有印象和偏見。

拉薩街頭的清真寺和回民聚居區(受訪者供圖)
由于女兒當時在云南大學讀書,拉克魯瓦20世紀90年代兩次到訪中國。1999年,他用近兩個月的時間走遍了四川、云南等與西藏交界的省份,其中包括一些藏族自治州和自治縣。一路上,他看到許多喇嘛僧人在當地藏傳佛教的寺院修行,這讓他頗為震驚,因為當時在他的固有印象中,這樣的宗教活動是“滅絕”了的。“在甘肅夏河、四川郎木寺、云南中甸等地,我看到許多宏偉華麗的藏傳佛教寺院,有些寺院還在進行古建修復。讓我記憶深刻的是當時在大殿中進行的一場祈禱儀式,好多藏傳佛教的教徒都參加了。儀式結束后,成群的喇嘛僧人走出大殿,在廣場上四散開來。他們可以在大街上自由地念經、拜佛。”拉克魯瓦回憶道。可是,讓他感到不解和遺憾的是,他親眼看到的情景與西方媒體報道中所描繪的內容大相徑庭,西方民眾沒有途徑看到這些。
正是這樣前后對比反差如此之大的經歷讓退休后的拉克魯瓦找到了新的興趣點—藏學研究。這也為他打開了一扇了解這片神秘雪域高原的窗口。后來,研究小有所成的他還成為西藏學者扎西次仁口述著作《西藏是我家》法文版的譯者。
在翻譯《西藏是我家》一書時,拉克魯瓦被主人公扎西次仁的故事打動,他決定來西藏,當面見見這位作者。2009年和2012年,拉克魯瓦兩度赴西藏進行實地考察并和扎西次仁促膝長談,對西藏和平解放有了全面客觀的認識。以教育為例:在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的學校,適齡兒童入學率不到2%,文盲率高達95%,像扎西次仁這樣普通農民家的孩子根本沒有讀書識字的權利。西藏和平解放后,經過幾十年發展,西藏的教育公平得到了有效實現,尤其是從1986年起,中國便普及了免費的義務教育,適齡的“兒童和少年”必須接受9年的義務教育。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藏,藏語還是中小學的必修課。
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態保護協同發展
兩次實地走訪讓西藏發展的點滴都印在這位比利時老人的心中。70年來,西藏的發展速度令他印象深刻。和平解放之前,西藏的交通事業極端落后,運輸基本靠人背畜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汽車公路。如今,西藏的交通基礎設施已經非常完善。當他2009年首次進藏時,特地選擇青藏鐵路,乘著火車去拉薩。在感慨青藏鐵路方便快捷的同時,他還看到了一個兼具傳統與現代、基礎設施完善的拉薩。
經濟的發展,會不會帶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拉克魯瓦坦誠表示,這樣的疑問和擔憂曾在他心頭縈繞過。不過,通過兩次西藏之行,這樣的疑慮被打消了。
“政府建立了許多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來保護瀕危物種。為了應對人口增長和氣候變化給生態帶來的挑戰,政府還在山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植樹造林。”說到這里,拉克魯瓦分享了一個故事:某次和妻子同游雅魯藏布江,當他們的車在岸上行駛時,妻子原本打算透過車窗拍攝雅魯藏布江的景色。然而,這樣的“偷懶”想法卻沒能實現,“因為茂密的植被在公路和江水之間形成了一道嚴實的屏障,她無法拍到雅魯藏布江那壯美的景色。”拉克魯瓦說,“最后,她只好讓司機靠邊停車,下車拍攝江景。”

2009年,拉克魯瓦(左)首次進入西藏并和扎西次仁(右)見面(受訪者供圖)
此外,讓這位老人欣喜的還有可再生能源在西藏自治區的廣泛運用。“人們特別注重對太陽能的利用,太陽能光伏產業的發展完善,既改善了公共設施的供電不足的現狀,又解決了當地部分農牧民的日常生活用電。”拉克魯瓦說。在很多牧場他都能看到,牧民們放牧時用小塊的太陽能板給手機充電。
他認為,西藏的巨大進步和快速發展得益于政府的各類政策的落實。“和平解放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派遣人民解放軍進藏,幫助西藏人民修建公路、學校、診所等。扎西次仁曾對我說,解放軍們從未向百姓們索取一分一毫,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深得藏民愛戴。”他說。
根據拉克魯瓦的長期觀察,政府還從人力、物力、財力給予大力支持,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此外,西藏自治區在人口政策、教育、環境、稅收等領域享有優惠政策的同時,西藏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