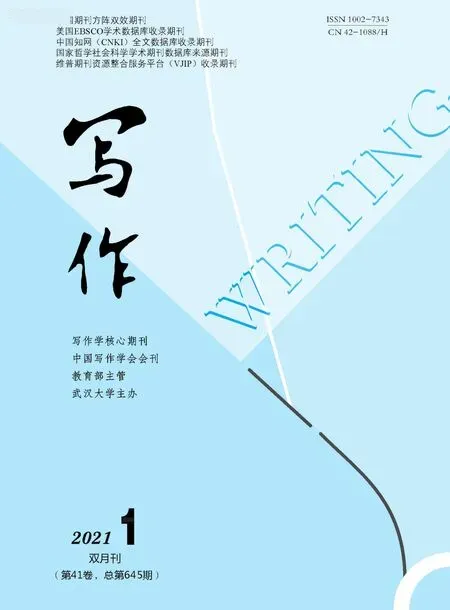作為自傳的寫作
——評齊邦媛《巨流河》
戚 慧
《巨流河》是齊邦媛在80 多歲高齡時寫就的一部史詩巨作,記錄她所經歷的時代變遷,不僅譜寫了一位傳奇女子在新舊過渡時代與艱難歲月里的奮斗史,而且書寫了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和文人的見證史。作為自傳,《巨流河》的寫作交織著歷史與個人記憶,其所采用的敘述聲音和視點形成了獨特的節奏與張力,亦彰顯著壯闊的史詩風格與真實而溫情的人性關懷。“《巨流河》最終是一位文學人對歷史的見證”①王德威:《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齊邦媛與〈巨流河〉》,《當代作家評論》2012 年第1期。,齊邦媛以書還鄉,記錄下那個“歡樂苦短,憂愁實多”的時代。
一、相互交織的歷史與個人記憶
“大歷史”②黃仁宇:《為什么稱為“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中國大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版,第1頁。的概念,是黃仁宇先生的創意。所謂“大歷史”觀念,是一種把視野放寬到世界歷史全過程的考察方法,宏觀地由前后(時)、中西(空)的往復觀照,去考量審視中國歷史,強調整體思維,整體史觀。而個人歷史屬于“小歷史”,是常態的、日常的、生活經歷的歷史。對“大歷史”的研究,易陷入絕對化、單一化的宏大敘事模式的問題中,并抽去“大歷史”的生活基礎。歷史本來就是一個,一旦把這個生活基礎(“小歷史”)歸還給“大歷史”,大、小歷史將回歸歷史原貌。個人歷史向來是作為“大歷史”的一部分,相對于刻板的、定論性的、枯燥的“大歷史”,它保持其唯一性和新鮮感,這也是“大歷史”所不及的。《巨流河》中歷史與個人記憶的相互交織主要表現在個人歷史的真實與大歷史的糾結以及個人記憶的時間次序與情感的輕重兩個方面上。
(一)個人歷史的真實與大歷史的糾結
《巨流河》流淌著坦誠而真率的文學血液,它記述了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以東北淪陷、中山中學西遷、齊家逃難、齊世英等仁人志士積極抗日、教育救國、齊邦媛南開求學為經緯,把個人的血淚經歷編織在大歷史中,書寫著大歷史中的個人歷史。在南開中學,老師們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希望和信心,教授學生獻身與愛以及自尊與自信;在陪都重慶,戰火紛飛、時局惡劣的情況下,西南聯大等學校仍弦歌不輟,繼續辦學興學,為國家和抗戰培養眾多人才。《巨流河》還以素樸的語言訴說中華民族歷盡劫難得出的血淚經驗與歷史教訓,從歷史深處解讀上半個世紀中國教育史的奇跡,南開、北大、清華、武大、中央大學等高校在中國現代大學史上聲名顯赫、至今回響,詮釋了在艱難困苦的時代環境下延續民族命脈、承繼文化血脈的歷史事實。作品從第六章開始細述齊氏一家遷臺后的種種境況,同時也向讀者展現了20 世紀50 年代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狀況。齊邦媛的一家終未能還鄉,這種縈繞于心頭的離愁別緒,如“千年之淚”,揮灑不去。齊世英夫婦去世后,安葬在靠海朝北的墓地,齊邦媛夫婦也在此預留了墓地。在這里,可以聆聽從巨流河輾轉千里奔流而來的問候與訊息,頭枕寶島可北望東北故土。
齊邦媛的一生,正是整個20 世紀波折動蕩的縮影,是大歷史中的個人歷史。她出生在多難的年代,在漂泊中度過一生,沒有可歸的田園,只有歌聲中的故鄉。在動蕩的年代里,在漂泊輾轉的歲月里,齊邦媛有幸接受了良好而完整的教育,并廣泛接觸到眾多仁人志士。戰亂中那些凄厲的哭喊聲,在許多無寐之夜震蕩,成為齊邦媛由文學的閱讀而擴及全人類悲憫的起點。她生長在革命者家庭,自童年起耳聞、目見、身歷種種歷史上的悲壯場景,許多畫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靜和幸福歲月的經驗,都無法將它們從心中抹去。齊邦媛由大陸輾轉到臺灣,立志于教書育人,參與教學改革,實現文學夢,推動臺灣文學發展,使臺灣文學走向國際舞臺。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她浸潤于中國文化與文學的教育教學中,沒有絲毫的懈怠,并不斷地進修、訪問、工作。她單純地把讀書當作生命的一部分,“在一本一本的書疊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從未停步”①齊邦媛:《巨流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43、370、5頁。,正是這份溫潤而充滿韌性的堅持使她成就斐然。齊邦媛說父親齊世英是溫和潔凈之人,錢穆先生是寬容溫熙之人,張大飛的一生“燦爛潔凈,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②齊邦媛:《巨流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43、370、5頁。。她懷著“對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③錢穆:《〈國史大綱〉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頁。,述說著大歷史中努力抗爭的個人歷史故事。《巨流河》既是一部洗練可靠的歷史資料,又是一部妙筆生花、情感純凈的文學作品。通過這樣一部作品,一方面得以窺見歷史的真貌,親歷逝去的歲月,另一方面感受人世的興衰,緬懷個人的顛沛流離,體味作品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潔的人性光輝”④齊邦媛:《巨流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43、370、5頁。。
(二)個人記憶的時間次序與情感的輕重
自傳是作者通過回顧和自敘生平的一種相對完整、真實、準確的敘事,是以作者為中心的一種敘述方式。自傳的寫作離不開對記憶的追尋與探索,而記憶是超越于時空之上重現逝去的往事,不管用什么樣的方式敘述過去,所有關于過去的再現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一種回憶活動。因此,回憶包含兩個時間維度:事件發生的時間(過去)和回憶事件的時間(現在)。《巨流河》沒有為了刻意制造虛幻的當下感而隱去回憶的痕跡,相反,她不斷提醒自己和讀者,一切都已成為往事。自傳者在回憶過去時,把過去詩化和美化,這是自傳寫作時常有的一種態度。隨著歲月的流逝,年歲的增長,人們對過去產生一種留戀與惜別的感情,這是人之常情,而種種不愉快的經歷會逐漸淡出記憶。自傳的寫作,蘊含著深深的留戀,淡淡的傷感和懷舊情緒也是自傳中常可感受到的氛圍。齊邦媛表示,她從東北到臺灣,一生學文學、教文學,最重視人類的痛苦問題。《巨流河》的文字來自作者的心靈深處,帶給讀者平靜的救贖力量。自傳的寫作主要依靠自己的回憶,或者以回憶為基礎,《巨流河》便依從了記憶本身的活動規律和事件之上的邏輯聯系來安排過去的人與事。對于漂流者來說,過去的消逝是一種異常徹底的現象,甚至無法借助空間的重返和殘存物事的重睹來喚回一些零星的印象,只有憑借記憶,才能找回失去的時光,以完成記憶對抗遺忘的寫作,最終獲得自我的救贖。
誠然,“《巨流河》是齊邦媛老人記憶的河流”①李厘:《如此悲傷,如此遼闊,如此獨特》,《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44期。。齊邦媛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璣的筆力,細致把握對生命、生存等實況的復現與細膩的追索,流露出真摯而率性的情感。在通向記憶的道路上,作者的感情不斷發生變化并不斷停下來,“此刻”的自己面對回憶中“彼刻”的自己及人與事,懷著對民族與國家的真摯熱誠,審視自我,重新思索歷史與現實。回望那條漫長的來時道路,感慨歷史浮沉,往事并不如煙,許多的人和事及情感,都已成為刻骨銘心的清晰記憶。齊邦媛的記憶是一種純粹的個人記憶,不同于那些已成型的權威歷史,她的文字不是史料的表述,而是更忠實于自己的記錄。這是一個艱難的寫作過程,獨自踏上靈魂的返鄉之旅,再次“經歷”最私密的初戀,以及人生中經歷過的難以忘懷的事件,因此以更虔誠的態度對待往事。在齊邦媛筆下,這些往事是比個人生命更龐大的存在,她不能也不愿將它們切割成零星片段,掛在必朽的枯枝上,而是必須傾全心之虔敬來作此大敘述②齊邦媛:《〈巨流河〉序》,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頁。。作者哀婉內斂的文字如靜靜的河流,沉靜而有力地流淌于心中。顛沛流離的祖國,幾代人的家國之痛……幾十年過去了,人們的心靈仍然布滿大大小小的彈痕。正如富蘭克林在解釋人們為什么寫自傳時所說:“人的生命的無法重復性,以至于只有回憶是最接近它的方法之一。然而,最像重演人生的事情,就是將生平經歷通過回憶,然后把它寫出來,使它們能夠在盡可能長遠的范圍內流傳下去。”③[美]富蘭克林:《富蘭克林自傳》,陳冬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頁。依靠記憶女神摩涅莫緒涅的力量,齊邦媛把歷史與生命的脈絡藏于細密的追憶與可見的情境之中,形成了一種圓形敘事模式。
二、獨特的敘述聲音與視點
自傳是一種“回顧”性的敘述,“回顧”是對過去發生的事的回憶,這就意味著真實,虛構自然不能成為“回顧”,只有對歷史的記憶和重現才是回顧。而這種回顧總是帶有強烈的、難以避免的主觀色彩。自傳作為一種自我敘述,作者的隱秘事件或心理活動,其他人無法核實,只有文化傳統所形成的慣例,即所謂“自傳契約”,對作者形成一種心理的約束。《巨流河》對敘述的聲音和視點的靈活處理與變換,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節奏與張力。
(一)敘述的聲音和視點
在自傳中,一般說來,作者就是敘述者,敘述者也就是傳主,他(她)敘述自己的親身經歷,作者、傳主、敘述者是同一的,否則就不能被公認為自傳。在文本中,同敘述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視點。所謂的視點,是敘述者觀察和敘述對象的立足點與觀察點,這是為敘述者提供的一個虛擬的位置。優秀的傳記家,總是恰當地進行著視點的轉換。作者采用全知視點,有時也會根據需要,轉入其他視點。如果一部傳記始終采用全知視點,對過去、現在、未來無所不知,把一切都敘述得清清楚楚,那也就失去了曲折和懸念,破壞了讀者對傳主的關注和好奇。《巨流河》的敘述方式顯得靈活,作者以自由或全知視點游走于人物內心。
有些自傳作品,視點是人物的,聲音則是敘述者的,敘述者只是轉述和解釋筆下人物包括過去的自己所看到和想到的東西,這樣雙方便呈分離狀態。這種現象既包括在講述有關他人的故事,也包括在講關于自己的或包括自己在內的故事。《巨流河》中,這種分離狀態表現在時間上,視點是當時的齊邦媛,而陳述者則是故事發生若干年后的齊邦媛。如齊邦媛與哥哥和其他大男孩一起去爬牛首山,當時“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著一塊小巖頂,進退兩難。山風吹著尖銳的哨音,我在寒風與恐懼中開始哭泣。這時,我看到張大飛在山的隘口回頭看我”。顯然,此處敘述的是往日的經歷。而“數十年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里由隘口回頭看我”①齊邦媛:《巨流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40頁。,則是在多年后齊邦媛講述的故事。時間的距離使敘述者能夠對往日的痛苦和快樂作出更為理性的評價。全知視點在此成為齊邦媛個人的獨特“心靈視點”,它不受時空限制,有點意識流的意味,但與意識流不同,那就是更在時間的粗線條之下展開的。
在自傳中,個人的敘述往往會擺脫所謂正史帶來的條條框框,可以看到更多從條框中逃逸出的真實瞬間。自傳敘述真實地重現個人及其生活的世界,歷史被個性化和故事化,更加具體、豐富、充滿細節,既是真實的故事,又帶著個性與溫情,同時也包含審美的愉悅。齊邦媛個人的敘述方式凸顯出更加細致和細節化的文學形式。
(二)傳記的節奏與張力
對于文學性較強的傳記來說,傳記家在進行敘事時不斷對視點進行或內或外的調整、或遠或近的變換,交替使用總體或是細部的敘述。敘述時態主要是采用現在時態的同步敘述,但也加入回顧敘述或前瞻敘述,針對傳主的經歷,進行時態處理,把在不同時空中發生的豐富多彩的事件和復雜的背景安排成明晰、流暢的線型敘述;他們精心選擇材料,把存在層次和行動層次的敘述加以合理地安排,適當進行情理層次的敘述;敘述的范圍在故事內可以適當加上故事外敘述,自我故事之外可以適當加上非我故事;在敘述的層次和敘述的范圍內,某些地方進行充分敘述,另外一些地方則作簡約敘述,或只是一筆帶過。敘述的視點、時態、層次、范圍和程度既符合傳記的基本的要求,又加以適當的變化。這樣,圍繞著傳主經歷、個性以及對傳主的解釋,展開了豐富的歷史內容,也同主體的感受結合在一起,時繁時簡,時遠時近,有時舒緩鋪陳,有時急促快捷,傳記家不斷變化的敘述態勢,再現了以傳主為中心的波瀾起伏的生活流,形成了獨特的自傳節奏和張力,給予讀者以閱讀的快感,也彰顯傳記家的才華與藝術個性。
齊邦媛通過溫婉和冷靜的敘述,引領讀者漫步于她那蜿蜒曲折的人生、生命回廊中。她的敘述所體現的含蓄與內斂,還表現在她對自己“初戀記憶”的分散化處理上。初戀的記憶是無法被時間打敗的,時間愈是久遠,感情愈加強烈,但是強烈的敘述語言反而會破壞情感的神圣性,齊邦媛把初戀這朵由記憶深處散發幽香的鮮花,鋪灑在敘述的道路上,自然而純凈,這樣看來,她在第一章就寫個人初戀故事,就不覺得奇怪了。而且,她這種先拿出個人私隱,一直到最后一章前往南京“尋墓”,前后是一體的,即首尾一致。相對于個人的“小歷史”來說,齊邦媛更看重私人感情,尤其初戀記憶,這是與其他自傳的最大區別。齊邦媛和張大飛在南開中學的最后一面是作者與讀者都難以釋懷的,敘述上的內斂讓人覺得仿若昨日,真實生動,情感細膩,情緒控制得恰到好處。
三、壯闊的史詩風格與真實而溫情的人性關懷
(一)壯闊的史詩風格
35 萬字的巨作,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廣闊的地域空間,從東北的巨流河寫起,以臺灣的啞口海結束,種種讓人難以忘懷的人物形象,以及齊邦媛大半生的經歷與內涵豐富的文學情懷,都于此書中體現出來。《巨流河》是用生命書寫成的記憶文學和天籟詩篇,彰顯壯闊的史詩風格。正如蔣勛先生的評價:“沉重的史詩,齊老師卻能云淡風輕寫出,展現文學的驚人之美。”她用真摯的筆調,講述在20世紀這個大時代背景下,個體和家族的命運:溫和潔凈卻為國投身政治的父親齊世英,一生為兒孫輩哼唱搖籃曲《蘇武牧羊》,最終埋葬于臺北淡水未曾再見過心中北海的母親,背負國恨家仇葬身藍天的張大飛,課堂上朗誦華茲華斯詩歌時突然哽咽的朱光潛,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國學大師錢穆……每個人都被歷史激流裹挾著向前,無從選擇無從逃避,但都有著難以言盡的不屈和堅守,演繹出一個個動人心魄的史詩故事。
齊邦媛滿含深情地寫下溫文儒雅的父親齊世英大起大落書生報國的一生。作為國民黨元老的齊世英,從民國初年的留德熱血青年,到“九一八事變”前的東北維新派,他畢生憾恨都圍繞著巨流河功敗垂成的一戰,“渡不過的巨流”象征著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凍于此,從此開始了東北終至波及整個中國的近代苦難,成為志士心中最深的隱痛。遷臺后,齊世英因反對國民黨通過增加電費以籌軍餉的做法而得罪蔣介石,被開除黨籍,過早結束事業。他一身傲骨,從來不能躋身權力核心,晚年每每提及東北淪陷,都不禁潸然淚下,郁郁寡歡。在兒女的眼中,他一生都是溫和潔凈的真君子。東北子弟張大飛,是抗日英雄的形象,他的家破人亡的故事更震人心魄,其父在滿洲國成立時任沈陽縣警察局局長,因協助抗日人士,被日本人澆油漆燒死。年少的張大飛不得不逃入關內,進入中山中學得以與齊家結緣,“七七事變”后放棄學業加入空軍,勝利前夕在與日本人的空戰中以身殉國。他短暫的人生,如曇花一現,但他是在黑暗里開放的艷麗花朵。少女時代的齊邦媛與英雄張大飛的接觸,成為她一生難以忘懷、割舍的記憶與體驗。
文學大師朱光潛,是齊邦媛人生道路上有幸遇到的另一位導師。齊邦媛考入武大哲學系,朱光潛賞識她的才華,親自促成她轉入外文系,從此齊邦媛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巨流河》中呈現出這位文學家鮮為人知的一面,在戰火中,講臺上的朱光潛講授華茲華斯的長詩時,突然取下眼鏡,眼淚流下雙頰,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①齊邦媛:《巨流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13、277頁。。在齊邦媛眼中,朱光潛的美學底色是“靜穆”,而這“靜穆”是痛定思痛后對掠奪、對燒殺的一種沉默的抗議,也是知識分子的自尊與悲憫情懷的體現。“一生為故國招魂”、渴望祖國安定的錢穆,為齊邦媛的忘年之交。錢穆當時隱居于臺北士林外雙溪素書樓,齊邦媛常親炙這位國學大師,他們共同經歷“國立編譯館”事件,被卷入政治爭端,在處世不驚中談人生、文學,齊邦媛從錢穆身上學到文人在亂世中的處世之道。然而1990年夏天,錢穆迫于陳水扁、李登輝之徒的壓力倉皇遷出素書樓,兩個月后含恨逝世。齊邦媛深感這種政治操縱下的歷史、文化的悲痛在所難免。然而在政治風暴中,個人記憶對歷史的溫情和敬意昭示著“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②齊邦媛:《巨流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13、277頁。。
(二)真實而溫情的人性關懷
長期以來,真實是自傳作品的最高標準甚至唯一標準。真實是自傳的靈魂,自傳的真實意味著準確和公正。自傳的事實被稱為心靈的證據。胡適指出:“傳記最重要的條件是紀實傳真。”③胡適:《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吳淞月刊》1930年第4期。自傳是對一個時代精神最深刻的記錄,是人的歷史,也是對真實人性的動態記錄,《巨流河》在一定程度上是齊邦媛的個人自傳,她采用了個人化的話語與寫作方式,敘述了知識分子真實的心路歷程。而這部自傳打動人心的力量之源正是它那令人震撼的真實。
一部自傳可以反映出一個人個性的成長和發展,一部自傳史就是人性成長和發展的歷史。自傳家把一種活生生的人格從歷史的主流中喚醒并再現出來,并給予同情性的理解,而這種同情性的理解正是人道主義的必由之路。自傳記錄和描述人性,也總是體現和宣傳人道主義精神。對人的同情、關懷和理解,是人道主義的精華和核心。齊邦媛在接受臺灣媒體采訪時曾說:“寫作過程中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渲染,不要抒懷,盡量讓歷史和事實說話。”①武云溥:《兩代人的家國情懷》,《源流》2011年第3期。對于一部未寫將死不瞑目的書,齊邦媛強烈克制自己的情感,讓書中人物回到歷史現場去“說話”,關懷每一個靈魂。
自傳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在挖掘內心世界的同時引起人性的共鳴,并使讀者認識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和特定的歷史時代。前代人的某些思想和行為,后人常常無法理解,通過自傳則多少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也理解那個時代人的思想和行動的方式,這就把過去與現在、古人和今人聯系成一個整體,歷史與文化傳統可以在這里延續下去。自傳把現實中的人同歷史中的人聯系起來,這不是虛構的人物,而是真實存在的人物,讓他們互相理解,進行對話,學會尊重和同情,也互相學習,為自身的發展和自我的完善汲取更多的思想的營養與動力。2009 年7 月《巨流河》由臺灣天下文化出版繁體字本,2011 年大陸三聯書店出版簡體字本,在日本版推出之際,齊邦媛對此表示“全世界應該了解書中時代的讀者,都到齊了!”她希望:“日本人可以借由這本書,知道中國人怎么想的,體會原來我們沒有不同,更應超越敵對與戰爭。”②蘇婭、齊邦媛:《如果注定漂泊,那么讓靈魂安頓》,《第一財經日》2011年8月19日第D03 版。無論社會有過多少黑暗和混亂,人性有過多少迷茫和掙扎,自傳總是在證明:社會和人性的進步。誠如齊邦媛所言:“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記述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③齊邦媛:《〈巨流河〉序》,《巨流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頁。
四、結語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寫道:“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十歲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④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頁。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巨流河》揭示了大時代里普通人顛沛流離的生涯,講述了時代變化中個人的堅守與追求,秉承了潔凈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高齡的齊邦媛決定不能不說出故事就離開,“即使身體的疲勞如霜雪重壓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盡燈枯,我由故鄉的追憶迤邐而下,一筆一畫寫到最后一章,印證今生,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一個完整的圓環。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將化成灰燼,留下這本書,為來自‘巨流河’的兩代人做個見證”⑤齊邦媛:《〈巨流河〉序》,《巨流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頁。。這亦是《巨流河》作為自傳文學的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