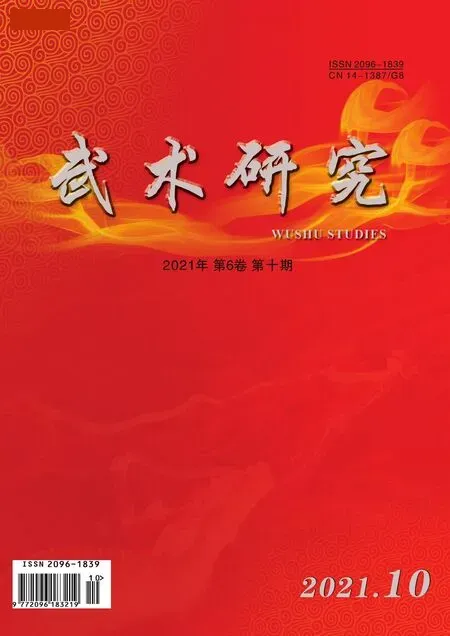清代武術(shù)發(fā)展的藝術(shù)化研究
鐘遠鳴 王 月
1.福建師范大學(xué),福建 福州 350117;
2.寧德市民族中學(xué),福建 寧德 355000
1 前言
對于中國武術(shù)的研究,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運動和項目的視角開展,更應(yīng)該關(guān)注中國武術(shù)的文化意義,甚至還要著重觀照中國武術(shù)的藝術(shù)價值和意義。“藝術(shù)是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需要專門研究和觀照的文化整體的一部分”。[1]對于中國武術(shù)的闡釋,如果忽略了對其藝術(shù)屬性的研究和探索,很可能就導(dǎo)致對中國武術(shù)整體把握的不全面、不準確,也就可能導(dǎo)致對中國武術(shù)價值判斷的偏頗和缺失。因為作為身體文化存在的中國武術(shù),很大程度上其藝術(shù)特性的存在是有目共睹的。“武術(shù)不是純體育,不是純運動,也不是純殺人術(shù)。武術(shù)是一門藝術(shù)”。[2]藝術(shù)是人類生活多層次、多維度的形式化過程,它讓人類的情感世界得以展現(xiàn),是人類的自造世界。[3]武術(shù)源自狩獵與戰(zhàn)爭,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大助力,它除了具備實用性外,也具備藝術(shù)性。武術(shù)套路是人們對武術(shù)經(jīng)過琢磨、推敲,對技擊術(shù)進行提煉、加工而創(chuàng)造出的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清代是武術(shù)發(fā)展快速階段,對此時期武術(shù)的研究更有價值。
2 武術(shù)的動態(tài)藝術(shù)
武術(shù)的動態(tài)藝術(shù)是以動態(tài)的形式呈現(xiàn)出藝術(shù)的效果。武術(shù)起源于狩獵與戰(zhàn)爭,它以動態(tài)形式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清代的冰嬉盛典和木蘭秋狝是以武術(shù)為主要元素的皇家大型動態(tài)藝術(shù)活動;武術(shù)是一項身體運動,這點與雜技是相同的,武術(shù)與雜技交相輝映,更具有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韻味。
2.1 冰嬉
“冰嬉”顧名思義就是在冰上嬉戲、嬉笑的活動,主要包括搶等、搶球、轉(zhuǎn)龍射球等項目,搶等項目類似于速度滑冰,搶球項目類似于冰球和橄欖球的組合項目,轉(zhuǎn)龍射球,則是把射箭技術(shù)融入冰嬉活動中的一個項目。在努爾哈赤(1559-1626年)入關(guān)前,生活在東北地區(qū)的滿族人就有冰嬉的傳統(tǒng)。清朝時期冰嬉這一滿洲傳統(tǒng)運動逐漸發(fā)展成為了大清的國俗。每年冬至入九以后,太液池(即今北京北海、中南海)結(jié)冰堅實,清代皇家便在此舉行冰嬉盛典,盛典一直持續(xù)到三九才結(jié)束。[4]武術(shù)在軍事中稱為“戰(zhàn)陣武藝”,士兵們的戰(zhàn)斗力除了精湛的武藝之外,還要有良好的身體和心理素質(zhì),冰嬉正是清代一種檢驗士兵戰(zhàn)斗力的方式。冰上武藝將冰雪運動與傳統(tǒng)武藝融為一體,將傳統(tǒng)武藝的本體元素與冰雪交融,呈現(xiàn)出活力四射的冰上“激情”;以八旗聲勢為傳統(tǒng)冰場鋪展色彩;以高難度的花樣滑冰技巧與驚奇險要的武藝技巧相結(jié)合,展現(xiàn)出唯美、浪漫的情懷,它既有花樣滑冰飄逸的身姿、灑脫的流動美,又兼顧了傳統(tǒng)武藝的高超技藝與驚險刺激。為了維持滿族人對于漢族及其他民族的統(tǒng)治,就必須保持滿族所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因此,冰嬉這一傳統(tǒng)活動被很好地保留了下來。統(tǒng)治者借此讓八旗士兵勤加練習(xí)武藝,提高其軍事技能,此舉對清朝統(tǒng)治者可謂是一舉兩得。冰嬉作為大清國的國俗,冰嬉背后的意義則是籠絡(luò)八旗士兵、提升他們戰(zhàn)斗力的政治手段。冰嬉主要以表演的形式展現(xiàn)清帝與八旗同樂的場景,其背后所帶著的政治寓意和軍事武術(shù)展演才是冰嬉的真正意義,是彰顯國力、宣揚國威的政治手段,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國家軍事武藝的高超技術(shù)上。
2.2 木蘭秋狝
木蘭秋狝是清代皇家的大規(guī)模的狩獵活動,清朝早在入關(guān)以前的太宗(皇太極)時期就已開始有狩獵活動。入關(guān)以后,清統(tǒng)治者仍沿襲滿族騎射和游牧的生活習(xí)俗,始終把“巡狩習(xí)武”作為其重要的政治活動。[5]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康熙二次北巡,發(fā)現(xiàn)北出長城喜峰口,經(jīng)寬城行至華北平原與內(nèi)蒙古草原接壤處,發(fā)現(xiàn)此處水草豐美,動物繁多,于是令人“前進相度地勢,酌設(shè)圍場”,[6]時稱木蘭圍場。木蘭圍場是清代皇家規(guī)模最大的圍場獵苑,康熙規(guī)定,自此清帝每年秋天帶領(lǐng)皇子皇孫和王公大臣在此打獵,即“木蘭秋狝”。清朝大部分八旗子弟生活驕奢淫逸,導(dǎo)致清王朝的戰(zhàn)斗力大不如前,為了提高滿族人的戰(zhàn)斗力,清帝規(guī)定每年清朝貴族必須遠行進行一次打獵活動。木蘭秋狝既是一次和平的圍獵,但同時打獵,場面威武,又不可避免地對塞外各部族具有一種耀武揚威的威懾作用。時人尹繼善在《木蘭隨圍感恩紀事》中描繪這一行圍的場面和影響作用時說:“霓旌動處武維揚,猛士聲喧共陟岡,信是天威能播遠,道旁舞拜盡名王”。[7]時人趙翼也說:“上每歲行狝,非特使旗兵肄武習(xí)勞,實以駕馭蒙古諸部,使之畏威懷德,弭首貼伏而不敢生心也”。[8]木蘭秋狝是清代皇家一年一度的狩獵活動。如果說冰嬉的主要藝術(shù)效果是安外的話,那木蘭秋狝的主要藝術(shù)效果就是安內(nèi)了,木蘭秋狝不僅要求皇位的繼承者們身手矯健,還促使其精于打斗、騎射之藝,是統(tǒng)治者妙心的藝術(shù)技藝。
2.3 雜技
雜技亦稱為“雜伎”,以高、難、險、奇而和諧的技能為特征,是各種技藝表演的總和。雜技比其他歌舞戲曲曲藝等表演藝術(shù)更接近武術(shù),兩者同時出現(xiàn)在中華大地上。武術(shù)與雜技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列子·說符篇》中記載到:“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并趨并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蘭子在高蹺上耍弄短劍以娛諸侯,將武技與雜技相互交融滲透。古時武術(shù)與雜技經(jīng)常交織在一起,許多兵器成為雜技的表演道具,如“飛叉”就是由武術(shù)器械演化而來。落魄潦倒的武林人物,常常流落江湖,打拳賣藝和跑馬賣解常常是武士們謀生的手段。雜技藝術(shù)行中也有許多武藝高超的人物,對于中國武術(shù)的發(fā)展和普及起到了有益作用,有的還成為反抗官府、發(fā)動和組織人民起義的領(lǐng)袖人物。如白蓮教的起義領(lǐng)袖王聰兒,她所領(lǐng)導(dǎo)的起義,震動朝野。20世紀80年代得獎長篇小說《白衣俠女》就是根據(jù)王聰兒的史跡創(chuàng)作的一部傳奇小說。
武術(shù)與雜技常常交織在一起,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合力不斷地將雙方推向嶄新的高度,從而各自的藝術(shù)內(nèi)涵更加深厚,兩者交織滲透流傳下來的各種藝術(shù)形式多樣,流芳百世。
3 武術(shù)的靜態(tài)藝術(shù)
3.1 繪畫
武術(shù)與繪畫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武術(shù)演繹時而氣勢如虹,時而溫柔婉轉(zhuǎn),他貫穿人類歷史,因此有人用繪畫的形式來紀錄武術(shù),從中國的壁畫、年畫中都看見武術(shù)的蹤跡。少林武術(shù)為武術(shù)正宗,在少林寺白衣殿的壁畫上,有大量關(guān)于武術(shù)的記錄圖畫。在白衣殿內(nèi)的南北墻壁上有清末繪制的“武僧演武圖”,又稱“羅漢手搏像”“少林錘譜”,其北壁繪的是少林武僧在大雄寶殿前格斗的場面,共16組,33位武僧,壁畫中除一個是一對二進行格斗外,其余均是兩兩相對。北墻壁畫是清代少林武僧演武的真實寫照,一招一式都體現(xiàn)出了少林功夫的精髓。白衣殿南壁的壁畫為《少林器械圖》,場面描繪的是麟慶觀看少林寺武術(shù)演練的情況,即少林僧人練刀,槍,劍等兵器格斗的場面,再現(xiàn)了少林兵器的特點,是珍貴的少林兵器實物資料。清代的武術(shù)家、書畫家傅元在畫墨竹時,依據(jù)醉舞拳藝而求靈感的故事,反映了中國武術(shù)與繪畫的相通之趣。繪畫與武術(shù)一樣,在前進的道路上是進無止境的。用繪畫以“靜”的方式記錄武術(shù)“動”的藝術(shù)之美,需要深厚的繪畫功底和對武術(shù)深深的了解,才能將武術(shù)描繪得栩栩如生。武術(shù)的形象通過繪畫得以展現(xiàn),繪畫則以獨特的手法使武術(shù)底蘊更加深厚,一動一靜,兩者相輔相成,以自身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為對方的領(lǐng)域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3.2 塑像
清代的雕塑繼明代之后是進一步衰退的,但民間和少數(shù)民族的雕刻有了進一步發(fā)展。[9]少林寺的錘譜堂原名西來堂,又名西來庵,在山門后碑林西側(cè)。據(jù)乾隆十三年《少林寺志》載,西來堂為康熙時曾任登封縣僧會司僧官的少林寺僧人真喜創(chuàng)建,真喜徒孫,時任登封縣僧會司僧官的海岱于乾隆初年重修,清道光時又重修主要將歷代少林寺武僧習(xí)武的主要拳法及僧兵歷史故事,分14組、215尊塑于長廊之中,由此名之“錘譜堂”。少林寺是武術(shù)的搖籃,對少林武術(shù)的呈現(xiàn)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其中塑像是最具體、最直觀的呈現(xiàn)方式。塑像藝術(shù)追求的意境有多種,在少林錘譜堂中的塑像,藝術(shù)性多則以寫實為主。武術(shù)的功能不僅局限于狩獵和戰(zhàn)爭,還包括健身功法、娛樂性表演等多種功能。習(xí)練武術(shù)想要達到一定的高度,學(xué)習(xí)方式除了師父的口傳身授外,自學(xué)自悟的學(xué)習(xí)習(xí)慣也得具備,這時塑像的作用對武術(shù)自學(xué)者的作用是巨大的。塑像對一個武術(shù)動作的呈現(xiàn)是全方位的,可供學(xué)習(xí)者360度臨摹,使學(xué)武者更快更直觀的掌握塑像所呈現(xiàn)的動作。若沒有塑像藝術(shù)對各種武術(shù)招式的呈現(xiàn),后來者很難整體把握其動作要求和領(lǐng)悟動作要領(lǐng)。
3.3 文學(xué)
中華民族的文學(xué),是以漢民族文學(xué)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學(xué)的共同體。中國文學(xué)有數(shù)千年悠久歷史,以特殊的內(nèi)容、形式和風(fēng)格構(gòu)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審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和理論批判體系。它以優(yōu)秀的歷史、多樣的形式、眾多的中國作家、豐富的作品、獨特的風(fēng)格、鮮明的個性、誘人的魅力而成為世界文學(xué)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瑰寶。比如少林功夫中許多套路動作名稱大都來自中國古典文學(xué)。如少林猛虎拳的“黃忠放箭”,少林降妖拳的“黃忠拉弓”,少林天罡劈水扇的“孔明揮扇”“關(guān)公擦袍”“趙云闖關(guān)”“張飛騙馬”等動作招式來源于《三國演義》的典型人物;少林五合拳的“哪吒攪海”,一路二路少林猛虎拳的“八戒翻耙”“天王托塔”,少林棍中的“悟空藏棍”,一路開山拳的“童子拜觀音”等的出處為《西游記》;“太公釣魚”“子牙斬將”出自“武王伐紂”的故事;“孫臏排兵”等出自歷史典故等。武術(shù)的傳承需要公正的載體。文學(xué)對于武術(shù)的傳承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它不似人為的傳承一般具有甄別性,其所知對武術(shù)學(xué)習(xí)者的傳承是毫無保留的,只看學(xué)武者對武術(shù)的悟性和自身的天賦了。武術(shù)在文學(xué)藝術(shù)的熏陶下,富有中華文化底蘊,極具歷史與神秘色彩,中華武術(shù)的博大精深,正如文學(xué)一般,意味深遠。兩者都有使人細細品味、意猶未盡的藝術(shù)效果。
3.4 書法
書法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傳統(tǒng)藝術(shù),是以文房四寶為工具抒發(fā)情感的一門藝術(shù),是一種展現(xiàn)文字美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武術(shù)與書法有相通之處,練功習(xí)武可使揮毫落墨猶如神助。正因為兩者密切相關(guān),所以才有草圣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后得到書法的神韻的佳話。在眾多武術(shù)家中,擅長書法者不計其數(shù),如孫祿堂的書法,運轉(zhuǎn)自如、骨力抱藏其中,渾如其拳法。[10]“山谷行書,長撇大捺;武當(dāng)拳法,鳳舞龍蟠。右軍小楷,鐵畫銀鉤;少林拳術(shù),其勁在骨”,這說明武術(shù)與書法同理,在理論和技法上有異曲同工之妙,書法講究的筋、骨、神、氣四者鋒勢俱全,都流露出內(nèi)在的勁力與其相通之理。武術(shù)也講究“勁力”,太極拳中的“勁”起于腳跟,發(fā)于腿,主宰于腰間,形于手指,發(fā)干脊骨,由腳而腿而腰,一氣呵成;發(fā)勁時則要求勁整,正所謂“周身合下成千斤”,如此方能借力使力,四兩撥千斤。武術(shù)與書法都來源于生活,通過相互借鑒、學(xué)習(xí)和探索,能夠開擴眼界,從而使書法藝術(shù)增強意境、氣勢、韻味、節(jié)奏感、美感和書法的功力;同時通過欣賞、研究、學(xué)習(xí)書法,引起共鳴和豐富的聯(lián)想,有助提高武術(shù)套路的演練、技巧和表演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
4 武術(shù)藝術(shù)化作用
4.1 提供終極的人文關(guān)懷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武術(shù)的性能從對人的較大傷害,到經(jīng)過藝術(shù)處理后形成了“美善統(tǒng)一,德術(shù)并重”的民族技藝,使原本殘忍的殺戮回歸到體育的范疇和為健康服務(wù)。武術(shù)的藝術(shù)化就是追求武術(shù)的審美價值,是武術(shù)從物化層面過度到武術(shù)的精神層面,最終回歸到天人合一的審美至高境界。從“技擊”到“技藝”是武術(shù)的最高境界,是對天道自然、宇宙萬物生化之理的體悟和體驗。[11]可見,武術(shù)的最高目標不是搏殺,而在修身養(yǎng)性,與自然、社會保持一種和諧或穩(wěn)定狀態(tài),充分體現(xiàn)了武術(shù)的人文之美與和諧之美。
4.2 豐富武術(shù)的文化內(nèi)涵
武術(shù)是一項集強身健體、修心養(yǎng)性、休閑娛樂于一體的文體活動,融入了哲學(xué)、美學(xué)、醫(yī)學(xué)、兵學(xué),倫理學(xué)等學(xué)說,豐富了武術(shù)的文化內(nèi)涵。近年來,以武術(shù)動作為素材并融入美妙動聽的旋律創(chuàng)編的武術(shù)類項目,比如武術(shù)操、搏擊操、太極拳等等,尤其是場面開闊的集體表演項目,圖案多變,威武雄壯,加上節(jié)奏清晰的民族音樂和古色古香的服飾陪襯,追求動作的整齊、歸一、規(guī)范、協(xié)調(diào)、連貫、和諧的審美視覺和優(yōu)雅的審美享受,這些藝術(shù)因素的介入大大豐富了武術(shù)的文化內(nèi)涵。
4.3 提升武術(shù)的審美價值
中國武術(shù)朝著體育化、虛擬化、程式化、娛樂化的方向發(fā)展,有效提高了武術(shù)的欣賞水平與審美價值。武術(shù)中雖然有擊、打、摔、拿、踢等技擊動作,但形成套路后,面向?qū)嶋H并不存在的“敵人”完成動作,只是間接提示、暗示、象征所要表達的技擊內(nèi)容,這種對技擊的表達方式旨在提高它的欣賞價值與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武術(shù)與藝術(shù)交相輝映,形成一道獨特的審美觀景。
5 結(jié)語
武術(shù)是人們在生產(chǎn)勞動的實踐中總結(jié)下來的生存技能,為了演繹或保留經(jīng)典的武術(shù)藝術(shù),人們采用動態(tài)或靜態(tài)的藝術(shù)形式將其流傳了下來。清代武術(shù)藝術(shù)流傳的動態(tài)形式主要有冰嬉、木蘭秋狝、雜技等;靜態(tài)形式主要有繪畫、塑像、文學(xué)、書法等。無論以何種藝術(shù)形式記錄武術(shù),都是對武術(shù)藝術(shù)的肯定。由于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化傾向的影響,在今后相當(dāng)長的時間內(nèi),藝術(shù)化將是武術(shù)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武術(shù)的藝術(shù)化之路將越走越寬廣,能更好地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弘揚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