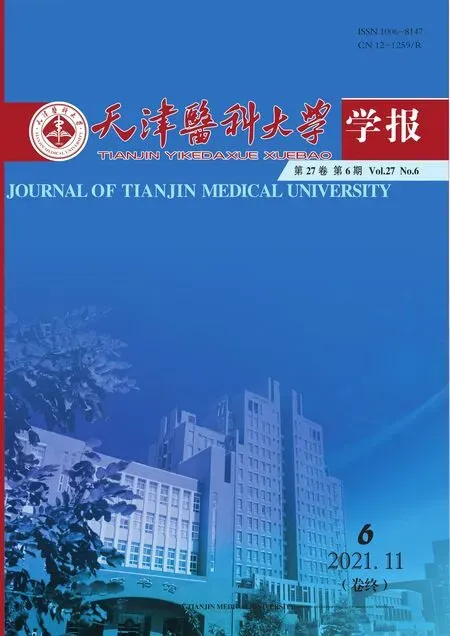Kallmann綜合征1例報告
趙悅,蔣海燕,鄭榮秀
(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兒科,天津300052)
卡爾曼氏綜合征(Kallmann綜合征,KS)是一種臨床上較為罕見的遺傳性疾病,是特發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功能減退癥中最常見的類型,伴有嗅覺減退或缺失,男性發病率較女性高,為1∶8 000,女性為1∶40 000,具有顯著的基因型和表型異質性[1]。近年來,隨著基因測序的廣泛應用,已證實超過20個不同的基因突變位點與KS有關系。現結合相關文獻對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收治的1例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1(FGFR1)基因檢測到新發突變位點致KS患兒報道如下。
1 病例介紹
1.1 臨床特征與一般資料 患兒,男,1歲4個月,生后3個月家長發現患兒陰莖短小,就診于當地小兒外科考慮“陰莖、睪丸發育較小”,未予特殊治療。隨后因患兒陰莖、睪丸仍無明顯增長,生后8個月于當地兒科門診就診,診斷為“不除外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癥(17-α羥化酶缺乏)”,未給予特殊治療。患兒現1歲4個月,陰莖、睪丸較出生時無明顯增長,為求進一步診療于2020年7月23日就診于我院兒童內分泌科。入院查體:營養良好,精神反應好,智力發育、運動發育與正常同齡兒無明顯差距。五官發育未見明顯異常,無特殊面容,胸腹部體格檢查無異常,脊柱、四肢無明顯畸形,四肢活動自如,肌力、肌張力正常,神經系統查體未見異常;專科查體:身高:82.4 cm(位于同年齡同性別同種族兒童第50~75百分位),體重:10.5 kg(位于同年齡同性別同種族兒童第25~50百分位),體重指數(BMI):15.46 kg/m2,血壓:91/63 mmHg(1 mmHg=0.133 kPa),上部量/下部量=1.03,指間距77 cm,頭圍47 cm,陰莖長度約1.5 cm,無尿道下裂,陰囊左右兩側對稱,顏色無明顯加深,少皺褶,兩側陰囊內均可觸及睪丸樣組織,體積約1 cm3(TannerⅠ期)。皮膚無色素沉著,粗測視野正常,耳廓外形正常,無耳位低下,粗測聽力正常,鼻腔內無分泌物,聞到酒精等刺激性氣味表現為皺眉、躲避等。
1.2 實驗室檢查 入院后完善相關化驗檢查(2020年7月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1)一般檢查:血常規血紅蛋白(Hb)↓、平均紅細胞體積(MCV)↓、平均紅細胞血紅蛋白含量(MCH)↓、平均紅細胞血紅蛋白濃度(MCHC)↓,余項大致正常,肝腎功能、尿便常規、血糖、腫瘤標志物均正常。(2)性激素檢查:黃體生成素(LH):0.03 IU/L↓(0.57~12.07),卵泡刺激素(FSH):0.53 IU/L↓(0.95~11.95),雌二醇(E2):8 pg/mL(≤13),催乳素(PRL):12.56 ng/mL(3.46~19.4),睪酮(T):<12.98 ng/dL(70~200),脫氫表雄酮(DHEA):36.8 ng/mL↓(140~3 230),雄烯二酮:55.7 pg/mL(<690),抗苗勒氏管激素(AMH):5.98 ng/mL,抑制素B:25.43 pg/mL。(3)性激素激發試驗:①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GnRH)激發試驗:注射戈那瑞林28μg,分別于注射前及注射后30 min、60 min、90 min測定血FSH、LH水平(表1);②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激發試驗:肌肉注射絨毛膜促性腺激素1 000 U×3 d,分別于激發前后檢測血液中睪酮、雙氫睪酮水平(表2)。(4)其他相關激素:游離三碘甲狀腺原氨酸(FT3)5.87 pmoL/L↑(2.63~5.7),游離甲狀腺素(FT4)12.31 pmoL/L(9.01~19.05),促甲狀腺激素(TSH)1.64μIU/mL(0.35~4.94);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38.8 ng/mL(Mean~+1SD),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結合蛋白-3(IGFBP-3)2.13μg/mL(Mean~+1SD);醛固酮(臥位)11.3 ng/dl(3.0~23.6),(立位)22.0 ng/dL(3.0~35.3),腎素(臥位)74.5μIU/mL↑(2.8~39.9),(立位)139.0μIU/mL↑(4.4~46.1);腎上腺皮質節律正常。

表1 注射戈那瑞林前后不同時刻患者激素水平(IU/L)

表2 肌注HCG前后不同時刻患者激素水平
1.3 影像學檢查 心臟超聲:心臟結構及功能均正常。腹部、腎上腺B超未見明顯異常。睪丸B超:左側睪丸8 mm×5 mm×4 mm(0.11 mL),右側睪丸9 mm×4 mm×4 mm(0.10 mL),雙側睪丸體積小。盆腔B超:盆腔內未見子宮卵巢回聲。因為該患兒年齡較小,頭顱核磁無法精準顯示嗅球結構,故尚未完善該檢查。
1.4 基因檢測 征得家屬同意,對患兒血液樣本進行性發育障礙相關基因檢測,應用基因測序分析檢測到SRY基因,應用高通量測序技術,發現FGFR1基因有1個雜合突變:c.871_872dupAA雜合突變,導致氨基酸發生移碼突變(p.H292Sfs*5)(圖1)。應用Sanger經家系驗證分析,c.871_872dupAA(p.H292Sfs*5)受檢人之父該位點無變異(圖2),受檢人之母該位點無變異(圖3),此變異為自發突變。文獻數據庫未有該位點的相關性報道,此變異為新發突變。根據美國醫學遺傳學與基因組學學會(ACMG)發布的《ACMG遺傳變異分類標準與指南》,該變異初步判定為致病性變異。

圖1 患兒血液樣本檢測結果

圖2 父親血液樣本檢測結果

圖3 母親血液樣本檢測結果
1.5 診斷和治療 目前該患兒KS診斷明確,予HCG 500 U肌注×BIW(一周兩次)治療,目前仍在隨訪中。
2 討論
2.1 KS的表現 KS于1856年第一次被提出,1944年遺傳學家Kallmann將其命名[2]。目前已報道約900例KS患者,其中男性病例數占96%左右,且多確診于青春期及成人期,本病例確診于幼兒期,既往鮮有報道。KS是一種特發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減退癥[3],遺傳方式主要為X-連鎖隱性遺傳、常染色體顯性遺傳和常染色體隱性遺傳,部分病例為自發突變。GnRH神經元的遷移從鼻基板開始,沿著犁鼻神經和嗅神經的軸突最終穿過鼻間質和篩狀板,之后沿著犁鼻神經腹支到達最終位置-弓狀核和下丘腦的視前區,緊接著,GnRH神經元將軸突延伸至中位隆起,到達下丘腦-垂體門脈血管的有孔的血腦毛細血管。根據解剖學位置關系,GnRH神經細胞可分為下丘腦型、中腦型及神經終末-腦端型[3],下丘腦型神經細胞未能從嗅覺胎盤遷移到視前區,胎兒發育過程中嗅覺神經元發育和遷移存在缺陷,而導致嗅覺喪失。隨著對KS的遺傳學研究的進展,目前已報道20余個基因突變與此征有關,常見的包括 :KAL1、FGFR1、FGF8、CDH7、ANOS1、HS6ST1、SOX10、SEMA3A、WDR11、IL17RD、PROKR2、PROK2、FEZF139[4-5]。本例完善基因檢測,發現FGFR1雜合缺失,FGFR1基因參與神經元遷移、胚胎發生過程中的分化和增殖以及嗅球的正常發育[1]。正確的基因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精準的剪接。此外,臨床分析經常忽略的內含子序列包含關鍵的剪接供體/受體位點,以及可以劃定外顯子/內含子邊界的分支位點。內含子突變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引起嚴重的疾病,包括錯誤的mRNA剪接、外顯子跳過、內含子保留、移碼,剪接位點的早期終止。這種雜合子內含子突變導致mRNA的異常截斷,從而減少GnRH神經元的數量,最終導致KS。
對于因第二性征發育不全而就診的典型病例中,借助性激素和激發試驗結果,提示性激素缺乏,可以臨床診斷該病;而部分不典型病例,尤其是青春期前尚未有性腺發育的兒童,臨床表現不明顯,診斷較為困難,需借助影像學及基因檢測來確診[6]。本例患者為1例幼兒期男童,主要有以下表現:(1)性腺激素缺乏。(2)外生殖器發育不良。(3)嗅覺缺失或嗅覺減退,但無法確認患兒是否能自行分辨各種味道以及是否存在嗅覺減退的癥狀,或患兒是因酒精揮發刺激眼睛而引起的躲避行為,還需進一步隨訪。此外,本病還可以伴發其他少見的臨床癥狀:如唇腭裂、孤立腎、骨骼畸形或牙齒發育不良、較特異的雙手連帶動作、感覺性神經耳聾、痙攣性截癱、尿道下裂及肥胖等,此例暫未發現[7]。在已報道的病例中,合并除生殖系統、嗅覺表型以外其他畸形的病例數約占15%,其中FGFR1突變發生唇腭裂的概率為30%,但基因突變的不完全外顯性可能為該患兒未表現出其他臨床癥狀的一大原因;且患兒年齡較小,生長發育不完全,應定期隨訪有無其他癥狀的發生。
2.2 KS的治療 對于KS至今暫無根治方法,目前較為成熟的治療方案主要是激素替代、性類固醇、脈沖性GnRH泵治療,從而最大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第二性征、促進性器官發育,甚至獲得生殖能力。根據患者的年齡、是否處于青春期、以及是否有強烈的生育意愿,來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男性患者治療的主要方法是采用GnRH、HCG肌內注射,或與HMG聯合治療,從而誘發精子產生,口服或外用十一酸睪酮可促進第二性征發育。女性患者主要采用注射HMG促進卵泡發育,獲得妊娠,口服/透皮雌二醇和環孕酮可促進青春期發育。脈沖性GnRH治療優點為療程較短,治療過程中容易監測及控制;此外,GnRH泵治療即使在GnRH耐藥的患者中也很有效,更重要的是,GnRH在青春期誘導中效果佳,10%~15%的男性和女性KS患者可以通過使用它進行逆轉。由于KS的病變在下丘腦,因此在下丘腦水平上治療是最好的[8]。對于部分患者的嗅覺缺失或減退,臨床上尚未發現有效的治療方法。隨著對KS更深入的研究,除經典的臨床特征外,基因檢測、基因治療將是未來的研究重心。
綜上所述,KS多根據典型臨床特征、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來診斷,但由于該病發病率低,且兒童內分泌專科普及不足,該病鮮為人群知曉,到青春期有明顯性發育異常時才引起關注,故多數延遲診斷從而錯過最佳治療時機。因此,早期診斷對治療該病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部分因為第二性征發育不良來就診的兒童,應積極完善相關激發試驗、影像學檢查,以求早期明確或排除診斷。KS臨床病例少見而又多樣化,通過此病例,希望能夠加強兒科醫生對此病的認識,結合基因檢測,做到早診、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