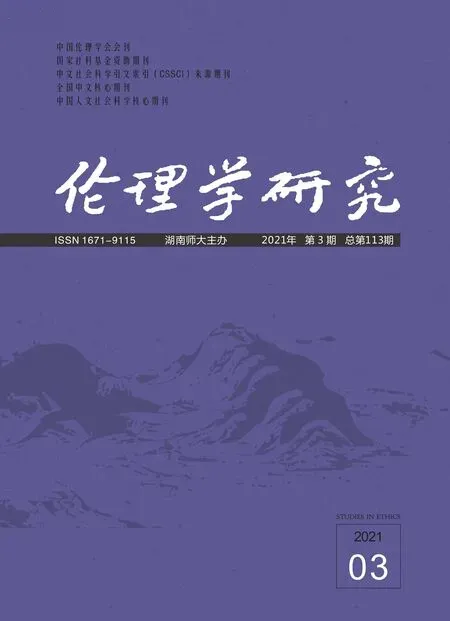麥茜特伙伴關(guān)系倫理解析
王云霞
人類應(yīng)如何看待自身與外在世界的關(guān)系,是一個(gè)常談常新的話題。在生態(tài)危機(jī)日趨嚴(yán)峻的今天,深入思考人類在大自然中應(yīng)扮演的角色,更是不容回避的時(shí)代課題。對此,當(dāng)代美國環(huán)境史研究領(lǐng)軍人物和環(huán)境哲學(xué)領(lǐng)域的著名學(xué)者卡羅琳·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給出了獨(dú)特的答案。在她看來,人類應(yīng)放棄“控制自然”的狂妄理念,向“視自然為伙伴”進(jìn)行轉(zhuǎn)變,也即要用“伙伴關(guān)系倫理”去重塑與自然之間的良性互動(dòng)關(guān)系。本文擬對麥茜特的伙伴關(guān)系倫理作一梳理評介,以推進(jìn)環(huán)境哲學(xué)的研究。
一、伙伴關(guān)系倫理對既有環(huán)境倫理模式之挑戰(zhàn)
麥茜特認(rèn)為,目前主導(dǎo)人類與環(huán)境關(guān)系的倫理模式主要有三種,即“自我中心倫理”(利己主義倫理)、“同心圓倫理”和“生態(tài)中心倫理”。自我中心倫理(egocentric),簡言之,就是以個(gè)體自我為中心的倫理。它的天然預(yù)設(shè)是:凡對個(gè)體有利的事情,也一定會(huì)對整個(gè)社會(huì)有利。“自我中心倫理建立在自我的基礎(chǔ)之上,認(rèn)為個(gè)體應(yīng)追逐個(gè)體之善,相信對個(gè)體而言的好也將有益于社會(huì)。因此,個(gè)人的利益優(yōu)先于社會(huì)的利益,而社會(huì)的利益作為一種必然的結(jié)果必將緊隨其后。”[1](P64)在此預(yù)設(shè)之下,原子化的個(gè)體(或個(gè)體化的公司)都把不遺余力地追逐自我利益視為一件天然合法的事情,并傾向于最大限度地將其生產(chǎn)成本社會(huì)外部化。由此,大自然便不可避免地成為霍布斯式的無主公有地,被當(dāng)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水龍頭,被看成免費(fèi)的垃圾收納器。“自然被概念化為一個(gè)死的機(jī)器,它的零件被操縱以用于裝配線的生產(chǎn)和未來的利潤。對資源的消耗和環(huán)境的污染不屬于損益表的一部分,因此無須承擔(dān)對自然的責(zé)任。”[2](P264)自我中心倫理最突出的國際表現(xiàn)形式便是《關(guān)稅及貿(mào)易總協(xié)議》(GATT)。眾所周知,該協(xié)議是一個(gè)政府間締結(jié)的有關(guān)關(guān)稅和貿(mào)易規(guī)則的多邊國際協(xié)議,其宗旨在于通過削減關(guān)稅和貿(mào)易壁壘,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資源,擴(kuò)大商品的生產(chǎn)與流通,以最大限度地促進(jìn)國際貿(mào)易的自由化。為保障世界貿(mào)易按照“各人為個(gè)人,上帝為大家”的利伯維爾場模式運(yùn)行,它對保護(hù)大自然勢必會(huì)采取仇視態(tài)度。“關(guān)貿(mào)總協(xié)議傾向于使環(huán)境成本外部化,并懲罰努力使成本內(nèi)部化的可持續(xù)技術(shù)。它把環(huán)境和消費(fèi)者的安全降到最低標(biāo)準(zhǔn),增加了公司控制,減少了地方控制。社區(qū)和資源被迫順應(yīng)全球市場的需求。這種方式大大消除了地方社區(qū)、國家、土著和部落人民對自身資源的控制。”[3](P213)“同心圓倫理”(homocentric),又稱“人類中心主義”,是以“大寫的人”為中心的倫理。它的理論基礎(chǔ)是邊沁和穆勒所開創(chuàng)的功利主義倫理學(xué),其倫理旨趣在于“實(shí)現(xiàn)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的和最長久的利益”。1992 年召開的“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會(huì)議”(UNCED),就是世界各國求同存異、致力于將全人類在未來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放在首位的嘗試。而基于此目標(biāo),保護(hù)自然資源不被快速消耗就成為應(yīng)有之義,但這并不影響它和關(guān)貿(mào)總協(xié)議的共同設(shè)定——自然是人類的資源和商品的來源。“正像GATT 的自我中心倫理一樣,對UNCED 的同心圓倫理而言,自然仍主要被看成是人類的資源和商品的來源。”[4](P214)只不過前者看重的是個(gè)體利益,后者卻意在維護(hù)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生態(tài)中心倫理(ecocentric),則是以非人類自然為中心的倫理。它的典型代表是著名環(huán)境倫理學(xué)家利奧波德所開創(chuàng)的大地倫理學(xué)。作為發(fā)展生態(tài)中心主義環(huán)境倫理學(xué)最有影響的大師,利奧波德強(qiáng)烈主張土地不是死的資源,而是一個(gè)有著內(nèi)在價(jià)值且需要保護(hù)的、活生生的生命共同體。微生物、植物、動(dòng)物以及空氣、土壤、水乃至人類都是共同體中的一員。人在自然界中的恰當(dāng)?shù)匚唬粦?yīng)是征服者的角色,而應(yīng)當(dāng)以大地共同體中的好公民面貌出現(xiàn)。大地倫理學(xué)所追求的,則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xiàn)的角色,變成該共同體中的普通成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其他成員的尊重和對共同體本身的尊重”[5](P204)。大地倫理學(xué)秉持生態(tài)整體主義的道德原則,并認(rèn)為“當(dāng)一件事情有助于保護(hù)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wěn)定和美的時(shí)候,它就是正確的;反之,則是錯(cuò)誤的”[5](P224-225)。
顯而易見,上述三種模式都存在著理論和實(shí)踐上的缺陷。自我中心倫理“將道德建立在個(gè)人利益是最高利益的假設(shè)之上”[1](P71),追求個(gè)體利益之最大化,無疑屬于一種極端自私的個(gè)人中心主義和利己主義。同心圓倫理雖反其道而行之,也即致力于追求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最大化,但很容易導(dǎo)致少數(shù)人的利益被侵犯。比如美國政府將核廢料放置在印第安人所居住地區(qū)的“環(huán)境種族主義”行徑,就是將多數(shù)人的利益凌駕于少數(shù)人之上并置后者的利益于不顧。另外,同心圓倫理和自我中心倫理的共同之處在于,二者所關(guān)注的核心對象都是“人”(個(gè)體或類),而非“自然”。此種致思理路造成的后果,便是非人類生態(tài)的利益得不到應(yīng)有的重視。與之相比,生態(tài)中心倫理的最特別之處,就是將生態(tài)放在了中心位置,以求避免前兩者“見人不見物”的“人類中心主義”思維的偏狹性,但它也極易導(dǎo)致出現(xiàn)“輕人重物”的嚴(yán)重后果。因?yàn)槿绻凑绽麏W波德所提倡的生態(tài)整體主義原則行事,就有可能出現(xiàn)那種極端的情況:當(dāng)一個(gè)人在森林里探險(xiǎn),卻不幸遇到饑腸轆轆且處于瀕臨滅絕的猛獸時(shí),他所應(yīng)當(dāng)做的并不是保護(hù)自己,而是要心甘情愿充當(dāng)猛獸的食物。因?yàn)橹挥羞@樣,才有助于維護(hù)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wěn)定和美麗。但這種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jià)來換取生態(tài)系統(tǒng)整體平衡的做法,無法擺脫“環(huán)境法西斯主義”(或“生態(tài)法西斯主義”)之嫌疑,故不可能被當(dāng)作切實(shí)的指導(dǎo)方針去踐行。
鑒于自我中心倫理、同心圓倫理和生態(tài)中心倫理都無法正確擺置人與自然關(guān)系之缺陷,麥茜特主張用伙伴關(guān)系倫理指導(dǎo)人類與自然的關(guān)系。伙伴關(guān)系倫理,要言之,就是主張人類與自然不應(yīng)是控制和奴役的關(guān)系,而應(yīng)以平等的伙伴關(guān)系共存共處。在伙伴關(guān)系倫理中,人和自然都是積極的主體,二者是盟友而非敵人。雙方在打交道時(shí),有時(shí)需以人類利益為重,有時(shí)需以自然的利益為重。也就是說,自然的持續(xù)存在和人類的基本需求必須被同時(shí)考慮到。“人類將不再把自然看成被動(dòng)的資源而是將其視為一個(gè)伙伴與之交流。伙伴關(guān)系倫理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互動(dòng)開啟了一種非支配、非等級的模式。自然不再是被操縱的機(jī)器、被開發(fā)的資源,或被研究和改造的對象,而是變成了一個(gè)主體。在伙伴關(guān)系中,大自然有時(shí)會(huì)勝出,在其他情況下,人類的需要將得到更大考慮。但雙方的聲音是平等的,雙方的聲音都將被聽到。”[2](P269)麥茜特認(rèn)為,自然之所以需要被視為伙伴,除了由于人類的過度征服和奴役而變得千瘡百孔并反過來會(huì)對人類進(jìn)行種種“報(bào)復(fù)”外,還有一個(g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態(tài)學(xué)、混沌學(xué)、復(fù)雜性科學(xué)等后現(xiàn)代科學(xué)已從不同層面揭示出了大自然的無序性、自主性、復(fù)雜性和不可預(yù)測性。而這顯然與濫觴于17 世紀(jì),且早已根深蒂固地形塑了人類思維的機(jī)械論自然觀大相徑庭。因?yàn)榘凑諜C(jī)械論的自然觀,自然不過是一架死的機(jī)器和一堆無生命物質(zhì)的堆積,并可用牛頓式的世界圖景和拉普拉斯的“妖”加以描繪、預(yù)測和控制。但在麥茜特眼中,“雖然自然的許多方面確實(shí)可用線性的、確定性的方程來表示,因此是可預(yù)測的(或者可以受到概率、隨機(jī)近似和復(fù)雜系統(tǒng)分析的影響),但一個(gè)非常大的領(lǐng)域只能通過不允許有解的非線性方程來表示。由機(jī)械科學(xué)和概率描述的封閉系統(tǒng)和古典物理決定論將讓位于開放復(fù)雜系統(tǒng)和混沌理論的后古典物理學(xué)。這些理論已經(jīng)表明,可知的世界是有極限的”[2](P269)。這就是說,自然的特征和全貌遠(yuǎn)非機(jī)械論的自然觀所能涵蓋囊括,它其實(shí)是確定性與隨機(jī)性、線性與非線性、簡單性與復(fù)雜性、有序與無序的辯證統(tǒng)一。既然如此,人類就應(yīng)遵從自然的特性和規(guī)律,給予自主性的自然以應(yīng)有的尊重。
伙伴關(guān)系倫理的提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挑戰(zhàn)了自我中心倫理、同心圓倫理和生態(tài)中心倫理的先天缺陷,并為人類探索與自然的和諧互動(dòng)關(guān)系提供了某種可能。如前所述,自我中心倫理以個(gè)體自我利益為第一要義,勢必會(huì)把對自然的保護(hù)視為絆腳石;同心圓倫理看似彌補(bǔ)了自我中心倫理將個(gè)體置于群體之上并使多數(shù)人利益受損這一后果,但依然是將人的利益置于首位,因而仍會(huì)導(dǎo)致自然的利益受損;生態(tài)中心倫理雖然看到了維護(hù)生態(tài)平衡的重要性,但其極端的生態(tài)利益至上思維卻也極易陷入“見物不見人”的泥淖。因此,三者都不可能是構(gòu)建人與自然之恰當(dāng)關(guān)系的良方。而與之相較,伙伴關(guān)系倫理既可很好地避免自我中心倫理和同心圓倫理對人的執(zhí)念,又不至于落入生態(tài)中心倫理的“環(huán)境法西斯”窠臼。因?yàn)樵诨锇殛P(guān)系倫理的視域中,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平等伙伴,而非“控制”或“被控制”的關(guān)系。尤為重要的是,將自然視為人類的平等伙伴,不僅暗含著人類對自然的承認(rèn)與尊重,更預(yù)示著人類在看待自身與自然之關(guān)系上的重大范式變革。
二、伙伴關(guān)系倫理之雙重維度:社會(huì)正義和生態(tài)正義
麥茜特認(rèn)為,雖則伙伴關(guān)系倫理意在調(diào)節(jié)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但人在和自然的交往中,通常又需以人與人的交往為中介,而人與人、團(tuán)體與團(tuán)體,國家與國家之間能否建立起良好和正義的伙伴關(guān)系,勢必會(huì)影響到他們與自然的關(guān)系。故此,伙伴關(guān)系倫理需由兩部分構(gòu)成,即“人類群體間的伙伴關(guān)系和人類與非人類間的伙伴關(guān)系”[4](P218)。而這兩重關(guān)系又可從伙伴關(guān)系倫理的五大原則或戒律[6](P221)加以體現(xiàn):其一,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平等;其二,對人類和非人類自然的道德關(guān)懷;其三,尊重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其四,將婦女、少數(shù)族裔和非人類自然納入道德責(zé)任準(zhǔn)則的范圍;其五,建立符合人類和非人類群落持續(xù)健康的生態(tài)管理機(jī)制。借此,我們不難看出伙伴關(guān)系倫理所蘊(yùn)含的兩重正義維度——人類內(nèi)部的社會(huì)正義和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生態(tài)正義。
伙伴關(guān)系倫理所指向的第一重正義,即人類社會(huì)內(nèi)部的伙伴關(guān)系。它不僅指涉?zhèn)€體之間的平等,也關(guān)乎性別意義上的平等,更謀求種族間的平等,特別是南北國家關(guān)系的平等。“伙伴關(guān)系可以在女人與女人、男人與男人、女人與男人、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之間形成,并借此去解決問題和構(gòu)建起一個(gè)社會(huì)正義的世界。”[4](P222)女人之間和男人之間的伙伴關(guān)系意味著同性個(gè)體相互間的平等;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伙伴關(guān)系意味著性別之間的平等——女性無須生活在“父權(quán)制”的陰影之下,也不必再遭受男性的奴役和壓迫。男性和女性均可在結(jié)成的伙伴關(guān)系中共同守護(hù)地球的安全,而無須像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將保護(hù)自然之責(zé)任與女性單純聯(lián)系在一起;北方與南方的伙伴關(guān)系則要求在富裕的北方發(fā)達(dá)國家和貧窮的南方欠發(fā)達(dá)國家之間,去努力建立一種基于平等和正義的國際經(jīng)濟(jì)政治新秩序。它意味著只有打破當(dāng)前由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家主導(dǎo)的不合理和非正義的國際框架,才能使所有國家在面對全球性環(huán)境難題時(shí),能本著全球伙伴精神進(jìn)行合作,以共同恢復(fù)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健康。此外,伙伴關(guān)系倫理原則中第三、第四條所提及的尊重文化多樣性,以及將少數(shù)族裔納入道德關(guān)懷的范圍,表明將有色人種和少數(shù)族裔視為平等伙伴之重要性。而麥茜特也坦言,這種靈感源自她對1991 年“第一屆有色人種領(lǐng)導(dǎo)高峰論壇”上提出的“環(huán)境正義要求在各類決策中人們擁有作為平等伙伴參與之權(quán)利”[4](P221)這一原則的吸收。換言之,政府在制定和實(shí)施各類環(huán)境決策,特別是當(dāng)作出對土著或少數(shù)族裔有著重大影響的決定時(shí),不應(yīng)無視、漠視甚至是蔑視他們作為環(huán)境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和正義訴求,而要將其視為真正的伙伴來對待,特別是要尊重其獨(dú)特的文化。
伙伴關(guān)系倫理所指向的第二重正義,即人類社會(huì)與非人類自然之間的伙伴關(guān)系。我們知道,人類與自然在歷史上先后經(jīng)歷了“自然為主,人類為仆”和“人類為主,自然為奴”這兩種狀態(tài)。在人類誕生后的大部分時(shí)期,受認(rèn)識水平之局限與束縛,大自然可以說是一直凌駕于人類之上。人類不得不服從自然,并宿命地接受自然的擺布與控制。在接受命運(yùn)安排的同時(shí),人們也利用禮物、祭祀和祈禱等方式去安撫和討好自然。例如古希臘人喜歡將他們的祭品放置在洞穴、泉眼和森林之中,以示對蓋婭女神也即大自然之旺盛生命力的崇拜與虔敬。然而,肇始于17 世紀(jì)的科學(xué)革命徹底扭轉(zhuǎn)了這一局面,并重塑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力量對比態(tài)勢。“借助機(jī)械論的科學(xué)、技術(shù)、資本主義和培根式的傲慢,人類應(yīng)該統(tǒng)治整個(gè)宇宙”[2](P268)開始成為主導(dǎo)觀念。借助科學(xué)技術(shù)之銳不可當(dāng)?shù)纳衿媪α浚祟愐搏@得了對自然的絕對優(yōu)勢。然而,20 世紀(jì)中后期爆發(fā)的全球性生態(tài)危機(jī)已頻頻向人類敲響警鐘,再加上生態(tài)學(xué)、系統(tǒng)論、混沌學(xué)、量子力學(xué)等后經(jīng)典物理學(xué)所昭示的自然的不確定性和復(fù)雜性,都使得機(jī)械論的世界觀、啟蒙進(jìn)步思想、理性,以及將不受限制的發(fā)展作為人類支配自然之必勝手段的倫理思想遭到深度質(zhì)疑。麥茜特認(rèn)為,正是這些因素迫使人類重新思考如何擺正自身與自然之關(guān)系,也由此成為伙伴關(guān)系倫理提出的契機(jī)。在她看來,人類與非人類自然之間的正義,或曰伙伴關(guān)系倫理,就是讓人類不要再把自然視為無生命、無活力和被動(dòng)的機(jī)器,而應(yīng)“將自然帶入與人類的積極關(guān)系之中,使之成為一個(gè)平等的主體”[4](P220)。在伙伴關(guān)系倫理中,人和自然都是創(chuàng)造性的、變化的、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主體。這種主體關(guān)系要求人類抑制自身的傲慢,將對食物、衣服、住所和能源的基本需求和對自然之利益的尊重很好地結(jié)合起來。自然的利益,簡言之,就是它繼續(xù)存在的需要。而作為倫理承擔(dān)者的人類,“必須承認(rèn)自然是一個(gè)自主的行動(dòng)者,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領(lǐng)域內(nèi)被預(yù)測和控制”[7](P162)。故而,人類要學(xué)會(huì)傾聽自然的聲音,并通過新的設(shè)計(jì)和規(guī)劃與之互動(dòng)。譬如,當(dāng)科學(xué)預(yù)測表明某座城市在未來可能出現(xiàn)地震時(shí),那么按照伙伴關(guān)系倫理,人們就應(yīng)該尊重自然作為主體的自主性,主動(dòng)限制對建筑的開發(fā),以留下更加開放的空間;如果某大河可能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人們就應(yīng)限制在其每條支流上修建水壩,以便讓河流自由奔放地流淌;如果某山脈在未來可能發(fā)生森林火災(zāi),人們就不應(yīng)在其森林邊緣修建房屋,而是要限制山脈周圍城市的擴(kuò)張,在建筑材料的選擇上使用阻燃材料,并大量種植防火植物。總之,只有通過培養(yǎng)傾聽大自然“言說”的新能力,進(jìn)行自然與人類身份的重新敘事與界定,人類才有望與自然和諧共存,實(shí)現(xiàn)共同繁榮。
三、伙伴關(guān)系倫理之意義及缺陷
作為關(guān)心人類在當(dāng)前所面臨的生態(tài)困境和自然在未來之生存命運(yùn)的學(xué)者,麥茜特堅(jiān)信伙伴關(guān)系倫理能夠?yàn)槿祟愔罔T與自然的和諧提供一個(gè)不錯(cuò)的選擇。而她所推出的伙伴關(guān)系倫理對我們反觀環(huán)境倫理主流模式之局限、省思人類在自然中之身份、檢討既往自然觀之流弊等,都有著很好的借鑒和啟發(fā)價(jià)值。具言之,伙伴關(guān)系倫理有著以下重要意義。
其一,挑戰(zhàn)了父權(quán)制和生態(tài)女性主義的慣常敘事。在環(huán)境倫理學(xué)中,“父權(quán)制”和“生態(tài)女性主義”是兩個(gè)常常被放在一起談?wù)摰脑~匯。父權(quán)制又叫“家長制”,是指以男尊女卑的意識形態(tài)確立男性對女性統(tǒng)治地位的一種社會(huì)倫理秩序。生態(tài)女性主義則是20 世紀(jì)70 年代由于全球生態(tài)危機(jī)的出現(xiàn),而在女性主義發(fā)展的第三次浪潮中應(yīng)運(yùn)而生的綠色環(huán)境思潮。生態(tài)女性主義將女性被男性壓迫和自然被人類奴役視為一個(gè)問題的兩個(gè)方面,主張女性的解放和自然的救贖彼此依存,認(rèn)為女性孕育生命、哺育后代的性別角色使她們與養(yǎng)育人類的大自然有著特殊的親緣關(guān)系,而其天然的母性思維也更適合在建構(gòu)人與自然的慈愛友善關(guān)系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例如文化生態(tài)女性主義的代表格瑞芬在其《女性與自然》等著述中,就喜好用奶牛、綿羊、狐貍、雌鹿、小兔來指代女性,以期加強(qiáng)女性和自然的天然聯(lián)系,并認(rèn)為這是女性與自然存在良好關(guān)系的基礎(chǔ),而這恰恰是男性所不具備和缺乏的。而我們從麥茜特的伙伴關(guān)系倫理框架中,既可看到她對父權(quán)制抬高男性貶抑女性的拒斥,也能感受到她對生態(tài)女性主義將女性刻板化和本質(zhì)化的不滿。在麥茜特看來,伙伴關(guān)系倫理能使男性和女性之間建立起平等的伙伴關(guān)系,而不是父權(quán)制所界定的女性天生就比男性卑微,因而應(yīng)該被男性所統(tǒng)治。而地球也不必在生態(tài)女性主義所熱衷的性別分類下被定義成“女神”,女性更無須在本質(zhì)主義的陰影之下被視為大自然的天然“親友團(tuán)”,并被要求獨(dú)立承擔(dān)起“清理由男性主導(dǎo)的科學(xué)、技術(shù)和資本主義造成的爛攤子”。“伙伴關(guān)系避免把大自然性別化為一位母親或是女神(對地球性別化),也避免賦予男性或女性與大自然或彼此之間的特殊關(guān)系(本質(zhì)主義)……事實(shí)上,關(guān)愛地球的伙伴關(guān)系倫理意味著:無論男女,都可以獨(dú)立于性別,并與彼此和地球建立相互關(guān)系。”[4](P216-217)這種打破常規(guī)思維路向的見解可謂獨(dú)樹一幟,令人耳目一新。因?yàn)樗粌H顛覆了父權(quán)制下的男性狂妄和女性的自我貶低,而且無意拔高女性并對其進(jìn)行“生態(tài)道德綁架”。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麥茜特強(qiáng)力主張破除陳舊的性別偏見,并力主男性和女性均可在保護(hù)地球方面貢獻(xiàn)其生態(tài)智慧,這必然有利于打破(男性)侵害自然與(女性)看護(hù)自然的性別標(biāo)簽,為構(gòu)建男女之間的性別平等與重構(gòu)生態(tài)的和諧注入活力。
其二,為人類和自然的非控制關(guān)系描繪了美好愿景。不難看出,麥茜特所推崇的伙伴關(guān)系倫理超越了自我中心倫理、同心圓倫理和生態(tài)中心倫理的局限。更確切地說,它綜合了同心圓倫理和生態(tài)中心倫理的優(yōu)點(diǎn),實(shí)現(xiàn)了對二者的突破與揚(yáng)棄。在伙伴關(guān)系倫理的框架中,無論是執(zhí)迷于個(gè)體利益并置公共利益和自然利益于不顧的自我中心主義倫理,抑或是只謀求人類之利益并罔顧自然利益的同心圓倫理,又或者是為維護(hù)非人類自然的利益而罷黜人類之主體地位,并不惜以犧牲人之性命來換取生態(tài)整體之和諧的生態(tài)中心主義倫理,都無法矯正人與自然之正確關(guān)系。而伙伴關(guān)系倫理嘗試將人類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辯證地結(jié)合起來,力求兼顧雙方之需求并在二者之間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與平衡。這無疑有助于打破人類對自然的控制,為二者的非控制關(guān)系提供可能。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麥茜特認(rèn)為若要有效建構(gòu)起人與自然的非控制關(guān)系,就應(yīng)注意避免落入深生態(tài)學(xué)所提倡的“自我實(shí)現(xiàn)”所導(dǎo)致的陷阱。我們知道,深生態(tài)學(xué)的理論家們?nèi)缒嗡埂①愋浪沟葹榱俗屓藗儗?shí)現(xiàn)從“個(gè)體小我”向“生態(tài)大我”的轉(zhuǎn)變,強(qiáng)烈主張個(gè)體應(yīng)克服自我的狹隘與局限,進(jìn)行從關(guān)心自我到家庭成員、他人、同胞直至非人類生物的深層次擴(kuò)展,并認(rèn)為唯其如此,自然方可獲得保護(hù)。在他們眼中,“如果自我得到擴(kuò)大和延伸,那么關(guān)懷就會(huì)自然地流露出來,因?yàn)槲覀冋J(rèn)識到了對大自然的保護(hù)實(shí)際上就是在保護(hù)我們自己”[8](P29)。但在麥茜特看來,這種做法實(shí)際上是抹殺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差異性,并有可能導(dǎo)致對自然更深的控制和殖民化。而伙伴關(guān)系倫理則有望避免這種風(fēng)險(xiǎn),因?yàn)樗安粌H承認(rèn)人類和自然的連續(xù)性,也承認(rèn)二者之間的差異性,而且無意讓人類去主宰和殖民自然”[6](P216-218)。這即是說,人類在與自然打交道時(shí),應(yīng)充分承認(rèn)并尊重自然的獨(dú)特性、自治性和自主性,要將其看成一個(gè)“他者”,避免在保護(hù)自然時(shí)將個(gè)體的意志理想化,反而給自然帶來不必要的傷害。更具體地說,就是要在對自我的主觀想象和自然的身份重塑上,保持理性的認(rèn)知。
其三,為重構(gòu)人類社會(huì)內(nèi)部的正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麥茜特正確地注意到了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這兩種關(guān)系的共振,意識到要想將人和自然之間的伙伴關(guān)系落在實(shí)處,就必須正視和改變?nèi)祟惿鐣?huì)內(nèi)部的不正義現(xiàn)狀。在她眼中,自由市場經(jīng)濟(jì)以利潤增長為導(dǎo)向的發(fā)展倫理挑戰(zhàn)了自然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之基礎(chǔ)的常識,而全球資本主義更是通過其主導(dǎo)的世界不公正的經(jīng)濟(jì)政治秩序這一“結(jié)構(gòu)性暴力”,將橫掃自然資源作為保障資本利潤持續(xù)增殖的必要前提,并置不發(fā)達(dá)國家人民的生存需求于不顧,由此造成了生態(tài)正義和社會(huì)正義全都缺失的后果——一個(gè)脆弱的星球和一個(gè)兩極分化嚴(yán)重的世界。“建基于自我中心主義倫理之上的以利潤最大化為導(dǎo)向的生產(chǎn),通過破壞其獲取免費(fèi)資源的環(huán)境,也削弱了自身生存的條件……而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的殖民主義,則犧牲了以基本需求為導(dǎo)向的地方/自給自足經(jīng)濟(jì)。”[4](P223)基于此,麥茜特強(qiáng)烈呼吁人類“為建立一個(gè)社會(huì)公正、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世界而努力”[4](P222),并用“與可持續(xù)發(fā)展、代際公平和伙伴關(guān)系倫理兼容的新經(jīng)濟(jì)形式”[6](P226)取而代之。麥茜特還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慣常用法提出了質(zhì)疑。在她看來,“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只會(huì)強(qiáng)化當(dāng)前支配性的發(fā)展模式,特別是會(huì)加深南北矛盾,加劇南方國家的貧困。麥茜特認(rèn)為,人類真正應(yīng)關(guān)注的是“可持續(xù)的生存”,因?yàn)樗攀且匀藶楸镜模⒅氐氖菍θ藗兊幕旧钚枨蟮臐M足,而非奢侈和浪費(fèi)。這些主張可說是為打破國際不正義的經(jīng)濟(jì)政治秩序和重構(gòu)人類社會(huì)內(nèi)部的正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但不能否認(rèn)的是,伙伴關(guān)系倫理自身也存在無法回避的問題。譬如,麥茜特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人類再不能將自己視為自然的主人,而應(yīng)認(rèn)識到“我們是它的伙伴”。她還聲稱伙伴關(guān)系倫理最具創(chuàng)新性的一點(diǎn),就是將非人類自然納入合作伙伴的范圍。“同樣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是,合作伙伴不僅指涉社會(huì)關(guān)系和機(jī)構(gòu),而且可以是個(gè)人甚至是自然本身……‘伙伴’一詞也可以用來代表昆蟲獵手、大馬哈魚、灰熊和棋盤格斑蝶。事實(shí)上,非人類自然也可以成為我們的伙伴。”[2](P263)不難看出,麥茜特希冀通過提升自然的地位以達(dá)到保護(hù)它的目的。但問題是,非人類自然縱然是被善意升格為和人類平起平坐的主體,試問它又該如何主張自己身為伙伴的權(quán)利?而即便是如麥茜特所建議的,讓一些人坐到談判桌旁,去充當(dāng)濕地、美洲獅、荒野的“代言人”并參與商談,但問題是無法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的代言人又當(dāng)如何替非人類自然發(fā)聲,進(jìn)而維護(hù)后者的利益?另外,麥茜特認(rèn)為人類應(yīng)充分尊重自然的自治性,盡量做到不去干預(yù),以便給自然的發(fā)展留出自由和空間,但卻未看到很多“天災(zāi)”往往由“人禍”引起,有太多看似自發(fā)的自然災(zāi)害實(shí)則與人類的過度活動(dòng)脫離不了干系。如澳洲發(fā)生山林大火的根本原因,其實(shí)和地球溫度過高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而地球多年的溫室效應(yīng)又與人類對石化燃料的過度依賴分不開。倘若按照麥茜特所建議的,不去干預(yù)自然的自治性和自主性而任其發(fā)展,恐怕不太現(xiàn)實(shí),而且極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在給自然的自治性以恰當(dāng)尊重的同時(shí),恐怕還需警惕其潛藏的風(fēng)險(xiǎn)并適時(shí)給予反饋調(diào)整。再有,麥茜特認(rèn)為男性之間、女性之間和男女兩性間的平等伙伴關(guān)系有助于共同守護(hù)大自然的安全,但卻忽略了這種伙伴關(guān)系也極有可能走向保護(hù)自然的反面——人們聯(lián)手去對抗和剝削自然。最后,盡管麥茜特有著較強(qiáng)的社會(huì)正義感,如對資本主義以利潤為導(dǎo)向的生產(chǎn)方式深惡痛絕,對發(fā)達(dá)國家向欠發(fā)達(dá)國家實(shí)施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行徑進(jìn)行了深入揭批,但她的伙伴關(guān)系倫理似乎對資本主義仍抱有幻想,對綠色資本主義仍寄予厚望。比如她雖認(rèn)為資本主義是伙伴關(guān)系倫理的主要障礙,但卻從未明確提出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且還直言在未來可期的可持續(xù)的全球環(huán)境、社會(huì)和倫理上,新英格蘭也即美國“可以引領(lǐng)前進(jìn)的道路”[3](P279),這不能不說是其理論的最大缺憾。在這方面,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或可為麥茜特的這一缺陷帶來啟示。在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中,資本主義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內(nèi)生對抗性使綠色資本主義這一提法純屬夢中囈語,因而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并建立起真正的社會(huì)主義,唯此才能奠定生態(tài)社會(huì)的根基。誠如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在北美的得力干將福斯特所言:“地球的治愈只能在追求平等和可持續(xù)的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下才得以可能。”[9](P156)的確,構(gòu)建人與自然的恰當(dāng)倫理關(guān)系也好,追求可持續(xù)的生產(chǎn)方式也罷,如果不能清醒地認(rèn)識到唯有推翻現(xiàn)存的資本主義制度,摧毀其主導(dǎo)下的全球不公正的經(jīng)濟(jì)政治秩序,那么對地球拯救的渴望終將落入不切實(shí)際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