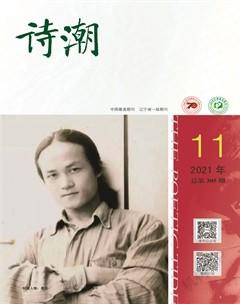手掌心的草原
2021-11-24 19:48:02敕勒川
詩潮 2021年11期
關鍵詞:情緒
多少年了,我悄悄地把草原攥在掌心
我跟著它綠,跟著它黃,我跟著它
從左手遼闊到右手
多少年了,我像一棵草一樣保持沉默
多少年了,我像一匹馬一樣停不下腳步
多少年了,我把月光匯聚成內心的河流
多少年了,我仍緊緊攥著
這童年的草原,仿佛攥著
不可言說的命運——
沒有人相信,這無邊的草原
太過單薄,一松手
就會被時光吹散
[李漢超賞讀]?讀完敕勒川這首詩,我們無不被作者濕潤而滄桑的情緒所打動,而這種情緒飽含著對草原的無限熱愛之情。詩的第一節,總領全詩,開啟下文。一個“攥”字,足見熱愛草原的力度和深度,“我跟著它……”三個分句,表明“我”與草原同呼吸,共命運。第二節,三個“多少年了”,用三個比喻構成排比,用草原的物象寄托作者內心的情感體驗:沉默,奔忙,但月光在心中流淌。其實,“我”也是草原的一個事物,與草原融為一體。第三節,行文向縱深推進,表明作者從小便與草原同在,自己的命運與草原緊密相連,不可分割。這命運為何“不可言說”呢?一個破折號引出詩的第四節:被作者一直攥在掌心的無邊無際的遼闊草原,如今草稀人疏,“單薄”得很,好像一松手就會驟然在時間里消散一樣。是土壤貧瘠,還是過度放牧?作者沒有言說,留給讀者去想。而這種感覺,是“沒有人相信”的,只有“我”信,那么“我”就只好永不松手,永遠把它攥在掌心。這是從反面來表達“我”熱愛草原是無條件的,無論單薄還是茂盛,草原都是“我”熱愛的草原。敕勒川善于在富有情彩的詩歌語言中,用閃爍思性和詩性的光芒來照耀或慰藉讀者,總是給人以溫厚、溫良、溫馨的審美愉悅。
猜你喜歡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10期)2018-10-18 18:38:04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9期)2018-09-13 19:18:16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8期)2018-08-19 15:35:52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7期)2018-07-18 15:00:04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6期)2018-06-21 17:50:54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5期)2018-05-16 12:03:46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4期)2018-04-19 16:18:48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3期)2018-03-15 17:07:26
風流一代·青春(2018年2期)2018-02-26 15:27:06
風流一代·青春(2017年6期)2018-02-14 19:2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