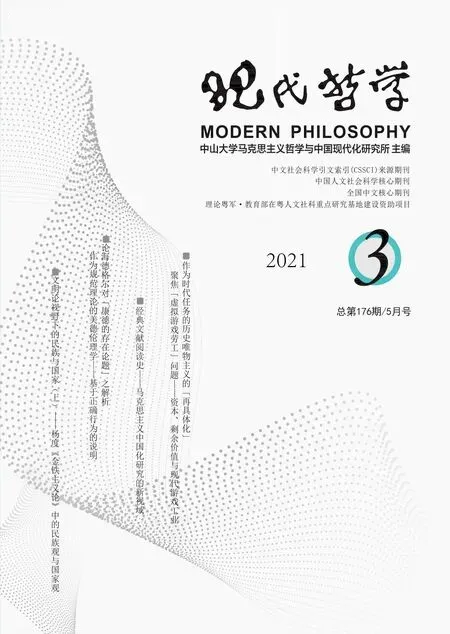王陽明晚年工夫論中的致知與誠意*
傅錫洪
學界一般認為,以正德十五年(1520)提出致良知宗旨為標志,王陽明思想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自此以后,他主要以致良知接引學者做工夫的同時,自身對致良知工夫的實踐也日臻化境。正德十五年前后,陽明思想尤其是工夫論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呢?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其變化可以大致概括為:從以誠意為本,轉向以致知或致良知為本。在正德十五年以后陽明的論述中,致知和致良知含義一致,可以互換使用。此處所說“本”,則是首要或根本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正德十五年前后兩個階段并非截然二分的關系。不少學者都注意到這一點,在此僅舉兩例。就良知而言,吳震認為:“若就義理的角度言,所謂陽明的早晚期良知說,其實并不存在本質上的歧義,只是在表述上的側重點略有偏差而已。”(1)吳震:《略議耿寧對王陽明“良知自知”說的詮釋——就〈心的現象:耿寧心性現象學論文集〉而談》,《現代哲學》2015年第1期,第122頁。就誠而言,陳立勝指出,“對‘誠’之強調一直見于陽明晚年思想”(2)陳立勝:《王陽明思想中的“獨知”概念——兼論王陽明與朱子工夫論之異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87頁。,誠包含了誠意的意思。上述學者的看法提醒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正德十五年前后陽明工夫論的關系。一方面,正如陽明的夫子自道——“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3)《傳習錄拾遺》第10條,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90頁,以下《王陽明全集》相關引文均出自此版本,僅標明卷數、頁碼。——所顯示的,從正德三年(1508)龍場悟道到正德十五年間,陽明工夫論乃至其思想整體,都可用良知理論加以詮釋。在這個階段,他也偶有提及良知概念。良知概念和同樣表示本體的其它概念,如心、天理、獨知和誠等一起,被他用來表示本體。另一方面,在正德十五年以后陽明晚年的論述中,不僅可見關于誠意的談論,而且可見他對誠意的重視甚至足以與對致知的重視相提并論。他極為重視誠意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在界定良知本體和致良知工夫的含義時,他均涉及了誠意。故而,與其說正德十五年前后陽明的立場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不如說在此前后,他的關注焦點或說論述中心發生了轉移。本文即欲在此思路中,探討陽明晚年工夫論中誠意與致知的地位及其關系。
一、致知使工夫可靠且簡易
從整體來看,陽明晚年無疑是以致知為中心展開工夫論述的。他之所以將致知突顯出來,主要是因為良知不僅保證了工夫的正確方向,而且使得工夫變得易于實施。換言之,致知由于揭示出能直接指引和推動工夫的本體,使工夫只要依循良知而行即可,因而滿足了陽明對工夫之可靠與簡易的要求,由此致知才在工夫論中成為關注焦點并獲得首出地位。
陽明工夫論是在與朱子工夫論的批判性對話中展開的。與朱子一樣,陽明也圍繞《大學》展開工夫論。中年時期的陽明認為《大學》工夫條目以誠意為本,這從他正德十三年(1518)《大學古本原序》“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4)《大學古本原序》,《王陽明全集》卷32,第1320頁。之說可看出。不過,在嘉靖二年(1523)的改本中,他雖在開頭保留了上述突出誠意地位及作用的論述,卻在隨后的文句中轉而用致知來貫穿解釋《大學》的工夫條目。他認為“致知者,誠意之本也”(5)《大學古本序·戊寅》,《王陽明全集》卷7,第271頁。按:學者已指出,《全集》此處所收為完成于嘉靖二年的改本,而非完成于正德十三年的初本,故不當標“戊寅”。,也就是說,他此時強調的是致知比誠意更根本。可見,其時致知在他圍繞《大學》展開的工夫論中已獲得首出地位。不僅如此,致知或致良知在陽明晚年的整體思想中都具有首出地位,如“‘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圣人教人第一義”(6)《傳習錄》第168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80頁。。
在“致良知”一語中,“致”的首要含義是依循,“致良知”即“依循良知”(7)關于陽明以依循解釋“致”字的思路,參見陳立勝:《王陽明“致良知”工夫論中的“依循”向度》,《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1—18頁。。陽明將致良知解釋為依循良知的例子俯拾皆是,如“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8)《答魏師說·丁亥》,《王陽明全集》卷6,第242頁。,又如“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9)《傳習錄》第165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78頁。。“致”之后的“良知”是本體。相比于其它工夫指點語,致良知一語的一大優越性就在于,它明確點出使工夫得以完成的本體,因而使工夫易于開展。陽明之所以以致良知為“學問大頭腦”,關鍵原因在于良知所具有的本體地位。就如陽明將“致良知”與孟子所說“集義”工夫對比時所指出的,“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故區區專說致良知”(10)《傳習錄》第187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94頁。。
在陽明處,本體的作用有兩層:第一,本體為工夫提供準則,從而使由其指引的工夫免于妄作之結果;第二,本體在保證工夫正確方向的同時,也直接提供充分的動力,推動工夫的完成。正是本體的這兩重作用,使得工夫變得不僅可靠,而且簡易。如所周知,陽明認為“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11)《傳習錄》第288條,《王陽明全集》卷3,第126頁。此處的好惡是本然好惡,亦即好善惡惡。原本好善惡惡指的是誠意,此處實際上是以誠意來界定良知本體的含義。陽明還說“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可見,作為致良知基本含義的依循良知,可進一步歸結為不欺良知,而不欺良知即是誠意。總之,無論良知本體,還是致良知工夫的含義,都可以歸結為誠意。(參見《傳習錄》第206條,《王陽明全集》卷3,第105頁。)良知是對是非的分別,由此可指引工夫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進一步,良知還是帶有動力的好惡。發自良知的好惡,亦即好善惡惡,正可引導和推動工夫的實施和完成。對此,吳震簡明扼要地概括為:“良知不僅是是非標準,更是一種好惡的道德力量。”(12)吳震解讀:《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傳習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455頁。良知對工夫的正確引導和有力推動,使工夫變得不僅可靠,而且簡易。并且,因為好惡是不假思慮的情感,所以良知的這兩重作用具有有別于反思性的直接性。正是這種直接性,使良知本體可以直接在工夫中發揮作用,而良知的直接性使依循良知以做工夫變得可能。事實上,將良知本體的這兩重作用最充分發揮出來的工夫指點語,也正是首先可以解釋為依循良知的致良知。依循良知便能將良知作為本體的兩重作用不受干擾而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
關于致知工夫的可靠性,嘉靖二年的《大學古本序》指出:“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13)《大學古本序》,《王陽明全集》卷7,第271頁。關于簡易性,陽明反復稱贊致良知工夫簡易明白,如“圣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14)《與陳惟濬·丁亥》,《王陽明全集》卷6,第247頁。,又如“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煉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15)《傳習錄》第262條,《王陽明全集》卷3,第119頁。。
問題在于,困知勉行以致良知,難道也是簡易的嗎?回答是肯定的。盡管不如完全出于良知之自然的工夫那樣簡易,但至少和“私意安排”的“紛紜勞擾”(16)《傳習錄》第169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81頁。,或者朱子學式格物窮理工夫的煩難比起來,即便困知勉行以致良知也是簡易的,簡易的原因在于工夫仍然直接受到本體的指引和推動。陽明明確指出,意識受私欲牽累之時,良知自然能夠發覺,進而推動去除私欲工夫的施行。“才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17)《傳習錄》第290條,《王陽明全集》卷3,第126頁。
進一步,正因致良知工夫直接受到本體的正確指引和有力推動,所以僅致良知工夫即可保證成圣境界的實現。“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圣學之的傳,但從此學圣人,卻無有不至者。”(18)《寄安福諸同志·丁亥》,《王陽明全集》卷6,第248頁。正德十五年揭出致良知宗旨之際,他對陳九川等門人說:“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19)《傳習錄》第206條,《王陽明全集》卷3,第105頁。正因致良知就是全功,僅此就可以保證成圣境界的實現,故他又說:“除卻良知,還有甚么說得!”(20)《寄鄒謙之·三·丙戌》,《王陽明全集》卷6,第228頁。基于此,他批評了那些將致良知與集義、勿忘勿助之類工夫指點語“攙和兼搭”的做法(21)《傳習錄》第188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95頁。。通過對“攙和兼搭”的批評,他維護了致良知工夫本是全功的地位。
二、誠意促成致知工夫的落實
盡管陽明晚年以致知為首出,他也不否認誠意的首出地位。他強調誠意首出地位的原因在于,致知主要突顯出工夫的簡易性,人們由此容易懷疑良知果真是否就是全功,或者忽視工夫的艱難和持久,這些都妨礙了致知工夫的落實。在此背景下,旨在強調工夫真切性的誠意,就有助于促使人們認真、切實落實致知工夫,從而對主要突顯簡易性的致知起到補充和糾偏的作用。
原本致知工夫簡易明白,學者得此指點,在工夫上應該大有長進。然而現實卻并非如此。嘉靖六年(1527),陽明提出致良知宗旨已達七年,良知學說已在弟子中廣泛傳播。然而,其時陽明卻感慨:“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為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22)《與馬子莘·丁亥》,《王陽明全集》卷6,第243頁。也就是說,致知工夫雖極為簡易明白,但現實中學者卻往往不能體認良知,以至于陷入疑惑的狀態中。處在這種疑惑的狀態中,切實落實致知工夫自然就更無從談起。
陽明在次年即嘉靖七年(1528)進一步分析了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他認為學者未能落實致良知工夫,其主要原因既有理解良知不真,也有輕視“致”字工夫。“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于此實用功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23)《與陳惟濬·丁亥》,《王陽明全集》卷6,第247頁。“見得良知未真”和“將致字看太易了”,正是陽明提出致良知宗旨以后學者不能切實做致知工夫的根本原因。這兩點原因會分別造成困與忘的問題。
困與忘是陽明弟子周沖自我反省時提出來的。他在給陽明的信中說:“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24)《傳習錄》第144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64頁。雖然只是周沖一人針對朋友講習一事而發,但困與忘恰可概括在陽明提出致良知宗旨,充分揭示出工夫簡易性的背景下學者面臨的突出問題。“困”就是困苦,就是不得要領,就是勞而無功。原本突出工夫可靠與簡易的致良知可以克服困苦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學者卻仍然陷于困苦的主要原因,是其未能真正理解良知。學者認為良知過于簡易,不相信良知足以應付復雜的世事,不相信致知就是全功,因而在做工夫時并不真正依循良知而行,由此便陷入在準則方面訴諸權謀智術而挖空心思,在動力方面則訴諸個人意志而苦苦支撐的困境之中。而“忘”就是不當一回事,就是輕忽,就是不肯切實用功。在陽明提出致良知宗旨的背景下,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將“致”字看得太輕易。在陽明晚年揭出致良知宗旨以后,學者之所以會看輕“致”字,主要原因就是陽明將“究竟話頭”“一口說盡”,學者“得之容易”,并不珍惜,以至于陷入不能將良知付諸實踐的怠惰之中(25)錢德洪《刻文錄敘說》引陽明語,《王陽明全集》卷41,第1747頁。。
陽明以下說法提示了解決困忘問題的思路:“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26)《答舒國用·癸未》,《王陽明全集》卷5,第211頁。要領即是致良知,把握要領以后的篤志,即是決心切實去致良知。事實上,這兩個要點都可以歸結為誠意。
首先看把握要領這一點。良知之所以是要領,是因其直接為工夫提供了動力和準則。知道要領,就可以免于疑惑。正如前文“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表明的,免于疑惑依賴于切實體認良知。而所謂切實體認良知,就是讓良知充實于意念,達到意念與良知本體的一致,這種狀態正是誠意的狀態。“誠意”的基本意思是不自欺、表里如一,在陽明處則指意念與本體一致,或說意念都是發自本體之念。而本體之念即是好善惡惡,因此也可說誠意即是好善惡惡。當然,在受到私欲阻礙之時,要做到好善惡惡必須有所刻意、執著,在此,誠意便是有所刻意、執著地好善惡惡。
接著再具體看篤志。陽明非常重視篤志。他在嘉靖四年(1525)給周沖的回信中說:“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27)《傳習錄》第144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65頁。真切立志就是篤志,而“真切”的基本含義是認真、切實。真切地好善惡惡實即誠意。篤志必落實為真切地好善惡惡,因此說篤志終究就是誠意。由此,陽明把立志看作“為學緊要大頭腦”,實際上就是把誠意看作“為學緊要大頭腦”。作為決心切實去致良知的篤志,意味著體認良知本體,讓良知本體充實于意念,從而推動致知工夫的落實。原本良知自有動力和準則,篤志不過是使得良知的動力和準則充分發揮出來。也就是說,篤志構成致知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而篤志即是誠意,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誠意,誠意構成致知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
總之,雖然為解決困忘問題需要知要和篤志兩個條件,但是這兩個條件的實質又都在于誠意,因此,解決困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誠意。陽明晚年強調誠意在工夫中的首出地位,其針對的正是致知話語下學者廣泛存在的困忘問題。
三、專一與自驅促成致知的落實
為解決致知背景下學者中存在的困忘問題,陽明賦予誠意以首出地位。那么,誠意如何解決困忘問題呢?解決困的問題,關鍵在誠之專一,由此使良知固有準則在具體事務中發揮作用;解決忘的問題,關鍵在誠的自我驅動,由此啟動致知工夫,進而發揮良知固有動力的作用。當然,這兩點又可歸結于誠意之自我驅動。只有啟動致知工夫,才能專一地發揮良知準則的作用。
陽明晚年給予誠和誠意以極高的地位。嘉靖五年(1526),他斷言誠足以概括天地之道和圣人之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圣人之學,誠焉而已耳。”(28)《南岡說·丙戌》,《王陽明全集》卷24,第1000頁。誠在他晚年思想中的地位,由此可謂顯露無疑。誠不僅是理想狀態,也是工夫要求。陽明認為圣人能以至為真誠、始終如一的態度做致知工夫,“圣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29)《傳習錄》第167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79頁。。圣人之所以能做到至誠無息,原因在于其抱有真切的態度。正是在真切的意義上,陽明才會在以致良知為“學問大頭腦”以外,還把誠意也視為“為學緊要大頭腦”。
誠意如何解決困忘的問題,從而發揮“為學緊要大頭腦”的作用?如前所述,陽明以好色比喻誠意,而好色具有意念專一而心無旁騖,自我驅動而無需外力推動兩個主要特點。陽明以此比喻誠意。因而,誠意也具有意念專一而心無旁騖,自我驅動而無需外力推動兩個主要特點(30)可以說,前述篤志之所以是誠意,其原因在于篤志和誠意一樣,具有意念專一和自我驅動的特點。正因篤志就是誠意,所以陽明才以原本用以比喻誠意的好色來比喻篤志。。正是意念專一和自我驅動兩點,克服了困忘的問題,促成致知工夫的落實。以下我們具體加以說明。
首先,關于困的問題。陽明曾致信歐陽德,指出其存在將處理事務與涵養良知本源分為兩事的錯誤。陽明說:“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這是說無論有事無事,終身只是致良知一個工夫。歐陽德的意思是,在處理事務感到吃力之際,寧肯不去做事,也不能不涵養良知。他意在通過涵養良知來使自己能勝任事務,并不認為自己把處理事務和涵養良知分為兩事,因此對陽明的批評表示了疑惑。針對歐陽德的疑惑,在嘉靖五年的回信中,陽明從良知自有準則的角度,進一步解釋了自己此前批評他的理由:“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于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陽明指出,歐陽德放下事務而轉向涵養良知的做法,表明他并沒有在處理事務中直接貫徹良知的準則,而是訴諸功利計較。因此,他已經把事務和良知割裂開來,并且事實上否定了致知作為全功的地位。
良知的準則不能貫徹于事務,就會使人陷入困苦之中。事實正是如此,歐陽德便被精力不足的問題所困擾。他說:“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于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于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因于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陽明在回信中首先指出精力不足問題的原因在于將良知與事務割裂為二,然后指出解決之道在于訴諸專一之誠,亦即“誠一真切”地致知。他說:“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于事勢,困于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勢、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31)以上見《傳習錄》第170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82—83頁。陽明在最后揭示出自我驅動的誠意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依靠,因其具有使良知之動力發用出來,從而推動致知工夫在具體事務中落實的作用。隨著致知工夫在具體事務中的落實,良知與事務割裂為二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陽明尚有與“誠一真切”相似的另一表述,即“誠切專一”。這一表述出現在他嘉靖六年回答另一弟子魏良弼的信中。魏良弼受“拘于體面,格于事勢”問題困擾。陽明指出其癥結也在于沒有認識到良知的準則可以貫徹于事務,而解決之道在于“誠切專一”地做致知工夫。“所疑拘于體面,格于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茍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為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于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32)《答魏師說·丁亥》,《王陽明全集》卷6,第242頁。
其次,關于忘的問題。在忘或說輕忽的狀態中,致知工夫并未真正啟動。而誠意所具有的自我驅動傾向,正可以激發良知固有的動力,啟動致知工夫,因而是這一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提出致良知宗旨后的正德十六年(1521),陽明說:“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33)《與席元山·辛巳》,《王陽明全集》卷5,第202頁。他在此指出致知之學不能光大的原因,就在于人們并沒有推動自身做致知工夫,而是讓致知工夫僅僅停留在口耳之間。這就是說,只有能夠自我驅動的誠意工夫,才能光大致知之學。同年,他在另一封信中正面表達了誠意的關鍵作用:“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于口而不明之于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于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34)《與朱守忠·辛巳》,《王陽明全集》卷5,第201頁。誠身、立誠,等同于誠意。立誠能推動口耳之學轉化為身心之學,使人把握良知固有的動力,啟動并落實致知工夫。正因為立誠能解決啟動并落實致知工夫的問題,所以才被陽明賦予“要在立誠而已”的首出地位。
四、誠意在不同階段的不同作用
前已論及,陽明中年工夫論便以誠意為本。其時他強調誠意在工夫中的首出地位,是針對朱子學以格物為首出而來。在他看來,朱子學以格物為首出,便使工夫陷于窮盡事物之理,無關身心修養的支離之弊中。他認為,唯有在好善惡惡的推動下做為善去惡的工夫,工夫才是關乎身心修養,并有助于達成成圣目標的。而好善惡惡正是誠意,為善去惡則是格物,由好善惡惡推動為善去惡,便是由誠意統領格物。唯其有了誠意的統領,格物工夫才免于支離;也唯其以格物工夫為下手處,誠意才能真正落實。這也是《大學古本序》所說“不本于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35)《大學古本原序》,《王陽明全集》卷32,第1321頁。的含義。克服工夫的支離,使工夫具有切要性,正是中年陽明工夫論關注的焦點。“切要”的意思是抓住根本,與之相反的支離的意思則是偏離根本。在陽明看來,朱子學唯其偏離了好善惡惡這一根本,所以才會陷入求理于事事物物的支離繁瑣中。
盡管在嘉靖二年的《大學古本序》中,陽明仍保留了上述對誠意與格物意義的評價,但這并不足以反映在致良知理論提出以后誠意在陽明工夫論中的地位和作用。因為致良知學說的提出,本身就意味著陽明在工夫論上的論述中心已經發生轉移,相應地,誠意在新的問題意識中究竟承擔什么角色,僅僅憑借《大學古本序》這類由前一時期文本修改而成的文本,是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來的。
事實上,即便是晚年新創作的文本,也未必都能反映誠意在陽明晚年工夫論中扮演的角色。如在嘉靖四年左右與顧璘的書信往來中,顧璘稱贊陽明的誠意學說具有矯正當時學者逐物支離、忽視身心修養之弊病的重要意義:“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陽明在回答中指出:“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圣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36)《傳習錄》第130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46頁。“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即是指朱子學者主張以格物為先、以誠意為后。從回答來看,陽明不僅沒有反駁顧璘的說法,反而還順承其說,認為誠意在儒學工夫論中擁有首出地位。盡管陽明晚年確實也認為誠意具有首出地位,不過很顯然,誠意在此針對的是工夫的支離,而非對致知工夫的懷疑和輕視。換句話說,誠意在此主要反映的是陽明中年而非晚年工夫論的問題意識。當然,我們不是說陽明晚年就不反對工夫的支離,只是說這不構成他晚年的主要關切。
總之,誠意在陽明晚年工夫論中仍然具有首出地位,而沒有因為致良知宗旨的揭出而被輕視。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正德十五年前后陽明工夫論的連續性。不過更應看到,誠意在陽明晚年工夫論中的地位,是基于陽明對工夫之真切性的要求。在致良知宗旨突顯出工夫之簡易性的背景下,人們容易懷疑致知作為全功的地位或輕忽工夫的困難與持久,因而對真切做工夫的強調就顯得非常必要和緊迫。與陽明中年借由誠意以保證工夫的切要性不同,誠意在陽明晚年工夫論中的作用,主要是保證工夫的真切性。從它們各自的反面來看,切要性對治的是工夫的支離,真切性對治的是懷疑或輕視工夫。誠意的不同角色,又反映出陽明工夫論的發展和變化。
在此還須討論的問題是,陽明同時以致知和誠意為首出,是否會構成矛盾?根據前述討論,致知與誠意均指好善惡惡。正因所指相同,所以陽明才說“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37)《傳習錄》第281條,《王陽明全集》卷3,第124頁。。正因本來只是從不同角度揭示同一工夫的內涵,所以陽明晚年同時以致知和誠意為本,就不會構成矛盾。用宋明儒學固有話語來說則是,陽明這樣做不會造成備受詬病的“二本”問題。
由此又產生一個問題,即致知和誠意既然本就是指同一個工夫,那既說致知又說誠意豈不是疊床架屋?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從不同角度對同一個工夫進行刻畫,不僅如前所述是不得已的“補偏救弊”,從根本上來說也是為了工夫的詳密。正德十五年,陽明在給羅欽順的信中說:“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38)《傳習錄》第174條,《王陽明全集》卷2,第86頁。這段話既說明格致誠正修雖各有所指但卻本就只是指一個工夫,同時也說明詳密是工夫的內在要求。正是為了工夫的詳密,所以才有必要從不同角度對同一個工夫進行刻畫。
最后,本文尚且遺留一個問題,即既然陽明晚年同時以誠意為本和以致知為本,那就有必要對他工夫實踐及理論的演進提出新的解釋框架。簡言之,相比于從以誠意為本轉變為以致知為本的解釋思路,工夫論的重心由真切轉向簡易,再由簡易轉向真切,或許更適合作為陽明中晚年工夫論演進的內在線索。限于篇幅,只能另撰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