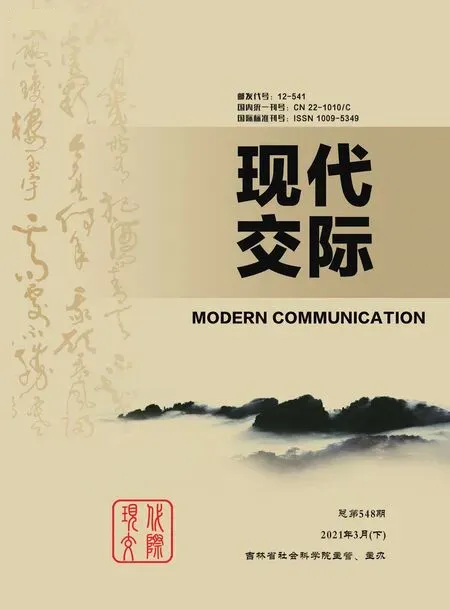共享發(fā)展與人的解放
梁 舉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xué)院)山東 濟(jì)南 250103]
堅(jiān)持共享發(fā)展,必須堅(jiān)持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表明我國各項(xiàng)事業(yè)發(fā)展的目的、動(dòng)力和成果屬性都是人民,換言之,共享發(fā)展是最終服務(wù)于人的解放的。
一、共享發(fā)展促使人與自身關(guān)系的解放
要實(shí)現(xiàn)人與自身關(guān)系的解放,首先要明確人是如何受到自身限制和束縛的。馬克思認(rèn)為實(shí)踐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因此,人的自我限制和束縛直接表現(xiàn)在實(shí)踐上,即表現(xiàn)為人的異化,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類本質(zhì)”的異化。異化狀態(tài)下的人是消極的、被動(dòng)的,勞動(dòng)對他來說是外在的,在勞動(dòng)中只會(huì)感覺到壓抑、束縛、不幸,以致“強(qiáng)制的勞動(dòng)—停止,人們就會(huì)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勞動(dòng)”[1]159。在異化勞動(dòng)中,人的主體地位徹底喪失,其根源則是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共享發(fā)展以我國生產(chǎn)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為基礎(chǔ),從而保證了人的主體地位。生產(chǎn)資料公有制為生產(chǎn)資料的共享提供了制度前提,這促使人成為生產(chǎn)資料的主人,勞動(dòng)成為為我的勞動(dòng),因而人就會(huì)以積極主動(dòng)的狀態(tài)參與勞動(dòng)。共享發(fā)展要求的“人人盡力”不再是被迫的強(qiáng)制狀態(tài)下的為了別人的勞動(dòng)過程,而是自覺自愿前提下積極地實(shí)現(xiàn)自我的過程,因此,勞動(dòng)對人來說就不再是外在的東西,而是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外化,在勞動(dòng)中人不再感到痛苦不幸,而是感到幸福,因?yàn)閯趧?dòng)是他自我確證、自我肯定的一種方式,它不再是人千方百計(jì)逃避的對象,也不再是人謀生的手段,反而成為人的第一需要。這樣共享發(fā)展就使人從異化狀態(tài)下解放出來,達(dá)到了人與自我的和諧。
共享發(fā)展促進(jìn)人的感覺的全面解放。馬克思對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階段的私有制造成人的感覺的全面異化進(jìn)行了尖銳的批判,“私有制使我們變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個(gè)對象,只有當(dāng)它為我們所擁有的時(shí)候,就是說,當(dāng)它對我們來說作為資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們直接占有,被我們吃、喝、穿、住的時(shí)候,簡言之,在它被我們使用的時(shí)候,才是我們的”,“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這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這就是人的本質(zhì)的絕對貧困,而“對私有財(cái)產(chǎn)的揚(yáng)棄,是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共享發(fā)展通過對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的積極揚(yáng)棄,讓物對人的關(guān)系成為一種“對象性的關(guān)系”[1]190,最終使“擁有”和“有用”不再具有決定性意義,只有如此,人的感覺的豐富性才能從被“擁有”的唯一感覺的遮蔽中顯現(xiàn)出來,物也就不再單純因?yàn)槠洹坝杏眯浴辈啪哂袃r(jià)值,而成為多種價(jià)值的載體為人們所發(fā)現(xiàn)和理解。換言之,共享發(fā)展將原本屬于人的感覺的豐富性歸還給人自身,讓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gè)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zhì)”[1]189。
共享發(fā)展促進(jìn)人的需要的解放。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人的需要也在逐步擴(kuò)展。在以工業(yè)文明為基礎(ch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需要發(fā)生了異化。尤其是處于底層的無產(chǎn)階級,在資本的統(tǒng)治壓迫下,其需要甚至退回到了動(dòng)物狀態(tài)。“光、空氣等,甚至動(dòng)物的最簡單的愛清潔習(xí)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人不僅沒有了人的需要,甚至連動(dòng)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1]225這種需要的異化是人對自身的一種否定。共享發(fā)展以共同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財(cái)富為基礎(chǔ),消除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帶來的弊端,讓人從資本的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勞動(dòng)不再是維持生活的一種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人對物質(zhì)財(cái)富的追求也不再以壓抑甚至犧牲自己的需要為代價(jià)來獲得滿足。人的需要不再局限于生理的滿足,而是擴(kuò)展到精神的享受,精神享受這種需要的產(chǎn)生,本身就是人肯定自身的一種重要方式。
人除了物質(zhì)生活以外,還需要精神生活,共享發(fā)展為提升人們精神生活品質(zhì)提供了保障。在生產(chǎn)力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占據(jù)了多數(shù)人的大部分生活,精神生活只是少數(shù)貴族的專利,隨著生產(chǎn)力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工業(yè)文明的到來和深度發(fā)展,人的工作時(shí)間逐漸減少,精神生活越來越成為人的本質(zhì)需要。以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為基礎(chǔ)的共享發(fā)展,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不僅使人能夠分享他人的精神產(chǎn)品。自媒體時(shí)代的到來,每個(gè)人都可以生產(chǎn)出自己的精神產(chǎn)品并分享給他人,每個(gè)人都擺脫了之前要么是生產(chǎn)者要么是消費(fèi)者的單一身份,集生產(chǎn)者與消費(fèi)者兩種身份于一身,使自己成為精神生活領(lǐng)域的完整的人。一方面,可以讓優(yōu)秀的精神文明成果普及到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精神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者感到實(shí)現(xiàn)自身的價(jià)值,激勵(lì)他們生產(chǎn)更多更優(yōu)秀的精神生活產(chǎn)品,通過精神生活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者和消費(fèi)者的雙向互動(dòng)和相互啟蒙,使自身的精神生活品質(zhì)得到提升。在共享發(fā)展的過程中,人們會(huì)逐漸突破自己原有的思想觀念的束縛和由分工所形塑的單一身份,實(shí)現(xiàn)由單面人向完整人的轉(zhuǎn)變,從而完成人的自身的更為徹底的解放。
二、共享發(fā)展促使人與他人關(guān)系的解放
人受自身關(guān)系的束縛,即人的類本質(zhì)的異化根源來自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這種私有制直接導(dǎo)致對立階級的產(chǎn)生,而階級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個(gè)人組成,因此,階級利益的對立必然造成人與人的對立,只要人與人處于對立的狀態(tài),那么人就永遠(yuǎn)處于他人的束縛之中。馬克思著重分析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人的對立狀態(tài),這種對立不僅包括工人與資本家對立,工人與工人之間,還包括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甚至工人與機(jī)器之間因?yàn)橄嗷ジ偁幎纬傻钠毡閷αⅰ1R梭將之形象地表達(dá)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他人即自己利益的邊界,是自己利益的妨礙,在這種狀態(tài)下,人的全面發(fā)展只能成為幻想,而共享發(fā)展,則是以每個(gè)人自由全面發(fā)展為目標(biāo),在發(fā)展過程中,每個(gè)人都有發(fā)揮自己才能的機(jī)會(huì)和舞臺,人人主動(dòng)參與,因此人人竭盡全力。共享發(fā)展條件下,每個(gè)人都是共同體的一員,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分歧,他人不再是自己利益的邊界,而成為自身利益的補(bǔ)充,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每個(gè)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2],人從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中解放出,不再受他人的束縛和妨礙而獲得對他人關(guān)系的自由。
馬克思明確區(qū)分了“真正的共同體”和“虛幻的共同體”,并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體中,才能實(shí)現(xiàn)人的真正的自由。“在真正共同體的條件下,每個(gè)人在自己的聯(lián)合中并通過聯(lián)合獲得自己的自由”[1]571。“虛幻的共同體”根源于階級的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對抗,后者采取國家的形式,國家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這種情況下,人的解放只有在階級內(nèi)部實(shí)現(xiàn),個(gè)人的階級身份優(yōu)先于其他身份,這種階級屬性本身意味著人的解放的有限性。雖然在階級內(nèi)部實(shí)現(xiàn)了解放,但是一旦超出所在階級的范圍,就必然與其他階級處于對抗?fàn)顟B(tài)。階級對立的產(chǎn)生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分工越來越精細(xì),由資本主導(dǎo)的全球化,使分工由一國拓展到世界范圍,分工是導(dǎo)致異化的根源,也是人與人對立的根本原因之一。共享發(fā)展力圖從生產(chǎn)方式入手,從根本上改變以往由自發(fā)而非自愿形成的分工狀態(tài),從而改變?nèi)说慕?jīng)濟(jì)關(guān)系,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對立狀態(tài)。
共享發(fā)展就是要超越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對抗,超越人與人關(guān)系的束縛,讓人從階級的個(gè)人過渡到自由個(gè)性的人,從而實(shí)現(xiàn)人的徹底解放。這種超越基于對傳統(tǒng)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雙重否定。從生產(chǎn)力方面來說,共享發(fā)展通過勞動(dòng)者、勞動(dòng)資料和勞動(dòng)對象等使生產(chǎn)力各要素的共享達(dá)到高度融合,充分有效地激發(fā)生產(chǎn)力,為共享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zhì)前提;從生產(chǎn)關(guān)系方面來看,共享發(fā)展超越了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的狹隘性,以公有或公有的方式消解剝削產(chǎn)生的制度根源,實(shí)現(xiàn)人與人在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方面的平等。通過雙重超越,共享發(fā)展將建立起馬克思所講的真正的共同體,為人與人關(guān)系的解放營造良好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奠定牢固的社會(huì)基礎(chǔ)。
人人共享從勞動(dòng)成果分配的角度,為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對立提供了物質(zhì)保證和可行性方案。共同富裕是我們始終堅(jiān)持的原則,只有落實(shí)為行動(dòng)才能切實(shí)增加人們的獲得感。改革開放時(shí)期,因?yàn)槲覀兊纳a(chǎn)力水平還普遍較低,所以采取“讓一部分地區(qū)和個(gè)人先富起來”的策略,這有利于激發(fā)人們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實(shí)踐證明,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和地區(qū)之間的發(fā)展不平衡,也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進(jìn)入新時(shí)代以后,我們的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槿藗內(nèi)找嬖鲩L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這要求我們必須實(shí)行共享發(fā)展,實(shí)現(xiàn)人人共享,逐步縮小收入差距,消除因地區(qū)差異而帶來的機(jī)會(huì)不平等,從根本上消除貧富差距,實(shí)現(xiàn)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利用分配手段消除對立、共建和諧。
三、共享發(fā)展促進(jìn)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解放
自然對人的束縛,一方面源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與人的需要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源于人對自然認(rèn)識的有限性造成的實(shí)踐的盲目性,以及對自然的破壞和對人類自身的傷害。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是一種客觀狀態(tài),當(dāng)其無法滿足人的需要的時(shí)候才會(huì)構(gòu)成對人的束縛,這也有一個(gè)歷史的過程。在原始社會(huì),自然對人的束縛主要表現(xiàn)在人對自然的無知,這種無知造成人在強(qiáng)大的自然面前無能為力,于是產(chǎn)生了自然崇拜。就人的物質(zhì)需要而言,自然并未構(gòu)成對人的束縛,人口有限,地域廣袤,人類可以通過采集、簡單耕作而滿足自身基本的生活需要。此時(shí),人對自然的束縛集中在精神領(lǐng)域。隨著人口的增長,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到來,一方面,自然在資本無限的拓展能力的征服下,被開發(fā)得越來越徹底;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無論規(guī)模還是質(zhì)量都大大增加,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越來越成為束縛人類發(fā)展的瓶頸。
人類社會(huì)初期,生產(chǎn)力低下,人類對自然的改造比較簡單,在改造中對自然的破壞可以通過自然界本身得以修復(fù),不存在自然對人類的報(bào)復(fù)。歐洲文藝復(fù)興,特別是啟蒙運(yùn)動(dòng)之后,人的主體性得到史無前例的提升,自然從人類精神的主宰下降為人類征服的對象,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促進(jìn)生產(chǎn)力提升的同時(shí),對自然的破壞也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氣污染、生態(tài)危機(jī)、臭氧層破壞、水資源短缺等全球性問題凸顯,自然逐步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否定性力量。為了緩解人與自然的緊張關(guān)系,人類提出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共享發(fā)展是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念的實(shí)現(xiàn)路徑。具體來說,共享發(fā)展是突破資源有限性障礙的根本之策,它通過將所有權(quán)與使用權(quán)分離,讓即使沒有所有權(quán)的人通過付費(fèi)等方式同樣可以共享資源的使用權(quán),這是對傳統(tǒng)只有擁有所有權(quán)才能獲得使用權(quán)的資源利用模式的揚(yáng)棄,有利于充分利用閑置資源,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緩解資源有限性帶來的矛盾,從而緩解工業(yè)文明以來造成的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緊張。
人與自然和諧關(guān)系的建立,是人從與自然的關(guān)系中解放出來的根本途徑。馬克思認(rèn)為,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經(jīng)歷了原始和諧關(guān)系、斗爭關(guān)系、和諧統(tǒng)一關(guān)系三個(gè)歷史階段,共享發(fā)展建立在對人與自然的斗爭關(guān)系的后果的積極反思基礎(chǔ)上,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為目標(biāo)。共享發(fā)展是一種可持續(xù)的發(fā)展,這要求在對待自然時(shí)摒棄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huì)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平等對待自然。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bào)告中重新定位了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把對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認(rèn)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yīng)自然、保護(hù)自然。”[3]既然人與自然是命運(yùn)共同體,那么發(fā)展就不應(yīng)當(dāng)僅僅是人的發(fā)展,還應(yīng)該包含自然本身的發(fā)展。換言之,自然也是發(fā)展的主體,也應(yīng)當(dāng)共享發(fā)展的成果,自然不再是人滿足需要的中介工具,而成為目的本身。人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者和支配者,而成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主體性的確證不再建立于對自然的利用和操縱之上,而植根于與自然人的和諧共生之中。此時(shí),自然不在人之外,不再因束縛人而成為人征服的對象,而是與人互為主體,這種狀態(tài)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共產(chǎn)主義的狀態(tài)。“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矛盾的真正解決”。[1]185因此,共享發(fā)展對自然規(guī)律認(rèn)識的深化,有助于我們從根本上緩解人與自然的矛盾,達(dá)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