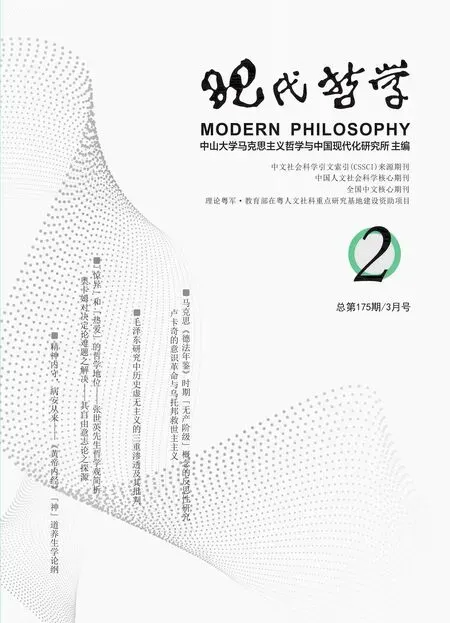盧卡奇的意識革命與烏托邦救世主主義
司 強
階級意識是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對現(xiàn)代世界所陷入的物化危機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物化和階級意識的思想得到西方學界的高度贊揚,并為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和社會批判理論提供了思想依據(jù)。但是,共產(chǎn)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認為,盧卡奇的觀點是極左派和修正主義。在1971年的自傳中,盧卡奇指出:“這本書有一定的價值,因為在那里面提出了當時馬克思主義回避了的問題。一般都承認,異化問題是在那里第一次提出的,這本書還嘗試把列寧的革命理論有機地納入馬克思主義的總概念。這本書的根本的本體論錯誤,是我只承認社會中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由于自然辯證法被否認,馬克思主義從非有機自然界推出有機自然界、從有機自然界通過勞動范疇推出社會的那種普遍性就完全失去了,這里還應該補充的是,在全面的社會和政治觀點中,剛才提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義起了很大的作用。”(1)[匈]盧卡奇:《盧卡奇自傳》,李渚青、莫立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118—119頁。也就是說,盧卡奇晚年一方面承認《歷史與階級意識》對異化問題的研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另一方面又認為這本書在本體論上有嚴重的錯誤,陷入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義。西方學界、蘇聯(lián)官方和盧卡奇本人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評價存在巨大差異。由于盧卡奇的主觀目的是總結十月革命的成功經(jīng)驗,并將它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以指導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實踐,所以只有從盧卡奇的主觀目的出發(fā),并將它與列寧的革命理論相比較,才能真正把握《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貢獻和局限。
一、物化意識與階級意識
一戰(zhàn)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戰(zhàn)爭的支持態(tài)度,使盧卡奇陷入普遍的絕望狀態(tài)。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將馬克思主義闡釋為庸俗唯物主義和科學主義,在理論上入宿命論,這種宿命論使他們面對1914年的革命形勢無法組織起有效的革命活動。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處在絕望中的盧卡奇找到了希望。1918年,盧卡奇加入匈牙利共產(chǎn)黨。1919年3月,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盧卡奇擔任教育和文化的副人民委員以及匈牙利紅軍第五師政治委員。革命期間,盧卡奇深入前線并參與了蒂薩費勒德保衛(wèi)戰(zhàn)。由于紅軍缺乏有效組織,紅軍戰(zhàn)士缺乏革命意識、喪失革命斗志,最終導致革命失敗。匈牙利革命的失敗,迫使盧卡奇進一步反省革命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盧卡奇寫作了《歷史與階級意識》。就此而言,盧卡奇的階級意識思想擔負雙重使命:在理論上澄清第二國際和匈牙利革命失敗以及十月革命成功的經(jīng)驗,其目的在于為走出現(xiàn)代社會的物化危機提供理論指導。
就階級意識的含義來說,階級意識既不是組成階級的單個人思想的總和,也不是這些思想的平均值,因為個人雖然能夠超出生活的限制和偏見,但個人總是時代的產(chǎn)物,無法超越時代的經(jīng)濟結構和經(jīng)濟地位的限制。“因此,階級意識——抽象地、形式地來看——同時也就是一種受階級制約的對人們自己的社會的、歷史的經(jīng)濟地位的無意識(Unbewuβtheit)。”(2)[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97頁。階級意識是與一定社會生活形式相關聯(lián)的階級的意識,它的產(chǎn)生是一個歷史過程。
在前資本主義階段,由于其社會結構分為等級、階層,且經(jīng)濟、政治、宗教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阻礙了階級意識的產(chǎn)生。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差別在于,商品形式成為占支配地位的經(jīng)濟形式,它滲透進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對社會進行改造。在客觀方面,商品形成物以及物與物之間關系構成的世界,廢除了等級制,經(jīng)濟因素在社會生活中起決定作用,法律、道德、宗教等意識形式隨著經(jīng)濟結構的改變被重塑。世界被改造為單一的商品世界,這個單一的世界作為異己的力量與人相對立。在主觀方面,隨著經(jīng)濟因素對社會起決定作用,人的經(jīng)濟活動越來越具有獨立性,主體主義、理性主義成為人的獨立性的理論表達。人們的越來越自覺的活動,卻創(chuàng)造了一個與人本身相對立的商品世界。這個世界服從商品的規(guī)律,反過來控制人。
在商品形式下,整個社會成為統(tǒng)一的整體,這使得資產(chǎn)階級能夠認識整體,獲得資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但資產(chǎn)階級在生產(chǎn)中的地位和利益的限制,使他們只能認識而不能克服這個商品的世界,于是資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表現(xiàn)為與社會發(fā)展相對立的“虛假”意識。這種對立使其遭受悲劇性的災難,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之中。這一悲劇性災難具體表現(xiàn)為三重矛盾:資產(chǎn)階級以自由的名義反對封建等級制,但在革命取得勝利后又形成一種新的壓迫;資產(chǎn)階級使階級斗爭表現(xiàn)為社會事實,但又想盡辦法將階級斗爭從社會意識中清除;資產(chǎn)階級賦予個性以前所未有的意義,但又通過商品生產(chǎn)的形式抹殺了所有個性。這三重沖突可以歸結為個人原則與社會原則之間的對立,即“資產(chǎn)階級思想始終地和必然地從個別資本家的立場出發(fā)來觀察經(jīng)濟生活,正因此也就造成了個人和不可抗拒的、超個人的推動一切社會的東西的‘自然規(guī)律’之間的這種尖銳的對立”(3)同上,第110頁。。盧卡奇把這種個人的立場與社會原則的對立,描述為物化意識。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無產(chǎn)階級運動的興起,“資產(chǎn)階級‘虛假’意識中的辯證矛盾加劇了:‘虛假’意識變成了虛偽的意識。開始時只是客觀存在的矛盾也變成主觀的了:理論問題變成了一種道德立場,它決定性地影響著階級在各種生活環(huán)境和生活問題上所采取的實際立場”(4)同上,第112頁。。資產(chǎn)階級的全部科學掩蓋其理論的社會基礎,法律、經(jīng)濟學、新聞甚至哲學都宣稱中立、客觀的立場。這種客觀和中立掩蓋了理論背后的物質利益,“虛假”的意識淪為“虛偽”的意識。
在資本主義時代,無論資產(chǎn)階級還是無產(chǎn)階級都陷入物化意識。資產(chǎn)階級由于其立場的限制而陷入“虛偽”意識,無產(chǎn)階級則陷入直接的物化意識。商品形式成為社會的支配形式,商品抽象形式的普遍性原則成為整個社會的原則。這一原則在具體交換過程中表現(xiàn)為合理化和數(shù)量化。勞動過程的合理化和可計算性,使勞動過程分解為可精確計算的局部過程,產(chǎn)品本身的統(tǒng)一性被破壞。與之相應,具體的勞動也分解為可精確計算、合理的機械勞動,這種機械勞動與工人的人的屬性相對立。“一方面,他們的機械化的局部勞動,即他們的勞動力同其整個人格相對立的客體化(它已通過這種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的出賣而得以實現(xiàn))變成持續(xù)的和難以克服的日常現(xiàn)實,以致于人格在這里也只能作為旁觀者,無所作為地看著他自己的現(xiàn)存在成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異己的系統(tǒng)中去。另一方面,生產(chǎn)過程被機械地分成各個部分,也切斷了那些在生產(chǎn)是‘有機’時把勞動的各種個別主體結合成一個共同體的聯(lián)系。”(5)[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37—138頁。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斬斷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面對這個物化的世界,個人只能采取旁觀的態(tài)度,只能看到直接的物性而陷入物化意識。
二、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實踐特性
通過對物化現(xiàn)象批判,盧卡奇認為無論資產(chǎn)階級還是無產(chǎn)階級,其直接的心理狀態(tài)都是物化意識。物化意識意味著現(xiàn)代社會陷入普遍的絕望狀態(tài),但拯救何以可能?通過對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陷入物化意識的不同處境,盧卡奇將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覺醒視為解決物化問題的關鍵,并以此論證了無產(chǎn)階級的歷史使命。
盡管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都陷入物化意識,但資產(chǎn)階級在物化中具有雙重地位:一方面單獨的個體面對客觀必然的社會陷入直接性,只能理解具體現(xiàn)象,而無法理解總體;另一方面,個人保持著一種表面上的主體地位,剝削程度的增加只是意味著地位鞏固和需求被滿足。工人卻不具有這雙重地位,當工人試圖幻想自己是生活的主體時,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將粉碎他的幻想,物化在工人身上達到頂點。剝削程度的增加對工人意味著毀滅,工人的勞動時間不僅意味著作為商品而出賣,更是涉及人的生存形式、人的靈魂。“工人以物化過程和變?yōu)樯唐罚m然毀滅他,使他的‘靈魂’枯萎和畸變(只要他不是有意識地表示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靈魂的本質沒有變?yōu)樯唐贰R虼怂梢栽趦?nèi)心里使自己完全客觀地反對他的這種存在。”(6)同上,第231頁。物化的極致同時意味著拯救的開始,工人完全可能反對他的殘酷現(xiàn)實。
當工人把自己作為商品出賣時,在工人身上發(fā)生了主客體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使工人意識到自己是商品,也就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工人意識到自己是商品,在原則和性質上不同于對某物的意識。關于某物的意識,某物為何物是純粹偶然的;而且對于某物的意識,并不會改變意識和對象的關系,某物的存在方式并不會發(fā)生改變。奴隸認識到自己的奴隸身份,認識到自己是奴隸,并不會帶來其地位的根本改變。當處于物化頂點的工人認識到自己作為商品的身份,工人對自己的認識就是商品的自我意識。與奴隸對自己的意識并不改變其地位不同,對工人來說,意識的改變意味著對象的改變以及與對象關系的改變。工人認識到自己是商品,這種商品的自我意識使人和物之間的關系發(fā)生改變,使隱藏在商品交換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得以呈現(xiàn),使在量化外衣下人的質的特性、工人靈魂不可量化的特性得以顯露出來。這樣,工人就從經(jīng)濟發(fā)展中未被認識的被動狀態(tài)轉化為主動狀態(tài),工人開始認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人與物之間關系的改變,同時帶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改變。作為個體的工人只能承認或拒絕自己的社會地位,并不能改變物化的社會現(xiàn)實。但當工人認識到商品交換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認識到在社會分工中彼此協(xié)作的個人是作為階級而存在的,就意味著歷史有可能改變。
工人認識到勞動的社會特性,也就意味著有可能消除孤立化、原子化,克服物化,無產(chǎn)階級就成為歷史和社會同一的主體——客體。“面對在思想、組織等等方面都占優(yōu)勢的資產(chǎn)階級,無產(chǎn)階級的優(yōu)勢僅僅在于,它有能力從核心出發(fā)來觀察社會,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聯(lián)系著的整體,并因而能從核心上,從改變現(xiàn)實上來采取行動;就在于對它的階級意識來說,理論與實踐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覺地把它自己的行動作為決定性的因素投放到歷史發(fā)展的天平上去。”(7)[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16頁。工人對自己共同利益和地位的認識而導致階級意識的覺醒,意味著改變現(xiàn)實成為可能。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特征在于對直接性的超越,是一種在物化極致狀態(tài)下,朝著社會總體前進并克服物化的意識。在此意義上,盧卡奇指出“工人認識到自己是商品,已經(jīng)是一種實踐的認識”(8)同上,第227頁。。
三、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與革命
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產(chǎn)生雖然具有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但根據(jù)無產(chǎn)階級運動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其階級意識也有不同的樣態(tài)。《歷史與階級意識》作為一本論文集,唯有《物化與無產(chǎn)階級意識》和《關于組織問題的方法論》這兩篇文章專門為出版所寫。如果說在《物化與無產(chǎn)階級意識》中,盧卡奇論證了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實踐特征,并指出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是解決物化危機和物化意識問題的關鍵;那么在《關于組織問題的方法論》中,盧卡奇以組織問題為中介,具體指出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實現(xiàn)途徑。
以組織問題為中介,盧卡奇闡釋了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實現(xiàn)中介。起初革命只是以抽象的可能性出現(xiàn)的烏托邦主義,理論與實踐之間沒有中介的環(huán)節(jié)。革命的組織問題,即無產(chǎn)階級的覺悟部分如何采取行動,尚未進入群眾和理論家的意識之中,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尚未覺醒,革命只是理論的(或抽象的)可能性。與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的發(fā)展進程相適應,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經(jīng)歷了從對革命無意識的烏托邦主義的“自在”狀態(tài),到對革命運動的自覺。覺醒的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處于自發(fā)的狀態(tài)。這種具有自發(fā)性質的無產(chǎn)階級立場,在理論上表現(xiàn)為無產(chǎn)階級自發(fā)的群眾斗爭理論。這一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所導致的帝國主義之間的戰(zhàn)爭及其帶來的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斗爭,必然會動員起無產(chǎn)階級的自發(fā)群眾運動。在這一階段,政黨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中起輔助作用,自發(fā)的群眾斗爭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誕生。盧卡奇認為,羅莎·盧森堡就是自發(fā)群眾運動理論的代表。
自發(fā)的群眾運動理論假設群眾是純粹的無產(chǎn)階級,但并不是只有純粹的無產(chǎn)階級參加革命運動,小資產(chǎn)階級、農(nóng)民、被壓迫的民族也加入到革命隊伍中。這些階層的意識并不是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反而會影響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在自發(fā)群眾運動中,政黨作為革命的輔助者,面對復雜的革命群眾,無法成為革命的領導者,最多達到工聯(lián)主義的水平。這就需要具有階級意識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主動介入,無產(chǎn)階級政黨需要從革命的“助產(chǎn)士”成為革命的領導者。
受物化意識和資產(chǎn)階級的影響,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可能產(chǎn)生資產(chǎn)階級化,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在其他的領域中則有著穩(wěn)定的假象(服務條例、養(yǎng)老金等等)和個人上升為統(tǒng)治階級的抽象的可能性。這樣‘地位意識’就被培養(yǎng)起來了,這種意識能有效地阻止階級意識的產(chǎn)生”(9)同上,第231頁。。如果不消除這種地位意識,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就無法產(chǎn)生,并陷入意識形態(tài)的危機。孟什維克黨就是這一危機的表現(xiàn)形式。孟什維克黨在思想上受到資本主義的直接性思維的束縛,陷入對資本主義穩(wěn)定性的信仰。在組織上,孟什維克黨及其影響下的工會,有意識地使無產(chǎn)階級運動停留在自發(fā)運動的水平。這導致面對高漲的革命形勢,孟什維克黨無法參與革命運動,革命仍停留在工人的自發(fā)組織階段。
自發(fā)的群眾運動理論無法掌握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孟什維克黨則陷入階級意識的危機,二者都無法真正擔負起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由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所實現(xiàn)的是社會的徹底變革,是從自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所以只能采取有意識的步驟,即只能由革命階級的最覺悟部分——先鋒隊來實現(xiàn)。布爾什維克作為革命的先鋒隊就是歷史與個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中介,是自由的、有意識的集體意志,是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實體化。
通過與舊式黨相對比,盧卡奇揭示共產(chǎn)黨與其他一切政黨的差別。在舊式黨中,“黨被劃分為能動的部分和被動的部分,后者只是偶爾而且只是按照前者的命令起作用”(10)[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367頁。。入黨只是意味著簡單承認黨綱,黨的組織對普通成員不具有約束力,只是松散的個人的集合體,資產(chǎn)階級類型的政黨和孟什維克黨是舊式黨的典型代表。與舊式黨不同,共產(chǎn)黨是有意識的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通過紀律性將革命付諸實踐。紀律性意味著參加共產(chǎn)黨必須積極地親自參加革命工作。但作為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化身的共產(chǎn)黨,“沒有每個黨員對整體性格和黨的紀律之間的聯(lián)系的至少本能的理解,這種紀律就必然蛻化為一種物化的和抽象的權利義務體系,黨就會重新陷入資產(chǎn)階級政黨類型的組織狀況中”(11)同上,第369頁。。結合當時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官僚化、等級化傾向,盧卡奇事實上對無產(chǎn)階級政黨可能陷入的官僚主義提出了含蓄的批評。
共產(chǎn)黨作為無產(chǎn)階級覺悟部分的集體意志是歷史發(fā)展的積極和自覺因素,它通過與革命進程的交互作用,實現(xiàn)了革命自發(fā)性和有意識的行動的互動,“在共產(chǎn)黨內(nèi),而且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階級意識的能動和實踐特征是直接影響所有個人具體行動的原則,另一方面,它在同時又是有意識地參與決定歷史發(fā)展的因素”(12)同上,第366—367頁。。在黨和階級的關系上,面對無產(chǎn)階級內(nèi)部的不同組成部分,共產(chǎn)黨必須以意識統(tǒng)一為基礎,將無產(chǎn)階級內(nèi)部的不同組成部分理解為階級意識的不同階段。就黨內(nèi)關系來說,共產(chǎn)黨的斗爭必須以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斗爭為核心,實現(xiàn)黨內(nèi)階級意識的一致;就黨與其他階級的關系來說,要將意識的統(tǒng)一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lián)合。黨內(nèi)生活是實現(xiàn)黨內(nèi)階級意識的統(tǒng)一,克服無產(chǎn)階級的資產(chǎn)階級化以及物化意識的手段,通過黨內(nèi)生活,黨員全身心地參與黨的活動,實現(xiàn)黨員意志和黨的領導人意志之間的相互作用,保證黨員的意志、愿望、批評受到重視。
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中,階級意識化身為黨,“黨擔當著崇高的角色:它是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支柱,是無產(chǎn)階級歷史使命的良知”(13)同上,第86頁。。革命成功的關鍵在于克服意識形態(tài)的危機以及保持黨的意識的統(tǒng)一。黨的意識統(tǒng)一又以黨員的全身心投入和自我批評為基礎,即以政治上忠誠且具有強烈道德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的參與為條件。革命最后落實為為黨的意識的統(tǒng)一而斗爭。
以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歷史性為線索,盧卡奇將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理論分為階級意識未覺醒的烏托邦主義階段、盧森堡為代表的自發(fā)斗爭階段、孟什維克為代表的物化階段、布爾什維克為代表的自覺階段。通過對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歷史性的分析,盧卡奇闡明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由于陷入階級意識的危機,成為物化的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代表,所以在一戰(zhàn)中向本國資產(chǎn)階級政府投降。而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自覺階段。以此,盧卡奇論證了列寧的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理論的合理性,將列寧的革命實踐上升到方法的高度。
由于盧卡奇將階級意識的覺醒視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關鍵,無產(chǎn)階級政黨等于掌握了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政黨,這樣盧卡奇就把黨演變?yōu)閭惱韺嶓w。新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特質在于要求其黨員全身心的投入革命,嚴格服從黨的紀律,為純潔的革命意識而斗爭。這種要求最終蛻變?yōu)椤皯摗薄⑼懽優(yōu)榈赖侣闪睢o產(chǎn)階級革命的政治斗爭轉化為革命意識的斗爭,階級意識成為革命的關鍵。但是,如何衡量和判斷革命意識的正確性?如何保證黨的革命意識的純潔性?由于沒有任何客觀的衡量標準,只能陷入意識的自我確認。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最終因為缺乏實踐中介,淪為“神話”,且有蛻變?yōu)闃O權主義的危險。就盧卡奇將無產(chǎn)階級革命等同于階級意識的革命而言,在原則上并不屬于馬克思主義。對于馬克思來說,思想的內(nèi)容被歸結為社會存在,思想的原則和歷史的原則統(tǒng)一于現(xiàn)實的生活,“意識[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xiàn)實生活過程”(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頁。。當盧卡奇以階級意識的自覺程度作為判斷無產(chǎn)階級政黨成熟與否的標準,在原則上屬于黑格爾的觀念論,因此共產(chǎn)國際第五次大會認為盧卡奇的思想是極左派有其合理性,列寧在《共產(chǎn)主義的“左派”幼稚病》中對左派幼稚病的批判也適用于盧卡奇的階級意識理論。
四、結 論
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敏銳地覺察出階級意識對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重要性,并通過對階級意識的歷史分析,注意到現(xiàn)代社會的物化危機和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產(chǎn)生問題,并以此引發(fā)了20世紀西方思想界對現(xiàn)代性批判和意識形態(tài)理論的研究。通過對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分析,盧卡奇從理論上闡明了列寧關于的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的實踐,證明了列寧先鋒隊理論的合理性。但當盧卡奇將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等同于以階級意識為核心的革命時,忽視了列寧和葛蘭西所高度重視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現(xiàn)實維度。與盧卡奇相反,列寧強調把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與無產(chǎn)階級利益攸關的被壓迫人民團結在一起,實行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利益的聯(lián)合取代意識的聯(lián)合,即從革命的實際形勢出發(fā),制定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斗爭策略。在列寧的革命實踐中,無產(chǎn)階級的利益是黨的階級意識正確性的保障,這與盧卡奇的階級意識的自我確認所陷入的主觀確認存在根本差別。所以,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在主觀上試圖以階級意識理論對十月革命的成功經(jīng)驗予以理論說明,但在客觀上卻與其背道而馳,最終陷入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陷入列寧所說的“左派幼稚病”。
對此,盧卡奇有清醒的認識。在列寧逝世后,盧卡奇立即寫作并出版了《列寧》,并對自己的階級意識理論進行了修正。在此,盧卡奇不再將列寧的革命理論視為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自覺階段,而是將革命的現(xiàn)實性歸結為列寧思想的核心。盧卡奇回應了修正主義對列寧的指責,并對列寧思想的意義作出詮釋:修正主義指責列寧對俄國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別缺乏認識,并且不加分別地把俄國現(xiàn)實中的問題和解決方法的一般化,加以普遍運用。盧卡奇指出“革命的現(xiàn)實性:這是列寧思想的核心,是他與馬克思的決定性聯(lián)系”(15)[匈]盧卡奇:《列寧》,張翼星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27頁。。正如馬克思從理論與歷史兩個方面,從英國的工廠制度這個微觀世界的社會前提、條件和后果,以及造成它的發(fā)展并且威脅它發(fā)展的歷史趨向中,探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宏觀世界。列寧是在革命作為一種實際的現(xiàn)實被提上議事日程之后,以其天才看到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現(xiàn)實性。馬克思與列寧的共同點在于抓住革命的現(xiàn)實,修正主義者忽視了這一問題,拐彎抹角地將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革命性剔除。列寧主義是革命現(xiàn)實性前提下的理論,其理論的核心在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它是在革命現(xiàn)實性的前提下,以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為指導,對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帝國主義和國家理論做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修正主義的本質在于放棄了無產(chǎn)階級的立場,以整個社會的利益作為其出發(fā)點,在方法上放棄了對總體的認識,將現(xiàn)存的資本主義狀態(tài)當作不可改變的現(xiàn)實,從而受到現(xiàn)存政治的束縛。與《歷史與階級意識》相比,在《列寧》中盧卡奇已經(jīng)從尋求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逐漸轉變?yōu)樵诟锩F(xiàn)實性前提下對辯證法的運用,從強調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純粹性轉而強調聯(lián)合一切革命的力量,從對現(xiàn)代社會的異化和工人處境的分析,轉向從階級斗爭、矛盾的觀點分析具體的革命策略。以《列寧》為核心,盧卡奇逐漸擺脫《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過度強調階級意識的作用而忽略了社會存在,從而陷入的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可以說,盧卡奇思想的發(fā)展是對列寧思想不斷消化和理解的過程,撇開盧卡奇思想發(fā)展的歷程,就無法真正洞察《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貢獻及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