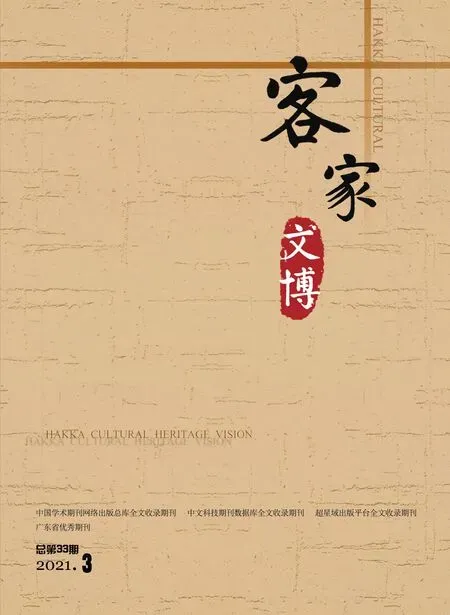東南亞客家影像中的族群意象書寫
——基于視覺人類學的分析
李小華 黃漫暉 陳詩潔
“族群”這一學術概念源于西方,一般認為族群是基于歷史、文化、語言等要素的共同體,主要用于研究某一民族內部或多民族地區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動。[1]客家是一個獨特的族群,客家人有著獨特的遷移歷史與人文性格,并廣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影響深遠。客家人在東南亞一帶尤其集中,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地都有大量的客家人聚居。
當前,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傳統社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文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正在消失。客家在東南亞各國本屬于少數族群,在當地政策導向和本地主流文化的雙重影響下,客家人不斷被同化,尤其是青年一代,已基本融入當地社會,客家族群的文化特性也逐漸消失,傳統的客家生活和文化習俗面臨瀕危的處境。但幸好,利用留存的影像可以重返歷史現場,探求歷史的真相,追尋族群的祖源與文化。[2]影像可以記錄一個地區或族群的生活變遷,海外客家族群的歷史不僅由文字書寫,也反映在各類影像文本中。這些影像不僅呈現客家人的社會生活,也折射出客家族群的民俗風情與精神信仰。本文即以客家影像為視角,探求這些影像如何展現一個族群的生活樣態與精神意識,影像與社會現實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與互動。
一、客家族群的遷徙歷程與集體記憶
客家人向海外播遷始于明清時期,且主要定居在東南亞一帶,經過世代的繁衍,在當地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性族群。隨著時間的流逝,早年客家人的生活日漸模糊,但借助影像的記錄可再現客家人這一艱難而悲壯的遷徙歷程。比如,一些20世紀50年代的老照片攝下了馬來西亞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客家華人被迫搬遷新村的情形,村民們曾遭受當局嚴厲的管控,除了與破舊的房屋、簡陋的基礎設施、臟亂的衛生條件為伴,還要面臨被政治軍事沖突波及的危險,這些影像真實地反映了早期馬來西亞客家華人的辛酸經歷。在1963年新加坡華人導演易水(Yi Shui)拍攝的電影《黑金》(Black Gold)中,客家人也是作為敘事的主體。影片講述了移居馬來西亞的客家人在錫礦池勞作的場景,其中的艱辛正如影片中的山歌所唱,“洗琉瑯1,洗琉瑯,趕著好陽光,走到溝尾上,白色溝尾沙,淘出黑金礦,年輕琉瑯妹,兩手洗到軟,兩腳站到酸,從早洗到晚,難求溫和暖”。[3]在原始簡陋的工作條件下,客家勞工終日頭頂烈日,赤腳涉水,彎腰勞作,受盡磨難。客家人在錫礦艱苦勞作的個體經歷在社群交往中得以互動,通過山歌對唱的形式建構了集體的記憶。
族群是以起源和文化為區隔的群體。其中,“祖源”文化與自我意識是構成族群的關鍵要素。[4]而關于族群身份,在英文中“身份”(identity)與”認同”所指同一,是一個識別象征體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與“他者”的差別。因而,族群身份也即族群認同,是一種文化的產物,不同的文化賦予個體不同的族群身份,從而成為一種構建知識、信仰和個人歸屬期待的模板[5],為個人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提供框架和基準。獨特的遷徙歷程造就了獨特的海外客家群體,并形成蘊涵豐富的族群歷史和記憶。
2009年泰國Thai PBS電視臺“亞洲精神”(Spirit of Asia)欄目曾播放4集專題片《客家人》(Hakka People),聚焦于中泰兩國客家人的歷史淵源,取景于福建、廣東、泰國等地,勾勒客家人從中國移居泰國的歷史圖景。通常,個體置身于群體的框架中進行自我表達,而群體的記憶又通過個體的實踐來實現。[6]這些客家影像真實地還原了早期客家人遠赴南洋的艱難歷程,以個人視角展現族群記憶,從而塑造了客家人這一群體意象。可見,記憶具有雙重性,既包括個體對過去經驗的詮釋,也含有群體對過去經驗的建構。[7]對于海外客家人來說,影像記錄了他們在居住國的生活和經歷,幫助他們延續并實踐與祖籍地相關的集體記憶。哈布瓦赫強調記憶的當下性,認為“往事”不是客觀事實,而是在“往事”過后,由社會框架重新建構的。[8]海外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并不是對客家傳統文化簡單的復制和回憶,而是與集體生活同步,是文化習俗與觀念不斷被實踐、創造和更新的社會過程。
二、客家傳統文化的堅守與延續
文化是受價值引導的觀念形態,源于人類對象性活動的實踐和結果[9],是規則、習俗和觀念的復雜結構,為個人提供了行為的意義,并使積極的自尊成為可能[10]。雷蒙·威廉斯曾把文化視作為一種“整體生活方式”和“情感結構”。[11]文化認同指個體對所屬文化及其文化群體形成的歸屬感和內心的承諾,從而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屬性的社會心理過程,[12]是一種個人與群體之間共同文化的確認。可見,族群身份與文化認同具有同一性,文化是族群的根本尺度,族群的存續本質上就是文化的傳承;族群成員依靠共同的社會特征承認共同體文化,以獲得群體認同,抵御自身無法抵抗的風險,滿足獲得認可和歸屬的情感需要。
文化是最深沉的情感力量,文化認同是各族群潛在的情感歸依。海外客家人對傳統禮俗的堅守與傳承體現了對族群文化的強烈認同,這點也在客家影像中得以反映。如新加坡電視劇《客家之歌》,敘述了四個出身于中國土樓的客家青年跨洋成長的故事;他們雖遷居異域,但仍保留傳統的宗教信仰和節日儀式,在家中安放牌位、點燭燃香、祭祀祖先,每逢過年掛紅燈籠、貼春聯、放鞭炮、吃年夜飯。劇中對東南亞華人延續中華傳統禮俗的大膽書寫;一是源自客家人深厚的族群觀念,二是傳達了客家人對中華文化的堅守精神。
邁向21世紀后,客家族群意象在更加豐富多元的影像介質中得到再現,順應著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認同的復興大潮。2007年馬來西亞制作了13集紀錄片《扎根》,攝制組遠赴中國福建、廣東,穿越馬來西亞的檳城、吉隆坡和馬六甲等地,記錄一系列華人在馬來西亞扎根的人生經歷。影片呈現了馬來西亞地區的“峇峇娘惹”2對中華傳統禮儀習俗的實踐,將東南亞客家人與中華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親近性表現得淋漓盡致。文化是可習得的,也是可傳承的,卻是不可遺傳的,跨越代際和語境的文化傳續與認同,依靠的是牢固的記憶;而記憶可以喚起文化聯想,產生文化心理共振。[13]共同的文化習俗是族群認同的重要源泉,且這種認同能以傳統的名義在海外客家族群中世代延續。
三、在地化發展的抗爭與調適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客家族群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都在力圖克服地理區域、政治地位、經濟條件、社會身份以及認同心理的劣勢,不斷從邊緣向中心抗爭。[14]相較于國內,身處海外的東南亞客家人面臨著更加復雜的生存環境,為了適應當地的生活,他們不得不進行不懈的抗爭與調適。早年,東南亞華人社群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占埠。”“客人開埠”,即指客家人富于開拓精神,敢于拓荒立業。一些具有史料價值的照片記錄了東南亞客家人在地化生存的圖景,最早一批“下南洋”的客家勞工為了謀生在碼頭搬運貨物、在錫礦搬運礦土,用肩挑背扛的方式販賣苦力,為當地的經濟建設做出了貢獻。這些影像再現了早期東南亞客家勞工的生存狀況,也讓我們見證了勤勞儉樸的客家人與艱苦條件抗爭的精神。
除了抗擊艱苦的生活條件,東南亞客家人也在積極地與當地的自然環境、社會文化進行交融與調適。比如馬來西亞客家人為了適應熱帶氣候,學會用“亞答”3的葉片編織穹頂,用以搭建房屋,這兼具客家特色與馬來西亞風情的“亞答屋”成為當地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客家文化與東南亞風俗在此發生了奇妙的碰撞。再如,泰國北欖坡府每年都會舉辦本頭公媽春節游神盛會,泰國客家人與其他華人一起舞龍、舞獅、畫臉譜、飾演觀音娘,以此慶祝農歷春節。這種可能源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土地神信仰的本頭公崇拜,成為泰國華人華僑特有的節日儀式,顯示東南亞客家人在宗教習俗方面的在地化過程。其他許多泰國春節禮俗,也與中華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華傳統文化從國內走向海外,在東南亞各國非主場語境下,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與影響力。弗里德曼曾說,在研究海外華人時,人類學家……必須調整他的視野,不僅從最直接的位置,而且從移民發源地的社會,從移民新安身立命的居住地,從他們融入的非華人社會等整體框架中發現其行為和思想。[15]將客家人所涉及的不同文化環境聯系起來進行整體考察的思維范式,更有助于全景化地探究客家族群的發展脈絡。東南亞客家人在地化發展的抗爭與調適,并不意味著消極的涵化,而是在海外場域下對中華文化進行因地制宜的詮釋。這種文化的延展性,也正是墨菲所強調的,“對于每個社會系統而言,需要柔韌性——隨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自身的能力——恰如需要穩定性一樣至關重要”。[16]
四、互聯網時代客家群體的文化展演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認為,“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17]顯然,文化的存在與演繹已經嵌入到互聯網構建的景觀社會中,影像擔起了文字的角色,書寫了全新的文化展演形態。展演的首要特征是視覺性,即以圖像運動和表演來吸引觀眾。[18]有別于傳統的田野攝影照片、民族志影片或官方影視劇,借助互聯網搭建的多元媒體資源和互動形式,東南亞客家族群得以從過去被敘述的文化他者,轉換為文化實踐的主體,實現了自我建構的影像文本生產與互動。在海外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上,一些地方客家社團或自媒體一起參與客家影像文本的生產與傳播,新媒體時代的網絡賦權使不同身份的創作者都能對客家傳統美食、禮儀習俗、民居建筑等文化景觀進行主位表達。
比如大伯公(Tua Pek Kong)是馬來西亞客家人民間崇拜祭祀的神明,YouTube自媒體用戶“I am Penangite 我是檳城人”漫步馬來西亞檳城最古老的海珠嶼大伯公廟,在場記錄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宗教禮俗,解說大伯公信仰的歷史來由,拍攝成vlog短片。網絡平臺上的其他客家用戶通過點贊、評論、轉發等方式進行意見表達,客家網絡用戶在“看與被看”的互動框架中不斷強化族群認同。而短視頻《這個家族的百年擂茶飯食譜》(This Family’s 100-year-old Thunder Tea Rice Recipe)則講述新加坡客家黃氏家族與擂茶飯之間的故事,擂茶飯對于黃氏家族來說,不僅是一種飲食習慣,也是一種凝聚家族精神的日常敘事。這種對擂茶飯的特殊情感體驗,超越了一個家族的界限,通過視覺文本的留存與傳播,建立起一種新的文化象征;并在與網絡觀眾的互動中共享與重現,強化“我們是一家人”的族群意象。互動使話語不再只是屏幕里的自我言說,移動設備終端與互動媒體平臺有助于東南亞客家人以主體在場的方式進入客家文化的海外場域中,超越了文化敘事的他者屏障,共同構建客家族群意象。
除了在互動媒體平臺進行零散的影像文化書寫,客家人也注重將更多影像資料進行整合呈現,各種自制的頻道、合輯集中地傳達了客家視覺文化。如新加坡YouTube自媒體用戶“ Hakka Moi”開設了“ Singapore Heritage”視頻頻道,制作有關客家傳統民俗的解說短片,講述乩童、媽祖等傳統民俗信仰。影像文本在生產中傳遞文化意義,再現客家敘事語境,族群化的文化展演以鮮明的特色吸引各方用戶的關注。
網絡社交平臺提供的點贊、收藏、關注、轉發、評論等互動功能,為海外客家網民自發進行文化表達、文化展演以及尋求文化認同提供了便利。在互聯網的客家影像相關評論中,廣大客家人對東南亞客家影像各盡溢美之詞。客家人借助一個個影像載體,建立了一個個相互重疊的客家受眾群,視覺空間的聯結也為分散在東南亞各地的客家人提供了賽博世界的歸屬感。
客家人用幾百年的時間走遍世界,在東南亞各國落地生根、建立家園。影像是認識、記錄、展現人類族群的視覺窗口,攝像之眼演繹著海外客家族群在時代長河中的生存圖景。在影像所攝取的空間里,每一個視覺符號都承載著特別的意義。一張張攝影相片上,定格了客家先祖的生活印記;一組組光影躍動的影像里,訴說著漂泊海外客家人的人生境遇。伴隨東南亞客家影像的實踐日漸增多,影像所書寫的族群意象愈發清晰。豐富的客家影像銘刻了客家族群的遷徙歷史和集體記憶,再現客家族群對中華傳統禮俗的堅守與傳承,也展現了客家族群與東南亞文化的融合與調適,反映媒介賦權時代下多元互動的文化展演。以視覺人類學的視角解讀客家影像文本,能夠體味多元文化語境中的客家族群建構,重現東南亞客家的族群意象,也能夠幫助我們在新興的視覺文化潮流中厘清客家族群歷史發展的脈絡,理解客家族群沿襲的文化傳統,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新時代意涵。
注釋:
1 洗琉瑯:是一種馬來西亞采錫的簡易方法。琉瑯,是用椰殼或木材挖成的一種狀如鐵鍋的淘錫盆。
2 峇峇娘惹:十五世紀初期定居在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一帶的華人后裔,原籍多為福建或廣東地區。峇峇娘惹是音譯,男性稱為“峇峇”,女性稱為“娘惹”。
3 亞答:馬來語音譯發音,指當地的一種水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