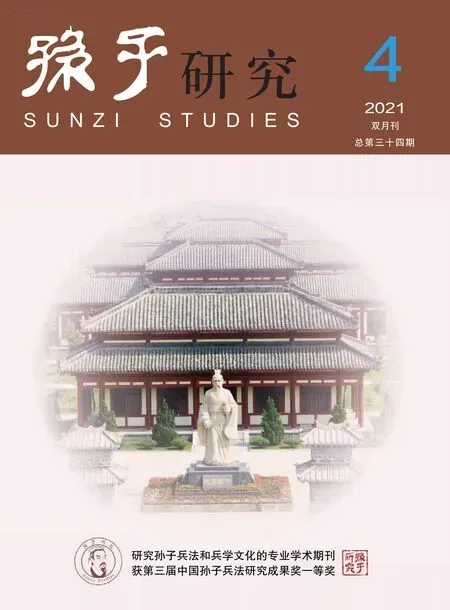袁世凱小站練兵中的軍事教育研究
張博臣
小站,位于天津東南部,海河下游南岸。因小站地區(qū)土地資源豐富,經(jīng)濟(jì)繁榮,各朝都曾在小站駐軍囤糧。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清軍屢戰(zhàn)屢敗,清政府為改變現(xiàn)狀,對舊軍隊進(jìn)行了一系列改革,開展小站練兵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huán)。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胡燏棻受命編練定武軍,1894年駐屯馬廠,1895年9月移駐小站。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11月,經(jīng)督辦軍務(wù)處奕?、奕劻親王和軍機(jī)大臣李鴻藻、翁同龢、榮祿等聯(lián)名保薦,光緒帝批準(zhǔn),袁世凱赴小站接任,編練新建陸軍。自1895年編練新建陸軍開始,至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奉命移防山東操演行軍陣法為止,袁世凱在小站以德國軍制為藍(lán)本,制訂了一套以近代陸軍的組織編制、軍官任用和培養(yǎng)制度、訓(xùn)練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糧餉制度等為內(nèi)容的建軍方案。
一、小站練兵中軍事教育的基本內(nèi)容
設(shè)立武備學(xué)堂是軍事教育正規(guī)化的實踐平臺,加強(qiáng)軍事技術(shù)訓(xùn)練是推進(jìn)軍隊近代化的主要內(nèi)容,加強(qiáng)思想教育是控制軍隊的重要手段。三者相輔相成,構(gòu)成了袁世凱小站練兵軍事教育改革的基本內(nèi)容。
(一)設(shè)立武備學(xué)堂,推進(jìn)軍事教育正規(guī)化
在小站練兵軍事教育改革的各項措施中,設(shè)立學(xué)堂是袁世凱最為重視的一件事。他在上書督辦軍務(wù)處時寫道:“章京擬呈練兵要則第四條曾有亟設(shè)學(xué)堂,造就將才,分班出洋游歷各語。到營后,查看情形,尤覺設(shè)立學(xué)堂為練兵第一要義。現(xiàn)必須趕為作養(yǎng),多多益善。”〔1〕因此袁世凱將設(shè)立學(xué)堂培養(yǎng)人才作為重要抓手來改革軍隊。
1896年新建陸軍行營兵官學(xué)堂和講武堂在小站建成,成為培養(yǎng)軍官的重要場所。學(xué)堂由朝廷每月?lián)芸盍賰砂足y作為經(jīng)費(fèi),學(xué)生可以借閱圖書,學(xué)堂統(tǒng)一配發(fā)軍服,學(xué)生除領(lǐng)取各營發(fā)給的餉銀外,還可每人每月領(lǐng)取一千文的菜錢。正如袁世凱所寫,學(xué)堂中“有教習(xí)以為師,有儀器以資其用,有圖冊以恣其瀏覽,給爾餉糈,贍爾衣食。”〔2〕
教習(xí)是學(xué)堂學(xué)生接受知識的重要來源,因此袁世凱對于中外教習(xí)的聘用十分重視。新建陸軍設(shè)有教習(xí)處,其中有洋員十三人,其中在行營兵官學(xué)堂中任職的包括德文學(xué)堂中管帶工程營洋員魏貝爾為總教習(xí),馬隊學(xué)堂中馬隊教習(xí)洋員曼德加教以測繪、武備各學(xué)。在德文學(xué)堂中,由督操營務(wù)處德文學(xué)生縣丞景啟充當(dāng)監(jiān)督,考選北洋武備優(yōu)等學(xué)生分充內(nèi)堂外場幫教習(xí)。炮隊學(xué)堂中段祺瑞充當(dāng)監(jiān)督,兼代理總教習(xí)。步隊學(xué)堂中派梁華殿充當(dāng)監(jiān)督、兼代理總教習(xí)。同時在講武堂中分派王世珍、孫鴻甲等作為教習(xí)“認(rèn)真講解,切實考詢,并飭令預(yù)為妥籌辦理在案”〔3〕。
學(xué)堂之中對于考核獎懲有著明確的規(guī)定,學(xué)生每月、每季度都要考試,每日的功課、分?jǐn)?shù)都要計入月考的分?jǐn)?shù)中。月考成績分等評定并且進(jìn)行張榜公示,優(yōu)異的學(xué)生可以領(lǐng)取賞銀,發(fā)給功牌,在周年大考后匯請褒獎。學(xué)生在季考連續(xù)三次獲得優(yōu)等,如果有空缺的哨官哨長則可以直接充任;如學(xué)生學(xué)業(yè)還未完成或年齡太小,則可以增加薪水,以示鼓勵。月度、季度的考試獎賞由袁世凱自掏白銀二百兩。袁世凱勸勉學(xué)生道:“學(xué)堂中季課有賞,大課有獎,學(xué)優(yōu)有保舉,以為進(jìn)身之階,學(xué)成有憑照,以為出身之地,爾不勤學(xué),于心何安。”〔4〕
(二)加強(qiáng)思想控制,樹立軍人價值觀念
袁世凱在教育將士時十分注重培育他們時刻忠于朝廷,忠于自己。他認(rèn)為將領(lǐng)首先要培養(yǎng)忠誠的品格,做官則應(yīng)當(dāng)稱職,受祿則應(yīng)當(dāng)圖報。他教育官弁“務(wù)當(dāng)時時以朝廷為念,事事以主將為心,絕不當(dāng)執(zhí)私見而昧公義,挾小嫌而忘大體”〔5〕。 而對于士兵來說,最重要的教育就是讓他們認(rèn)識到朝廷重餉養(yǎng)兵,自然應(yīng)當(dāng)忠于朝廷,感激天恩,為國雪恥。《勸兵歌》中就寫道:“為子當(dāng)盡孝,為臣當(dāng)盡忠。朝廷出利借國債,不惜重餉來養(yǎng)兵。一年吃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6〕士兵要時時刻刻懷著與百姓同仇之念,為朝廷雪恥之心,在出征作戰(zhàn)時奮勇殺敵。即使還未出征,為國作戰(zhàn)的意志也不能有絲毫松懈。士兵更需要敬重官長,平時應(yīng)當(dāng)“如子弟之敬父兄”,戰(zhàn)時應(yīng)當(dāng)“如手足之捍頭目”。
有勇尤貴知方。由于中國的舊有將弁多行伍出身,勇氣可嘉,但不注重知識的學(xué)習(xí),因此袁世凱勸誡將領(lǐng)應(yīng)當(dāng)有勇有謀,以勇氣來運(yùn)用謀略,以謀略來增添勇氣,二者相輔相成。提升謀略則需要將領(lǐng)勤學(xué),“如我以一介匹夫之勇欲當(dāng)其狡展不窮之術(shù),我拙彼巧,勢必難支”〔7〕。他告誡將領(lǐng)“毋師心自用,毋畏難茍安,毋一得自矜,毋淺嘗輒止,收學(xué)古有獲之益,免不學(xué)無術(shù)之訾,則庶幾矣”〔8〕。他教育士兵應(yīng)當(dāng)“以遠(yuǎn)大自期,倘或不知檢束放蕩邪僻,使同儕目為敗類,途人斥為無賴,既壞品行,尤玷軍聲。惟各懷廉恥,謹(jǐn)守法度,或推為仁義之師,或號為君子之兵,人莫不望而敬之,稱而頌之,美譽(yù)流傳,光榮匪 淺”〔9〕。同時,戰(zhàn)陣攻守是士兵的本分技藝,因此更要勤奮操練,才能有所收獲,運(yùn)用自如,可以保衛(wèi)自己,保衛(wèi)國家,博得功名富貴。
袁世凱認(rèn)為清軍之所以屢戰(zhàn)屢敗,就是因為官弁在平常不懂訓(xùn)練之法,導(dǎo)致戰(zhàn)場上不會指揮,敵軍官弁在訓(xùn)練中都親自指揮,且敵國將領(lǐng)大多學(xué)堂出身,深知教練之法,平時的訓(xùn)練課目在戰(zhàn)場上可以發(fā)揮作用,臨陣從容不迫,而我方將領(lǐng)訓(xùn)練時只將任務(wù)交予教習(xí),官弁不知如何臨陣調(diào)度,教習(xí)在作戰(zhàn)時又不領(lǐng)兵參戰(zhàn),訓(xùn)練與作戰(zhàn)脫節(jié),因此軍隊遇敵則受殲。因此,袁世凱要求將領(lǐng)在平常也要躬親教練。雖然創(chuàng)練之初,難免需要洋人教習(xí)進(jìn)行指導(dǎo),但是等各官弁“業(yè)經(jīng)從學(xué),練有成規(guī),又何可始終隱忍,樂旁貸而忘己責(zé)”〔10〕。各統(tǒng)兵將弁應(yīng)當(dāng)時刻做好臨戰(zhàn)準(zhǔn)備,牢記戰(zhàn)法戰(zhàn)陣,以免臨陣慌張失措。況且新建陸軍已經(jīng)操練多年,當(dāng)遇到征調(diào),將弁更無推諉塞責(zé)之理。
(三)加強(qiáng)軍事技術(shù)訓(xùn)練,提升軍事教育近代化水平
行營兵官學(xué)堂分為德文學(xué)堂、炮隊學(xué)堂、步隊學(xué)堂和馬隊學(xué)堂,每一學(xué)堂分別設(shè)有專門課程,力求培養(yǎng)各種專門人才。德文學(xué)堂學(xué)生學(xué)習(xí)德國語言以及武備,同時學(xué)習(xí)漢文,學(xué)成之后送往外洋留學(xué),學(xué)習(xí)西人兵法戰(zhàn)陣。炮隊學(xué)堂學(xué)生學(xué)習(xí)漢文、測算、輿圖、壘臺、炮法各學(xué)。步隊學(xué)堂學(xué)生學(xué)習(xí)行軍、兵法、測算、繪圖、槍隊攻守各法。馬隊學(xué)堂學(xué)生學(xué)習(xí)測繪、武備各學(xué)。德文學(xué)堂學(xué)生學(xué)成后可到外國留學(xué),后任各級軍官,步、馬、炮三學(xué)堂學(xué)生兩年學(xué)習(xí)結(jié)束后,可以直接充當(dāng)官弁。
袁世凱教育各級官弁要追求上進(jìn),認(rèn)真學(xué)習(xí)打靶、行軍、對敵作戰(zhàn)等各類學(xué)問,在軍中建功立業(yè),以殺敵報國。“爾諸生多少年英俊,將來成就,正未可量,今茍習(xí)于浮囂,怠于上進(jìn),即不體本督辦裁成之雅意,獨(dú)不為一生功名事業(yè)計乎?為此傳爾學(xué)生等,自是以后,務(wù)各洗心改轍,力求精進(jìn)。”〔11〕
新建陸軍中所有操練均以德國陸軍為模板,由洋人教習(xí)進(jìn)行指導(dǎo),并由官弁監(jiān)督。其中號令操法等,都按月刊發(fā)為課冊,同時考慮到軍中的兵丁多不識字,便將其中一些篇目制成押韻的歌詞,供兵丁背誦,如《偵探歌》中記錄了探知敵情所需要掌握的技巧,如何刺殺敵人哨兵,如何防地雷,選擇何處進(jìn)行偵察等內(nèi)容。《對兵歌》中則教授了駐扎營地時的隱蔽、保密、暗語等事項。《行軍歌》中記載了行軍過程中如何應(yīng)對敵人,采取何種戰(zhàn)法、隊形等。同時將需要了解的訓(xùn)練方法編成問答的形式,如一般士兵都需要掌握的《行軍規(guī)矩問答》《臨戰(zhàn)要則》,步隊中需要掌握的《槍件問答》《發(fā)槍問答》,炮隊中需要掌握的《查驗各炮法》《試炮說》等,兵丁均需熟練背誦。其后的考核、晉升官長頭目,都以這些科目為準(zhǔn)。倘若兵丁熟于操練,也有機(jī)會在北洋武備學(xué)堂中充當(dāng)教習(xí)。
二、小站練兵中軍事教育的方法特點
小站練兵作為晚清軍事變革的一次重要嘗試,既是對中國傳統(tǒng)練兵方式的繼承,也是對西方先進(jìn)軍事教育理念的吸收,呈現(xiàn)出軍事教育近代化的趨勢。
(一)采用兵儒并濟(jì)的教育方法
“在兵家與其他諸子互補(bǔ)兼容過程中,兵儒合流是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的一大特色,這種兵儒合流文化形成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兵儒合流對于中國古典軍事文化構(gòu)建的意義從主導(dǎo)方面而言是積極的。”〔12〕兵儒關(guān)系一直是中國古代、近代軍事思想中的重要內(nèi)容。在中國軍事史中,兵家與儒家逐漸呈現(xiàn)出相互融合的趨勢,戚繼光、曾國藩、胡林翼等人都是中國典型的儒將形象。袁世凱編練新建陸軍,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曾國藩、胡林翼治兵的經(jīng)驗,用儒家傳統(tǒng)的君臣父子以及忠義孝悌的觀念對官兵進(jìn)行思想教育。士兵之間應(yīng)當(dāng)相互關(guān)愛,相互幫扶;士兵要尊重、愛戴、依靠官長;將領(lǐng)之間應(yīng)當(dāng)和睦相處,對朝廷忠誠,不可為圖個人利益而損害朝廷利益。士兵的糧食、衣物、餉銀都出自百姓,因此士兵應(yīng)該愛護(hù)百姓,這也體現(xiàn)了儒家民本思想。
但由于袁世凱本人軍人政客的形象,使其對士兵的教育中體現(xiàn)出很強(qiáng)的個人依附傾向。袁世凱并沒有向?qū)⑹壳宄仃U明家國大義,以及“仁戰(zhàn)”“義戰(zhàn)”等儒家的戰(zhàn)爭觀,而是更多通過有功有賞,有勞有酬,受朝廷、統(tǒng)帥俸祿,為求博取功名,因此要盡忠賣命的方式,對部隊進(jìn)行控制,這也是新建陸軍無法成為新式軍隊、無法擔(dān)負(fù)起救亡圖存大任的最大障礙。
(二)重視學(xué)習(xí)西方軍事實踐經(jīng)驗
“照得此次軍興,不乏猛將,然戰(zhàn)無不敗,守?zé)o不失,其故何也?良以敵兵依照西法,訓(xùn)練甚精;我軍仍拘舊習(xí),不思變通。彼巧我拙,彼利我鈍,遂致莫能相抗。夫無勇固不足以御敵,而徒勇亦斷難以制勝。時至今日,講求西法,實屬刻不容緩。”〔13〕甲午戰(zhàn)后,袁世凱就向盛宣懷建議:“宜速延名教習(xí), 募學(xué)徒千人, 教兵官認(rèn)真講究西法, 另改軍制。為將來計, 此軍務(wù)決非老軍務(wù)所能得手。”〔14〕新建陸軍中的教育起初都是模仿德國軍制,主要由教習(xí)處的十三名洋員教習(xí)負(fù)責(zé)新建陸軍的教育訓(xùn)練,因為學(xué)堂課程教授西人兵法,所以學(xué)堂中洋人特別是德國教習(xí)的聘用至關(guān)重要。正如督辦軍務(wù)處奏稱:“至應(yīng)用教習(xí)洋員,最關(guān)緊要,應(yīng)由臣等咨會出使德國大臣與德國外部選商聘訂,其人數(shù)、銀數(shù),均按該道所擬合同辦理。”〔15〕其中,有參贊營務(wù)兼教練巴森斯;施壁士、伯羅恩任德操教習(xí);騎兵教習(xí)兼稽查曼德;炮隊教習(xí)祈開芬;德文教習(xí)慕興禮;魏貝爾教授禮節(jié)和軍械的稽查;高士達(dá)負(fù)責(zé)號兵樂隊教習(xí)。新建陸軍中以西法操練部隊,用西學(xué)培養(yǎng)官弁,促進(jìn)了清末軍事教育向西方的學(xué)習(xí)。在戰(zhàn)法、戰(zhàn)陣、訓(xùn)練方式、武器裝備、教育理念等多個方面有效推進(jìn)了軍事教育的近代化。
(三)注重發(fā)揮軍法軍紀(jì)的約束作用
袁世凱注重運(yùn)用嚴(yán)格的軍法、嚴(yán)明的軍紀(jì)來管理教育部隊。袁世凱制定了十八條斬律,并且規(guī)定了學(xué)堂、訓(xùn)練場的紀(jì)律。此外,袁世凱還規(guī)定了嚴(yán)格的禮節(jié)制度,對于舉手禮、舉槍禮、稍息、立正等基本的隊列動作都有了規(guī)定,促進(jìn)了新建陸軍的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同時,學(xué)堂中對學(xué)生也有著嚴(yán)格的紀(jì)律約束。行營兵官學(xué)堂中制定了22 條堂規(guī)、講武堂中制定了12 條堂規(guī)來約束學(xué)堂學(xué)生。學(xué)生在學(xué)堂中應(yīng)當(dāng)嚴(yán)格遵守紀(jì)律,其中行營兵官學(xué)堂條規(guī)第四條就規(guī)定:“學(xué)生均系本軍兵弁,應(yīng)恪守營規(guī),并將本督辦所訂訓(xùn)條律令,熟誦牢記。如有過犯,除幼童量加戒斥外,余仍按軍令責(zé)辦。”〔16〕
這些規(guī)矩涉及方方面面,在課堂紀(jì)律上,行營兵官學(xué)堂要求學(xué)生按晝夜長短規(guī)定起床時間,與操課時間相契合。每日操課內(nèi)容、時間、次數(shù)都由課單規(guī)定,學(xué)生要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集合入場,不得延誤。在課堂授課時應(yīng)當(dāng)端坐靜聽,有不能理解的問題,應(yīng)當(dāng)前去教習(xí)處詢問,不得隨意發(fā)言,不得四處走動,在休息的時候方可喝茶告便。講武堂中則要求“各官長在講堂內(nèi),不準(zhǔn)隨便亂會,亦按兩翼分坐兩邊,再按各營,前后左右各隊,左中右各哨,挨次列坐”〔17〕。各項條規(guī)的制定讓小站練兵中的軍事教育向近代化、正規(guī)化轉(zhuǎn)變。
三、小站練兵中軍事教育的意義
小站練兵是晚清軍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其培養(yǎng)了一批軍事人才,加速了軍事教育近代化的過程,但也無法擺脫地主階級軍隊的局限性,仍然無法發(fā)揮推動歷史發(fā)展的作用。
(一)培養(yǎng)、造就了一批近代軍事人才
“曰練兵練兵何先,曰儲將儲將何道,曰興學(xué)于蒞軍之初即創(chuàng)設(shè)德文步炮馬隊各學(xué)堂,其為國家培人才,為天下開風(fēng) 氣。”〔18〕袁世凱始終把軍事人才培養(yǎng)放在首位,并一再勸誡官弁學(xué)生:“思中邦之弱非由于我武不揚(yáng)乎?則當(dāng)知恥。外國之強(qiáng)非由于彼學(xué)之日盛乎?則當(dāng)知奮。知恥知奮方能成才,能成才方能致用,能致用方能建功立業(yè),雪國恥,紓敵患。”〔19〕袁世凱十分重視讓軍官接受學(xué)堂教育,對學(xué)堂學(xué)生進(jìn)行專門教育培養(yǎng),頗有成效。1898年 榮祿奏稱:“ (袁世凱)輪調(diào)各生, 親加考驗, 所學(xué)兵法、戰(zhàn)法、算學(xué)、測繪、溝壘、槍學(xué)、炮學(xué)、操法及德國語言文字, 均能洞悉窾要,日臻精熟。”〔20〕同時在選拔軍官、教習(xí)、監(jiān)督時,大量任用武備學(xué)堂出身的學(xué)生,參與教材編寫,操練考核,以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等人為代表的武備生不僅在新建陸軍中擔(dān)任要職,日后更是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中的重要人物。
(二)促進(jìn)了軍事教育的近代化
小站練兵中,袁世凱將改革教育作為改革清末軍隊的重要手段。他認(rèn)為清軍與列強(qiáng)存在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朝缺乏懂得近代戰(zhàn)爭的人才。其他各國將弁重視武功韜略,大多學(xué)成于學(xué)堂,專習(xí)兵法,兼學(xué)繪圖、測算、軍械等技藝,以備戰(zhàn)爭之需。在軍隊中擔(dān)任軍官后再進(jìn)行輪訓(xùn),重新回到學(xué)堂學(xué)習(xí),讓軍官的學(xué)問與實戰(zhàn)經(jīng)驗并進(jìn),提高部隊?wèi)?zhàn)斗力。而清朝將弁多為行伍出身,缺乏系統(tǒng)的近代軍事知識教育,往往只憑經(jīng)驗行事,恪守古法,而又驕傲自滿,難以適應(yīng)近代戰(zhàn)場。因此,袁世凱大量吸收西方近代軍事教育經(jīng)驗,培養(yǎng)德文學(xué)生學(xué)習(xí)西方語言文字,在學(xué)堂設(shè)置上大量參考德國陸軍學(xué)堂,制定嚴(yán)格的規(guī)章制度,聘用西人教習(xí)來引入德國陸軍操練方法,教育官弁分科目掌握西方練兵方法,進(jìn)而指導(dǎo)士卒,使部隊在裝備運(yùn)用、戰(zhàn)陣隊形的訓(xùn)練上有章可循,讓將士具備行伍經(jīng)驗的同時掌握系統(tǒng)的理論知識,向近代軍事作戰(zhàn)需要靠攏。小站練兵中的學(xué)堂設(shè)置、操法戰(zhàn)陣、規(guī)章制度等成為清末軍事教育改革的經(jīng)驗,為之后的軍事教育所借鑒。
(三)無法擺脫舊式地主階級軍隊的局限性
新建陸軍中,無論在教育官弁還是士兵時,都堅持“道必師古”〔21〕的精神教育,始終以灌輸封建思想為指導(dǎo),用“人之生死皆由命數(shù)”〔22〕、“如再不為國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23〕等思想來麻痹士兵。在課本中多以古喻今,綱常為本,學(xué)生在學(xué)堂中仍需抄錄經(jīng)史,抄完功課后,呈請漢教習(xí)圈點句讀,講解文義。在價值觀上,袁世凱對于士兵的教育是在營中遵規(guī)守紀(jì)、勤奮訓(xùn)練,自然就能升為頭目。而官弁則是可以得到主帥賞識,謀求功名,仕途升遷,加官晉爵,通過個人掌握士卒前途命運(yùn)(個人效忠)來使部隊置于自身控制之下。這也就讓小站練兵中的班底成為袁世凱日后進(jìn)行封建統(tǒng)治的左膀右臂,使新建陸軍在性質(zhì)上仍然無法脫離封建個人依附式的地主武裝的形式,無法成為為國家、民族根本利益而奮斗的武裝力量,這也是新建陸軍教育中最大的局限性。
【注釋】
〔1〕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一,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68、69 頁。
〔2〕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4 頁。
〔3〕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二,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175 頁。
〔4〕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4 頁。
〔5〕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23 頁。
〔6〕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四,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310 頁。
〔7〕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6 頁。
〔8〕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7 頁。
〔9〕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0 頁。
〔10〕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8 頁。
〔11〕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四,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367 頁。
〔12〕郗孟祥:《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構(gòu)成要素及特征探析》,《南京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2004年第1 期。
〔13〕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四,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301 頁。
〔14〕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上冊,第326 頁。
〔15〕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一,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67 頁。
〔16〕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一,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73 頁。
〔17〕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二,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175 頁。
〔18〕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4 頁。
〔19〕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4 頁。
〔20〕朱有 :《中國近代學(xué)制史料》第1 輯(上), 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541 頁。
〔21〕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2 頁。
〔22〕袁世凱:《訓(xùn)練操法說析圖說》卷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第10 頁。
〔23〕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四,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第31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