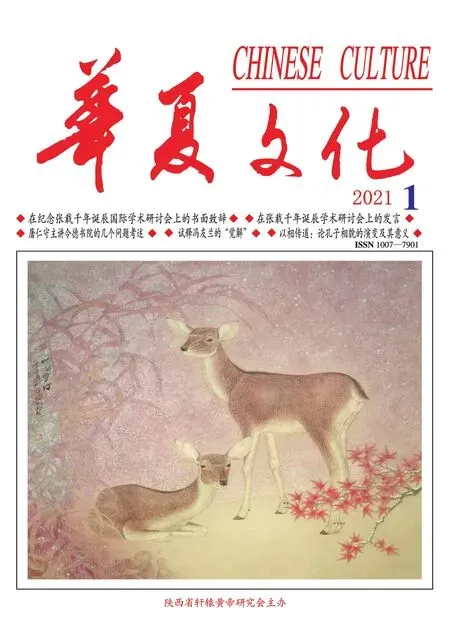以情著理 以理馭情
——略論斯賓諾莎《倫理學》的情理關系
□黃 熙
當情感與理性發生沖突時,何者為第一決定因素?情理之間復雜的關系困擾著古今中外諸多哲學家。無論是西方哲學還是中國哲學,情理關系都是一個有趣而又眾說紛紜的難題。作為西方近代哲學重要的理性主義者——斯賓諾莎,因不滿笛卡爾人心對情感的絕對控制一說,故他在《倫理學》中對情感的起源與基礎做了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論證,“這一自然主義的情感理論,無疑是給近年‘情感轉向’饋贈了一個科學主義的傳統”(陸揚:《“情感轉向”的理論資源》,《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第34頁)。在此過程中,斯賓諾莎進一步提出了理性對情感的作用。關于斯賓諾莎情理關系的論述,學界已有諸多成果,但是他們都忽略了斯賓諾莎情理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斯賓諾莎在此問題上的困境與不足。應該指出的是,情為理之基礎,理為情之主導,這是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一書中著重構建的情理關系。然而,“他對主要觀點、主要問題每每只是一瞥即過,講的不夠充分”([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98頁)。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對情理關系的論述,分析斯賓諾莎對情理關系論述的不足之處,并進一步對情理關系的問題做出一些思考,以期未來有更進一步的研究。
一、以情著理:情為人之本
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一書中,從人之本性出發,論人的情感就是論人,這也是該書取名為《倫理學》的原因。在《倫理學》中,作者認為各種情緒都是人之本性(有正面的情緒亦有負面的情緒,人常常被情緒所控制,所左右)的表現。這種情既是人之本性,又是理性的基礎。斯賓諾莎從經驗的角度,對情感下了定義:“我把情感理解為身體的感觸。”([荷蘭]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98頁)也就是說,情感來自人的官能器官(也就是斯賓諾莎所說的身體)對實體的感知(知覺、想象與概念等)。他進一步指出:“人心不僅知覺人身的情狀,并且知覺這些情狀的觀念。”(斯賓諾莎:《倫理學》,第68頁)對外界接觸后從而產生對該物該事的觀念,“觀念總是在先的,假如一個人有了一個觀念,則將必隨之具有其余的樣式”(斯賓諾莎:《倫理學》,第54頁),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也就是觀念不斷豐富與形成的進程。這便是人之情感的基礎。
人類最初都受到這樣的情感影響,并且情感指導著人類的行為,斯賓諾莎稱之為心靈的奴役,便在于此。“所以每一個人都是依據他的情感來判斷或估量,什么是善,什么是惡”(斯賓諾莎:《倫理學》,第130頁)。與中國傳統哲學不同的是,在斯賓諾莎那里,情是心靈的基礎,心靈受情的控制,中國哲學則更為強調心為體,情為用,心為未發,情為已發。在情感的作用下,“便形成善惡、條理紊亂、冷熱、美丑等觀念;又因為有了人是自由的這個成見,便產生了如褒與貶,功與罪等觀念”(斯賓諾莎:《倫理學》,第41頁)等。可以說,斯賓諾莎論人的基礎便在情上,情為基礎。在此基礎上,“任何事物并不是我們追求它、愿望它、尋求它或欲求它,因為我們以為它是好的,而是,正與此相反,我們判定某種東西是好的,因為我們追求它、愿望它、尋求它、欲求它”(斯賓諾莎:《倫理學》,第107頁)。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斯賓諾莎對善與德性的建立也基于情所產生的愛與恨的兩種快樂與痛苦的情緒之上,“愛不是別的,乃是一個外在的原因的觀念所伴隨著的快樂”(斯賓諾莎:《倫理學》,第110頁),“仁愛不是別的,只是由同情引起的欲望”(斯賓諾莎:《倫理學》,第121頁),“所以善是指一切的快樂,和一切足以增進快樂的東西而言,特別是指能夠滿足愿望的任何東西而言”(斯賓諾莎:《倫理學》,第130頁),由此可見,說情是斯賓諾莎論人、論理性以及構建倫理哲學的起點,當不為過。
二、以理馭情:理性充塞情本體
基于情感的基礎上,斯賓諾莎認識到:“當人心在自然界的共同秩序下認識事物時,則人心對于它自身,它自己的身體,以及外界物體皆無正確知識,但僅有混淆的片段的知識。因為人心除知覺身體情狀的觀念外,不能認識其自身。”(斯賓諾莎:《倫理學》,第72頁)正因如此,人心需要理性來彌補。斯賓諾莎進一步強調需要用理性對情感進行駕馭,“絕對遵循德性而行,在我們看來,不是別的,即是在尋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礎上,以理性為指導,而行動、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斯賓諾莎:《倫理學》,第187頁)。他認為:“理性的本性在于某種永恒的形式下來考察事物。”(斯賓諾莎:《倫理學》,第84頁)意即僅靠情感作為動力因來指導人的行為便會存在不穩定性,因各人情感的不同,因人而異,所以以情為主導便會存在標準不一的問題,無法使其成為普遍的價值。“理性所真正要求的,在于每個人都愛他自己,都尋求自己的利益——尋求對自己真正有利益的東西,并且人人都力求一切足以引導人達到較大圓滿性的東西。”(斯賓諾莎:《倫理學》,第183頁)因此,只有以理性為指導,才能夠建立起普遍的滿足大多數人存在的共同觀念。
斯賓諾莎進一步指出:“人之所以被欺騙由于他們自以為他們是自由的,而唯一使他們作如是想的原因,即由于他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行動,而不知道決定這些行為的原因。”(斯賓諾莎:《倫理學》,第75頁)只有知道決定這些行為的原因,才能夠坦然而不惑,才算是真正意義的自由。正因為如此,只有對自身的情感加以理解與考察后,才能夠實現心靈的解放,不受情欲的控制。他認為:“心靈具有不正確的觀念愈多,則它便愈受情欲的支配,反之,心靈具有正確的觀念愈多,則它便愈能自主。”(斯賓諾莎:《倫理學》,第99頁)正確的觀念,從某一種程度上便是受理性而影響的觀念,也就是理性充塞在情之中形成的觀念。
斯賓諾莎強調以理馭情,這一點頗似中國宋明理學中的程朱一系。李澤厚認為:“朱學在強調人用理性觀念主宰感情的自制力、意志力等人性能力的培育上,王學在培育同情心、共同感的仁民愛物的人性情感上,各有千秋。”(李澤厚:《人類學歷史本體論》,青島:青島出版社,2016年5月,第143頁)在宋明理學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中,對情理關系的論述也著重強調“天理”對人心、對人的情感的主宰與引導作用,整體上表現出以理馭情的傾向。而以陽明為代表的“心學”,則進一步將人的內在情感提升起來,以此直做本體,進一步將情感與理性統一起來,“實際上都是講道德情感而具有理性特征”(蒙培元:《情感與理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43頁)。然而斯賓諾莎并未止步于此。他不僅強調以理馭情,而且還含有回歸到情上做主導的趨勢,有學者指出:“斯賓諾莎試圖以‘正確觀念’(adequate idea)對形而下的心物關系進行邏輯彌補,從而構建人類‘主動情感’(action)的理性根基。”(崔露什:《斯賓諾莎情感理論中“觀念”的作用及其動態結構》,《求索》,2015年第12期,第85頁)這種主動的情感實際上已經含有由理性返回情感,以情為本指導人的行為的趨勢。然而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的論述并未將此明確提出。
三、評價
在《倫理學》一書中,斯賓諾莎渴望建立以理馭情的理性哲學——理性充斥人心,人心征服情感,這是斯賓諾莎哲學的主旨。他講以理馭情,即是基于情之基礎判斷上,“唯有純出于理性的命令的行為,我們才確實知道是善的行為”(斯賓諾莎:《倫理學》,第208頁)。他又強調用理性充實情感,“除了理智的愛以外,沒有別種的愛是永恒的”(斯賓諾莎:《倫理學》,第260頁)。他意識到只有充實了理性的情感,才可以產生正確的觀念。葉秀山指出,對斯賓諾莎哲學的重點把握也在于此,即“把握這個‘重中之重’,‘重點’在于,這時的‘情感’已由‘被動’轉化為‘主動’”(葉秀山:《斯賓諾莎哲學的歷史意義——再讀〈倫理學〉》,《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第9頁)。而“心靈卻非武力所能征服,但可被愛或德量所征服”(斯賓諾莎:《倫理學》,第230頁),也只有如此,才能夠建立起人類世界的倫理法則和規范。
盡管斯賓諾莎強調以理馭情,但是他所謂克制情感的良藥,即“在我們能力范圍內去尋求克制感情的藥劑,除了力求對于情感加以真正理解外,我們實在想不出更良好的藥劑了”(斯賓諾莎:《倫理學》,第242頁),這便是斯賓諾莎的辦法。這樣的方法基于情之上,最終回到利用身體的官能知覺以及知識對情感加以理解,他希望以此形成理性判斷。然而究竟如何是理性的情感,斯賓諾莎的論述并不明晰。此外,在對待情感的問題上,斯賓諾莎也存在著一些模糊不清的態度。同時他又意識到“法律的有效施行,不能依靠理性,而須憑借刑罰,因為理性不能克制情感”(斯賓諾莎:《倫理學》,第200頁)。在情與理之間,斯賓諾莎最終難以分辨出究竟誰為第一原則。由此可以看出,斯賓諾莎在情理關系上也有其困境之所在。造成這樣困境的出現,即在于“斯賓諾莎的哲學里,精神性的個體卻只是一個樣式,一種偶性,而不是一個實體性的東西”(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第130頁),實際上也在于他以情著理,由情出發,以理馭情,卻最終未能返回情本體,將情與理的關系在此處割裂開來,最終成為互不統攝的兩個主宰。
所謂情本,不僅僅指情感一意,“在情當中,既有形而上之‘道’的涵義(‘情性’),也有形而下之‘器’的意義(‘情實’),還有居中并上下聯通的意蘊(‘情感’)‘情性’、‘情實’與‘情感’恰是三位一體的從而形成三角架構”(劉悅笛:《“情性”、“情實”和“情感”——中國儒家“情本哲學”的基本面向》,《社會科學家》,2018年第2期,第12頁)。“情——理——情”才是正確的發展階段,人以情為端,為始,進一步需要以理馭情,當所有理性充塞心中之時,自然而發便是以情為本,始于情,終于情,方為人之本。第一階段之情即人之身體感觸外界而產生的情感、情緒等,這種出于本能的欲望,同樣也支配與控制著人的行為。然而,作為人類社會的共同體,需要創立普遍的適合所有人的存在價值,因此,唯有以理馭情,用理性才能夠保證彼此的權益,這種理性的態度與灌注,即是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以及受人類社會的文化和教育影響而來的。
李澤厚認為“人的‘本體’不是理性而是情理交融的感性。這正是當年棄‘實踐理性’而用‘實用理性’一詞的重要原因”(李澤厚:《人類學歷史本體論》,青島:青島出版社,2016年5月,第70頁),因此李澤厚強調情本體,強調實用理性,從而提出了“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參見李澤厚:《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第24頁)的說法。李澤厚的觀點正好可以與斯賓諾莎的情理關系進行互補。斯賓諾莎的一大不足之處即在于未能將充塞理性之情作為情本體,以這樣的“情”作為指導人類行為的最高原則和最終原因。當理性充塞情感之中,再發動情時,便是充滿理性的情本體,此時之情即是既符合人類自然本性,又符合人類社會普遍價值的行為背后之真理。“因為人雖無知,究亦是人。對在困難中的人,他們也能給予出于人情的助力,須知此種人情內的助力,是人所有的最有價值的助力。”(斯賓諾莎:《倫理學》,第224頁)由此,“將使心靈充滿著由對關于德性的正確知識而引起的愉
快”(斯賓諾莎:《倫理學》,第248頁),使人不再空虛與毫無支點和方向的生存。中國宋明理學所構建的道德哲學,著重論述的問題也在于此。對情理關系的探討,也成為宋明理學乃至中國古代儒學探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斯賓諾莎繼承了西方哲學以理馭情的傳統,對情感的起源和基礎做了細致入微的考察與探究,并對理性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論述,他對情理關系的論述也影響了后來諸多哲學家。在情理關系的論述上,休謨恰恰與斯賓諾莎相反。休謨指出:“理性是并且也應該是情感的奴隸,除了服務和服從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職務。”([英]休謨:《人性論》,關文運譯、鄭之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4月,第449頁)休謨將情視為比理更為重要的基礎,這一點恰好對斯賓諾莎做出了很好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