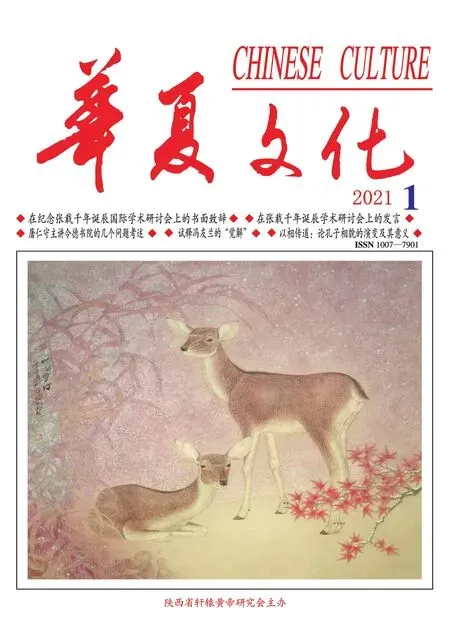試釋馮友蘭的“覺解”
□陸建華
馮友蘭哲學的精華在于其所提出的人生境界說。在討論人生境界時,馮友蘭引入“覺解”這個概念,認為人生境界決定于“覺解”,人生境界的高低、不同決定于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解”程度。這說明馮友蘭人生境界的關鍵點在“覺解”,不過,他沒有給“覺解”下明確的定義,而是分別解讀“覺”和“解”:“覺是自覺”,“解是了解”(《新原人》)。這表明,“覺解”在馮友蘭那里似乎不是一個復合詞、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兩個單純詞的簡單組合、是兩個概念。也就是說,在馮友蘭那里,“覺解”就是“覺”“解”,或者說“覺、解”。不過,馮友蘭顯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而是將其作為復合詞、作為一個概念加以運用。不然的話,馮友蘭首先就要處理“覺”和“解”的關系,論證“覺”和“解”的一致性,論證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和“解”始終是處于同一水平。要不然,如果出現“覺”“解”不一致,從“覺”來看,人處于某種人生境界;從“解”來看,人卻處于另一種人生境界,那么,其人生境界理論就會變得支離破碎、無法自圓其說。
雖然馮友蘭說:“解是了解,我們于上文已有詳說。覺是自覺。人作某事,了解某事是怎樣一回事,此是了解,此是解;他于作某事時,自覺其是作某事,此是自覺,此是覺。”“了解必依概念,自覺是否必依概念?于此我們說:了解是一種活動,自覺是一種心理狀態,它只是一種心理狀態,所以并不依概念。” (《新原人》)這里試圖區分“覺”和“解”,認為“解”是對事、對物的理性認知,在這種理性認知過程中“必依概念”作為其認知工具、手段,而“覺”是一種心理活動、一種對自己外在行為的內心體悟,在這種心理活動、內心感悟過程中“不依概念”,也即不需要概念作為其感悟的工具、手段。但是,馮友蘭這種“覺”和“解”的分別只是單純就“覺”和“解”這兩個概念而言的,在論及對“事”、對“物”的“覺”“解”時似乎這種分別是有效的,在論及對宇宙人生的“覺”“解”時,這種分別又是沒有意義的。馮友蘭在討論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解”時,其實就是在討論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或“解”而已。這么說,“覺”“解”在人對于事、物“覺”、“解”的領域是有區別的,在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解”領域是沒有區別的,“覺”和“解”是可以混用的。這么說,馮友蘭關于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解”就是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或“解”。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解”被表述為“覺”或“解”,“覺”“解”“覺解”三者似乎名異實同,馮友蘭的意圖可能是想為“覺解”這種心理體驗、心理感悟既染上非理性的色彩,又披上理性的外衣。
由于人對于宇宙人生“覺解”程度的高低、不同決定人生境界的高低、不同,從人生境界的維度看,也就是決定人的差異、不同。據此推論,如果人對于宇宙人生沒有“覺解”就意味這樣的人沒有人生境界,從人生境界的維度看這樣的人就不能成為人。好在問題沒有這么絕對,在馮友蘭看來,所有的人都是有“覺解”的,人與人的差異、不同不在于有無“覺解”而在于“覺解”程度的高低。基于此,馮友蘭從“覺解”的維度論述人的本質或者說人與禽獸的質的區別。他說:“若問:人是怎樣一種東西?我們可以說:人是有覺解底東西,或有較高程度底覺解底東西。若問:人生是怎樣一回事?我們可以說,人生是有覺解底生活,或有較高程度底覺解底生活。這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人生之所以異于別底動物的生活者。” (《新原人》)這是說,從“覺解”的維度看,人是有“覺解”的存在,而且是唯一有“覺解”的存在,而禽獸是沒有“覺解”的存在,因此,“覺解”是人之為人的本質之所在,當然也是人與禽獸本質區別之所在。所以, 馮友蘭說:“有覺解不僅是人生的最特出顯著底性質,亦且是人生的最重要底性質。” (《新原人》)
為什么人有“覺解”而其他生命存在沒有“覺解”?馮友蘭解釋道:“人之所以能有覺解,因為人是有心底”“在宇宙間,有心底雖不只人,而只有人的心的知覺靈明的程度是最高底”“有覺解是人的心的特異之處,所以我們專就知覺靈明說心” (《新原人》)。這是說,其原因在于人不僅有“心”,而且人之“心”具有最高的“知覺靈明”之特征。這么說,人的本質、人與禽獸之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之“知覺靈明”。
由“心”而發而有“覺解”,有“覺解”而有人之為人的特質。馮友蘭從人之心靈的維度解釋人之“覺解”的由來,并以“覺解”界定人與禽獸之別,顯然受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的啟發。在馮友蘭看來,孟子的人心能“思”,相當于人心“有覺解”;孟子的人心是“天之所與我者”,是人所獨有的,相當于以人“心”界定人,而以人“心”界定人,也就是以人“心”之特質“思”來界定人、以“覺解”來界定人。
由上可知,提出“覺解”概念,又在人對宇宙人生的“覺解”方面把“覺解”解讀為“覺”或“解”。提出“覺解”概念,本是為了討論人生境界問題,又以“覺解”為依據討論人與禽獸之別,并為此而引入“心”。這是馮友蘭“覺解”的基本內容與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