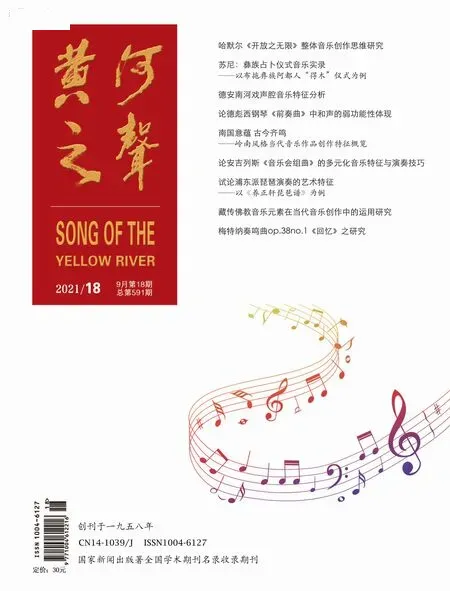羅忠镕古詩詞藝術歌曲《秋之歌》的藝術特征
劉 璇
引 言
藝術歌曲是一種源于西方浪漫主義音樂早期的聲樂體裁,由舒伯特、舒曼等人在德奧民間歌曲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而來。藝術歌曲不同于歌劇、合唱以及一般的抒情歌曲,它以有著深邃思想和哲學意蘊的詩歌為歌詞,聲樂旋律與鋼琴伴奏建立在統一構思的基礎上,因此屬于一種“立體思維”的聲樂體裁形式。在20世紀上半葉,黃自、青主、譚小麟等作曲家以我國古詩詞作為歌詞,結合西方作曲技法創作了一批具有中國傳統文化韻味的藝術歌曲,體現出了“以中為體,中西結合”的聲樂創作模式,從而對古詩詞藝術歌曲這一聲樂體裁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文以當代著名作曲家羅忠镕創作的《秋之歌》為例,著重從音樂特征和演唱分析的角度進行探討,以期能夠從此部作品的分析中一觀當代古詩詞藝術歌曲的創作和演唱特點。
一、羅忠镕與古詩詞藝術歌曲《秋之歌》
羅忠镕是我國當代著名作曲家、音樂教育家,從上世紀四十年代起在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學習小提琴,兼學作曲,從四十年代中期開始,在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師從譚小麟、丁善德學習作曲理論技術。在其數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先后創作了為數眾多的交響曲、室內樂、聲樂作品,其中《第一交響曲》、弦樂隊《弦樂三章》、民族管弦樂《春江花月夜》等經演不衰,成為我國當代音樂史上的經典之作。作為教育家,羅忠镕長期在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擔任作曲教授,培養了諸多活躍于當代樂壇的著名作曲家,并編著、翻譯了《作曲初步練習》、《傳統和聲學》(興德米特作品)等作曲教材,至今仍作為音樂學院作曲專業教材廣泛沿用。從羅忠镕的音樂創作特征看,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立足傳統,面向現代。羅忠镕的作品以中國傳統音樂題材內容居多,但是在創作技法上并不拘泥于傳統音樂元素。如古琴與室內樂《琴韻》、《云南民歌六首》等,這些作品的主題并不是直接引用原來的旋律素材,而是在原素材的基礎上重新進行組合、排列,呈現出了時代化的氣息,但是在音響風格上則完全是中國化的;二是銳意開拓,創新技法。羅忠镕在對西方現代音樂創作技法的借鑒的同時,創新式的將中國五聲音階和表現主義樂派的十二音體系相融合,創造出了在作曲界有著高度影響力的“五聲性十二音集合”理論體系,在此體系基礎上所創作出的交響音詩《暗香》、藝術歌曲《涉江采芙蓉》等作品對當代中國作曲技法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
古詩詞藝術歌曲《秋之歌》以晚唐詩人杜牧的三首七言絕句為歌詞,分別為《山行》、《南陵道中》、《寄揚州韓綽判官》。作曲家將三首詩歌合為一體構成了一部聲樂套曲作品,標題命名為“秋之歌”,實際上抒發了詩人在同一季節所表現出的不同情感。《山行》是一首歌頌秋景制作,作品以深秋山林為背景,表現了行人迷戀自然之景、沉浸其中的心情,并通過對比的手法贊頌了楓葉之美、林間之聲。此詩在行文上采用了由遠及近、由外而內的景、情交融創作技法,自然之美和人性的關懷融為一體,具有虛實相生的美學意境;《南陵道中》創作于杜牧在宣州擔任團練判官期間。在詩的開始處,以南陵地界的湖水入境,營造出一幅水波不興的畫面,進而將視角引申到風、云上面,用空間轉換的手法襯托出秋高氣爽之感。第三句借景抒懷,觀照自身,頓生客居他鄉孤獨之情,第四句則采用聯想的方式想起心中所思念的愛人。此詩旨在通過對秋色的描繪,來襯托心中的孤獨之情,但是最后一句筆鋒一轉,以“紅袖”二字沖淡了心中的霧霾,具有浪漫主義幻想的情調。《寄揚州韓綽判官》是詩人的一首憶友之作,以揚州美景作為描述對象,贊美了友人寄情山水的志向,同時也表達了對揚州生活的懷念。全詩充滿了沁人心脾的意境,雖然在寫秋,但是絲毫沒有悲秋之意。
從以上對杜牧三首寫秋的詩歌作品看,它們的共性特征在于以秋色為題材,在對形象的刻畫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在情感背景上卻不盡相同,因此作曲家在選擇這三首作品作為歌詞時,也正是考慮到了三首詩歌在情感表達上的個性特點,以三首作品組成“套曲”,體現出了題材與情感上的統一與對比特點,這種套曲結構也賦予了作品具有描繪性、抒情性和戲劇性的特征。
二、古詩詞歌曲《秋之歌》的音樂特征
(一)調式音階
對不同音樂作品在風格方面的探究,調式音階的運用是最為明顯的風格辨別途徑。中國音樂體系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三大音樂體系之一,除了它具有獨特的音樂審美特征和風格傳統外,在音樂要素方面最為突出的標志就是五聲音階的運用。所謂五聲音階,又稱為為五聲性音階,它以中國傳統宮調理論為基礎,注重對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的運用,與此同時,在歷史進程中,由于與多民族民間音樂的融合,又形成了以五聲音階為基礎的六聲音階、七聲音階。在套曲《秋之歌》中,《山行》和《南陵道中》采用了五聲音階體系,分別為降B徵調式和降E宮調式,《寄揚州韓綽判官》為B角七聲雅樂調式。從調式音階的選用上看,作曲家繼承了中國傳統音樂中宮調理論的運用方法,著重在音階的運用上體現出對傳統音樂元素的繼承。
(二)節拍特征
古詩詞由于遵循了嚴格的格式和韻律規范,所以在創作上有著較強的律動性,加之漢語言口語表達注重輕重抑揚的律動效果和情感表現效果,所以在節拍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秋之歌》中,交替拍子、混合拍子的運用較為突出,這也是作曲家在古詩詞藝術歌曲方面的獨創性。《山行》一曲采用了二拍子和三拍子的交替拍子,《南陵道中》采用了二拍子、三拍子、五拍子的混合拍子,《寄揚州韓綽判官》在記譜上雖為二拍子,但是由于采用了弱起節拍,從重音的變化和規律看,則具有二拍子、四拍子的交替特征。因此從套曲的節拍特點看,主要是以單拍子作為音樂的基礎拍子類型,通過交替、混合、變化手法使音樂的進行服從于歌詞的韻律和情感表達的需求。如在《山行》一曲中,作曲家就運用了傳統詩樂吟誦調的風格,使每一個字在旋律的緩吟慢誦中表達出了內心對山間秋景的贊美,雖然節拍變換頻繁,但是在情感的表達上卻追求到了一種極致。
(三)旋律特征
在20世紀上半葉黃自、趙元任等人的中國藝術歌曲的創作中,就十分深刻地注意到了旋律進行和語言聲調之間的密切關系,并有意識、有目的的將語言聲調融入到了旋律的進行中,以此而彰顯出中國風格藝術歌曲旋律表現的個性化。在當代古詩詞藝術歌曲的創作中也基本上沿用了這一傳統,于是體現出了獨特的古風韻味。在《秋之歌》中,其旋律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依據字調書寫旋律。如《南陵道中》的第一樂句“南嶺水面漫悠悠”,在旋法上就基于歌詞中的字調,其中“水”為上聲調,故在旋律進行上運用從降E-G的大三度音程上行,“面”為去聲字,其字調呈現出下行趨勢,所以緊接著G音之后采用了下行大二度的進行;“悠悠”為兩個疊字,根據字調則采用了同音反復的進行,由此可以看出,作曲家在旋律的寫作上參考了字調的走向問題;二是根據詞意形象構建旋律。古詩詞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強調對文學形象精雕細刻,并將情感內蘊其中,從而形成形象與情感相交織的意象。如《寄揚州韓綽判官》中的第一樂句“青山隱隱水迢迢”,其中在“水迢迢”一詞的旋律構建上,作曲家運用了小三度、小二度、大二度三種音程的級進連接,細入的刻畫出“水”的形象,并在流暢的旋律進行中表現出了綠水蕩漾的意境。
(四)鋼琴伴奏特征
聲樂旋律與鋼琴伴奏同時寫就是藝術歌曲在創作過程中最顯著的特征,鋼琴伴奏不僅能夠有效地對聲樂旋律進行襯托,還有營造音樂意境、深化情感表達的作用。從《秋之歌》鋼琴伴奏的特征看,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每一首歌曲都有相當篇幅的鋼琴部分用以明確標題。如在《山行》中,前奏部分由鋼琴演奏出連續相同的由琶音構成的單旋律線條,以此表現出曲徑通幽的山路形象,并在同音反復的三和弦連接上表現出主人公閑適的心情,由此為聲樂旋律的出現進行鋪墊。二是注重運用各種織體的變化來襯托出歌詞所要表達的情感。在《南陵道中》一曲中,作曲家運用四度雙音的級進、模進和五、八度和弦連接使情感的表達此起彼伏,層層推進,有利于體現出歌詞應有的意境,同時也具有民族和聲的特征。
三、古詩詞歌曲《秋之歌》的演唱解析
(一)氣息的運用
氣息是歌唱的基礎,合理地運用換氣方法和有效地控制呼吸,對音色、音準和情感的表達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演唱古詩詞藝術歌曲時,為了能夠表現出應有的音樂形象和意境,需要從氣息技巧的運用上進行布局化的思考。由于古詩詞在格律上十分的規范,當加入旋律時,又在節奏、節拍上發生諸多的變化,所以在分析作品時,找準句逗位置便能夠把握好換氣點。以《寄揚州韓綽判官》第一樂句為例,此樂句有兩個句逗,其中“青山隱隱”為一個分句,落音為四分音符的E,此處為第一個換氣點,需要在四分音符的E音上留出半拍的換氣時值,根據后面第二分句節奏緊湊的特點,應當運用急吸緩呼的方法,吸氣時應當盡量吸入的飽滿一些,在唱第二分句時則需要根據腹部肌肉和橫膈膜的控制將先漸強、后漸弱的力度表現出了,用氣息控制體現出力度上的層次變化,這樣便能夠將詩人內心的矛盾得到充分地展現。
(二)咬字、吐字的處理
在演唱古詩詞藝術歌曲的過程中,應當以中國傳統聲樂中的字腔要求為規范,即在行腔的過程中注重咬字和吐字的運用,以此達到依字行腔、字正腔圓的表現的音響效果。以《南陵道中》“南陵水面漫悠悠”為例,“面”字的發音為“mian”,其字頭為“m”,咬字需要做到輕、巧為準,在歸韻的過程中應當根據旋律音程的進行合理的進行安排,從旋律上,這個字采用了一字雙音的旋律,建立在從G—F的大二度下行上,這種下行音程與“面”的字調相吻合,因此在行腔的處理上需要加入一個下行的滑腔,通過氣息的控制調整音準,才有利于歸韻的完整。在最后“悠”字的表現上,這個字由于建立在一個全音符上,演唱時應當注意口型的保持,使雙元音“ou”發音準確,如果口型發生變化,則很容易改變字韻,傳達不出應有的字義。因此,在演唱古詩詞藝術歌曲時,對字的把握是行腔的基礎,也體現出了演唱者的語言運用能力。
(三)情感表現
由于古詩詞藝術歌曲在創作上的獨特性,決定了演唱者在二度創作中需要建立系統的情感表達機制。首先,古詩詞藝術歌曲中的歌詞均為古人所作,由于在時代上的跨度較大,造成了歌詞創作和歌曲創作上的二元性。作曲家在進行譜曲的過程中,需要從史學、文學、美學等多學科的角度對歌詞的創作緣由、文學背景和美學追求進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夠運用與之相對應的音樂元素進行創作,因此一首古詩詞藝術歌曲實際上包含著詞作者和曲作者的雙重情感,這種情感以詞作者的創作心理機制為基礎,并融入了曲作者對歌詞的情感體驗;其次,作為演唱者,對古詩詞藝術歌曲的詮釋,既需要了解歌詞的相關內容,還需要理解作曲者的創作動機和創作風格,并再解讀作品的過程中融入自身的感受,由此可知,缺乏對歌曲的全面理解則難以達到情感的表現要求。從《秋之歌》每一首歌曲的情感表達看,實際上在情感指向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在情感的表現上,需要有所區別,這就決定了演唱者在演唱這部套曲時,需要注意演唱情緒的布局和轉換,而不是以一種演唱情緒完整的表達出來,要做到依曲而抒情。
結 語
由作曲家羅忠镕創作的《秋之歌》在題材上以敘秋為主,但是每一首歌曲在音樂形象的塑造和情感的表達方面是不盡相同的。從整部作品的音樂特點看,體現出了作曲家對傳統音樂創作手法的繼承和創新,完美地再現了原詩作的內涵和意蘊。在演唱上,則應當堅守中國傳統聲樂的美學表現手法,注重從氣息、咬字、吐字和情感的表現上進行詮釋,以此才能夠體現出歌曲的音響之美和意境之美。作為演唱者,在詮釋作品的過程中,既需要不斷的鞏固自身的演唱技巧,還需要加強自身的文化修養,現在很多演唱者在演唱古詩詞藝術歌曲方面之所以韻味不夠、情感表達模糊,實際上與個人的文化修養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因此,古詩詞藝術歌曲的意義不僅在體現在創作上的繼承和創新方面,而且對于演唱者整體水平的提高也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