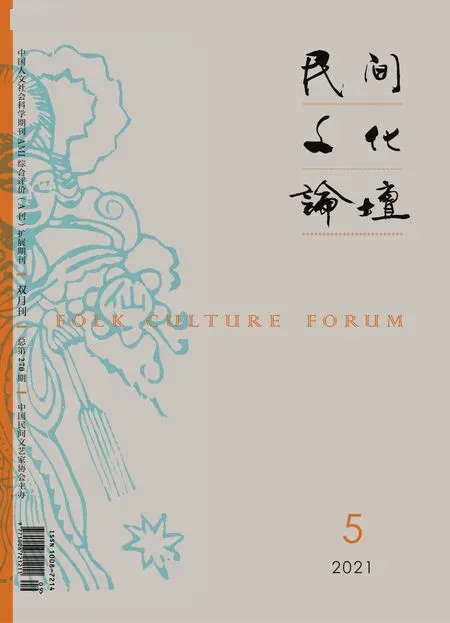推開童話的禁忌之“門”
—— 試析禁室型故事中“門”的意涵
石子萱
禁室型故事(AT313B:Forbidden chamber type)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與之相關的有“因破禁而失去妻子”(C392:Loss of wife for breaking tabu)、“禁室”(C611:Forbidden chamber)等母題。關于此類故事,已有不少前輩學者進行過研究,但就筆者所見的文獻來看,對作為禁忌空間“邊際”(merge)的“門”進行意象解析的成果較少。本文將試著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以《瑪麗亞?莫列夫娜》《藍胡子》《菲特謝爾的鳥》及《銀鼻子》等童話文本中的“門”為例,結合相關理論分析其意象內涵。
一
萬建中在《時間差:神圣與世俗邊界的構建及洞穿——禁室型故事中禁忌母題的文化闡釋》一文中指出,“禁忌是世界‘格式化’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式,凡是有神圣與世俗之界限出現的地方,就有禁忌這個忠誠的衛士,在空間領域也不例外。”具體到“禁室”而言,他認為“‘室’應作寬泛的理解,凡為人們所不能隨意窺視的空洞之物皆屬其列。”并且結合我國的“蛇郎”、盤瓠及關羽故事,提出禁忌母題的成功構建與“室”這類原始意象即原型(archetype)的復出有很大關系,“‘室’或金鐘或蒸籠或柜或甏或缽等,直接導源于大量始祖神話中的生殖象征原型……秉承著濃厚的生殖意蘊。”當人們不再需要為生殖焦慮,這些意象便“成為一種生命樣式向另一生命樣式轉化的神圣容器(holy container),向世人反復展示著其脫胎換骨、更新生命的奇異功能……”使這些神圣容器成為禁忌的,就是容器內外(也即仙界和人間)的“時間差”。a萬建中:《時間差:神圣與世俗邊界的構建及洞穿——禁室型故事中禁忌母題的文化闡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除了這篇文章外,萬建中在《蛇郎蛇女故事中禁忌母題的文化解讀》b萬建中:《蛇郎蛇女故事中禁忌母題的文化解讀》,《思想戰線》,2000年第5期。《日本民間故事中三種禁忌母題的解讀》c萬建中:《日本民間故事中三種禁忌母題的解讀》,《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等文中也對禁室型故事進行了精彩的論述。張婷婷在《林蘭民間童話中的禁忌主題研究》沿用萬建中的研究思路,認為林蘭童話中的“禁室型禁忌通過將‘室’概念的具象化表達展現出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不窮究理性之限,將對價值的探求作為自我內心的檢驗工具”a張婷婷:《林蘭民間童話中的禁忌主題研究》,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第55頁。。此外,徐丹的《歐洲民間童話中的分離主題》b徐丹:《歐洲民間童話中的分離主題》,《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孫云鳳的《論西方古典童話中的禁令與象征》c孫云鳳:《論西方古典童話中的禁令與象征》,《名作欣賞》,2012年第17期。和毛夢嬌的《論民間童話的儀式維度——以歐洲民間童話為例》d毛夢嬌:《論民間童話的儀式維度》,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等文也從“成年禮”的角度分析了禁室型故事的內涵。
普羅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在《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中提到,“禁入的儲藏室”是起源于“大房子”情結的禁忌母題,里面可能有動物相助者、可怕的場面、蛇、女性等e[俄]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賈放譯,施用勤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72—178頁。。雖然普羅普在論述“與暫離相關的禁令”時沒有提及禁室,但其禁忌性質是同質的,下文會詳述。關于禁室,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在《原型與集體無意識》中給出的解釋是:在童話中,英雄的阿尼瑪人格(anima)會被“陰險的父親意象”囚禁起來,而這位“靈魂公主”(the Princess Soul)“遵守下層世界的游戲規則,公開通過禁止年輕人進入那間屋子的辦法,設法阻止他發現自己被囚禁的秘密。但是,她背地里通過禁止這一事實,把他引向了那間屋子。”f[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原型與集體無意識》,徐德林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90頁。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1903—1990)在《童話的魅力:童話的心理意義與價值》中以《藍胡子》和《圣母瑪利亞的孩子》等為例,指出了童話精心表現的禁屋主題:“人們不準走進那間屋子,但主人公總是不顧一切地打開了房門。”g[美]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童話的魅力:童話的心理意義與價值》,舒偉、丁素萍、樊高月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464頁。河合隼雄(Hayao Kawai,1928—2007)則在他的著作《民間傳說與日本人的心靈》中指出,不允許被偷看的“禁忌房子”實際上就是人類心理中潛意識的世界,以《黃鶯之家》為代表的日本“禁忌房子”型故事傳達了日本文化獨有的“無”的境界和“憐憫”的美學意識。h詳見[日]河合隼雄:《民間傳說與日本人的心靈》,范作申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2—16頁。
由以上綜述可見,關于禁室型故事的研究并不鮮見,除了萬建中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廣義的“室”(如金鐘、蒸籠等)外,禁室多為真正的房間。現有研究多從整體意義上來把握禁室的意涵,但筆者認為,被禁止打開的那扇“門”作為童話故事的核心情節展開的標志也是值得討論的,下文將以四則禁室型童話中的“門”為例進行分析。
二
法國童話《藍胡子》i文本可參考[英]沃爾特?克蘭:《藍胡子》,南來寒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是被改寫版本最多的童話文本之一。普羅普在《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中提到,在《格林童話》中,被巫師發現進入過小房間的女主人公也被殺死并分尸了j[俄]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賈放譯,施用勤校,第110頁。,這與后來廣為流傳的主人公依靠哥哥幫助逃出生天的文本有所差異。貝特爾海姆認為,《藍胡子》故事和動物新郎故事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格林童話》中的《菲特謝爾的鳥》k文本可參考[德]格林兄弟:《格林童話》,潘子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年,第103—105頁。和《藍胡子》表現了同樣的主題:“作為一種信賴考驗,女性絕不能探究男性的隱秘”a[美]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童話的魅力:童話的心理意義與價值》,舒偉、丁素萍、樊高月譯,第460頁。,而會使暴怒的丈夫殺死妻子的就是性的不忠。《藍胡子》中表現出了“嫉妒之愛”和“性愛情感”兩種情緒,該故事的道德意義就是告誡女性不要向對性的好奇心屈服,而男性也應該原諒異性的失貞,并且故事沒有表現向更高的人格階段的發展b詳見[美]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童話的魅力:童話的心理意義與價值》,舒偉、丁素萍、樊高月譯,第458—464頁。。在《藍胡子》和《菲特謝爾的鳥》中,主人公打開禁室的門,看到的是被殘忍殺害的先行者們,并且引來災禍的破禁標志都是昭示著背叛的“擦洗不掉的血跡”。
相對于《藍胡子》,意大利童話《銀鼻子》c文本可參考嘉羽主編:《銀鼻子紳士》,北京:知識出版社,2002年。和俄羅斯童話《瑪麗亞?莫列夫娜》就沒有那么膾炙人口了,已有分析相對也比較少。通過文本對比不難發現,《銀鼻子》和《菲特謝爾的鳥》類似,都有“季子勝利”以及少女破禁卻未被發現并運用智慧戰勝加害者的情節。在《銀鼻子》的文本中,主人公打開禁室的門,看到的是魔鬼和煉獄,破禁標志是被地獄之火烤干的“枯萎的鮮花”。在《瑪麗亞?莫列夫娜》中,主人公打開禁室之門的后果則是釋放了妖魔科謝依,并因此失去了妻子,踏上了冒險的旅程。
這四則童話中都有一道禁忌之“門”。雖然主人公的性別和境遇有所差別,但這四則童話都可以從“成年禮”以及“阿尼瑪”與“阿尼姆斯”的人格調和角度來進行分析,下文將進行論述。
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四個故事文本中,設禁者與違禁者的關系都是“(準)夫妻”。盡管在《銀鼻子》的文本中,三姐妹是以女仆的身份跟銀鼻子回家的,但筆者認為,“可以任意巡視除了禁室之外的房間”的權限以及小妹妹露琪亞有能力支使銀鼻子回家送臟衣服的情節都可以表明她們并不是真正的仆役,故事中的三姐妹與銀鼻子是事實上的準夫妻關系,這一情況也符合文本的現實背景。另外,在違禁者打開禁忌之門之前,設禁者的角色都是某種程度上的“保護者”,他們為違禁者提供了優渥的物質生活資料,并且顯得十分友好和善。
在違禁者為女性的童話文本中,“藍胡子”和“銀鼻子”這兩個殘忍的加害者都有著令人不安的、異于常人的體貌特征,但故事中的女性仍然會被他們的財富吸引,跟隨他們來到陌生的空間,《菲特謝爾的鳥》中的巫師也正是用優裕的物質條件打動了被他用魔法劫掠到家中的姑娘們。正如河合隼雄所指出的:“很多故事中,所謂禁忌,就是用來打破的……”d[日]河合隼雄:《神話與日本人的心靈》,王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43頁。,在這些童話文本中,設禁者對禁令的強調實際上是慫恿和誘惑,“擦洗不掉的血跡”和“枯萎的鮮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年輕女性失貞的隱喻,而設禁者(同時也履行“懲罰”職能)加害違禁者的方式是讓她們“也進入那道門”,即實質上的墮落。這種(違禁者的)“被迫進入”是惡的顯現,一旦原來處于“被保護”地位的未成年者觸犯禁忌(作為女性即失去童貞),引誘者就會摘下偽善的面具。
在違禁者為男性的文本《瑪麗亞?莫列夫娜》中,設禁者作為主人公的妻子,在“禁忌之門”被打開之前是一個強大的“尚武領袖”e[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原型與集體無意識》,徐德林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92頁。,但在主人公伊萬放出科謝依后卻仿佛失去了力量,只能等待伊萬的救援,這實際上象征著成年禮主體進入“閾限”狀態后父母等舊日保護者的無能為力。莫列夫娜的設禁是好意的提醒,然而卻無法改變這種保護性的禁止實質上仍然是一種誘惑的事實。“禁忌之門”內鎖著的科謝依對違禁者的懲罰是強行讓其與保護者分離并離開相對熟悉的環境遠行,這種(違禁者的)“被迫離開”昭示著善的失效,面臨“保護者失能”局面的違禁者只能為必然的越界付出代價,出發去尋找完善的人格。
盡管普羅普和心理分析學派對故事的分析切入角度不同,但有關“故事的開端”的論述卻有相似之處。普羅普認為神奇故事“始于遭受某種損失或危害……或希望擁有某種東西……”a[俄]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賈放譯,施用勤校,第4頁。,而在貝特爾海姆看來,“童話故事總是以主人公受到一些人的欺壓擺布作為開始。”b[美]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童話的魅力:童話的心理意義與價值》,舒偉、丁素萍、樊高月譯,第214頁。質言之,成長型童話總是在主人公意識到某種缺失的不適中展開其核心矛盾情節。
童話故事的情節與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儀式未必具有對應關系,但人類學的民族志材料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參考。成人禮是典型的阿諾爾德?范熱內普 (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之所謂“過渡禮儀”(the rites of passage)。“禁忌之門”作為兒童進入分隔禮儀 (rites of separation)和聚合禮儀(rites of incorporation)之間的閾限(liminary)狀態的標志,其誘惑力就好比伊甸園中的智慧果,是保護者和誘惑者都無法阻止主人公觸碰和開啟的。童話中“不許打開門從而進入某空間”的禁忌是對即將體驗成人禮的兒童的特殊身份的指認,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在《金枝》中指出,禁忌的屏護“就好比電絕緣體,保藏這些人身上所充滿的靈性的力量……”c[英]J.G.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汪培基、徐育新、張澤石譯,汪培基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371—372頁。。簡?艾倫?赫麗生(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總結,“……在成人儀式上假裝把孩子殺死這種做法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幾乎可以說是世界性的。”d[英]簡?艾倫?赫麗生:《古希臘宗教的社會起源》,謝世堅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0頁。童話中違禁即會受到傷害的情節與成人儀式中“模擬的殺害”或許有著密切的聯系。赫麗生提到,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底比斯被稱為“雙重門之神”(Dithyrambos),因為其“進入生命第二道門”的新生是在父親宙斯的大腿(男性子宮)中完成的。而“從男性子宮把孩子分娩出來,就是要使孩子擺脫母親的影響——使他從一個女人味十足的小孩變成一個男人”e[英]簡?艾倫? 赫麗生:《古希臘宗教的社會起源》,謝世堅譯,第30—32頁。。值得關注的是,在本文所舉的四個故事文本中,受害的違禁者(在《銀鼻子》和《菲特謝爾的鳥》中是主人公的姐姐)在核心沖突爆發前都表現出了守貞、同情、輕信(如伊萬王子給科謝依喂水)等女性特質,而在違禁受難后想要禳解加害者的迫害,就需要凸顯主人公的支配(露琪亞要求銀鼻子在送衣服的路上不能讓麻袋著地)、好戰、殘酷等男性特質。在《藍胡子》中,幫助主人公殺死藍胡子的兩個哥哥就被視為主人公的男性人格的具象化。童話中主人公的性格發展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阿尼瑪”和“阿尼瑪斯”相互融合的人格調節過程,只有在成功地完成調和之后,主人公才能脫離困境,從母性家庭走向父性社會。
四
綜上,筆者想試著對禁室型故事中“門”的意涵進行總結。首先,“不許打開門”是一種對兒童的保護性設禁。故事中的假象是只要不打開門,主人公就會衣食豐足,設禁者就是保護者,然而“只要不知實情,人類在某個時點之前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倘若有人意欲超越前行,他將必須面對‘禁觀之真實’”a[日]河合隼雄:《神話與日本人的心靈》,王華譯,第44頁。。主人公要獲得成長,其“無知而無憂”的假象就必然會被打破。
普羅普在《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的“開場”一節中提出,“長輩們憑某種方式知道有危險在威脅著孩子們,在他們周圍就連空氣中都充斥著成百上千神秘莫測的危險和災難。當父親或丈夫自己出門,或者放孩子出去時,這個暫離總是伴之以禁令。”b[俄]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賈放譯,施用勤校,第28頁。而且令人感興趣的禁令暫時只有一個:禁止出家門。盡管這里沒有提到禁室,但筆者認為“除了這里哪里都不能去”和“除了這里哪里都可以去”其實是同質的“誘惑式禁忌”,這種禁忌將主人公的注意力吸引到那個唯一的例外之處,為作為潛在違禁者的孩童指明了“違禁”的目標,讓他們因為處于另一個世界(成人社會)的保護者發出的禁令而產生缺失感,并在這種缺失感的指引下違禁,繼而失去保護并陷入困境,進入過渡的閾限狀態。
事實上,阿諾爾德?范熱內普在《過渡禮儀》中對“門”的作用已經有過闡釋。他提出“……對某地實施禁入令,其本質是巫術—宗教性的。”c[法] 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張舉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4頁。“……跨域這個門界(seuil)就是將自己與新世界結合在一起。因此,這也是結婚、收養、神職授任和喪葬儀式中的一項重要行為。”d同上,第17頁。“門”在現實生活中所具有的遮蔽視線、分隔空間的功能被抽象化并被賦予神圣意義,在禁室型童話故事中成為“禁忌”的具象表征。它既是對違禁者的拒絕和考驗,也是對他們的邀請和誘惑,同時作為違禁后進入的“神圣閾限”的界碑而存在。主人公推開“禁忌之門”后,保護者或將失能,加害者亦會顯形,違禁者將被迫進入一個異常的時空,或者被迫離開自己熟悉的場域。如果違禁者能成功完成過渡,實現自身的人格調和,那么主人公就會獲得“成人”的新身份。
艾倫?奇南(Allan B.Chinen)在《秋空爽朗》中提到,“……青少年必須擺脫心理上的家庭安全感去‘尋求自我’。”e[美]艾倫?奇南:《秋空爽朗——童話故事與人的后半生》,劉幼怡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66頁。禁室型童話故事中的“門”是一種對兒童的保護性設禁,但無論是有利于違禁者的一方還是意圖加害違禁者的一方都無法阻止“必然的違禁”的發生。相對于“警戒和教訓”f孫云鳳:《論西方古典童話中的禁令與象征》,《名作欣賞》,2012年第17期。,筆者認為,或許童話更大的作用在于“……為孩子們的心理成長和心理調節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工具”g[美]布魯諾?貝特爾海姆著,舒偉、丁素萍、樊高月譯:《童話的魅力:童話的心理意義與價值》,譯者序,第9頁。。當人們接受童話時,“與童話主角的認同往往帶來做決定和創造成就時所必要的勇氣。借此‘封存在原型中的希望’(archetyisch eingekapselte Hoffnung)真的會釋放出來。”h[瑞士]維雷娜?卡斯特著,林敏雅譯,陳影修訂:《童話的心理分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200頁。禁室型童話故事讓受眾代入童話主人公推開“禁忌之門”,從而“借助幻想超越幼年期”。現實生活中為孩子們講述童話的保護者們,大概是希望孩子們在那個“必然的違禁”到來時,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樣,逢兇化吉,快樂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