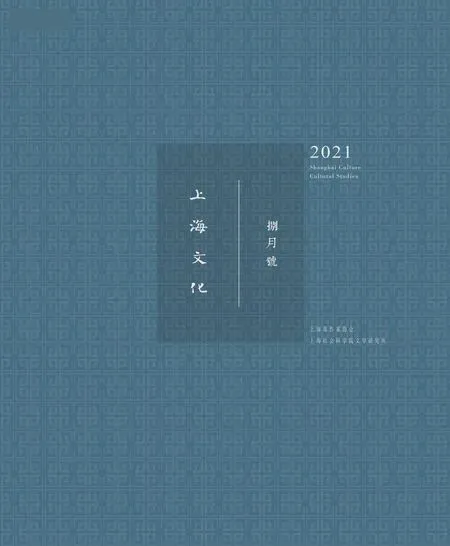《邏輯哲學論》之為世界的極簡設定
——以卡夫卡的《訴訟》為例
李宏昀
本文旨在以“設定”概念為切入點,給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①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韓林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本文中所有《邏輯哲學論》的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下文不再標注。提供一種試驗性的“打開方式”。卡夫卡小說中的世界,在相關的問題領域(包括人生意義問題,也包括數學危機)與《邏輯哲學論》形成“互文”。
文中解讀卡夫卡《訴訟》的想法,部分受到《卡夫卡與維特根斯坦》(Kafka and Wittgenstein)②Rebecca Schuman, Kafka and Wittgenstei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5.一書的啟發,在此致謝。
一、何為“設定”
“設定”這個詞的用法,是容易了解的。比如在武俠小說中,“內力”是武術的基礎;“哈利波特”系列作品中,有巫師、“麻瓜”的區分;這些都是虛擬世界不同于現實世界的“設定”。拿現實世界來說,自然規律也可以算是“設定”,當然不僅限于自然規律。在此引入“設定”這個層面,是為了同“事實”層面相區分。比如玩游戲,我們說裝備了什么寶物就能獲得什么能力,這方面的討論屬于“事實”層面;當我們說,這個寶物太強了,影響游戲平衡,這時的討論就屬于“設定”層面了。其實“設定”層面是相對于“事實”層面而言的,并沒有什么話題天然就屬于“設定”或“事實”。當游戲設計師在修改游戲設定時,我們也可以把他進行的操作視為“事實”層面,而把他所依賴的語言或引擎視為“設定”層面。拿科學上的發現或發明來說,我們說屠呦呦的成果青蒿素屬于“事實”層面,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體系屬于“設定”層面,這是不是順理成章?其實,屠呦呦的成果也可能影響到一個領域的整體格局,這時把它視為“設定”層面也可以。說某件事屬于“設定”層面,意味著我們是站在影響整體格局的角度看它的。
還是拿打游戲來打比方。要了解一個游戲的世界設定,我們有兩種途徑:一是直接問設計師,或者看攻略;二是站在游戲角色的視角,一邊玩,一邊一點一滴地“看出”這個游戲的世界設定。那么,當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游戲而是世界總體的時候,要了解這世界的“設定”,是不是只有“途徑二”這一條路可走了?這也意味著,我們所“看出”的這個世界的設定,其中不能不包含假設、試驗的成分,是允許進一步修正的,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成功,無論這里的“設定”指的是自然規律還是別的什么。
二、從“極簡設定”到認知格局
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說的是什么呢?簡單地講,它就是說,一個可以用語言來描述的世界,其基本設定是怎樣的。我說,它是“關于設定的設定”或“極簡設定”,這兩個表述說的是同一件事,但側重點不同。我將用《邏輯哲學論》中的原話作為例子來呈現。
2.0121正如我們根本不能在空間之外設想空間對象,在時間之外設想時間對象一樣,我們也不能在其與其他的對象的結合的可能性之外設想任何對象。
這話的意思是說,一旦設想了一個“對象”,那么這個對象和其他對象相結合的一切“可能性”就都被設定了。比如,當我們把一個空間區域視為“對象”,那么這個“對象”就具有和各種“顏色”相結合的“可能性”;離開了與顏色相結合的可能性,這個對象本身就無從設想。另外,這樣的對象不能直接和“音色”相結合(起碼先得設想這個空間區域存在某種“聲音”,然后“音色”才能結合到這“聲音”上去),不然就是邏輯錯誤,相當于“人設崩塌”。
不妨把“對象”理解為小說、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把對于“對象”的設想理解為“人設”,這樣有助于理解維特根斯坦的意思。小說中的“人設”立穩了,就意味著這個人物和怎樣的命運、行動相結合,這一切的可能性都已經有了邏輯一貫的設定。我們常說,創作者應該被人物本身的邏輯牽著走,指的就是這個。不然,就是所謂“人設崩塌”,創作就失敗了。
從這里可以看出,維特根斯坦講的不是任何具體的“設定”,而是“關于設定的設定”:比如說,你要設定一個“對象”,最起碼要滿足怎樣的條件,才能讓這個“對象”成立?在這里,“極簡設定”這一側面也可以看得出來,因為維特根斯坦說的是“對象設定”在最低限度上必須滿足的條件,不涉及更具體的條件,所以必然是“極簡”的。再看下一個原文例子:
2.061諸基本事態彼此獨立。
2.062從一個基本事態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不能推斷出另一個基本事態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這里說的意思就是,“事態”之間沒有邏輯聯系。比如從以往太陽每天總是升起,不能推出明天太陽也會升起;比如太陽曬石頭是一個“事態”,石頭變熱了也是一個“事態”,它們彼此獨立。這是在否定因果聯系嗎?不,這只是把因果聯系和邏輯聯系區分到不同的層面上。對哲學史有了解的話就可以看出來,在這里,維特根斯坦的問題意識相通于“休謨問題”(即人何以相信事件之間有因果聯系)的問題意識。我們可以說,維特根斯坦簡潔地呈現了“休謨問題”:因果聯系不包含在世界的“極簡設定”中。在一個虛擬世界中,因果聯系是可以打破的(比如《恐龍特急克賽號》中的“時間停止”);但是,我們無法設想一個不符合邏輯規則的世界——所以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邏輯規則包含在世界的“極簡設定”中;同時,無論人為地給出怎樣的設定,總是不能不符合邏輯規則,所以邏輯規則也是“關于設定的設定”。
在《邏輯哲學論》所描述的“極簡設定”中,語言中的“命題”必須和世界上的“事實”有對應關系,這就意味著它們之間必須有共同的“邏輯結構”,這樣前者才得以“描述”后者——也就是說,共同的“邏輯結構”是語言描述世界的“可能性”所在。維特根斯坦打比方說,演奏出來的音樂、樂譜以及唱片上的刻紋,它們之間都有共同的“邏輯結構”。但是我們從哪里看出這“邏輯結構”呢?我們能看到的,不過是音樂、樂譜、刻紋之間可以相互轉換罷了。正是在這樣的相互轉換中,共同的“邏輯結構”就“顯示”出來了。
由此可見,維特根斯坦所說的“邏輯結構”,就是“話語”和“事實”之間的“轉換規則”。確實,任何一套描述系統都少不了這樣的“轉換規則”,“極簡設定”中必然要容納它。倘若這套描述系統針對的是世界整體,那么其“轉換規則”不是別的,就是我們日常用“世界觀”一詞所指的東西;當我們把“世界觀”往“簡之又簡”的方向提煉,試著將它收納到“極簡設定”中,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就是“認知格局”。世界、人生若有“意義”,“意義”的源頭就在于這“認知格局”。
也可以用“光”來比喻這“認知格局”:它既是意義的源頭,也是意義的界限。正如這個故事所表達的:有人在路燈下找鑰匙,死活找不到。路人問他:“你確定鑰匙丟在這里了嗎?”“不確定,但是只有這里有光啊。”
三、是“謎”還是問題?
我們區分出“事實”和“設定”的不同層面,并且從“極簡設定”說到認知格局,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建設性的東西呢?我想,關注問題所包含的不同層面,有助于正確地提出問題。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
6.5相對于一個不能說出的答案而言,人們也不能將[與其相應的]那個問題說出來。[與這樣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的]那個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問題終究是可以提出來的,那么它也是可以回答的。
很多時候,所謂的“難解之謎”,是因為問題未被正確地提出。比如所謂的李約瑟之謎:“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科學和工業革命?”如果你調整了認知格局后再來看世界,你會發現“為什么歐洲發展出了科學和工業革命”才是一個可以回答的問題。再如史學“五朵金花”之一的所謂“為什么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后未能發展成真正的資本主義”,假如你明白中國近代根本沒有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那么你也就知道了,這個問題本身沒有提對(話說回來,從“假問題”未必不能產生出真學問)。
要正確地提出問題,需要具備相對有效的認知格局,這就意味著對于“設定”的正確領會。其實“設定”往往就是在我們對于事實的具體描述中“顯示”自身的。比如對于同樣一件事實,我們表述為“農民起義”還是“農民暴動”,這背后的設定就是不同的,這時候“設定”——以及與之相關的認知格局——已經把自己顯示出來了。
有時候,人生出現問題,也是由于對“設定”的領會有局限,即認知格局出了問題。著名的“十里坡劍神”大家知道嗎?當年電腦游戲《仙劍奇俠傳》剛出來的時候,有個人只曉得在最初的戰斗場景(十里坡)那里打小怪,以為這個游戲的目的就是打怪、升級、練出新的華麗招式,不曉得這個游戲還可以推進故事情節。結果,他在十里坡這個地方硬是練成了“劍神”,半年后才知道還有推進情節這回事。就是說,他從一開始就理解錯了這個游戲的“設定”。微信上有篇文章叫“如何分三步毀掉一個普通青年”,三步很簡單:販賣焦慮,消費主義,成功學。會被這樣的套路套進去的普通青年,就是把人生理解為只有打怪升級了。
四、問題的消失就是問題的解決
有些問題,比如說“力是什么”,看上去像是物理學問題,其實是哲學問題。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放到“極簡設定”中,這個問題就消失了,而這正是問題的解決。這種非常“維特根斯坦風格”的解決方式其實不是出自維特根斯坦,而是出自維特根斯坦少年時看過的一本書——赫茲的《力學原理》。赫茲不使用“力”這個概念,就成功地把事物之間的力學關系完整表述出來了。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力”不包含在“極簡設定”中。我們可以說它是人為引入的概念,出自人自己“用力”感受的類比,引入這個概念便于我們日常的表達——比起通過“設定”層面的“顯示”來化解問題,這樣的“解釋”其實是容易的。“解釋”可以無窮無盡,但并不必然導致問題的解決;問題的解決,是由有效的認知格局所導致的正確“顯示”的后果。
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就是通過“邏輯結構”的正確“顯示”,化解了“羅素悖論”。這里不談這個問題,而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幫助我們想象一下維特根斯坦的解決方案是怎么回事。這個例子就是,現代微積分中的“極限”理論如何化解作為“芝諾悖論”之一的“飛矢不動”問題:飛行的箭在每一個時間點都占據著一段確定的空間,故而在每一個時間點它的速度都等于零,所以飛矢是不動的。破解這個悖論的關鍵在于“每一個時間點的速度”,這個說法本身就具有悖論性:所謂“速度”,就是一段時間中的距離變化率,而當“一段時間”變成了“一個時間點”,那么當然就不存在所謂的“速度”(而非速度等于零)——可見,追問飛矢在某個時間點的速度乃至追問它在這個時間點是“動”還是“不動”,都沒有意義。悖論產生于一個不成立的視角(在這個不成立的視角發生的事情,就相當于前文說的“人設崩塌”),當我們“看出”這個視角的悖謬,悖論就“自我消解”了。
在“時間—速度”的函數圖像中,我們貌似能夠指出每個“時間點”對應的“速度”;但現代數學的極限概念告訴我們,每個“時間點”對應的數值不是“速度”,而是“這個時間點到附近時間點的距離變化率的極限”(這個數值往往不等于零)。這樣通過正確的符號操作,我們就避免了造成悖論的視角;不需要“言說”或規定更多東西,悖論就已經消解掉了,因為正確的視角已經“顯示”了自身。
哲學史上會說,有個不同于《邏輯哲學論》時期的“后期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里面的不少具體“設定”都被拋棄了。但是,通過正確的“顯示”來化解哲學問題,這是維特根斯坦一以貫之的路徑。
拿人生問題來說,當你找到對于你的問題的正確“表述”,是不是就意味著你已經找到“答案”?假如有所謂“維特根斯坦式的心理治療”,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或者也可以說,只有當你找到了通向“答案”的正確方向,你才能得出正確的“表述”。由此,我們接近了卡夫卡。
五、卡夫卡的《訴訟》說了什么?
這里用卡夫卡的中篇小說《訴訟》作例子。《訴訟》有些版本譯作《審判》,《訴訟》是全集版①卡夫卡:《訴訟》,章國鋒譯,《卡夫卡全集》第2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下文關于《訴訟》的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標注。的譯法,我覺得這個譯法好,可以體現出過程的“沒完沒了”。卡夫卡是先寫出了《訴訟》的結局(主人公K家里來了兩個看守把他帶走,K終究放棄了掙扎,甘愿受死了)然后再寫前文的,前文的故事可以無窮無盡地展開,而結局是被卡夫卡注定的。
在《訴訟》的開頭,主人公K家里莫名其妙地來了兩個看守,說K被捕了。K說他自己是無辜的,并且說,法律的事他弄不懂。看守之一說道,你說你不懂法律,卻又認為你自己是無辜的,沒見過你這么不講道理的人。這里就可以類比《邏輯哲學論》了:你若想知道一個命題是真是假,你得拿它和現實世界中的事實作比較。K說自己是無辜的,又說自己不懂法律,這情況其實就是:他雖然依舊相信某些命題是真的,但他已經不知道該用現實世界中的什么“事實”來和這個命題作比較了——用前文的話說,就是“話語”和“事實”之間的“轉換原則”失效了。所以,K的被捕不是“事實”層面的事情,而是“設定”層面發生的事情:語言的意義發生了游離/他的認知格局不再充分有效/他的整個世界觀、他的世界的“意義”遭遇危機——這幾句,說的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側面。
語言意義的游離,其實是卡夫卡經常涉及的主題,也是我們當今生活中容易觀察到的事情。我讀本科一年級的時候,教我們中國古典文學的駱玉明老師經常跟我們談人生。他說,男人啊,被人形容為“狡猾”“兇狠”什么的,都還好;最要不得的,就是被形容為“猥瑣”。我們覺得有道理,因為那時候“猥瑣”這個詞看起來真的挺猥瑣。可是今天,我們有不少“好詞”,漸漸地都在現實中喪失了與之相應的對象;相比起來,原本的“壞詞”,像“猥瑣”“屌絲”等,倒還留著“真”,從“真”里面就透出可愛了。
這里把《訴訟》中K的被捕放在“設定”層面來理解。把這個當成“事實”來理解也不是不可以,就如同某些評論所說,《訴訟》講的是司法系統的腐敗之類,但是這樣理解的話,小說中的各種局部就晦澀了。而照我這樣來理解,小說中各種局部都能呈現出清晰的內涵。
卡夫卡的《變形記》是比較不晦澀的一篇,整個故事比較容易引起當今“中產階級”的共鳴。《變形記》中的主人公一早起來發現自己變成一個大甲蟲,這不妨就理解為一些中年程序員“失業焦慮”的具象化。這一點完全可以放在“事實”層面理解,而這樣的具體事實也影響了主人公生活世界的整體格局。
六、當世界的意義遭遇危機
在講解《訴訟》的幾個局部之前,先講一個數學史上的著名案例,這就是“第一次數學危機”,即“不可公度量的危機”,也就是“無理數的危機”。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一切量都是可公度的——意思就是一切數都可以表示成分數,無理數不存在。畢達哥拉斯有個得意的學生叫希帕索斯,他用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反證法”證明了就是無理數,不可能表示成分數——這個就相似于K所遭遇的危機:出現了原有的語言系統無法與之相應的“事實”,原有的認知格局動搖了。于是希帕索斯被畢達哥拉斯的忠實門徒拋進海里淹死了——這個結局也和K相似。
小說中,K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斗爭,想證明自己無辜。他自己到法庭去,用了點小伎倆拿到了“關于法律的書”,卻發現書里面只有畫得很拙劣的男女色情圖。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里包含“語言圖像理論”,說語言相當于世界的“圖像”,語言通過它與世界共同的“邏輯結構”而表述了世界。重點在于,當且僅當你看出了這個“邏輯結構”(即你的認知格局充分有效)時,語言就成為“有意義的圖像”,畫得拙劣不拙劣是無所謂的。可是K所遭遇的危機正是“世界意義”層面的危機,這個危機也就意味著使得“語言描述世界”得以可能的“邏輯結構”不再“顯示”給他了,所以即便他拿到了法律書,他也讀不懂,只看到畫得很拙劣的男女色情圖。
為什么是色情圖?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細節。K在希望證明自己無辜的努力過程中,總是在找女人幫忙,和各種女人建立了各種關系。也是駱玉明老師,當年給我們講《紅樓夢》的時候是這樣說的:“當整個世界失去意義的時候,女性的美或許是男性最后的慰藉。”這個主題,表現得蘊藉一點是《紅樓夢》,表現得露骨一點是《金瓶梅》,表現得抽象一點,就是卡夫卡了。
當世界的意義沒有對你充分呈現,你讀出色情圖,你在世界上看到各種墮落;當世界的意義次第呈現,你原先看到的東西依然如故,但“意義”會層層變化(參考《莊子·逍遙游》:“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當然,各種“墮落”的行為依舊,可是人追求性的快感,不就是因為害怕孤獨、追求與他人的一體感嗎?貪圖財富不就是追求自由嗎?爭權奪利不就是“上進心”的表現嗎?人固然是糊涂,在原本美好的動力中迷失從而走向各種墮落;但整個圖景,其間的因果絲絲入扣,稱其為“壯美”也無不可。當圖景越來越充分地展開,你尋求的“答案”就在其中(倘若你需要“答案”的話)。
檢驗自己的認知結構,相當于哲學思考;當認知結構發生動搖、不再充分有效的時候再去檢驗,相當于“困而學之”(《論語·季氏》)。K多次親自去法院辦公室,可是他在那種地方待不久,每次都感到“呼吸困難”。其實,有過真正的“哲學思辨”體驗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當你進入哲學思辨的時候,感受到的就是某種“呼吸困難”;這種時候,原先“稱手”的概念都要經受檢驗,你缺乏依傍、摸索前行。或許當你“想通”了一兩個關節,得到了某種正確的“呈現”的時候,會覺得呼吸順暢了些。這里說的“呼吸困難”是比喻式的形容還是真實的情況?兩者兼而有之吧。或許,這種時候大腦確實比平時更加需要氧氣和營養。
也可以參考一則八卦:
維特根斯坦建議自己的朋友和學生離開學術界,因為他相信學術界的大氣太稀薄,不能支持正當的生活。他告訴德魯利,劍橋沒有氧氣。他自己無所謂——他制造自己的氧氣。①瑞·蒙克:《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王宇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39頁。
七、畫家的建議和“無理數的危機”
《訴訟》中的K后來經人介紹,去找一個畫家(依然和《邏輯哲學論》的“語言圖像”相通)幫忙。其實這個畫家也是法院的人,他屋子的后門就直接通向法院辦公室。畫家給他三個選擇:
您希望獲得那種形式的無罪判決?有三種可能性,一種是真正宣判無罪,另一種是表面宣判無罪,第三種是無限延期審判。
畫家又說,真正宣判無罪的,只有這樣一種情況,就是你真的是無辜的,在這種情況下,你肯定會被宣判無罪,你也不用找我幫忙。這種情況,就相當于前文說的“芝諾悖論”。芝諾說“飛矢不動”,這并沒有引起什么危機。你相信你眼中看到的,飛矢千真萬確是動的;即使你無法駁斥芝諾的理論推演,你不理他就沒事了。至于錯誤的理論推演,早晚會有人去駁斥它。假如K真心相信自己是無辜的,不去千方百計地證明自己無辜,是不是任何人都拿他沒辦法?可是當他想辦法去證明自己無辜的時候,就被套進這個邏輯了(這又反過來證明他的認知格局本來就不是充分有效的)。畫家說,“真正宣判無罪”這種情況幾乎沒有發生過。
表面宣判無罪,這需要下功夫打點法院的下級官員(畫家說,上級官員他也接觸不到),讓下級官員們聯合寫個保單保他無罪。但這個辦法的問題在于,不知道什么時候上級官員會發現這個情況,這時候就會重新啟動訴訟程序。什么時候會發現呢?說不定隔天就會發現,說不定要一年兩年。
這個辦法,拿前面說的“無理數的危機”作類比,就相當于是給找一個可以用分數來表示的近似值,然后“表面宣布”問題解決。可是,誰知道這個近似值在哪個操作環節會鬧出問題呢?
無限延期審判,需要的是一直保持警醒,不斷地打點法院的官員,讓審判一直推遲,不發生,那么在現實上也就等于你無罪了。這個相當于什么呢?在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里面,處理和無理數相關的問題時,有所謂“窮竭法”,在操作上足以應對。盡管由于其對“無限”的探索尚不充分,使得操作略顯繁瑣;但是,“窮竭法”已經是一種嚴格的證明了。
K作了何種選擇?小說中沒有寫明。而且畫家的情節已經接近小說結局了。
八、何處見生機?
在《訴訟》的倒數第二章,K在大教堂見到神父。神父給K講的故事,常常被單獨抽出,作為一篇名為《在法的門前》的短篇小說刊行于世。這故事說,有個鄉下人來到法的門前,守門人告訴他,現在還不能讓他進去。鄉下人從此再也不敢往門里邁步,但他也舍不得離開。他一直待在門口與守門人周旋,就這樣直到生命終了。直到他臨終前的一刻,守門人對他說:
誰也不能得到走進這道門的允許,因為這道門是專為你而開的。現在我要去把它關上了。
在這個世界上,如魚得水也好,格格不入也罷,你終究是你自己世界的唯一主角;檢驗、調整你自己的認知格局,畢竟是你與生俱來的任務,參考《莊子·達生》:“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卡夫卡《訴訟》的結尾:
雖然世界上的邏輯是不可動搖的,但它無法抗拒一個想活下去的人。
他看見那兩個人就在他的面前,頭挨著頭,觀察著這最后一幕。“真像是一條狗!”他說,意思似乎是,他的恥辱應當留在人間。
第一句,和《邏輯哲學論》的這段文字形成了呼應:
6.43如果善的意欲或者惡的意欲改變了世界,那么它只能改變世界的界限,而不能改變事實;不能改變借助于語言所能表達的東西。簡言之,這時世界必定由此而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可以說,它必定作為一個整體而縮小或增長。由幸福所構成的世界是這樣一個世界,它不同于由不幸福所構成的世界。
當世界的意義遭遇危機時,可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下》),“一個想活下去的人”,可以“處處見生機”。
“他的恥辱應當留在人間。”確實,K的結局,畢達哥拉斯的弟子希帕索斯的結局,說可恥并非沒有道理:人,或學派,被自己的認知格局限制住了。可是,每個時代都會有難以突破的限制。
“真像是一條狗!”周星馳《大話西游》結尾的“他好像一條狗耶”,應該不是對卡夫卡的致敬。周星馳沒紅的時候自己被人這么說過。
《大話西游》結尾的“他好像一條狗耶”,可以說是有點瀟灑的:人認識到自己的有限,認識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