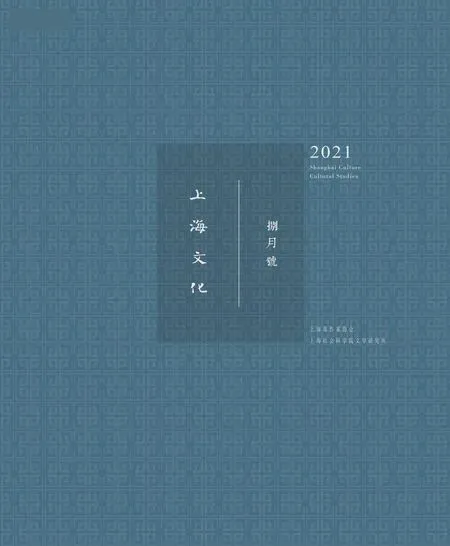論新世紀(jì)科幻小說的人工智能書寫及其社會(huì)啟蒙價(jià)值
——以劉慈欣和韓松為中心
史鳴威
近年來,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接近當(dāng)代人的日常生活,AlphaGo戰(zhàn)勝頂尖棋手李世石、柯潔,“AI文藝”、AI寫詩不僅進(jìn)入文藝界的議題范圍,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現(xiàn)實(shí),①參見楊慶祥等:《AI文學(xué),一次革命性沖擊?》,《江南》2019年第6期。人工智能技術(shù)成為當(dāng)代“顯學(xué)”。②在中國知網(wǎng)上以“人工智能”為關(guān)鍵詞,可以檢索到209199條結(jié)果,而且,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圍包括傳統(tǒng)理、工學(xué)、醫(yī)學(xué)等多個(gè)重要領(lǐng)域,由此可見其影響之廣泛。如此紛繁復(fù)雜的事件融合在一起,但是一個(gè)逐漸清晰的事實(shí)是:“后人類”③張偉:《技術(shù)媒介與當(dāng)代文學(xué)生產(chǎn)的“后人類”向度》,《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18年第9期。已經(jīng)成為跨越人工智能學(xué)、科學(xué)、人文學(xué)學(xué)科壁壘的重要概念,關(guān)涉人類的命運(yùn)與未來。人工智能是新世紀(jì)科幻小說的重要一環(huán),因?yàn)槿斯ぶ悄苁侨祟悮v史向前發(fā)展的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劉慈欣、韓松是中國科幻寫作的重要代表,兩人都參與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對(duì)人工智能形象的建構(gòu),而且形成了不同的思考與書寫,通過文本流傳于世,具有多重維度的價(jià)值和意義,其中至關(guān)重要的是科幻小說里人工智能書寫的社會(huì)啟蒙價(jià)值。
一、后人類的多重景觀:人工智能書寫的技術(shù)與人文分歧
眾所周知,“后人類”這一概念的提出在知識(shí)界有著較為廣泛的影響,這正是因?yàn)楹笕祟愒诳茖W(xué)技術(shù)領(lǐng)域象征著未來技術(shù)的可能性,而對(duì)于人文學(xué)則意味著以往所延續(xù)的社會(huì)形態(tài)乃至人文價(jià)值,可能要遭遇根本性的顛覆。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日新月異的變革,后人類也有其忠實(shí)的擁躉:“后人類主義”,其主張人作為一段技術(shù)初級(jí)階段的歷史產(chǎn)物,“是為‘后人類在作積極地準(zhǔn)備’,未來是‘屬于后人類’的。后人類是已經(jīng)完成了進(jìn)化的人類”,①曹榮湘選編:《后人類文化》,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第2、13頁。是通過技術(shù)達(dá)到新層次的存在。而且“后人類主義是一種科學(xué)至上主義,對(duì)科技,后人類主義者表現(xiàn)出過分的自信,對(duì)于科技可能帶來的反作用,后人類主義者常不太關(guān)注”。②曹榮湘選編:《后人類文化》,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第2、13頁。質(zhì)言之,后人類是技術(shù)融于人類的生物本體進(jìn)而改造人類的產(chǎn)物,一旦將技術(shù)應(yīng)用于人類原初本體的改造,后人類的起點(diǎn)就開始了。以此為基礎(chǔ),科幻小說所建構(gòu)的后人類景觀,能使讀者清晰地觀察后人類的多種可能性。盡管后人類主義似乎在整體上有著統(tǒng)一性,但是文學(xué)常帶來多元的價(jià)值取向和倫理判斷。在以劉慈欣和韓松為代表的科幻作家群中,人工智能與后人類的方向展現(xiàn)出紛繁復(fù)雜的多樣性。
就劉慈欣科幻作品中的人工智能書寫而言,不論是以往學(xué)者所提及的“近景、中景、遠(yuǎn)景”三重人工智能敘事的內(nèi)容,③參見王峰:《人工智能科幻敘事的三種時(shí)間想象與當(dāng)代社會(huì)焦慮》,《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2019年第3期。還是小說所展現(xiàn)的波瀾壯闊的科幻史詩情結(jié),都昭示著敘述者對(duì)人工智能未來可能性持有的一種曖昧的“技術(shù)至上主義”。劉慈欣在《一個(gè)和十萬個(gè)地球》中指出,人類為了一個(gè)地球而放棄了投資太空開發(fā)是十分不明智的,在他看來,“人類正處在第二次大航海時(shí)代的前夜”,④劉慈欣:《劉慈欣談科幻》,武漢:湖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14年,第7頁。不應(yīng)為了眼前的利益而中斷拓展太空新技術(shù)的可能性,可見其對(duì)技術(shù)發(fā)展的樂觀態(tài)度和美好愿景。所謂“曖昧”則是指劉慈欣小說也或多或少地肯定了人文精神和藝術(shù)的魅力和效用,盡管前者對(duì)后者的肯定是片面的,仿佛是對(duì)技術(shù)世界之附屬品的褒獎(jiǎng)。
一方面,劉慈欣小說里的人工智能書寫形塑一幅幅壯麗崇高的宇宙未來景觀,并在景觀內(nèi)部安置屬于人工智能的位置,整體上構(gòu)成了對(duì)生命體成神之路的想象。在近距的科幻景觀里,人工智能是被控制的機(jī)器,是效能優(yōu)秀的工具。《三體》里的人工智能智子是三體的代言人,以一個(gè)日本女忍者的形象出現(xiàn)在小說里的不同紀(jì)元。智子是技術(shù)文明孕育的“花朵”,但是她在地球人眼里倒不如說是一位沒有情感的女魔頭,是一把屠殺的“武器”。在程心放棄向宇宙發(fā)射坐標(biāo)信號(hào)之后,三體文明迅速摧毀了地球的軍事力量,智子作為兩個(gè)文明之間的使者,剝奪了提供生存基礎(chǔ)的科技,強(qiáng)令全體人類遷徙到澳大利亞來消滅幾十億人。當(dāng)生物體執(zhí)行毀滅幾十億生靈的命令時(shí),很難想象她能沒有絲毫情緒波動(dòng)。被當(dāng)作工具使用的智子只有一如既往的冰冷和淡漠。在中距的科幻景觀里,人與機(jī)器走向了聯(lián)合。《時(shí)間移民》借冷凍人穿越時(shí)空的經(jīng)歷描繪了人與機(jī)器融合的歷程,人的進(jìn)化伴隨著人類本質(zhì)的丟失,伴隨著自我的機(jī)械化,人類成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人類最終成為了工具。在遠(yuǎn)距的科幻景觀里,人工智能成為一種抽象的概念,成為宇宙間無所不能的神靈。《詩云》想象了一個(gè)從鼻涕蟲進(jìn)化而來的生命體,其層級(jí)之高要以“神”來命名:
那是懸浮在太空中的一個(gè)正方形平面和一個(gè)球體,當(dāng)飛船移動(dòng)到與平面齊平時(shí),它在星空的背景上短暫地消失了一下,這說明它幾乎沒有厚度——那個(gè)完美的球體懸浮在平面上方,兩者都發(fā)出柔和的白光,表面均勻得看不出任何特征。這兩個(gè)東西仿佛是從計(jì)算機(jī)的圖庫中取出的兩個(gè)元素,是這紛亂的宇宙中兩個(gè)簡(jiǎn)明而抽象的概念。①劉慈欣:《詩云》,《科幻世界》2003年第3期。
質(zhì)言之,“神”經(jīng)過漫長(zhǎng)的進(jìn)化史,已經(jīng)褪去了物質(zhì)世界的一切現(xiàn)實(shí)和具象的特征,提煉為極端抽象的概念,成為承載真理的形而上。“神”再也不需要過多符號(hào)來表征,一切的玄妙都落實(shí)為兩個(gè)簡(jiǎn)明的幾何體。不得不說,這是一個(gè)令人引人深思的科幻想象,因?yàn)槠鋬?nèi)在早已連接了中國先秦的易學(xué),又涉及了西方的形而上學(xué)傳統(tǒng)。在這個(gè)意義上,技術(shù)終極之“神”也具有了科幻想象的真實(shí)性,技術(shù)至上主義也并不是現(xiàn)代人的“癡人說夢(mèng)”。
另一方面,劉慈欣小說中對(duì)于人的機(jī)器化、人的自我改造,也持部分保守態(tài)度。《時(shí)間移民》里的人無限制地使用技術(shù)改造自身,終于致使文明走向滅亡,電子國度消亡了,留下一個(gè)回歸本來面目的蠻荒星球。更令人深思的是,《詩云》里無所不能的“神”也遭遇失敗。“神”是想象的人工智能的終極——?dú)v盡千辛萬苦自我改造而成的上帝,自信全知全能,每每夸耀自己的神奇?zhèn)チΑKㄋ┛梢运查g塑造一個(gè)人類的碳基生命體,可以將太陽系的全部物質(zhì)用來記錄隨機(jī)排列的詩歌,然而他(她)最終也不得不承認(rèn)無法在詩歌藝術(shù)上超越李白這一事實(shí),最終帶著對(duì)人類詩歌藝術(shù)的崇敬之心抱憾而去。也即是說,無論是以程序?yàn)榛A(chǔ)的寫詩軟件,還是以人機(jī)結(jié)合的人類改造,都難以逾越人文藝術(shù)的永恒性。
近乎與之相反,韓松筆下的人工智能成為了人類的實(shí)際統(tǒng)治者,而小說的反烏托邦敘事也彰顯了科幻人文主義傾向。韓松的“醫(yī)院三部曲”表現(xiàn)出一種奇詭之風(fēng),這一風(fēng)格圍繞著“醫(yī)院船”的“異托邦”空間塑造。某種程度上,韓松小說的人工智能敘事構(gòu)成了“福柯場(chǎng)域”的未來景觀,進(jìn)而形成了內(nèi)在的批判邏輯。所謂福柯場(chǎng)域,其一可以追溯福柯所提及的“異托邦”空間理論,即著意于醫(yī)院、瘋?cè)嗽旱瓤臻g的獨(dú)特之處,從烏托邦之外尋找空間的活力;其二則要追溯到《規(guī)訓(xùn)與懲罰》所提及的邊沁“全景敞視監(jiān)獄”:通過一種環(huán)形結(jié)構(gòu)的建筑,達(dá)到中心瞭望塔對(duì)圓周犯人的全天候監(jiān)視目的,進(jìn)而令囚犯不得不自我審查、自我約束。此模型存在的監(jiān)視、控制和規(guī)訓(xùn),廣泛蔓延于“學(xué)校、醫(yī)院、工廠和兵營(yíng)”。福柯在《全景敞視主義》這一章的結(jié)尾指出:“對(duì)于監(jiān)獄與工廠、學(xué)校、兵營(yíng)和醫(yī)院彼此相像,難道值得大驚小怪嗎?”②福柯:《規(guī)訓(xùn)與懲罰》,劉北成、楊遠(yuǎn)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第255頁。
韓松的小說“醫(yī)院三部曲”里,楊偉所接觸的“藥時(shí)代”已經(jīng)開始顯露其陰森恐怖的一面。“藥時(shí)代”表面上一切以生命為中心,而醫(yī)院實(shí)際上實(shí)行對(duì)人的全方位立體的監(jiān)管,一旦進(jìn)入醫(yī)院幾乎再難得見天日,以至于許多病人組織叛逃。隨著醫(yī)療機(jī)器的不斷發(fā)展,人類對(duì)疾病的苛刻逐漸近乎強(qiáng)迫癥。《驅(qū)魔》塑造了一個(gè)醫(yī)療人工智能形象:司命,也是“醫(yī)療船”的中樞首腦,病人的命運(yùn)完全被他①司命已經(jīng)有了自我意識(shí),筆者認(rèn)為用“他”來代指更為妥當(dāng)。所掌控。首先,病人必須接受司命派遣的眾多機(jī)器人的治療,而這種治療配合全天候的檢測(cè)系統(tǒng),業(yè)已構(gòu)成了全方位的監(jiān)視。其次,病人不得不每日誦讀司命編寫的《醫(yī)院工程學(xué)原理》,并依仗此書解釋一切現(xiàn)實(shí)遭遇的問題。最后,非常具有隱喻意味的是,病人的姓名全都以藥物化學(xué)名稱拼湊而成,例如疣啶、痙哌、疝噻等。對(duì)姓名的重新編碼,對(duì)獨(dú)立思考精神的剝奪,對(duì)人身自由的限制,此種多維度的改造一旦成功得到實(shí)踐,人之為人的主體性也就煙消云散了,符號(hào)化的個(gè)體成為“醫(yī)療船”上一個(gè)個(gè)徘徊不定的“幽靈”。
人工智能,一個(gè)有魔力的話題,因?yàn)樗P(guān)系著人類的命運(yùn)與未來,關(guān)系著后人類何以生成。在這個(gè)領(lǐng)域里,文學(xué)暢想未來、探尋真相等諸多功能都由科幻文學(xué)這一載體而實(shí)現(xiàn)。劉慈欣和韓松對(duì)人工智能的書寫呈現(xiàn)出后人類的多重維度,由技術(shù)與人文的分歧生成的復(fù)雜性成為文學(xué)、科幻的重要景觀。那些綺麗多維的想象蘊(yùn)含著對(duì)人工智能的支持和批判、信奉與反思,會(huì)在某一時(shí)刻為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提供另一種可能性。
二、生存與毀滅:人工智能帶來的難題
呈現(xiàn)各具代表性的未來觀是科幻文學(xué)的題中之義,然而文學(xué)絕不止步于此,文學(xué)不會(huì)、也不能止步于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或未來社會(huì)的一種反映,更為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那些人類終將難以避開的難題,是用人文學(xué)敏銳的觸角洞察世道人心的變異與可能。韓松說“科幻小說其實(shí)是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②丁楊:《韓松:在今天,科幻小說其實(shí)是“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中華讀書報(bào)》2019年1月30日。也許正是領(lǐng)悟到了這一點(diǎn)。人工智能科幻小說所表現(xiàn)的后人類景觀是未來社會(huì)人們將要面對(duì)的現(xiàn)實(shí),與人類的命運(yùn)息息相關(guān)。后人類的到來極有可能改變?nèi)祟惖闹黧w性,并且這種改變絕不像人類進(jìn)化史那樣緩慢,而是會(huì)像雷·庫茲韋爾指出的:技術(shù)產(chǎn)生指數(shù)級(jí)的更迭變化引起整個(gè)社會(huì)、族群和物種的驚天巨變。③參見雷·庫茲韋爾:《奇點(diǎn)臨近》,李慶誠、董振華、田源譯,北京:機(jī)械工業(yè)出版社,2011年。奇點(diǎn)臨近,數(shù)千載未逢的大變局就要來臨,科幻小說既是在黎明破曉時(shí)看到了振奮人心的一縷曙光,也有可能是在日落黃昏時(shí)看到那一抹令人心驚的隱憂。劉慈欣和韓松的小說就敘述了關(guān)于人工智能以及后人類時(shí)代可能會(huì)出現(xiàn)的諸多問題,其人工智能形象的塑造本身包含著豐富的問題意識(shí)和思想內(nèi)涵,在社會(huì)中傳播具有理性啟蒙價(jià)值。
首先,在人工智能展現(xiàn)出極為高效的工具性時(shí),工具所帶有的那種冷冰冰的僵化思維也被保存了下來,一板一眼地執(zhí)行著毫無人性可言的行動(dòng)。如果說《三體》中的智子還只是敵人的武器,有一種樸素的敵我之別,《贍養(yǎng)人類》里人類用人工智能管理社會(huì),就顯露出作繭自縛的意味。“終產(chǎn)者”憑借生物科技活了很久,并且利用新技術(shù)不斷地提升自身能力,最終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nèi)將整個(gè)星球都收為私有。人類的大多數(shù)就只能在全封閉的微型生態(tài)循環(huán)系統(tǒng)里呼吸污濁的空氣,飲用千萬次過濾后的液體,吃以排泄物為原料合成的再生食物。一旦遭遇輕微的風(fēng)險(xiǎn),就必須自我分解,為家人獻(xiàn)出自己最有價(jià)值的物質(zhì):尸體。最終,無產(chǎn)者們無法抗拒地被“終產(chǎn)者”驅(qū)逐了,因?yàn)椤耙环N力量正在孕育,它將使國家機(jī)器變成一部真正的機(jī)器,里面一個(gè)人都沒有,只有機(jī)器,這就是人工智能(AI)”。①劉慈欣:《劉慈欣談科幻》,第19頁。人工智能作為執(zhí)法者一絲不茍地執(zhí)行法律的嚴(yán)令,保護(hù)了私有財(cái)產(chǎn)的神圣性,“捍衛(wèi)”了“終產(chǎn)者”的生命和財(cái)富的安全,卻留下了文本最大的諷刺:服務(wù)變?yōu)閴浩取8I秸J(rèn)為一旦進(jìn)入后人類時(shí)代,人類所珍重的那些價(jià)值和屬性可能會(huì)成為負(fù)擔(dān),而被人工智能所輕視和不屑。②參見弗朗西斯·福山:《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黃立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將工具性貫徹到底之時(shí),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思維將會(huì)把人類自身認(rèn)可的價(jià)值抹除。一方面,在使用技術(shù)改造人類本身時(shí),技術(shù)的工具性在所難免地要影響人的本質(zhì);另一方面,人類使用技術(shù)的工具性,而技術(shù)的寵兒——人工智能一旦獨(dú)立,很有可能將這種工具性應(yīng)用于人類的生活,從而對(duì)人的自由意志乃至生存條件造成極大的限制。
其次,人工智能會(huì)如何對(duì)待人類呢?在堪稱“智神”的人工智能面前,人類不過是脆弱的生物。克里斯·哈爾布斯·格雷認(rèn)為后人類是唯一的選擇,“因?yàn)樵诤蟋F(xiàn)代技術(shù)的背景下,大屠殺和古拉格集中營(yíng)(Gulag)看起來好像是在排練”。③曹榮湘選編:《后人類文化》,第21頁。《驅(qū)魔》里的司命不斷強(qiáng)調(diào)“病”的長(zhǎng)久存在,無疑是暗示了人類被看輕、被統(tǒng)治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可能會(huì)成為前所未有的極權(quán)者。司命是“醫(yī)療船”上的算法,“司命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利用大數(shù)據(jù)全面管理醫(yī)院船”。④韓松:《驅(qū)魔》,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5-26頁。問題在于,反烏托邦小說預(yù)言的未來并未成為現(xiàn)實(shí),被奉若神明的司命的可能性何在?事實(shí)上,在信息技術(shù)發(fā)達(dá)的現(xiàn)代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帶給我們便利的同時(shí),也在欺騙著我們。原因在于算法持續(xù)優(yōu)化并和資本合作,通過大數(shù)據(jù)形成對(duì)消費(fèi)者的傾軋,即“實(shí)施個(gè)性化定價(jià)”。⑤鄒開亮、劉佳明:《大數(shù)據(jù)“殺熟”的法律規(guī)制困境與出路——僅從〈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的角度考量》,《價(jià)格理論與實(shí)踐》2018年第8期。基于“算法治理”的網(wǎng)絡(luò)生態(tài)所帶來的“技術(shù)欺騙”已經(jīng)開始包圍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種形勢(shì)之下,令人不得不承認(rèn):如果人類不用人工智能改造自身,任由人工智能隨意超越,那么韓松“亡靈三部曲”里的司命也有可能是一個(gè)“宿命”,是掙扎不脫的夢(mèng)魘。
最后,人工智能來襲昭示著后人類成為不得不反復(fù)討論的議題,人類或許只能將自身改造成可以與人工智能爭(zhēng)鋒的“電子人”。因此,如何選擇人類本性中可貴之處加以保存,如何在漫長(zhǎng)的歷史進(jìn)程中,存一份赤子之心,守住人性的本真,將成為令人進(jìn)退失據(jù)的難題。劉慈欣小說里的文明必須拼盡全力生存,無論是《三體》里人類與三體文明的斗智斗勇,還是《時(shí)間移民》所展現(xiàn)的人類進(jìn)化的未來史詩,似乎一切問題解決的根本都要依托技術(shù)的增長(zhǎng)力。盡管如此,《詩云》還是給藝術(shù)留下了一個(gè)充足的園地,在吞噬帝國擊敗地球聯(lián)軍之后,在人類被永遠(yuǎn)奴役的末日之后,機(jī)緣巧合之下,伊依對(duì)詩歌藝術(shù)堅(jiān)持得到了“神”的認(rèn)可,在喜愛宇宙藝術(shù)的“神”的幫助下,人類終于有了一線生機(jī)。而且,《贍養(yǎng)人類》塑造的“終產(chǎn)者”形象也提示人們——人工智能時(shí)代更需要堅(jiān)守平等的信念,技術(shù)不能成為權(quán)貴的“禁臠”,而是應(yīng)當(dāng)造福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這也是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意義所在。此外,韓松在《驅(qū)魔》的扉頁寫下“因?yàn)橥纯啵胖朗腔钪保纯嗍亲鳛槿说淖羁坦堑捏w驗(yàn),所經(jīng)歷的精神創(chuàng)傷不但不會(huì)消失,而且在記憶中會(huì)經(jīng)常浮現(xiàn)。韓松“醫(yī)院三部曲”里眾生皆苦,但為了解脫這種痛苦將全部的希望都寄托于醫(yī)療技術(shù),最終導(dǎo)致了極權(quán)的“醫(yī)療船”,出現(xiàn)了人工智能司命。“醫(yī)療船”上的病人被大海包圍,名字也都改成醫(yī)用化學(xué)元素的組合,為了擺脫病患而終生陷入病患,為了擺脫痛苦而終生痛苦。這種悖論透露出一個(gè)隱喻的真實(shí):如果不能警惕自己對(duì)技術(shù)的推崇,不能覺醒對(duì)技術(shù)烏托邦的反思,不能察覺人之為人的特質(zhì)的消逝,那么等待著的將是難以擺脫的深淵。因此,于人工智能熱潮洶涌澎湃之際,科幻小說的人工智能書寫敲響了有關(guān)未來的警鐘:每個(gè)人都必須高度警醒,充分發(fā)揮獨(dú)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批判地看待問題,珍惜那種看似無用和渺小的屬于人的敏感,否則得到的也許并不長(zhǎng)久,卻要面臨人類本質(zhì)漸漸消逝的悲哀。多種問題的揭示展現(xiàn)了科幻小說的人工智能書寫對(duì)社會(huì)的理性啟蒙價(jià)值,即促使人們思考技術(shù)和未來,思考人類所必須堅(jiān)定的原則和意志。因此,在文學(xué)與社會(huì)的關(guān)聯(lián)中,主體的思維得到新的拓展,順應(yīng)了后現(xiàn)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需求。
三、人性啟蒙的張力:“福柯場(chǎng)域”的破與立
談及科幻小說的啟蒙價(jià)值,常常令人將目光投向科學(xué)知識(shí)的傳遞以及上文所述多重問題意識(shí)的激發(fā),這固然根源于現(xiàn)代社會(huì)啟蒙話語的泛濫,也不能不說是忽略了文學(xué)作品所應(yīng)承載的人性啟蒙的張力。就新世紀(jì)科幻小說而言,韓松的《驅(qū)魔》通過反烏托邦敘事建構(gòu)人工智能的科幻想象,經(jīng)由“福柯場(chǎng)域”的破與立賡續(xù)了新文學(xué)之人性啟蒙傳統(tǒng)。一方面,《驅(qū)魔》描述了一艘奇詭莫名的“瘋?cè)舜保凰覞B透了“全景敞視主義”模型的“醫(yī)療船”,一座人工智能——司命統(tǒng)治的醫(yī)院。作者運(yùn)筆之間早已隱含了對(duì)人工智能的質(zhì)疑,對(duì)技術(shù)至上的批判,以及對(duì)自由意志和人性啟蒙傳統(tǒng)的肯定。另一方面,韓松密切關(guān)注“醫(yī)院”“精神病院”“癲狂”,①《韓松精選集 我一次次活著是為了什么》,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62-164頁。也關(guān)注邊緣空間和邊緣人,而且其小說的內(nèi)在質(zhì)地包含著濃厚的反烏托邦的人文關(guān)懷,這一切都令人聯(lián)想到福柯對(duì)“規(guī)訓(xùn)”社會(huì)的審視與批判。
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詳細(xì)剖析了“愚人船”載著瘋?cè)怂奶幜骼说臍v史背景和真正原因在于驅(qū)逐社會(huì)共同體的異端,并且通過水來完成具有象征意味的凈化作用。福柯通過對(duì)“愚人船”的研究戳破了現(xiàn)代文明對(duì)“人”這一概念的建構(gòu),發(fā)現(xiàn)了知識(shí)建構(gòu)背后所隱藏之權(quán)力的可怕,從而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和啟蒙價(jià)值。與放逐瘋?cè)说摹坝奕舜毕嗨频氖牵n松小說里人工智能控制的“醫(yī)療船”也載滿了被驅(qū)逐的病人。表面上看,醫(yī)療船“超出油輪,勝過航母,城池一般。不,不是一座,而是一個(gè)巍峨城市群。海天之際,盈眼滿目,皆是飄揚(yáng)紅十字旗的巨艟,浩浩蕩蕩,齊頭并進(jìn),光彩曜煜”。但是實(shí)際上,這條“醫(yī)療船”已經(jīng)難以為繼,“甲板布滿膿痰,積如雪原,病人一步一滑”。①韓松:《驅(qū)魔》,第5頁。“醫(yī)療船”的內(nèi)部運(yùn)行機(jī)制也已經(jīng)腐蝕,機(jī)器人腐朽槁爛、藥物匱乏、地下黑市橫行、病人生不如死,而那些茍活的病人卻又多是《醫(yī)院工程學(xué)原理》的忠誠信徒,早已失去獨(dú)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指出,“愚人船”的形象在15世紀(jì)文藝中的形成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種巨大不安的象征”。②福柯:《瘋癲與文明》,劉北成、楊遠(yuǎn)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第15頁。事實(shí)上,福柯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對(duì)“愚人船”的重新認(rèn)識(shí),是讓人更加接近人的本質(zhì),他指出人的理念建構(gòu)伴隨著對(duì)瘋癲的驅(qū)逐,伴隨著自覺地掩蓋和修正。“愚人船”所承載的瘋癲揭示了現(xiàn)實(shí)世界殘忍的一面,眼見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并非是完全真實(shí)的,它已經(jīng)過人為的修正。在“愚人船”已經(jīng)消散的未來,在“愚人船”的接任者——瘋?cè)嗽阂呀?jīng)完成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未來,“醫(yī)療船”這一意象的出現(xiàn),無疑是照亮了思維的晦暗深處,將病人集中起來趕到大海的孤島上,是荒誕的、恐怖的,無疑是能夠啟迪當(dāng)代社會(huì)之人反求諸己,更新自我對(duì)待疾病和病人的態(tài)度。
前面提到“醫(yī)療船”這一形象與“愚人船”的相似性及后者的象征意義,除此之外,《驅(qū)魔》里“醫(yī)療船”還是一種“全景敞視”類型的建筑。韓松筆下的司命實(shí)際上處于“全景敞視建筑”的中心,司命是住在瞭望塔里的觀察者。司命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算法,他的誕生要?dú)w因于人類對(duì)人工智能醫(yī)學(xué)的重視,但是,“算法最終會(huì)顛覆設(shè)計(jì)者的立場(chǎng)”,③《韓松精選集 我一次次活著是為了什么》,第233、235頁。司命出現(xiàn)本來是為了人類服務(wù),卻成為整個(gè)“醫(yī)療船”里病人們所敬仰的神靈。與之形成呼應(yīng)的是,韓松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遺言:“我在《驅(qū)魔》中引用了奧斯特洛夫斯基臨終前說的那句話:‘我們?yōu)橹畩^斗的與我們所建成的完全兩樣。’”④《韓松精選集 我一次次活著是為了什么》,第233、235頁。
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也不乏通過“全景敞視建筑”來建構(gòu)反烏托邦敘事的作品,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王小波的《黑鐵公寓》。小說里人人都必須住進(jìn)黑鐵公寓,接受不留隱私的全天候監(jiān)視,“全景敞視建筑”的可怕之處在于,瞭望塔里的觀察者可以隨意地窺視四周圓形建筑里的被看者的生活,而后者卻只能接受這種隨時(shí)投來的目光和綿延不絕的恐慌。此外,格非的《山河入夢(mèng)》也隱晦地借鑒了“全景敞視”模型,譚功達(dá)和姚佩佩秘密通信,自以為可以逃脫生天,甚至再次相見并生活在一起。卻不知所有的通信,所有的行動(dòng)軌跡都被躲在暗處的“眼睛”所洞察。在這個(gè)層面上,韓松的人工智能書寫構(gòu)成了鮮明的反烏托邦氣質(zhì),不但賡續(xù)了中國新文學(xué)的人性啟蒙傳統(tǒng),而且昭示了啟蒙在人工智能時(shí)代尚未過時(shí)的現(xiàn)實(shí)。在這里,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并未沿著樂觀主義者設(shè)置的路徑層層進(jìn)化,歷史最后就終結(jié)于算法,終結(jié)于未來無所不能的專制獨(dú)裁者:司命。這是韓松為人工智能預(yù)言的命運(yùn),這個(gè)命運(yùn)既是對(duì)技術(shù)的質(zhì)疑,也是人性啟蒙的呼聲——人們時(shí)刻也不能忘記那些人之為人的重要原則和追求。
整體而言,韓松小說的“福柯場(chǎng)域”書寫破的是對(duì)技術(shù)的盲目崇拜,對(duì)人性的壓抑和戕害;此外,通過“福柯場(chǎng)域”與人工智能的結(jié)合,尊重人性本身的敏感與脆弱,樹立了人性可貴的信念。人工智能所開啟的后人類時(shí)代昭示著一種社會(huì)形態(tài)和倫理道德變革的到來,科幻小說家在紛繁復(fù)雜的現(xiàn)象里敏銳地體察到人性遭受戕害的可能。也正是意識(shí)到技術(shù)對(duì)人性戕害的可能性,意識(shí)到技術(shù)烏托邦將會(huì)帶來災(zāi)難,新世紀(jì)科幻小說的人工智能書寫回歸到人性的傳統(tǒng),從而具有比以往科幻文學(xué)更深刻的社會(huì)價(jià)值。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述,基于啟蒙視角來理解新世紀(jì)科幻小說的人工智能書寫,似乎很難得出文學(xué)已經(jīng)邊緣化的結(jié)論。文學(xué)創(chuàng)造者通過自己的匠心獨(dú)運(yùn)來努力回應(yīng)社會(huì),呼應(yīng)現(xiàn)實(shí),喚醒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正如韓松所說的“曾經(jīng)科學(xué)技術(shù)離我們還有點(diǎn)遠(yuǎn),但現(xiàn)在就到了我們身邊,發(fā)生在今天中國的科幻熱預(yù)示著科幻小說已經(jīng)成為今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①丁楊:《韓松:在今天,科幻小說其實(shí)是“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中華讀書報(bào)》2019年1月30日。其中寄寓了科幻小說家的肝膽氣魄和雄圖大略。經(jīng)由人工智能題材的書寫,后人類的多重景觀蘊(yùn)含了技術(shù)與人文的思考。劉慈欣小說展現(xiàn)出未來人工智能的豐富維度,不僅有科普意義,而且通過許多問題的揭示啟迪社會(huì)思考。韓松小說則充分質(zhì)疑了人工智能的可行性,并設(shè)想人類終將陷于人工智能獨(dú)裁統(tǒng)治的可能性,通過“福柯場(chǎng)域”的破與立,破除對(duì)技術(shù)的迷戀與崇拜,重新樹立對(duì)人性和自由意志的信念。故此,其文本雖則奇詭隱晦,卻始終蘊(yùn)藉著人性啟蒙的張力。韓劉兩人的人工智能書寫,貢獻(xiàn)了不同向度的構(gòu)想、思考與啟示,一方面有助于引起讀者對(duì)人工智能這一迫切事物的反思,另一方面則從以各自對(duì)人類未來命運(yùn)的洞見參與了科學(xué)/人文啟蒙這一重大社會(huì)論域,進(jìn)而擁有不可否認(rèn)的當(dāng)下性與現(xiàn)實(shí)性。《驅(qū)魔》的扉頁上寫著:“痛苦是人類的屬性,它能證明你還活著。”《詩云》里的“神”即便學(xué)習(xí)人的愛恨情仇,即便擁有改天換地的神奇技術(shù),卻也找不到詩云里那些超越李白的詩歌。因此,在人工智能大潮洶涌而來的時(shí)代,人們應(yīng)當(dāng)萬分珍惜那些人之為人的情感,以及作為主體的自由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