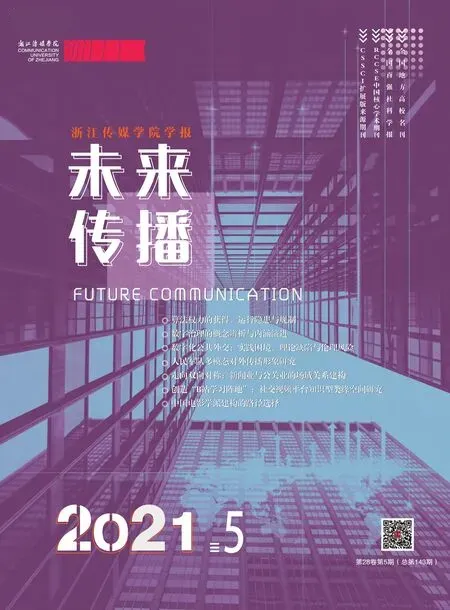是枝裕和電影新現實主義美學特征及其創新
任 萍
(浙江工業大學,浙江杭州310023)
是枝裕和是本世紀以來日本最為著名而重要的電影導演之一,尤其在繼承新現實主義電影特征及美學創新方面有特別建樹。在新現實主義電影高潮退去半個多世紀之際,以此來研究探析是枝裕和的電影及其創作,也許是更好地理解這位著名導演及其作品的一個別樣視角,對當前相對薄弱的中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創作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一、關于是枝裕和電影與新現實主義
是枝裕和是一位以拍攝現實題材影片著名的電影導演。國內外關于其影片的批評研究,一般都不會缺少現實主義的視角,不過很少談及其電影創作及作品的新現實主義屬性。就筆者進行的相關文獻檢索結果來看,近年來,只有在中國學術界,偶爾有人提到是枝裕和部分電影“有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1],進而有人將其稱為“新現實主義大師”[2]。但是,目前能夠看到國內所有涉及是枝裕和電影新現實主義概念的少量相關學術論文,大多只是給其冠以名號而已,沒有展開起碼的相關論述或闡釋。例如,有的論文顯然采納了國內之前研究者(見北京電影學院朱峰博士與是枝裕和的對談一文)關于是枝裕和是“新現實主義作者電影代表人物之一”的觀點[3],但是基本沒有對是枝裕和電影為何可以稱之為新現實主義展開闡述,甚至其相關闡釋與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思想精神毫不相符。再如,有的研究是枝裕和電影的相關論文,稱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是“一部具有‘新現實主義’創作風格的電影”,但繼而又說“該片繼續保持了是枝裕和‘后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4],將新現實主義與后現實主義等同,讓人不知所從。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北京電影學院朱峰博士發表在《當代電影》上的《生命在銀幕上流淌:從〈幻之光〉到〈小偷家族〉——是枝裕和對談錄》一文中,開篇背景介紹部分說“是枝裕和是新現實主義作者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談到了新現實主義概念,但在與是枝裕和的整個對談過程中,卻完全避開“新現實主義”這個詞,只談現實主義——當然,是枝裕和的回應也完全一樣:
“朱峰 :電影《小偷家族》展現出您在現實主義中,詩意化表達的新特點。這種詩意色彩,是通過運用一些抽象的視聽元素加以外化的。
是枝 :是的。電影《小偷家族》在創作中增加了許多不同于以往作品的處理手法。我以前的作品,大多著力運用現實主義的手法進行創作。《無人知曉》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小偷家族》非常不同的一點是在電影的現實主義底色中增加了寓言性這一特征。
朱峰 :可以具體談一下這個寓言性嗎?
是枝 :比如說,給那個家族,一層一層疊加在電影里的,引用過的作家李歐·李奧尼所著童話《小黑魚》的那種感覺。電影30分鐘處,深夜在停車場,父親和兒子在追逐嬉鬧。那個景致是充滿藍色光暈的,看起來就像是水底一樣。電影70分鐘處,一家人仰望看不見的煙花,也給人一種從海底仰望水面的印象。”[5]
也許有人會說,朱峰所謂“詩意化表達的新特點”,是枝裕和自己認為他的電影在“現實主義底色中增加了寓言性這一個特征”,不就成為一種新的現實主義嗎?這樣的理解表面上看并非不可,但其實與新現實主義特定內涵完全不是一回事。作者在既無鋪墊、亦無論證的基礎上就對是枝裕和電影特色進行了“新現實主義”+“作者電影”的表達,難以令人信服。
相對而言,朱曉豐、袁萱的論文有一些試圖對是枝裕和影片與新現實主義電影進行比較的探討分析:“是枝裕和對細微的觀察,經歷了一個成長的歷程。這其中,有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關于電影《偷自行車的人》,是枝裕和對片尾的三次觀影感受都不同。小時候看,是枝裕和覺得偷自行車的父親在兒子面前被捕是一個悲劇。大學時候,卻覺得車主放過了父親非常溫暖。而第三次觀看,是枝裕和將注意力轉移到了影片結尾的一處細節,父親耷拉著肩膀無精打采地走著,兒子走近,拉住了父親的手。父親無法面對兒子,這只溫暖的小手,像刀一樣捅破了父親的心臟,看似溫暖的牽手卻比被捕還要殘酷。”[1]筆者以為,也許是枝裕和確實是這樣認為的,但這樣的認為及相關研究的解讀,其實不太符合新現實主義思想精神及美學理念。從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創作視角及思想精神來看,這普通父子之間的溫暖牽手,就是他們父子之間充分的理解和善心的溝通,就像該影片中父親帶兒子去餐廳用餐那個片段所能表達的父子情深一樣。因此,這種溫暖應該解讀為是兒子對父親表示理解的親情溫暖,并且與影片中那些決定不追究父親里奇偷自行車行為的人間溫暖一樣,都是那個特別艱難的時代中社會普通人中間依然存在的特別感人的溫情與力量——這才完全符合新現實主義思想精神及美學理念。
從邏輯上來說,有新現實主義電影,就應該有舊現實主義電影。相對而言的舊現實主義電影,在歐洲大陸曾經被稱為“通俗化”電影,具有“平民主義”傾向,也受到強調影像真實與生活真實渾然一體的紀錄電影的美學影響。由于各方面原因局限,舊現實主義電影在歐洲大陸并沒有取得很好的成績(尤其是對于普通人乃至社會底層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做得不夠好),也沒有獲得很大的影響。[6]在世界電影發展歷史中,關于新現實主義電影有特定所指及特定含義。其表現在創作層面,比如“新現實主義創作六原則”:用日常生活事件來替代虛構的故事;不給觀眾提供出路的答案;反對編、導分家;不需要職業演員;每個普通人都是英雄;采用生活語言(方言)。[7]在其文化核心要義方面,國內外專家都十分強調其思想內容的進步性。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導演魯奇諾·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觀點鮮明地指出:“新現實主義首先是個內容問題。”[8]邵牧君先生認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這個電影藝術運動同時也是一個具有強烈的社會進步和民主傾向的運動。”[8](84)倪祥保教授則更具體地特別強調了新現實主義電影“積極反映社會民生現實,自覺表現社會普通人日常生活及美好人性,努力關注影片的社會接受效應,既體現了社會進步思想、民主傾向,又產生了難能可貴的文化價值及傳播影響”[9]。
基于以上目前主要可見相關學術論述情況及關于新現實主義電影的一般認知來看,關于是枝裕和電影中的新現實主義學術研究,迄今為止其實在國內外都還沒有真正開始。本文在此不僅嘗試從新現實主義電影美學角度闡釋是枝裕和的部分電影創作及特色,而且努力闡釋其對新現實主義電影美學的某些創新發展,希望能為學術界提供一得之見,同時獲得專家和讀者的批評指正。
二、是枝裕和電影新現實主義美學主要特征
國內外世界電影史學家對于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研究,已經達成很多共識。其中,關于影片故事內容更多來源于現實生活,強化紀實風格,積極關注底層人群并對他們給予更多同情及贊賞的態度,直面社會問題而不局限于解剖和批判,提倡編導合一等等,都是非常核心的內容。是枝裕和的很多現實題材電影創作,在這些方面或多或少相符,盡管他本人也許沒有自覺意識到其現實主義電影創作事實上具有一定的新現實主義特征——因此他與北京電影學院朱峰博士對談的整個過程中,完全沒有強調自己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具有一般意義上的新現實主義特征。
是枝裕和電影新現實主義的創作屬性及審美表達之一,是故事一般都基于現實社會新聞事件,并且在創作過程中盡量貼近相關的現實生活景象,即努力于一切仿佛如生活一樣的做法。例如,影片《無人知曉》以一則“道西巢鴨棄嬰案”的真實報道作為其影片的創作素材;《奇跡》以九州新干線全線開通為相關題材;《如父如子》受到記錄20世紀70年代日本多起嬰兒錯抱事件的報告文學啟發而創作;《小偷家族》的創作啟發來源于一則一家人賣掉所有盜竊的物品卻因保留盜竊的魚竿而事發被捕的新聞;《步履不停》和《比海更深》的電影故事則是根據作者自身經歷而創作的。事實上,諸如這樣向現實社會生活俯拾即是地獲取故事來源的電影創作方式,世界各國都有,但是就電影發展史來看,一個導演如此多的影片都特別青睞于將底層社會普通人的真實事件改編成電影,并不多見。由此可見,是枝裕和創作電影的基本理念,事實上在遵循新現實主義電影直接面向現實社會生活、努力表現普通人故事的基本創作理念及方法。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解釋為什么是枝裕和影片的故事展開和情節設計,沒有特別描寫戲劇性起伏,而是幾乎像日常生活那樣按部就班。這使得是枝裕和的影片創作及故事講述,與真實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是枝裕和應該希望通過這種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使觀眾感受到真實的社會生活與人生故事。值得強調的是,是枝裕和曾經有過這樣的明確表達:“生活就是這樣,千瘡百孔中也會有美麗的瞬間。我想捕捉的正是這些瞬間。”[5]這其實非常符合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內在屬性和審美特征。在他的影片中有很多與之完全呼應的相關情景處理。比如《小偷家族》中,影片以俯拍方式表現一家人夜晚時分聚在一起仰望天空的畫面,既可以理解為表達他們對未來生活充滿美好憧憬和祈求,又可詮釋為上蒼也看到了毫無血緣關系的組合家庭所有成員真實而溫馨的內心。毫無疑問,這樣的創作手法、美學理念和人文思考,同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思想內涵及創作手法如出一轍。
在努力使自己成為一部影片的編劇與導演方面,是枝裕和也許是世界電影史上相對不多的成功者之一。他的相對成功,不一定是編導合一做得無人能比,而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有如此多的影片都由自己編導合一來進行創作,而這一點,正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所倡導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優秀電影創作的一種成功方法——導演至少要提前成為編劇之一。1998年,是枝裕和自編自導的《下一站天國》在30個國家上映,被視為史無前例熱映的日本電影。之后,《無人知曉》《步履不停》《奇跡》《如父如子》《比海還深》《第三度嫌疑人》《小偷家族》等是枝裕和自編自導的電影作品受到日本國內以及世界各大電影節的普遍認可,特別是2018年自編自導的《小偷家族》一舉榮獲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第91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第44屆法國凱撒獎最佳外語片獎,在第42屆日本電影學院獎中榮獲最佳影片獎等8個獎項。這些成就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影片細膩表現出“家庭”這一人類社會基本單元的豐富存在形態,激發人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及人生現實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因為編導合一的創作方式有利于他自覺遵循新現實主義電影對于百姓生活、人文關懷的更好表達。
是枝裕和電影創作的新現實主義理念及方法,使得作品傳播影響不斷擴大。正如是枝裕和自己所說:“電影能讓人緩慢地改變,其結果是世界緩慢地變化。”[10]這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因為他的電影創作特別關注底層人群,積極直面社會問題。是枝裕和的電影作品重視取材于生活,因而很容易獲得比較好的社會性,同時還因為這些故事反映了現實底層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而吸引人去觀看和思考。是枝裕和喜歡圍繞某個真實事件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將現實社會中出現的眾多問題逐一疊加到這個事件中,使電影作品的故事得以豐富。例如《無人知曉》中,男人拋棄女人,女人拋棄孩子,生而不養,鄰里對這些無法自食其力的孩子也視而不見,任其自生自滅,在不負責任的一群大人的熟視無睹下,兒童們就這樣成為無人關注乃至無人知曉的社會存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又進一步擴大了如此不可清晰感受并看到的人群:奶奶初枝、父親治、母親信代、姐姐亞紀、弟弟祥太、妹妹百合,他們每個成員其實都脫離了“地域”“企業”“家族”等原本應有的社會共同體,或者說被那些社會共同體無情地排除在外,成為社會邊緣人。因此,他們每個成員都是某種社會現象或某個社會問題的直接而生動的反映。在《小偷家族》這部優秀作品中,是枝裕和集中反映了貧困問題、虐待兒童問題、獨居老人問題等當代日本社會客觀存在的生活現實及社會陰暗。其與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相關的社會思想內容,溢于言表而發人深省。
是枝裕和具有新現實主義屬性的電影創作,有一點很特別,那就是通過登場人物的語言針砭時弊地指出許多社會問題——這與新現實主義電影注重表現社會普通人在生活艱難困苦中依然保持人性之善和向上的思想有所不同。雖然,是枝裕和表示自己從來沒有以表揚或者批評為目的制作電影,但是他的作品總有一針見血的臺詞指出這個社會的弊病——這其實無異于關愛社會底層艱難人群的一種特殊表白,也無異于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別樣表達。比如在《比海更深》中,良多一邊坐在地板上從父親祭壇的香爐灰燼中挑出焚香中剩余的殘渣,一邊和母親聊天。母親告訴良多:“你以為你焚的香就能帶回你父親嗎?人走了以后,再深的思念也無法把他帶回來了,應該在人活著的時候用心對待他們。”《小偷家族》中,信代因為要主動承擔收養百合的責任而被捕,審訊員說:“孩子都是需要母親的。”信代回答說:“生下孩子就自然成為母親了嗎?”通過這樣的臺詞,是枝裕和或是赤裸裸地揭露了這個時代的社會問題,或是對某些社會人表現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無奈,或是贊美社會普通人的人性之善,同時希望社會不斷向善。總之,是枝裕和電影將社會現實批判與憧憬美好社會的人文情懷很好地糅合了起來。
三、是枝裕和電影新現實主義美學創新發展
國內外研究專家大多有這樣的共識: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最大特征在于內容,是枝裕和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創新發展也首先體現在影片內容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枝裕和影片的新現實主義美學特征,具有今天一般意義上所說的“守正創新”。
是枝裕和的作品總是被認為具有濃厚的社會性思想意義,比如那些既是“家庭電影”又是“兒童電影”的影片,既涉及人類文藝創作的普遍主題,也表達新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從處女作《幻之光》(1995年)到在法國拍攝完成的最新作品《真實》(2019年),是枝裕和共拍攝了15部故事片,其中以家庭為題材的作品有13部。是枝裕和認為,現代社會中“大家都住在同樣的家里,穿著同樣的衣服,在同樣的價值觀中生活,這種‘安心’實際上是人類失去了作為生物的多樣性的非常不健康的狀態。”[11]因此,他“一直想通過制作影像與社會和世界產生聯系,激發人們的想象力。”[12]是枝裕和通過豐富的想象力,以電影為媒介為人們展現了世俗眼中非一般形態的豐富別樣的家庭樣態。是枝裕和在影片中一直反復呈現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親情與隔閡、生命與死亡、記憶與創傷、喪失與和解等主題,這使得他的影片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表層,凸顯出生命中更具有普遍意義的難題,并嘗試給出他獨有的思考。[13]
是枝裕和的電影特別注重反映多層面社會“共同體”的變化,常常展現現實社會中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稀薄,單身群體增加并最終走向孤獨死的“無緣社會”現象。是枝裕和作品在多次展示這一問題的同時,也在深入思考人們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以及應該如何解決這樣的社會問題。如果說《幻之光》通過讓觀眾從逐漸消失的住在郁夫和由美子隔壁的老爺爺“活著的信號”中感受到死亡的到來,比較含蓄地表現了獨居老人的孤獨死現象,那么《比海更深》則清晰地揭示了獨居老人孤獨死的悲涼。良多回到母親家時,鄰居提到有個孤寡老人死了三周都沒人發現,小區廣播里正播放老人走失的新聞。這些細節都揭示了獨居老人的孤獨死問題。《小偷家族》中,奶奶初枝的角色設定展現了害怕孤獨死的獨居老人會走向何方——征地者來到初枝的家里勸說她搬進養老院,告訴她鄰居家的老奶奶雖然有三個子女,但無人贍養,已經搬入養老院。除了現實生活中無奈搬進養老院之外,是枝裕和依靠豐富的想象力為初枝構筑了一個不同常態的“小偷之家”。在這里,初枝不僅有人照顧,還得以享受子孫滿堂、承歡膝下的天倫之樂。這樣的故事內容實質是新現實主義的,但又具有日本當下社會在地性,因此表征著一定意義上的創新處理及與時俱進。
新現實主義強調關注社會普通人,但不怎么聚焦家庭和兒童。尤其兒童,本來不是新現實主義電影特別關注的重點,但在是枝裕和的電影中,社會普通家庭和生活艱難的兒童則成為其鏡頭聚焦和情感關注的重點——這構成了是枝裕和電影與一般新現實主義電影社會關注點的不同,或者可以說是枝裕和電影的創新、發展與深化。是枝裕和廣義的“兒童電影”或者說是“兒童問題電影”特別關注日本當代社會中的兒童問題。比較典型的代表作品是《無人知曉》,其中的明和京子為了照顧弟妹,二人承擔了原本該是父母承擔的維持生計和操持家務的責任。《海街日記》中,由于父親的出軌和母親的再嫁,三姐妹被家庭遺棄,大姐在祖母去世后擔負起照顧妹妹們的責任。還有《小偷家族》中被父母遺忘(棄)在車里的祥太,被母親虐待的百合。比較耐人尋味的是,導演在充分暴露兒童問題的社會原因時,又常常講述有人愿意為此提供幫助乃至庇護,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將揭露與贊美融為一體。這或許是社會常態之一,或許是導演特別珍視和內心充滿憧憬的真情所在。《無人知曉》中通過援交幫助明一家的紗希,時常關注著明的超市售貨員姐姐,還有總是偷偷拿臨(過)期食物給明的超市售貨員小哥。《小偷家族》中,信代為了百合不再回到那個沒有母愛的家庭,不惜以要殺人來威脅聲稱會把百合的事說出去的人。諸如這樣的情節安排,雖然不同于傳統的新現實主義電影處理,但導演內心深處流露出來的道德褒貶意味及人文關懷精神,似乎與新現實主義電影并無二致。
四、是枝裕和電影新現實主義美學歷史比較
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特點之一,是在充分暴露各種社會問題的同時,展現對社會發展的信任與希望,期盼社會和人性回歸向善,尤其注重贊美社會普通人的良善品性。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早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出現的中國新現實主義電影,有更多反映底層百姓生活并且贊美肯定其善良本性及家國情懷的影片面世。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誕生于二戰結束之際,無論是贏得戰爭勝利還是建設滿目瘡痍的社會都離不開人民群眾,電影藝術家更多著力表現社會普通百姓的內心向善和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努力。同時,客觀上因為缺乏足夠的專業人員、先進的拍攝裝備,不得不提倡編導合一、大量起用非職業演員、采用更接近現實生活景象的拍攝。
拍攝紀錄片的經歷,使得是枝裕和的很多電影畫面情景都自覺不自覺地注重紀實,不怎么刻意追求畫面景觀的光鮮亮麗——這其實不僅是現實主義的,也更是新現實主義的。除此之外,是枝裕和影片在描寫傳統家庭構造解體后出現諸多社會問題的同時,努力尋找解決或緩解這些問題的途徑,體現出特別有社會文化價值的思考及表達。相對而言,這也是是枝裕和電影新現實主義表達與一般新現實主義電影美學比較所具有的不同所在。是枝裕和拍攝了不少事實上既是“兒童電影”也是“兒童問題電影”的影片,其實都與家庭密切相關。當然,他也拍攝了不少直接關于日本當代社會家庭問題的影片。他曾經這樣說過:“在一個家庭里面, 母親一直在家, 她通常會去批評孩子。但是如果連父親也批評孩子的話, 孩子不就沒有逃避之處了嗎?如果家里有爺爺奶奶, 孩子被兇之后還能跑去找他們, 這種不是垂直而是斜向的關系, 我覺得很重要。真正的家庭, 應該不是只有家長和孩子, 還應該有爺爺和奶奶。”[14]《無人知曉》中,祖輩的不在場讓孩子們失去了賴以成長的最后保障。與此相對,《海街日記》中三姐妹的成長雖然遭遇父母的拋棄,但外婆的庇護讓她們能夠順利長大。是枝裕和關于家庭的思考和對傳統家庭回歸的期盼,在《小偷家族》中有深刻的表現——很多基于血緣關系的家庭反而不如小偷們無血緣關系組合的家庭更像一個理想家庭的表達及思考。比如,作為父親的柴田治對作為兒子的柴田祥太在一家人去海邊游泳時很自然地進行正常的性教育——這自然是家庭教育的正常內容——這在現代很多完全具有血緣關系的家庭中反而是缺失的。這樣強烈的社會批判意味,又與意大利和中國的新現實主義電影都有所不同,但卻很好地體現了更具當代性的社會批評思考與強烈的人文情懷。
是枝裕和經常通過日本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行為“祭祀”與“沐浴”場景來構筑家人之間的親密關系,這與是枝裕和影片中“并非只靠血緣維系的家庭關系”這一重要思想主題聯系在一起。以自己家的仏壇和神龕為中心舉行的家庭祭祀,是日本人經常和最主要的祭祀。參與祭祀的家的成員可以是非血緣關系者,血緣關系并不是構成家的唯一紐帶。[15]是枝裕和電影中幾乎都有關于祭祀的場景,往往以家庭男性成員的死亡、葬禮或忌日作為故事開端和情節驅動。[16]《步履不停》中,哥哥純平的忌日,母親帶著良多、由香里和淳史一起去掃墓。多年后良多帶著家人去給父母和哥哥純平掃墓,通過掃墓,良多實現了與父親和哥哥的和解,心里不再為父母對死去哥哥的偏倚而感到不滿與計較。《海街日記》中,鈴來到姐姐們的家里后,三姐千佳帶她到外婆靈位前祭祀。外婆忌日時,回來祭祀的母親臨走前和幸一起去給外婆掃墓,在那里母親獲得了幸的諒解。是枝裕和電影中的亡者通過生者對他們的祭祀,即使在他們死后,仍能繼續發展與生者之間的關系。是枝裕和還通過讓登場人物共享沐浴時光作為促進親情發展的場景。《步履不停》中,良多和繼子淳史一邊沐浴一邊聊天。《如父如子》中,雄大和慶多一起沐浴,關系融洽。《小偷家族》中,信代和百合一起沐浴,百合發現信代的手臂上有和自己一樣的燙傷疤痕,增進了兩者之間的理解以及惺惺相惜。這種不是親情而勝于親情的情節處理,平淡而悠遠,是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當代日本表達。
一般來說,新現實主義電影因為特定歷史發展階段民生艱難而出現(比如意大利在二戰剛結束時的民生艱難和中國的民族危亡之際),但是枝裕和電影的誕生背景不是這樣。具體來說,是枝裕和相關電影的新現實主義電影創作,主要來自導演個體對現實社會的思考,并不與某種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關。這也就是說,是枝裕和電影的新現實主義屬性,更多來自個人對社會現實的有感而發。隨著日本經濟發展,生活成本提高、職場工作壓力加大等原因,傳統家庭關系的弱化傾向日益凸顯。不婚、不育家庭增多,離婚率增高,傳統家庭養老優勢喪失。日本社會進入“上不必養老,下不想養小”的狀態,而一個國家中既不想承擔家庭責任,也不愿承擔人類再生產社會責任的人多了,談何可持續發展?[15]正如同在現代社會中其他種種面臨危機的傳統價值和組織形式一樣,家庭作為最親密也最為天然的情感的依托也處于岌岌可危的境遇里。[17]現代倫理對傳統倫理的僭越體現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現代都市單元結構層級上,主要由傳統的注重宗法和地緣紐帶關系變為注重契約與規則意識的現代城市“陌生人倫理”的誕生。[18]是枝裕和通過《海街日記》《小偷家族》這樣的作品嘗試探索家庭的新型變體,這種嘗試基于傳統家庭的背景以及對傳統家庭回歸的憧憬。導演將目光投注于影片中每一個平凡普通的家庭,用樸實的敘事手法、紀錄-片式的拍攝方式,捕捉生活中的本真與人的精神,試圖給現代家庭關系及發展尋找更好的答案與出路。
五、結 語
日本著名導演是枝裕和的影片,不僅其故事較多來源于社會現實生活,特別關注當下日本社會傳統家庭發展變化,關注兒童現實生活和無緣社會(1)“無緣社會”這個詞源自日本NHK電視臺拍攝播出的紀錄片《無緣社會——3萬2千人無緣死的沖擊》,主要指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稀薄,血緣、地緣、社緣崩潰后,單身群體增加并最終走向孤獨死的社會現象。問題,而且往往帶著贊美與肯定的意味去表現影片內容及相關人物,這使得其影片在思想文化方面與新現實主義電影內在相通。由于當代社會歷史的發展、日本現實社會語境的不同和導演人文思考的獨特,是枝裕和帶有新現實主義電影特征的創作,非常自然地形成不同的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方向及思考成果,表現手法也與眾不同。所有這些,都使得是枝裕和電影所帶有的新現實主義思想精神及審美表達別具匠心且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