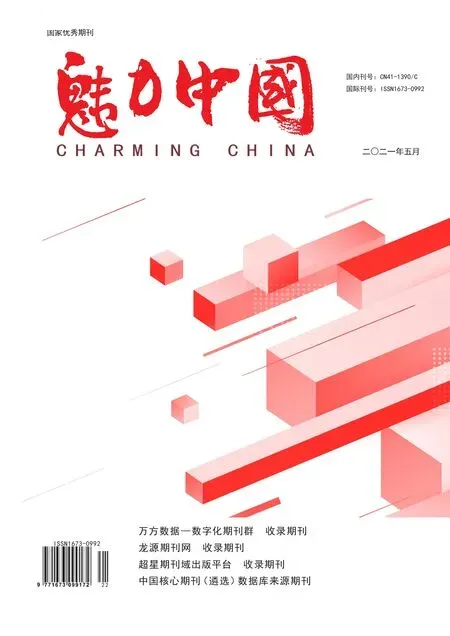從《九人宮女圖》看唐代的包容氣度與開放胸襟
程千金
(乾陵管理處,陜西 咸陽 713300)
繪畫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源,在彌補文字史料的不足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而壁畫則是古代常見的繪畫形式。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壁畫被發現,成為歷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圖像資料,其中,《九人宮女圖》是唐代歷史研究中經常提到的壁畫之一。《九人宮女圖》也稱《九宮女圖》,發現于唐高宗乾陵的陪葬墓---永泰公主墓,以內容豐富、人物形象精美而著稱,不僅有著獨特的藝術價值,更是今人了解唐代歷史文化風貌的重要載體。
一、基于服飾發式妝容的分析
(一)《九人宮女圖》的服飾
除漢族傳統服飾中,《九人宮女圖》中尚有胡服的身影。胡服為少數民族服飾的統稱,早在戰國時期便有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美談。唐代國力強盛,文化極為開放,少數民族服飾乃至異國服飾廣為流行。正如沈括所言,“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1]。”《九人宮女圖》中的胡服主要體現在畫面最右側懷抱包袱的宮女身上。該宮女身穿男子袍服,袖緊窄,領為翻領,下身為至膝蓋以下的窄袖小袍,腳上則穿著短靴,具有非常濃厚的胡風。不僅如此,該宮女也是《九人宮女圖》中唯一佩戴帽子的宮女,并且,所戴帽子為少數民族以動物之皮制作的渾脫帽。該宮女的服飾與唐代的時代環境和文化氛圍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唐代民族政策開明,少數民族在唐朝任職的不在少數,他們帶來了胡服,并推動了胡服在民間的流行,另一方面,唐代是中國古代女性地位最高的時代,唐代女性“具有不同于中國封建社會其他朝代女性的社會風貌”[2],以女身而穿男服、胡服,正是鮮明的表現。
(二)《九人宮女圖》的發式
愛美是女性的天性,唐代女性更以愛美而著稱。唐代女性的發式繁多,常見的有驚鵠髻式、反綰式、螺髻式等。《九人宮女圖》中的發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螺髻式。這種發式以發髻如同螺殼而得名,具體做法是先用絲絳將頭發固定,使頭發帶垂腦后,再用盤卷的方法將頭腦盤在腦上,有如螺形。圖中手持拂塵、如意、方盒的宮女均為螺髻式。另一種是反綰式。這種發式是一種雙高髻發式,具體做法是從頭的兩側分別引出一縷頭發向腦后反綰,再將頭發高聳于頭頂,能夠使頭發不蓬松下垂。無論是螺髻式,或是反綰式,均屬于高髻式,以發髻高為主要特點[3],而發髻高則可以使人物形象看起來更為婀娜、修長。《九人宮女圖》中的高髻體現了唐代女性自信樂觀、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也彰顯了唐代開放的文化氣度。
(三)《九人宮女圖》的妝容
《九人宮女圖》中宮女的妝容同樣體現了唐代包容氣度和開放胸襟,尤以眉毛的修飾最具特色。早在戰國時期,女性便有畫眉的習慣,唐代,畫眉更在女性中風靡,如朱慶馀詩中的“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九人宮女圖》中宮女畫眉以闊眉為主,此一樣式的畫眉以眉毛細密且闊為主要特點,能夠使女性的儀容富有英氣。如圖中捧杯的宮女,左右眉毛用線多達五筆,且微微向上傾斜,凸顯了唐代女性地位較高,不讓須眉的文化氛圍。當然,《九人宮女圖》的妝容既有英氣逼人的一面,也有女性婉轉柔美的一面,最為典型的便是唇容。《九人宮女圖》中唇容為點唇,即用點的方式將唇脂點于唇上,具有較小秀麗之感。
二、基于造型特色的分析
(一)《九人宮女圖》的神態
多人多面是《九人宮女圖》最大的藝術特點,作為一幅群像創作,《九人宮女圖》中共有九個不同的宮女,如何讓每個宮女都生動活潑,躍然紙上,對畫家的技法有著很高的要求。畫中的第一位女子雙手隱于袖中,面露一絲微笑,步履輕盈松快,從其在畫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并未手執任何物件來看,她應為宮女領班。左起二、三、四宮女在小心地交談著什么,特別是手持蠟燭的宮女,眉頭緊鎖,極為專注。第五位手持團扇的宮女,用團山擋住了右臉,嘴角微微泛起,仿佛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而最后一位宮女則男性裝扮,面色凝重,極富個性。《九人宮女圖》賦予了不同宮女不同的神態,使每個宮女均栩栩如生,這既和畫家個人的刻意追求有關,也和唐代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有關。唐代是個人精神高揚的時代,也是女性解放的時代,唐代女性身上不僅有女性婉轉的一面,也有勇于挑戰、斗志昂揚的一面,中國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便出現于唐代。
(二)《九人宮女圖》的身姿
《九人宮女圖》的身姿最大限度地呈現了女性身姿的曼妙婀娜之美。圖中宮女身段造型為曲線型,即S 型,有苗條勻稱、輕盈靈動之美。不僅如此,S 型身姿也明顯地增強了畫面整體的節奏感,使畫面富有靈氣,打破了平面造型在人物傳達中的僵硬感。根據郭嵐的分析,《九人宮女圖》的宮女的S型身姿和外來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有很大的關系[4]。唐代皇帝雖然以老子李耳后裔自居,而武則天則信奉佛教。武周時期,佛教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佛教造像對畫工也帶來很大的啟發。印度人極善歌舞,佛教造像有輕盈靈動之感。畫工將這種輕盈靈動之美融入到傳統的仕女圖中,催生了S 型身姿。國傳統繪畫講究隨類賦彩,即根據繪畫對象的不同而賦予不同的色彩,并且,不同于西方繪畫注重物體顏色的再現,中國傳統繪畫追求單一色彩的運用。《九人宮女圖》中的色彩運用總體較少,主要為朱紅、蛤粉、石綠、墨等大塊顏色,這些顏色無一例外具有視覺刺激性強的特點。以紅色為例,先秦時期我國便形成了尚紅的傳統,紅色在民間更有喜慶、熱鬧的含義。《九人宮女圖》中宮女的服飾以紅色為主色,極為引人注目。盡管《九人宮女圖》所用的色彩并不多,但卻具有絢爛飽滿之感。畫工單一色運用的同時,也注重色彩間的對比,通過冷暖、虛實、明暗等對比方式,使得畫面整體的色彩風格具有典雅自然的氣息。
三、基于社會文化的分析
(一)以豐腴為美
一直以來,中國對女性的審美都是以纖瘦為美,如戰國時期的“楚王好細腰”,唐代對女性的審美則以豐腴為美,這和以前朝代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如魏晉繪畫中,女性多“秀骨清象”。以豐腴為美是唐代國力強盛的一大特點。初唐時期,在唐太宗的勵精圖治系,唐朝一片繁榮,并出現了貞觀之治的盛世。《九人宮女圖》中的宮女恰如當時的唐朝,正處于冉冉升起的階段,以青春活力而著稱,特別是豐腴圓潤的面部,體現出一種自信,而服飾妝容等,則具有強烈而又鮮明的時代感,彰顯了唐代的開放胸襟。
(二)文化兼容性強
唐代是古代最為開放、包容的時代,甚至連皇家私事也可街談巷議,如“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極強的文化兼容性是《九人宮女圖》中唐代包容氣度與開放胸襟的重要成因。首先,儒釋道合流。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是我國的傳統思想,自先秦以來,代代傳承,其中,儒家思想是統治者推崇的思想,而道家思想則在知識分子中間有著很大地與影響力。佛教東傳后,佛教思想廣為流行,并在士大夫群體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次,外國文化雜糅。唐代開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強盛的國力使得少數民族乃至異國人士雜居長安,他們帶來了頗具異域風情的文化,如《九人宮女圖》中的渾脫帽。
(三)強烈的進取精神
具有強烈的進取精神,特別是初唐、盛唐時人,進取精神更為強烈。唐代詩人多有建功立業的渴望,不少詩人均留下了大量的邊塞詩作品,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唐代的進取精神。《九人宮女圖》中流露出來的唐代的包容氣度和開放胸襟與唐代的進取精神有著密切的關系。《九人宮女圖》雖為反映宮女的作品,但圖中的宮女形象和以往封建王朝的宮女形象有著很大的差別。最為典型的便是宮女形象的“男性化”特征。圖中宮女,既有穿著男裝的形象,而這一裝扮在當時并不稀罕,現存繪畫中,不少反映了唐代女著男裝的風氣,也有具有男性英武陽剛之美的畫眉形式,體現了巾幗不讓須眉的進取精神。
四、結語
唐代是我國封建王朝中國力最為強盛的朝代,唐太宗更有“天可汗”的稱謂。強盛的國力使得唐代的文化氛圍極為開放,形成了封建王朝中少見的包容氣度和開放胸襟。時至今日,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反映唐代歷史文化風貌的文物出土,而《九人宮女圖》則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種。《九人宮女圖》不僅形象生動地刻畫了九位宮女,更在服飾、妝容、身段等中表現出唐代的包容氣度和開放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