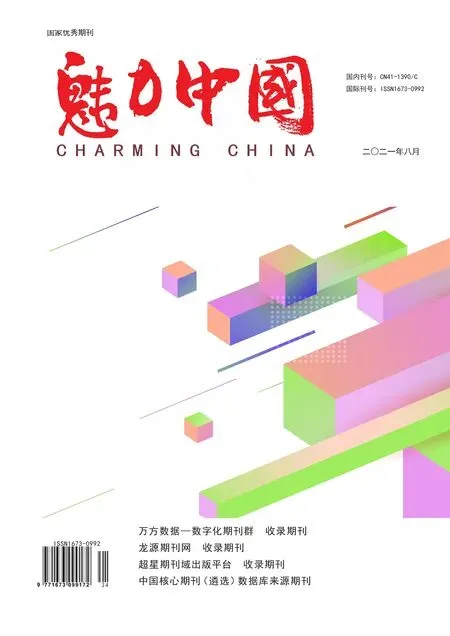淺談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問題
陳曉紅
(合肥市土地整治辦公室,安徽 合肥 230071)
人工智能著作權的歸屬問題是當下相關行業討論的焦點問題,如基于人工智能技術所產生的作品是否能夠被著作權法所保護,以及人工智能著作權的認定以及歸屬問題等。立法層面、司法層面、理論、制度和實踐層面如果能以切合實際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就能夠給予人工智能作品更好的發展前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一、人工智能著作權身份認定問題
當今社會科學技術迅速發展,人工智能作品也逐步滲透到了人們的生產生活中,但是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并未對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給出明確的定義。在我國的著作權法中,著作權歸屬的原則是作者享有著作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二條 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為作者,且該作品上存在相應權利,但有相反證明的除外。在我國的著作權法中,對于著作權歸屬的認定標準為:以作者以及署名為基礎進行著作權歸屬認定,在認定的過程以確認相關人員實際參與了作品的創作為基礎。
國外的做法:在美國的相關法律法規中,明確表示了一切非人類作品都不享有著作權,在另外一個層面,美國對于人工智能版權的認可是基于人工智能是有人類創作的原則。在日本的相關機構,近年來已經開始對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權的相關問題展開一些保護計劃,相關機構期望以立法的方式對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進行保護,比如,相關機構正在以商標保護制度為依據,設計建立一種能夠保障人工智能作品合法權益的保護制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以及民眾已經開始重視人工智能作品對人類作品的沖擊。由此可以看出,這些相關規定都沒有對于非自然人擬制作者的擬制創作進行否定,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給人工智能作品的創作場合很大的預留空間,因此,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今天,國內外的相關部門應該及時對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權的相關問題作出明確的解釋以及界定[1]。需要注意,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著作權歸屬與傳統形式創作作品的著作權歸屬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這些不同點對人工智能作品的主體創作角色定位以及著作權的歸屬認定有一定的影響。
通過系統歸納,人工智能在近幾年的發展十分迅速,并且其也在相關領域展現出了非常強大的發展勢頭,同時,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也給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條件,因此應該對人工智能作品進行合理的保護,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將其納入法律軌道,讓其在法律的軌道內發展,這樣可以避免由于法律法規不健全引起混亂問題。另外,在對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人進行認定時,應該要進行全方位的考慮。人工智能作品牽涉到研發者,所有者,使用者等各類人員。要關注到對各類人員權益的保護。
二、人工智能著作權歸屬制度面臨的挑戰
人工智能是由人類研發出的能夠自主分析問題,處理信息程序的產品,并且該產品能夠獨立自主的進行學習并且生成新的作品。在現階段,雖然還未確定人工智能是否能夠完全脫離人類生成新的作品,但是對于人工智能來說,人類只不過是輔助其工作的角色[2]。
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是帶有特殊性質的。在工業革命時代,之所以人類的物質生產得到了加速,是由于人類用機械設備代替了手工業;在信息技術革命時代,之所以社會需要得到了有效滿足,是由于人類用高科技設備代替了人類自己分析處理信息。創作者的意志是通過其創作的作品體現出來的,可是人工智能創造的作品很難能體現出人的意志,更不能夠體現出人工智能的意志,因此不能因為人工智能的主體資格被否定,就否定其作品的意志,但是如果法人在法律上可以被擬制為“人”,那么人工智能的著作權問題也可通過法律擬制的途徑解決。
在現階段,從外觀上已經無法區分人工智能的作品和人類的作品,但是人類的創作速度與人工智能的創作的速度無法相提并論。據調查,相關人工智能軟件可以用不超過一分鐘的時間,完成一篇將近1000字的新聞稿子,或者在接收到一張圖片后,可以快速地根據圖片的意境做出一首詩。由此,人類擔心如果人工智能作品可以合法的獲得著作權,那么人類創作在競爭中就會處于弱勢地位,社會經濟利益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3]。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權承認與否如同一把雙刃劍,承認其享有著作權無疑會打擊人類的創作激情,但是如果人工智能作品不被認定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有可能會產生道德風險,即人們會隱瞞人工智能創作的事實。
三、人工智能著作權歸屬問題
人工智能著作權的歸屬問題大致可以分為編程者以及操作者獨立權說、虛擬法律人格說等一系列理論,以此來對人工智能作品版權的合理性進行解釋。筆者認為,在未來,應該承認人工智能在法律上的主體地位,也就是說承認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權。
(一)理論基礎
人工智能的產生就像計算機的產生一樣,是人類發展的結果,人工智能創作作品在給人類創作帶來競爭壓力的同時,也可以增加人們的知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類科技文化的發展。人工智能作品的大量增加,對人類來說不僅有效地減少了其在相關方面的勞動投入,其還可以吸取人工智能作品的精華,從而創作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人工智能的設計以及生產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工智能的學習來源。由于人工智能的算法來源于人類,這就使人工智能著作權的歸屬更具復雜性。事實上,人工智能的創作過程并不是人類所能決定的,其具有自身主導性,也就是說人類對于人工智能作品的輔助性十分有限[4]。雖然人工智能無法感受著作權對其的激勵,但是人類可代理人工智能,可以激勵人類積極地對人工智能進行開發,同時還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有益知識的增加,這也符合著作權法的激勵精神。
(二)認定實踐
在20 世紀90 年代,美國版權局對至少兩份計算機創作的文字作品進行登記,并且授予了版權。美國版權局將編程者作為了版權人,把計算機軟件作為了作者。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的相關機構把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著作權歸屬于人工智能的創造者。
在日本,相關機構將著作權賦予有思想以及感情的創作作品,因此人工智能所創作出的作品,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5]。但是人工智能作品也可能存在侵權和被侵權的現象,所以日本相關部門即將研究制作新的相關法律,與此同時,相關部門還面臨著人工智能創作時間短,效率高的問題,因此,接受保護的一方僅限于深受大眾喜愛,并且在市場中具備一定價值的作品。日本的相關機構并沒有對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問題進行明確,只是明確表示相關機構會對人工智能作品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6]。
依據當下實際情況來看,美國相關機構的作品若出于人工智能,則會標明“該文章產生于人工智能”;日本人工智能創作出的作品,其作者署名為“機器人”;我國的人工智能創作出的作品,則作者署名為該人工智能自身的名字。例如:在騰訊新聞中,若有人工智能創作出的非時事性新聞稿件,那么其作者署名為Dreamwritrer。
2020 年深圳南山區法院審結人工智能生成文章作品糾紛案,法院認定構成作品。這是全國首例認定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構成作品案件,該案判決已生效。
綜上所述,理論和實踐上都傾向于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權,并給予一定的保護,這也與著作權法的立法宗旨激勵原則相吻合,一方面鼓勵利用人工智能積極創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此行業的良性發展。
(三)輔助制度
著作權發展應該是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合作發展,因此相關部門應該注重以下輔助制度。首先,設立人工智能創作登記制度,這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工智能作品的授權效率,同時相關機構必須要明確人工智能的主體角色,否則就會對著作權的秩序產生一定的影響。其次,應該強制人工智能作品進行登記,并且對其作品的保護期限進行相應的縮減。因為人工智能創作作品所需的時間非常短,這也就給從事相關行業的人類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因此,強制人工智能作品進行登記,并且對其作品的保護期限進行相應的縮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相關人類的利益,也能更好地避免作品造假問題。再次,相關部門應該設立針對人工智能的基金管理。在發生關于人工智能作品侵權的問題時,相關部門應當及時對人工智能進行法律上的規制,可以進行相關的損失賠償等,以上這些都是以人工智能基金管理為依據進行的。設立針對人工智能的基金管理,有助于加強人工智能著作權的主體地位。接著,相關人員需要對人工智能在民法中的主體地位進行明確,因為民法中包含著作權法,也就是說,著作權法是以知識產權法的身份存在于民法中的。因此,相關部門必須確定在民法中人工智能具有民事主體的地位,著作權法中人工智能的主體地位才能夠得到肯定。最后,相關機構應該對人工智能作品的授權機制進行完善,提倡人工智能作品的成果共享,這樣可以使相關作品的使用渠道更加便捷,由此才能更好地共享人類作品以及人工智能作品的發展成果。
結語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充分顯示了我國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視。由于科技的迅猛發展,對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不能預見未來,表現為法律的滯后性。科技的發展需要法律加以規制。這也正是法律的意義之所在。筆者認為,首先從立法層面來看,當理論爭議和實踐運用達成共識,條件成熟時應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明確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問題,可以促進人工智能作品良好發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們的生產生活效率,同時還能夠提高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所以應該積極肯定人工智能作品的社會地位,并且給予其相應的法律保護。其次從司法層面來看,通過法院對每一個個案的審判,推動完善著作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再次從理論和實踐層面來看,通過理論界不斷的爭論和探討,實踐中通過制度的創新。對于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問題最終會達成共識,推動法治建設的進程。推動社會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