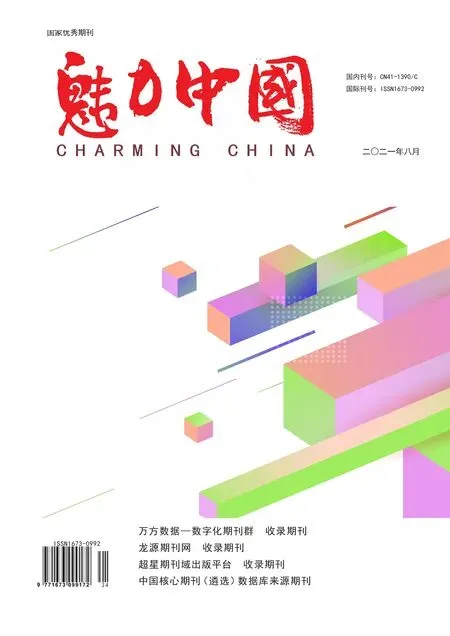淺論豫劇演唱者的案頭工作
馬玲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豫劇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昌吉回族自治州 831100)
演唱者若在創作的作品中被安排角色,則已可說明,該演唱者在演唱理論和演唱實踐方面,均已具備了一定的演唱必備條件。從目前的豫劇界來看,諸多演唱者在闡釋其自身聲腔的演唱理論時,多是對演唱實踐的一種“感覺性”的描述;或是口傳心授教育體制下的口耳相傳。例如:演唱時一定要注意咬字、共鳴、爆發力等技術手段,以及一定要講究“字正腔圓”等諸多靠個人聽覺評判過后的“結果”式的答案。在演唱過程中,演唱者會出現“涼弦”等諸多外現失誤,究其原因,大多數演唱者的回復多是嗓子不舒服,而從未考慮是發聲系統的那個環節出了問題。由此可見,研究好演唱過程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
一、演唱基礎
隨著戲曲聲樂學科的出現,界內掀起了科學發聲法的浪潮。部分專家認為:基于河南當代“五大名旦六大家”的演唱分析,一位豫劇演員若可成家成派,聲音的辨識度是最重要的一個衡量標準,也是促成風格流派標志的首要前提。而所謂科學發聲法卻培養出了“千人一聲”或戲不像戲,像民歌、像美聲的場面。另一方則認為:科學發聲法的出現,確實解決了眾多演唱者在演唱技術中遇到的問題。例如嗓音嘶啞、聲帶不閉合等發聲問題。
在筆者看來,好的發聲技巧與方法,需要演唱者們借鑒和學習。但是,兩者并沒有太直接的沖突,其重中之重便是權衡好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在筆者看來,其實就是“字、氣、勁、味”這四大板塊的關系比例問題。語言在任何歌唱藝術體系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一)字準
在豫劇演唱中,念準確中州語顯得尤為重要,但是,對于演唱者的“母語”較接近中州語體系的演唱者來說,拼讀式的念字是被忽略的。若沒有正確的拼讀過程,便會出現有“家鄉方言”“倒字”等語言性問題。
崔派經典劇目《桃花庵》竇氏的唱段“九盡春回杏花開”中,有幾句采用排比句式。
音樂設計在進行旋律創作時,會將字的聲調作為重要的參照標準進行作品的譜寫,必須做到字與音聲調的有機吻合。在豫劇的唱腔結構中,演唱者在演唱垛子板時,辭格排列相對密集的字會容易出現聲調不準確的“倒字”現象。當出現這一現象時,演唱者可以陽平、去聲等聲調技巧對倒字進行上下二度音程關系的倚音或滑音。這些裝飾音的運用,更能夠彰顯河南豫劇的潤腔特色。
(二)氣順
氣息在演唱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氣息的運用本身是人體自然的一種本能反應,而在演唱作品中,也成了歌唱的動力。所有氣息的運用皆是由“呼”和“吸”兩部分組成的。準確地說,是先吸氣后呼氣。演唱時的吸氣要求是在自然吸氣的狀態下更加夸張,從而使得口腔鼻腔等腔體可以充分打開。打開后有效保持的狀態便是能更好唱出音色共鳴的前提。而呼氣則是聲帶在完全擴充的喉口內振動并在以空氣為媒介的條件下有效傳聲的一種發聲機制。在有效呼吸的情況下,根據自身氣息的機能以及表達人物情緒的要求,選擇合理準確的換氣,才能使得演唱作品有更好的表現力。
在豫劇崔派經典劇目《桃花庵》中,“盤姑”一折中,出現了“一字多音”的滾白唱法。在竇氏知道丈夫去世時,為了渲染悲傷的情緒,便運用了滾白的演唱技巧。
竇氏一陣淚雙傾
我的張才夫你你你
你的鬼魂聽
在豫劇傳統聲腔的演唱中,韻母的準確是能否唱好該樂段的中心環節,也是腔圓表達共鳴的核心所在。最后落音“聽”的收音應該為“Ting”,在一字多音的延長中,便隨著旋律線條的走向,對“Ting”中的韻母“i”向韻母“a”進行韻母替換。這種巧妙的替換也是一種演唱科學的體現所在,狀態不會因為呼吸等外在影響因素打破,反之,更易于向外敘述。在延長部分的演唱中,多是演唱者在沒有任何樂隊輔助音做支持的情況下,大線條的清唱狀態。
此處的滾白演唱技巧是演唱者對所刻畫人物內心情緒的一種外化推動,通過多變的節奏型、度數較大的音程關系、恰當到位的換氣處理以及源源流動的氣息支持才能將其內心情緒表現出來。
(三)勁恰
在演唱的過程中,對旋律線條恰當正確的勁頭表達也是一個重要的要求之一。所謂演唱勁頭的把握與演唱者自身的人文地理環境素養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有些演唱者善于演唱輕柔綿綿的風格作品,有的則善于演唱勁頭十足、高亢明亮的藝術作品。例如,在河南豫東一帶的豫東調,上五音旋律走向,高亢激昂是其特色所在。而“紅臉王”的演唱特色家喻戶曉,奔放剛勁的演唱定是迎合受眾群體審美情趣的一種需求表現。從觀眾的角度來說,有些觀眾覺得真過癮啊,但也會有觀眾認為過火了,太咋呼了。
而河南豫西一帶的豫西調,則是下五音行腔,低沉婉轉是其演唱特色。例如豫劇崔派經典劇目《對花槍》,南營一折中,當姜桂枝看上羅藝后,上堂樓見母親細說情況,看著自己的母親不太愿意,
唱到:那小嘴噘得能拴頭驢
在演唱這句時,一向以低沉為主要行腔特色的大青衣,怎能講此句的俏皮給刻畫出來,不過不欠,這就需要演唱者對唱腔進行仔細研讀,規范念字、規范呼吸。
在演唱時,演唱者應當該強則強,該弱及弱,該長則長,該短及短。但是,強弱、長短這樣的對比詞匯中卻又隱含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無論書法、還是傳統武術等多種藝術形式,都講究著欲左先右、欲前先后的美學精神。在演唱中,為了更好地做出對比,凸顯音樂內在的張力,演唱者需要注意以上范式。其中,在長短關系的運用上,演唱者與樂隊之間的平衡關系亦是最核心的問題。用句通俗易懂的話表述便是,該是誰的就是誰的,該樂隊演奏員進入旋律過門演奏時,演唱者沒必要對字的尾音一直延長,直到把樂隊刻畫的色彩遮蓋。這是不成熟的表現,也是沒有把握好演唱勁頭的表現,更是沒有和演奏員完美協和配合的表現。
(四)味正
每一個劇種、一個流派、一個行當都有著各自不成約定的審美規定。從目前的流派沿襲角度來看,其流派傳承的參考指標多數停留在與師祖唱的“像不像”的評判標準上。而這些評判標準也都是在傳統戲當中會影響比較大。而在一些現當代創作的作品中,味道則不是向各流派師祖的聲腔特色作為參照的比較,而是在演唱者自身的演唱中,是否唱的是純正的河南豫劇。演唱內容不是民族聲樂版本的,更不是美聲版本的。
由此可見,演唱好作品的基礎需要做到以上四點。在筆者看來,以上四點相輔相成、環環相扣、相互影響。
二、案頭工作
唱段是詞曲作家編創出來的,曲譜便是一種沒有生命力的呈現方式,演唱者的天職便是將詞曲做“有聲化”的處理。通過演唱者的二度加工,刻畫出豐富的舞臺人物藝術形象。
光鮮亮麗的藝術形象的塑造,不僅僅要求演唱者具備良好的演唱基礎,并還需其具備綜合的藝術修養。經過發自于內心而表現于外的再創作過程,從而獲得撼動心靈的藝術境界。
詞曲的處理過程便是演唱者將書面的曲譜,變成感人唱腔的加工過程,在長期的藝術實踐過程中,筆者的案頭工作按著下面的步驟進行。
(一)熟讀
學習一段新唱腔的第一步要先熟讀,詞要拼讀準確,曲調的音準和節奏型要把握準確。只有充分的熟讀,才能更好地理解詞曲的意思、基本的故事梗概、曲式結構和藝術風格的把握等。
(二)精思
此過程是一個逐步深入、刻意練習的過程,是需要進一步揣摩、曲不離口的精思過程。在第一過程的基礎上進行細化,以詞曲表達的情感內容為主要突破點,分析曲譜內容所表達的層次、高潮,確定好重點段、句,甚至落實到重點字,再順著其表達的情感主線拓寬內涵,對演唱唱段有一個全面合理的整體布局。
(三)深化
演唱者的演唱也是一個心理構想、創造、應用的過程。對每一句唱腔與“潛臺詞”的嫁接是演唱是否“走心”的關鍵之處。正所謂,沒有內在的“走心”便沒有外在的“練口”。一個唱段之所以可以演唱到一定的藝術水準,必定是演唱者的內心情感與聲音達成了協調一致,內外和諧的統一結合便是深化過程。
(四)巧練
在具體的演唱過程中,演唱者已經對場上的演出有了或多或少的設計,但是,完美的設想在現實演出過程中總會出現差強人意的地方,這便需要演唱者在演唱的過程中,做進一步的放粗取精。練習的方式是否得當也是其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因素。筆者常采用的是小聲哼練、少大聲唱的巧練方式。要多練習在演唱過程中的重難點。但是,在每次練習結束前,要堅持放聲、完整的唱幾遍,其藝術水準按照展演的標準要求自己,爭取做到各種藝術設想可以無縫隙的運用到實踐的過程中。
以上四點便是筆者的案頭工作。若將演唱者在舞臺上的表現與舞臺下的表現相提并論,顯然,因為受演出環境、受眾群體等諸多主客觀因素都會使得演出效果出現一定的誤差。但是,這也跟演唱者的個人藝術修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如自身的戲曲儲備量、臺上臺下的舞臺經驗、臺上臺下的心理承受力等。當然,“藝高人膽大”成為了眾多演唱者的追求名詞。藝高也是演唱者憑借著自身的努力腳踏實地一點點磨練出來的,膽大也是可以戰勝自我恐懼的前提。
唱功作為戲曲四功之首,我們作為新一代的年輕演員有必要將自身多年的舞臺實踐做以總結,相互交流,踏踏實實地做好自己的專業,認認真真地各司其職。個人藝術水平的提高必定會對團體藝術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最后,筆者想提倡一種“外熱內冷”的狀態。外熱要求演唱者精神飽滿、情感充沛以及表現熱烈。內冷則要求頭腦要清醒冷靜,隨時隨地的根據外在的客觀條件調整自己的心態,以便能做到應付一切的突發狀況,從而更好地把握住演出成功的命脈。演唱結束后,善于總結正反兩面的經驗,不斷豐富自己,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