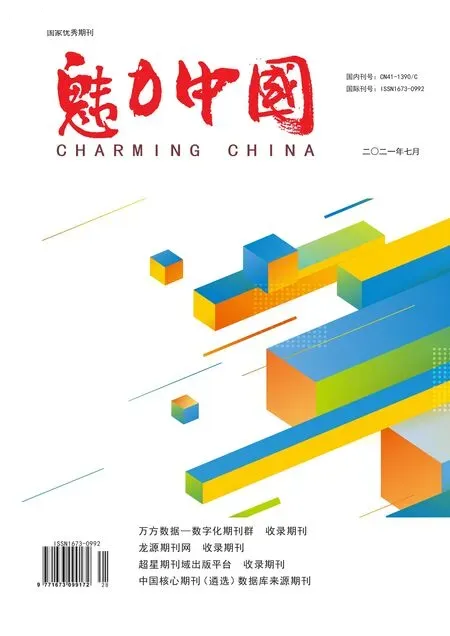再解讀經(jīng)典作品《北京人》
黃山
(中國傳媒大學(xué),北京 100020)
身為中國現(xiàn)代戲劇真正意義上的奠基人,曹禺的戲劇作品在中國現(xiàn)代戲劇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說中國現(xiàn)代戲劇的輝煌離不開曹禺的貢獻(xiàn)。《雷雨》里,我驚慟于不平等的社會里,命運對人殘忍的捉弄;《日出》里,我驚詫于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都市群丑光怪陸離的生活以及社會的糜爛腐朽;《原野》里,我驚嘆于人生困境下的難以抉擇;《北京人》里,我驚喜于封建主義下精神統(tǒng)治的破產(chǎn)。這些優(yōu)秀劇本值得我們一再品讀,總有細(xì)節(jié)值得再回味,總有意象值得再解讀,總有情感值得再體會。本文以鴿子意象的應(yīng)用和賴聲川導(dǎo)演的《北京人》中色彩對情感的重構(gòu)為切入點重新解讀《北京人》。
一、意象的再解讀——鴿子意象為例
對于成名作《雷雨》,曹禺先生在《<日出>跋》中直說自己對它產(chǎn)生了厭倦,討厭它的結(jié)構(gòu),覺著太像戲了。然后表明現(xiàn)在的自己醉與契訶夫深邃艱深的藝術(shù)里,一顆沉重的心怎樣為他的戲感動著。想要再拜一個偉大的老師,低首下氣地做個低劣的學(xué)徒。劇作家契訶夫在戲劇創(chuàng)作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遵循著“客觀寫實”原則去構(gòu)建劇情,不滿于“佳構(gòu)劇”的刻意技巧,不喜于情節(jié)上的故意矛盾,反對當(dāng)時俄國戲劇的嬌柔做作。他的戲劇革新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盡可能的刪去劇本中違背生活的虛假因素;盡可能避免強烈的戲劇沖突,劇情發(fā)展遵循平和節(jié)奏,如小溪一般緩緩流動;善用象征手法來代表階級或形象。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創(chuàng)作完《雷雨》后對自己進(jìn)行反思的曹禺想要學(xué)習(xí)的,學(xué)習(xí)成果在《北京人》中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通過描寫沒落士大夫家庭曾家的瑣碎無奇的日常生活,充分展現(xiàn)了人物內(nèi)心光明與黑暗的矛盾以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渴望。著重于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而不是為了沖突而沖突,在不是那么動人的情節(jié)里蘊含著真善美與腐朽落魄的深刻矛盾。《北京人》中令人稱贊的一個意象就是日常生活中極易見到的鴿子。
鴿子有翅膀,可以在藍(lán)天中自由自在的翱翔,這無疑是自由的象征。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圈養(yǎng)鴿子為寵物的做法,這一行為又顯示出鴿子是容易被人類束縛的。沒有折斷翅膀,籠子卻斷絕了飛向藍(lán)天的可能,明明有著飛翔的能力卻無力逃脫是最為可悲的。《北京人》劇本中不止一次出現(xiàn)的鴿子意象也兼帶著自由與束縛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形態(tài)。
從劇本出發(fā),最表層的“鴿子”指的是本意,真正的動物鴿子。自由的鴿子是指未被豢養(yǎng)的曾家院外的鴿子們和從鳥籠里奮力逃出的鴿子。處于束縛環(huán)境下的鴿子是指那只被命名為“孤獨”的鴿子,它沒有逃出,被同伴拋棄。對比意味不必言說,自在其中。拋去本就自由的鴿子不說,逃走的那只鴿子是注定不會被關(guān)住的,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哪怕它曾與“孤獨”共同關(guān)在一個牢籠里,它的自由精神是“孤獨”遠(yuǎn)遠(yuǎn)不及的。深層次來剖析鴿子意象,這兩只鴿子無疑是愫方及曾文清的代表,二人在曾家這個大牢籠里惺惺相惜、相互取暖多年,在曾文清擁有出逃機會時,本以為他會毅然決然逃向自由,與光明共度。卻萬萬沒想到,最后遠(yuǎn)走高飛的是愫方,曾文清吞食鴉片死亡后永遠(yuǎn)的被困在了曾家這個行將就木的深宅大院。對于鴿子的逃離,愫方說:”苦,苦也許;但是并不孤獨的”。而反觀曾文清在回答袁圓問為何只剩下一只鴿子時,他卻說“那個在半路上飛了”,并且給籠子里剩下的那只鴿子取名叫“孤獨”。“孤獨”,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孤獨?曾文清是真的不懂嗎?不盡然。劇本中有這么一個細(xì)節(jié),愫方呆呆望著籠里的鴿子。曾文清 (沒有話說,凄涼地) 這,這只鴿子還在家里。愫方(冷靜地) 因為它已經(jīng)不會飛了!曾文清 (一愣) 我——(忽然明白,掩面抽咽) 。愫方 文清。文清依然在哀泣。愫方 (皺著眉) 不要這樣,為什么要哭呢?曾文清 (大慟,撲在沙發(fā)上) 我為什么回來呀!我為什么回來呀!明明曉得絕不該回來的,我為什么又回來呀!愫方:飛不動,就回來吧!曾文清:不,你不知道啊,在外面的風(fēng)浪……。這個小細(xì)節(jié)足以表明籠子里被困的“孤獨”就是曾文清,而那只勢必會逃離的鴿子是愫方。曾文清把自己沒有任何出逃意味的出逃失敗歸結(jié)于外面的“風(fēng)浪”過大,在曾家牢籠里,這個曾經(jīng)被譽為神童的曾文清終究是喪失了拼搏的勇氣、反抗的精神,不心甘不情愿的過著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怯弱的他活在自我與現(xiàn)實的矛盾中無法和解,沒有能力改變現(xiàn)狀,不甘于改變自己,最終只得通過吞食鴉片摧毀自己。畢竟籠中之鴿只有兩個選擇,要么努力逃出,要么在籠子里度過一生,或許悠閑自在但終究不是鴿子的正路。劇本中的女子形象愫方最終同瑞貞一起乘坐汽車出走的情節(jié)讓我想到了《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娜拉從不合理的被豢養(yǎng)的婚姻中毅然出走,被視為女性解放的代表形象。愫方是從無盡的束縛中出走,逃離了無結(jié)果的愛情,擺脫了一眼可以望到頭的生活,去追尋自我生活的激情,或許是艱難險阻的,但一定是充滿希望的。希望才是人活一輩子最重要的東西,有些桎梏注定是要被人來打破,愫方超越了曾文清,完成了他沒成功的任務(wù),還是以女性獨有的姿態(tài)完成的。有些學(xué)者提出愫方其實是個不理性的女性形象,而我卻認(rèn)為愫方若想沖破愛欲裹挾下的生活大牢籠,勢必是要打破理智思維,放棄本我,才能像平庸宣戰(zhàn),獲得自我的救贖與解放。
劇本中還頻頻出現(xiàn)了鴿哨聲,這在如今的北京也是十分常見的。鴿哨聲的存在首先透露著濃厚的生活氣息,符合曹禺先生想要在平凡日常生活中賦予主題的想法。鴿哨聲還有著更重要的作用,代表著曾家老宅里每個人的希望。身為內(nèi)心希望的外在表達(dá),劇本里對開幕里的鴿哨聲是這樣描述的:“屋外,主人蓄養(yǎng)的白鴿成群地在云霄里盤旋,時而隨著秋風(fēng)吹下一片冷冷的鴿哨響,異常嘹亮悅耳,這銀笛一般的天上音樂使得久羈在暗屋里的病人也不禁抬起頭來望望:從后面大花廳一排明凈的敞窗望過去,正有三兩朵白云悠然浮過蔚藍(lán)的天空。”詩意美麗的語言構(gòu)建了一個美妙的甚至不合理、帶有虛幻色彩的曾家宅子。整個劇本三幕里,在第一幕,鴿哨聲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調(diào)劑著劇本節(jié)奏,韻味十足。而在第二幕里,鴿哨聲就不再出現(xiàn),雖感覺稍稍刻意,但象征意味明確,希望在此刻已不復(fù)存在了。到了第三幕甚至變成了嘎——嘎——嘎——的粗劣嘶啞烏鴉叫聲,此刻的曾家宅子被濃濃的絕望與無盡的黑暗籠罩著,蒼老的榆錢樹上盤旋著、扎堆著一群群的烏鴉,像墨點子似的噪個不休。烏鴉叫聲取代了鴿哨聲,不僅意味著希望消失,還帶來了不詳?shù)纳剩咽局茢〉脑易⒍ㄒ呦驓纭S汕宕鄲偠镍澤诼曨l頻出現(xiàn)到鴿哨聲消失再到出現(xiàn)令人反感的烏鴉聲的過程更是曾家眾人由滿懷希望到失去希望再到共同投降毀滅的過程。
二、情感的再體會——賴聲川版《北京人》的色彩運用
在經(jīng)典巨作一次次被搬上戲劇舞臺時,再創(chuàng)作要做到的不僅僅是尊重原作,還要做到考慮當(dāng)下戲劇觀眾的審美接受方式。總體來看,賴聲川導(dǎo)演的《北京人》中外化的生活本質(zhì)與內(nèi)化的人物內(nèi)心走向更為明確,句中的人物形象越來越像人,而不簡簡單單是他們背負(fù)的角色。賴聲川導(dǎo)演在三幕間大膽運用色彩,用白、黑、彩色來引導(dǎo)觀眾的情緒,彰顯《北京人》的情感特質(zhì)。從此作用來說,色彩符號的運用與原劇本里的鴿哨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第一幕幕啟,舞臺上是一片純白,徹徹底底的白,無生機的白,包括布景包括道具甚至演員服裝。時尚感與刻意感兼而有之的呈現(xiàn)在觀眾眼前,白茫茫的一切,就是劇中整個破敗又封建的曾家的真實寫照——無可奈何、壓抑無助。每個人物形象都活在自己的“白色世界”里。曾思懿拿著白色的冰糖葫蘆,想要盡全力的撐住整個家,白色意味著身為大奶奶的她的一切所作所為勢必是徒勞無功的,同時又很巧妙的是她的妝造卻不是黯淡的,五官立體分明凸顯個人的冷清,鮮明的唇色讓她整個人更顯精明利落。曾文清和愫方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可能性為零,空虛的情感錯位令二人苦惱惆悵,他們兩個的情感世界也是純白無物的。荒蕪的色彩里,沒有一筆亮色,就好比如遠(yuǎn)海廣闊的水面上沒有明燈指明方向,大家都是虛無的。曾霆無任何選擇的、只得跟曾瑞貞在一起,曾文彩無力的只能包容著自己好吃懶做、還要實現(xiàn)大夢想的丈夫江泰。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無力感,感覺做什么都沒有任何用處。曾家就像一灘看不出危險的沼澤,越陷越深,人不再是人,是“耗子”是“鴿子”。
第二幕發(fā)生在夜色里,這場戲的壓抑氛圍靠舞臺上的黑色渲染出來。與第一場截然不同的對比色,相同的是包括布景包括道具包括演員服裝全是黑色。黑色外殼下,整部劇的凝重與悲傷感一覽無余,曾家里形形色色的人、內(nèi)心里藏著滿滿的憤懣,桎梏下的悲劇無法逆轉(zhuǎn)。內(nèi)心緊繃到了極點的眾人試探著觸碰曾家的底線,比如說曾老太爺?shù)呐鼋羌抑形ㄒ灰粋€明確喊話對抗的形象,但他反抗的言語與所作所為又是相互矛盾的。他酗酒成癮、不斷家暴、不停喊話來麻痹自己、表達(dá)內(nèi)心的不滿與憤怒,但又沉迷于這些行為,附著在曾家這個腐朽的溫床上不愿清醒,始終沒有做出任何觸碰底線的行為,徒剩“喝茶”“死人”的喊話。我內(nèi)心里認(rèn)為江泰的確是看透了曾家在時代裹挾下只會一直腐敗,他或無力或無能于此趨勢,只能自我麻痹。舞臺上一簇簇蠟燭的燈火不是希望的象征,反而徒增詭異與壓抑。但另一方面,在瑞貞決絕的做出打胎決定后,燭光微弱得跳動突然讓我感覺黑暗中多了一些微弱的生命力,調(diào)和了整個舞臺的色調(diào),柔軟溫柔的抗拒了封建抗拒了人吃人的文明。
喪事專用黑白兩色,第一幕與第二幕已無言中宣判了曾家的必然頹敗與死亡,第三幕是彩色的。該結(jié)束的聽到了臨終的呼喚,該新生的看到了未來的指引。舞臺上的燈光有了非黑非白的顏色,樹染上了墨綠色,斑斑駁駁的墻壁是暗黃色的,青綠色的瓦片之上是靛藍(lán)的夜空,演員服裝、道具也有了五顏六色。彩色的終曲,這才是所有人本來的最真實面目。打破了黑白的束縛,迸發(fā)出了不一樣的色彩,這個破敗的大家庭已無力承受這一切。曾文清選擇吞鴉片膏死去,這是他絕望又無奈下的無聲反抗,這副軀殼帶來的只有束縛。原來的安慰是“再等等也許就好了”,色彩的碰撞表明這個曾家不會再好了,已經(jīng)不必再強撐了。曾老太爺懷揣著“等來年開春,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奢望;身著憂郁紫色的姑小姐曾文彩懷揣著“泰快回來了”的奢望;愫方懷揣著“我?guī)退疹櫤眉依锏囊磺校粫倩貋砹恕钡纳萃烧f到底,這些奢望都是假的,假到連自己都無法說服。還好,第三幕還是有希望的,沉默堅強、溫婉和善的愫方最終醒悟,曾家大院就像個遲暮的老人,大半截入土無可救藥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只是感動了自己,別的毫無作用。瑞貞與自己還能脫離,如果再執(zhí)迷不悟,也會深深的陷進(jìn)這個沼澤中無法自拔,隨它消逝。這個時候,“原始的北京人”上場了,他穿著現(xiàn)代的西裝并開口說話,如同一面新時代的旗幟充當(dāng)著舊時代的拯救者形象,幫助身著綠色衣服的瑞貞和愫方撬開了曾家大宅的門鎖,沖向了未來擁有著無限可能的新世界,逃出牢籠后的她們獲得了新生,渾身充滿著生機與活力。除此之外,袁圓身著亮紅色,如初升的朝陽溫暖又富含著希望。
賴聲川導(dǎo)演的《北京人》三幕間的色彩運用的確大膽又出色,是他新審美主義的一個表現(xiàn),也給觀眾帶來了新的審美體驗。白與黑的色調(diào)對比也的確加深了《北京人》的凝重感與無力感,突出了更為深沉的戲劇張力,明確了劇中人物的情感,使人物內(nèi)心世界更為外化。但色彩符號帶來的新鮮感又讓我感覺稍顯刻意。雖然說,舞臺導(dǎo)演對劇本的闡釋與表達(dá)本就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或許是借鑒運用了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想要明確的告訴觀眾,臺上的人物就是在演戲,這是否與曹禺先生的初衷所背離?
結(jié)語
有些學(xué)者對于曾家的眾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北京人》還是給人以希望的,18 歲的瑞貞說服了愫方一同出走,蠻性的代表“北京人”打開了沒有鑰匙的大鎖,也打開了困住愫方三十載的心靈枷鎖。本來是啞巴的“北京人”開口講了話也象征著走向新時代的人們有了發(fā)言權(quán)。文明的發(fā)展是進(jìn)步的,但反過來又壓抑著人性,操控者人生的主動權(quán),只有“蠻性”才能摧毀腐朽,開辟新生者的未來之路。曹禺先生的戲劇劇本之所以感人,是因為悲中蘊含著喜,喜中蘊含著希望。時代變遷,可對人命運的探索是用不褪色的,人文氣息的厚重、含蓄的暗示色彩才是真正的高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