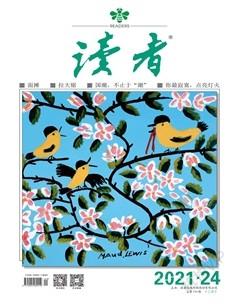畢業紀念冊
余斌
所謂“三搬當一燒”,幾次搬家,好些舊物扔的扔,丟的丟,沒丟的也不知在哪個旮旯里“蒙塵”。跨入大學校門至今,居然已有四十年,沒了“物證”,偶爾回想起來,更有“事如春夢了無痕”之感。事實上當年的許多人與事并未當真忘個干凈,有時還浮現得相當真切,有畫面,有細節。只是隔了幾十年回首遙看,未免亦真亦幻。舊物也還是有遺存的,比如我們班的畢業紀念冊。書以外,這可能是本科四年我僅留的“物質文化遺產”了。
紀念冊像個賬簿,紅綢的封面,燙金的大字,大概當年只有這種樣式的,里面卻是“圖文并茂”。“圖”是照片,每人一張標準照、一張生活照;“文”則是相互間的留言,這是精華所在,最有看頭。
題寫臨別贈言,有不假思索一蹴而就的,也有字斟句酌費了心思的;有泛泛而說的,也有針對你的;有摘錄名人名句的,也有自說自話的。內容五花八門,卻也可以歸類。
“勵志共勉式”無疑是大宗:“向現實猛進,又向現實追尋。”又一類是“友情為重式”:“時間不會改變我們。”當然,大都是正能量的,但負能量的也不是絕對沒有,至少葉姓同學所寫的就有這嫌疑。他寫得簡省,只寫“好了”二字,加個句號。讀作“好le”也不是不可以,表示一事終結,可以是“成了”的意思,畢業意味著在大學修成正果了嘛,但讀作“好liǎo”當更得其意,出處應該是《紅樓夢》里的《好了歌》,所謂“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大家就要各奔東西,說這個,是故意搗糨糊,還是要大家來參禪?
另一位的留言也有意思:“獨把花鋤淚暗灑,情孤潔,誰解林妹妹?手執鋼鞭將你打,媽媽的,學學阿Q哥。”將林妹妹與阿Q混作一處,前一段凄凄慘慘戚戚,何其大雅,后面畫風突變,“媽媽的”也出來了,混搭在一起,很有幾分無厘頭的效果。
留言有時雖不免“逢場作戲”,卻也可以見人,上面留言的兩位與大多數人相比不大正經,他們原本就是好開玩笑、搞惡作劇的人。
至于“前程似錦”“預期日后不可限量”等,當然屬于“善頌善禱式”的范疇,看了不受用也受用。在這一派祥和之中,程姓同學的留言可謂“變徵之聲”:“揀盡寒枝,無處棲身。愿你,也愿我自己,能在這混濁的星球上找到一片凈土。”這顯然是有上下文的,時過境遷,一時竟想不起這悲涼之音從何而來。回頭細想,這話原來正扣著當時的語境,是有“典故”的。其時,畢業分配大局已定,不如意者當然是有的,程同學和我,皆在其中。
這是“觸景生情式”,另一關系頗密切的哥們兒則不似“率爾言之”,更像通盤給我下考語,口氣像在做鑒定:“此君足可委以信賴(作為朋友)與摯愛(作為女朋友)。最大優點,年輕。對于我,他將永遠保持這個優勢。最大缺點,吃虧太少。最可有可無的特點,尚具才華。”這比時下好話說盡卻沒人當真的例行公事的推薦信有誠意多了。我的領悟是,“吃虧太少”不是損我吃不得虧,意思是未經挫折,少不更事,目下無塵,尚欠磨煉。這一條,不認也得認。最后一句有棒喝之效,換成大白話:有點兒小聰明,而小聰明不可恃。時至今日,我更不敢自詡有什么才華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留言有沒有讓別人不爽。雖屬小字輩,人微言輕,我卻有上面那位老兄一樣點醒他人的沖動。記得一位京城來的張姓同學,見多識廣,剛入校時,意氣風發,有一覽眾山小之勢,幾年下來,似乎收斂鋒芒,遁入學問,對現實什么的趨于回避,且正談著戀愛,在我看來,似乎是要奔著小日子去了。我便抄了黃仲則一句“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自覺大有深意存焉。
又有一位姚姓同學,從部隊考過來,比較正統,管班級諸事,仍有幾分部隊作風。我是散漫慣了的,他雖不大管到我頭上,我卻也要夸張地表示一下不滿,留了一句“何不帶吳鉤”。言下之意,你這一套還是收收疊疊,帶回部隊去吧。小字輩的話,他哪會在意?唯我自己,好像在暗下針砭。有意思的是,后來姚姓同學和我成為同事,來往漸多,居然很是投機。他為官多年,一無官氣,且開放得很,我當年對他的不好印象蕩然無存。每每喝酒閑話,說起當年事,“相與拊掌大笑”。
真是當年事了。有個同學戲題的是起承轉合的套語:“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做什么解都可以,雖是戲言,說其中透出點對未來的信心滿滿也不是不可以。到如今不管是不是后事已了,算是分解了還是未分解,大體上已是沒什么“下回”了,我們都已退休或將退休。
這時候看鮑姓同學給我的留言,就覺得特別有意思。我們算是老鄉,他隨手寫了句:“四十年后,我們一起去故鄉度晚年。”“四十”這個數字不知從何而來,或者就是屈指算來四十年后應已退休。無論如何,說這話時,他肯定只是那么一說,并未當真想到“晚年”之類。畢竟四十年太遙遠了,我們的好戲剛拉開大幕,“未來”對我們可以意味著其他的一切,但絕不會是“晚年”——誰會當真去想這個?
一不留神,居然是為了入學四十年,要聚了!
(滄 海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時過境遷:提前懷舊四編》一書,本刊節選,〔韓〕Jamsan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