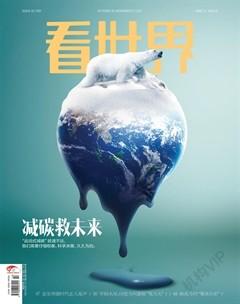碳中和,一起摸著石頭過河
王偉康

安徽銅陵,長江邊清潔能源特高壓電網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如果要提一句標志性話語,最沒爭議的大概是“摸著石頭過河”吧。這句話也適用于當前我國的碳減排事業。
2020年9月雙碳目標(“碳達峰”“碳中和”)的提出,表明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有了統一的階段性目標。朝著這個目標,各地區、各行業因為不同的背景和發展方式,必然走上不同的實現路徑—“摸著石頭過河”時,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自己的實際情況、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方法和途徑,大概就是河里的石頭。
截至2020年底,超過120個國家正在考慮或者已經提出碳中和目標,其中超過30個國家通過政策宣示、法律規定、行政命令等方式,設定了碳中和目標年。不過,如果這些國家都有完善的執行規則,也就不會出現最近異常熱烈的“能源危機”之討論—歸根結底,還是能源系統的轉型面臨階段性的挑戰。
德國經驗無法照搬
據統計,全球碳排放約有75%來自能源應用行業,比如交通、電力、建筑、制造等。在現行能源結構中,全世界的化石能源占比大概為84%,中國大概為84.6%。
推進能源轉型,意味著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減少化石能源的份額。這要求現有的能源系統更具彈性,能夠克服系統脆弱性的風險。
在復雜的能源轉型過程中,各國提出的碳中和目標,對本國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發達國家也不例外。比如,德國電力體系中的可再生能源已達51%,由于可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這個電力系統面臨發電和用電平衡的挑戰。德國通過精準電力供需預測、電力天氣預報、匹配可再生能源的儲能系統、火電調峰等多種手段來解決。目前可以說,德國是電力系統轉型的典范國家之一。

2020年2月15日,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安裝在湖面上的太陽能發電板
德國電力體系中的可再生能源已達51%。
在全球的能源轉型中,從可再生能源占比和能源系統穩定性的角度來說,德國的電力系統已經是遙遙領先,但他們仍面臨像部分化石能源的比例階段性提升、2050年碳中和時約15%的電力缺口不知道該如何解決等問題。德國的政府部門也在摸著石頭過河,努力尋找解決方案。
德國的經驗有很強的參考價值,但這塊石頭如搬到我們國家,也有不少問題。
首先,我們國家的電力系統是高度統一的,與德國較為分散的電力系統有明顯差異;要想照搬經驗,就要調整管理機制,但這可能連帶造成社會保障和共同富裕方面的挑戰。
其次,德國電費之高是有目共睹的。德國居民電價在過去21年漲了78%,2019年德國電價是中國電價的約4.7倍。在我國,提高電價所帶來的經濟和民生影響,使得這個市場化的手段往往無法發揮作用。因此,德國經驗這個石頭在德國的河里看起來非常牢靠,但要想復制到我們國家這條大河里,也是需要打磨的。
不僅如此,我國在能源轉型上面臨的挑戰,比德國等發達國家更大。從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報告來看,未來30年內,我國的能源體系需要實現劃時代的變革—非化石能源占比從16%增長至78%,煤炭的絕對消費量減少90%,與此同時,還要支持實際GDP翻兩番,電氣化水平大幅提高等。
形象點說,爬同一高度的山,德國現在已經站在半山腰了,而我們才剛走了1/10。從全國用電量數據來看,德國524太瓦時(2019)與中國75110太瓦時(2020)相比,體量規模的差異也給我國電力系統脫碳提出了更大挑戰。
期待政策協同效應
除了電力這一典型行業之外,金融行業作為國家經濟的動脈,面對碳中和的國家雄心時,也一定會出現摸著石頭過河的局面。
行業企業的減排目標設置,一般是依托其年度排放基準情況,以碳中和的目標倒推,形成階段性時間和減排比例。如果是行業領軍企業,可能還將參考國際先進實踐,將企業自身實現碳中和的目標設定為早于國家整體目標。

2021年3月31日,江蘇蘇州,施工人員在維護變電站設備
金融行業自身的碳排放活動十分有限,因此對于國家碳中和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其金融活動支持實體經濟行業企業的減排行動上。
為了降低金融行業范圍三(價值鏈)的排放足跡,首先得要求企業對排放進行數據報送,其次要提升金融機構相關部門人員的碳排放水平的評估能力,在項目(企業)洽談、風險評估、投(貸)后管理等環節,將這一目標納入每單業務。
面臨這一全新的要求,中國的金融行業也經歷了較長的接受過程。從僅有政策研究部門的工作人員參與討論,到市場、風控甚至董辦的工作人員開始研究如何實操,從質疑企業碳排放是不是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到探討金融機構如何引導和支持企業進行低碳轉型,這一變化顯著發生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
今年6月11日召開的“聚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加快發展綠色金融”的推進會,以及在會上成立的“中國銀行業支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專家工作組”,可以體現這樣的變化。
不過我們也看到,摸著石頭過河也時有滑落濺水。國際上有對“能源危機”的討論,國內也有對“運動式減碳”的熱議、對“拉閘限電”的困惑和對政策協同效應的期待。
在國家宏觀碳中和目標提出之后,各個省市都在探討自身的碳中和目標設置。有不少省份和城市積極提出,要在國家提出的2030年達峰目標之前,實現本省本市的達峰。這本來值得鼓勵,但如果未經科學分析和充分論證,過于冒進的目標和一刀切的執行,可能會給產業轉型過短的時間和不足的支持,影響轉型的公平性,給企業和個人造成重大損失。
不同部門為實現碳中和,有著不同的政策措施安排,比如,應對氣候變化部門的“碳市場”、能源部門的“能耗雙控”和“綠色電力交易”試點,都是非常值得贊賞的單項政策。但各項政策之間的打通和協同,在短期內仍需提升。譬如,2021年9月購買了綠色電力的企業,在面臨能耗雙控時能否順利保持生產,在核定年度碳排放完成情況時能否得到認可等,都是需要不同主管部門之間進行協調、爭取協同作用的;否則,不只是造成實踐中的重復工作,更可能打擊企業的轉型積極性,影響整體進程。
盡管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但隨著國家宏觀目標的逐步清晰和各個行業、地區的覺醒與行動,我們可以期待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不僅是強有力的行動者,也逐步成為國際社會上的領導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