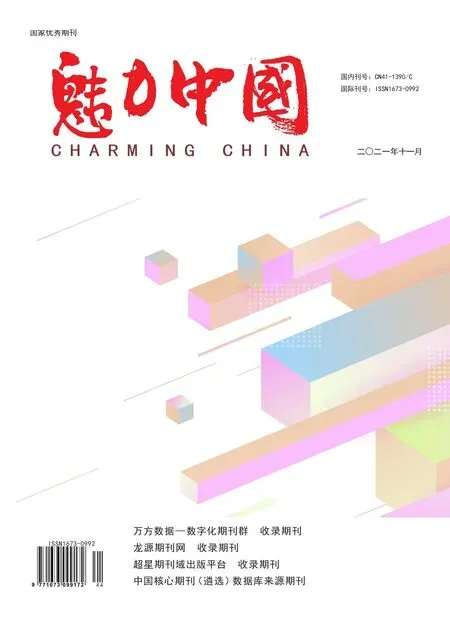情緒調節對患方對醫道德判斷的影響
鄶一杰
(延邊大學,吉林 延吉 133000)
一、患方對醫道德判斷
醫患沖突、暴力傷醫現象一旦出現,便會引起社會關注,成為社會熱點問題。2000 年到2015 年間媒體報道暴力傷醫事件290 例;從2013 年到2017 年的5 年間,公開報道的傷醫案例228 例。可見,醫患關系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就醫質量的重大社會問題,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而影響醫患和諧最重要的問題為醫患信任缺失。[1]患方信任是指患者及其家屬所代表的患方對醫方的信任,可以分為“醫技信任”和“醫德信任”。醫技信任是對醫生診斷和治療疾病能力的信任,醫德信任是指患方相信醫生能夠將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并努力實現患者健康利益的最大化。醫技信任較易判斷,可通過醫生的技術職稱、學術地位、行醫經歷、患者口碑等外顯因素進行判斷。醫德信任的內隱性較強,對醫生醫德的判斷成為患方信任的核心要素。患方對醫方可信度的判斷,往往傾向于看重醫德而非醫技,因為醫技通常超過患者的醫學知識而無法判斷,但醫德判斷卻可脫離知識背景,從醫患互動的細節,如醫生的表情、語氣等直觀線索中加以推斷。[2]而這部分信息的獲得,受到患方當時的情緒、身體健康狀態等主觀因素影響較大,所以對同一位醫生的道德判斷差異也比較大。潘峰等人的研究表明,大學生對醫生的整體道德行為上的贊揚程度顯著低于對照組,對醫生的整體不道德行為比對照組更加嚴格。[3]即使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后,大學生對醫生的道德判斷在關愛、忠誠、權威行為維度上顯著高于疫情前,但對醫生整體不道德行為的評價則比疫情前更加嚴格。該研究說明,患方對醫方道德判斷低于其他群體的現象并沒有因為新冠病毒疫情的發生而得到緩解,這仍然是一個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所以有必要對患方對醫道德判斷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研究。
患方對醫道德判斷屬于道德判斷在特定醫患情境中的一種體現,兩者具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要想分析患方對醫道德判斷的影響因素,首先要從已有研究中證明了的道德判斷的影響因素入手。道德一直是人類生存和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也是哲學、倫理學中的重要課題,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所探討的核心問題。在倫理學詞典中將道德定義為“道德是人類社會所獨有的一系列有利于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的行為準則,是在特定的社會中產生,同時也是在一定的社會階級制度上建立起來的用來處理個體間、個體于社會間的各種復雜的關系的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這種行為規范能被社會中大多數人所接受和遵守。”。根據該定義可以看出,規則是構成道德的基礎。道德判斷實質上是個體對這些規則認可和理解程度的外在表現。哲學家們用思辨的方式去思考如何去解決道德困境,即個體如何做才是符合道德的,而心理學家們則是在實驗室中觀察人們是如何解決道德困境,以及為什么這樣去解決?哪些因素影響個體的道德判斷?在心理學的領域的研究中,主要以道德判斷作為衡量道德水平的指標,道德判斷也成為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中的熱點問題。早期的研究者認為道德判斷是一種心理建構,并將其定義為:人們在特定情況下確定道德行為和不道德行為的過程。美國社會心理學家Hadit(2001)提出,道德判斷是一種對社會事件中其他個體或者行為的評價,評價的依據是被社會廣泛認可的美德或善行。近年來,圍繞道德判斷及決策過程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和細化,但是道德判斷形成的機制中存在的“情理之爭”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尚未形成統一的理論。
二、情緒對道德判斷的影響
情緒影響道德判斷的研究主要是通過情緒誘發技術使被試產生不同的情緒,然后在誘發的目標情緒下就一些道德故事或者行為進行判斷。起初的研究對情緒影響的關注主要是基于不同效價,后來的研究開始重視具體情緒對道德判斷的影響。但無論從哪個角度進行的研究都已證明情緒因素是影響道德判斷的重要因素。已有的研究表明,無論是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都會直接影響人們在道德兩難問題中的道德判斷和決策。Zarinpoush,Cooper,&Moylan(2000)的研究表明,中性情緒和悲傷情緒狀態下的道德判斷能力顯著高于快樂情緒。但Van den Bos(2003)的研究則發現,快樂狀態下的道德判斷能力高于悲傷狀態。還有研究中發現,相同效價的不同情緒對道德判斷產生的影響不同。
患方在就醫情境中的情緒主要是消極情緒,比如患方易從消極角度理解醫方的某些中立的、無特定指向性的語言,并產生負性情緒。由于生理病變、病痛折磨、經濟負擔和家庭成員的照料負擔等因素的影響,患方存在的主要情緒為憤怒和悲傷。憤怒是常見的基本情緒之一,是由于目的和愿望不能達成或一再受到挫折,逐漸積累而成的。患者在就醫過程中產生的消極情緒中,憤怒情緒的影響最大,直接影響醫患關系,甚至引發患者攻擊行為,是暴力傷醫等惡性事件的前奏。因此,為了維護醫療秩序,減少醫患暴力沖突,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對患方憤怒情緒進行干預和調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目前國內有關患方憤怒情緒的研究還很少,且停留在調查研究層面。主要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探討不同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職業的患者,在表達憤怒情緒時的特點,對憤怒情緒的干預手段也是比較宏觀的政策性干預。悲傷是失去所盼望的、所追求的或有價值的事物而引起的情緒體驗,其強度依賴于失去的事物的價值。悲傷情緒是患者及主要照顧者的常見情緒之一,尤其是絕癥患者。在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時,患者及家屬的悲傷情緒往往不可避免。于文華等人研究表明悲傷情緒會引起照顧者生理、心理、行為、社會等方面的不適,甚至出現功能障礙,導致不良居喪結局。[4]
情緒對道德判斷產生的影響已經被多次驗證,而在患方就醫情景中充斥著多種消極情緒,這些消極情緒對對醫道德判斷的影響卻沒有通過實證研究進行深入分析和討論。如果能夠通過實驗研究證明醫患情境中常見的憤怒和悲傷情緒對患方信任產生影響,并通過情緒調節策略干預患方消極情緒來提高患方信任,可以為醫患信任的破裂和瓦解提供保護因子,并為已經破裂的醫患信任提供修復的可能。
三、情緒調節對負性情緒的干預
情緒調節是指個體通過改變自身情緒體驗的強度、持續時間和品質等來改變情緒反應。情緒調節策略是指個體為了改變情緒的性質、產生時間、主觀體驗和表達方式為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或措施。當個體情緒反應與外界環境要求不一致時,個體會傾向于采用情緒調節策略進行調節,以達到對當前環境的適應。最早將情緒調節引入心理學領域的是精神分析學派,早期精神分析的理論認為情緒調節的任務就是使自身盡可能少地受到消極情緒的左右,通過行為和心理上的控制來降低消極情緒的體驗,是一種降低消極情緒體驗的被動心理防御機制。20 世紀80 年代,情緒調節開始作為一個獨立概念被發展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所關注,隨后在成人情緒研究中也開始關注這一概念。隨著近年來國內外關于情緒調節研究的增多,人們認識到情緒調節對人的身心健康、幸福感具有重要意義,對情緒調節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問題。已有關于情緒調節和情緒調節策略的研究中,大多以Gross 提出的情緒調節過程模型為理論基礎。該模型認為,情緒調節是一個由多階段組成的過程,情緒調節可以通過改變過程中的一個或多個階段來達到情緒調節的目的。Gross 認為,最常用和最有價值的降低情緒反應的策略有兩種,即認知重評和表達抑制。認知重評是指通過改變個體對情緒誘發事件意義的認識和理解調節個體的情緒,或將情緒性事件的發生與結果合理化,它屬于認知改變策略,是先行聚焦策略的代表策略。表達抑制是指通過個體的自我控制,抑制即將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情緒表達行為,它屬于反應調節策略,是反應聚焦策略的代表策略。在對憤怒和悲傷這兩種負性情緒調節效果的研究中,已有研究表明,認知重評策略具有穩定的效果。如Mauss 等人的研究表明認知重評能夠成功調節憤怒情緒的情緒體驗和個體的心血管反應;[5]劉振會等人的研究表明認知重評策略對調節9-12 歲兒童的悲傷情緒有效。[6]
作為應對情緒性情境的即時心理反應,情緒調節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密切,情緒調節也是一種有效的自我保護機制。情緒調節可以對負性情緒進行有效的干預。前人的研究表明,情緒調節策略可以有效降低個體負性情緒水平,并通過實驗研究找到神經機制上的證據。也有一些研究證明了情緒調節可以通過影響情緒進而對道德判斷產生影響。[7]但研究較少,沒有在醫患情境中對該影響進行驗證的研究。研究情緒以及情緒調節對道德判斷的影響,并以研究結果為依據提出具體可行的干預患方信任和道德判斷的措施,可以為緩解醫患矛盾、和諧醫患關系、促進醫患信任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