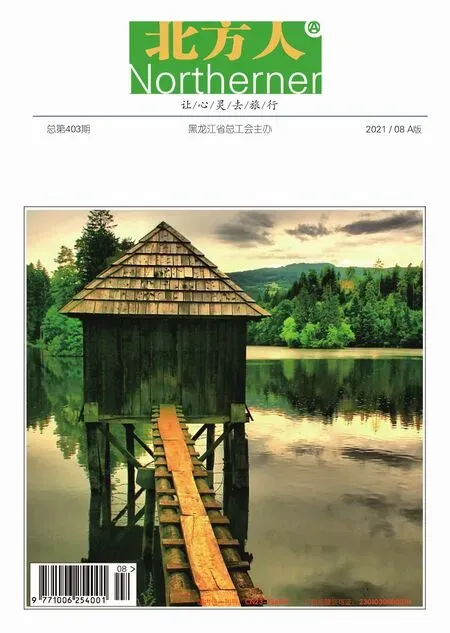你不是朋友圈里最窮的人
文/周欣悅

看看朋友圈,你會不會覺得很多人比你有錢?他們買著你買不起的衣服,在你覺得很貴的餐廳就餐。
不光你是這樣,大多數人都有這個感覺。來自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的威廉·馬修斯教授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揭示了這個現象。研究者招募了190個年齡在18—67歲之間的人,讓他們估計一下,在這次參與實驗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比自己有錢,又有多少人比自己更窮。
結果,大多數人覺得比自己有錢的人更多。他們估計有59.1%的人比自己有錢,覺得比自己更窮的人只有37.1%。參與這次實驗的有年輕氣盛的大學生,有歷經人間百態的花甲之人,也有三十而立的壯年之人,可他們都覺得自己的錢不如其他人多。
我們為什么會錯誤地以為別人比自己有錢呢?一個原因是,我們經常看到和聽到有錢人的新聞和消息。我們的朋友不會把自己節衣縮食吃泡面榨菜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但是買了新車新房卻會迫不及待地要讓大家知道。另一個原因是,新聞記者喜歡報道有錢人的生活。媒體往往會花費大量篇幅描述其奢侈消費的行為,所以我們總是在新聞里聽到那些富二代一擲千金的故事。
長此以往,就給我們造成了一個印象,那就是有錢人很多,窮鬼似乎只有自己一個。如果讓我們想一個比自己有錢的朋友,我們可以一下子想起很多個。但是如果讓我們想一個比自己窮的朋友,我們就需要絞盡腦汁才能想出來了。這種很容易提取有錢人信息的記憶庫就會讓我們誤以為身邊的有錢人很多。
我們之所以會認為別人比較有錢,除了有錢人的信息更加泛濫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社會比較。我們對事物的認知往往是相對的,是基于事物之間的比較得出的:今天比昨天更冷,飛機比火車更快。而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也需要通過跟別人比較來獲得。如果我們每個月賺2萬元,那么我們到底是一個成功人士還是一個失敗的人呢?這就需要我們把自己跟別人進行對比。如果我們身邊的人都是每個月才賺幾千元,那么我們就很成功。如果我們身邊的人都是年收入上百萬元,那么我們就不那么成功了。
美國密歇根州霍普學院的著名社會心理學家戴維·邁爾斯研究了奧運會上的運動員,他發現銅牌選手比銀牌選手要更加快樂,雖然他們的名次更低。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比較的對象不一樣。銀牌選手喜歡把自己跟金牌選手比較,他會覺得自己很失敗,因為差一點就拿到了金牌。但是銅牌選手喜歡把自己跟沒有拿到獎牌的那群人相比,比起他們來說,自己太幸運了,因為差一點就沒有獎牌了。
人們通過社會比較來衡量自己的價值。著名美國記者亨利·孟肯曾詼諧地調侃:“人生贏家就是比你老婆的閨蜜的老公多賺100美元的人。”
有趣的是,比較收入時,你更加傾向于和比你賺得多的人去比較。你的薪水可能僅僅是一些同事薪資的幾個零頭,也有可能是一些同事全部收入的好幾倍。但你發現了嗎?你總是喜歡拿自己跟有錢人比較,而不是跟窮人比較。盡管你知道手頭拿到的這點錢已經遠遠勝過那些非洲國家的人們,也足夠應付你偶爾燃起的消費欲了,但是只要想到那些肆意揮霍金錢的土豪,你還是會咽不下這口氣。
所以,你總覺得別人比較有錢,那是因為你眼里看到的只有那些比你更有錢的人。同事曬出的去新加坡環球影城的照片讓你羨慕不已,你在心里想了這件事情好幾天;但你沒有發現,你國慶節去上海迪士尼時有些同事宅在家里哪兒也沒去。
這樣的社會比較不但會使你產生自己很窮的錯覺,還會偷走你的幸福感。
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說的那樣,比較就是一個小偷,它會偷走你的快樂。
你有沒有覺得網絡時代人們變得更加不快樂了呢?《紐約時報》曾經有一篇報道,講到了這個話題。他們認為根本原因是網絡讓人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人們的視野發生了變化。30年前,如果你是小縣城的首富,那么你的日子相當愜意,覺得自己就像皇帝一樣。但是在網絡時代,你經常會看到馬云,就忍不住把自己的財富跟馬云比較,覺得自己簡直是個窮光蛋。在過去,你跟你的同學比成績,跟你的鄰居比財富。在網絡時代,你跟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比成績,跟“馬云們”比財富。這樣一來,自然幸福不到哪里去。
錯誤估計別人的有錢程度,還可能導致生活中的一些錯誤決策。例如,你開始創業,為產品定價時,如果目標客戶是身邊的人,你會錯誤地以為這些人比較有錢,就可能制訂一個偏高的價格,導致產品無人問津。又比如,拍賣競價時,如果你認定其他競爭者更有錢,會給出更高的價格,你就可能過早地放棄競價或者盲目地開出高價。
所以,你絕對不是朋友圈里最窮的那個人。如果你覺得是,那只是一種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