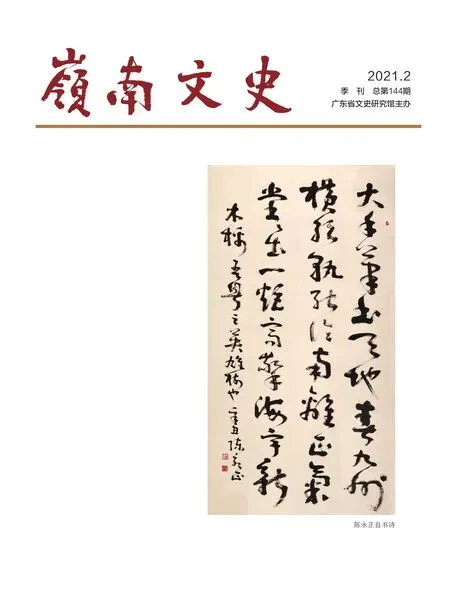讀朱光文《番禺蓼涌四村歷史文化論集》
李 博
《區域社會的結構過程——番禺蓼涌四村歷史文化論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0)由廣州市番禺區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文著。內容主要涉及今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板橋、南村、市頭、羅邊四村的歷史,是朱光文先生對番禺暨珠江三角洲鎮村歷史文化細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在此領域已耕耘多年,先后出版了《番禺文化遺產研究》(2011)、《番禺歷史文化概論》(主撰,2017)兩部概論性著作,《名鄉坑頭:歷史、社會與文化》(主撰,2013)、《省會海門番禺名鎮——石樓地區歷史、社會與文化》(2017)兩部鎮村研究著作,發表論文多篇。
一、主要內容評述
全書分導論,上篇、下篇及附錄四部分。上篇為區域內四村的個案研究;下篇為三個專題研究,最后以南村鄔氏宗族家訓、重要人物小傳,今南村鎮范圍內主要宗族的科第職官表,和有關海云寺、員崗崔氏宗族的三篇論文,以及坑頭村歷史文化概述等為附錄。在導論部分,作者即首先指出蓼涌區域的地理環境基礎——珠江后航道(瀝滘水道)的最大支流。這一基礎賦予該區域獨特的交通樞紐地位,北宋時即曾設“蓼涌渡”,之后隨著村落的發展、經濟社會活動的展開,以及今日仍然興盛的民間誕會、儀式信仰等,均由此演生而來。
上篇四村四論。第一篇主要探討板橋村黎氏宗族從明中期黎瞻取得功名之后至清末,其祖先譜系不斷被塑造、凸顯的過程,尤其是其女性祖先黎道娘形象的“正統化”,以及抗清志士黎遂球由清初遺民記錄,至清中期逐漸進入官修志書,最終以“黃牡丹狀元”的文學形象被推舉為嶺南先賢之一的經過。第二篇主要關注南村鄔氏宗族的發展與整合、祠堂營建與改作、里坊聚落演變的過程。無論是祖先譜系的梳理,還是祠堂的營建,固然包含了后世子孫維護和壯大宗族的努力,但其背后還有更重要或者說更深層的因素——這些物質和文化層面的建構,往往是特定時期經濟、政治訴求的手段。劉志偉教授的開拓性研究即表明,番禺沙灣何族對祖先譜系的梳理,對珠三角普遍流傳的珠璣巷移民傳說的附會,背后就是明清時期何氏開發并掌握了大規模沙田,作為控產機構的何氏宗族進行自我整合以及與小欖何氏等開展區域間宗族聯盟的需求。[1]本書關注的南村鄔氏宗族的興起,即與鄔鳴謙在清嘉慶年間(1796-1820)開始參與沙田開發有關。其后鄔氏家族財富不斷積累,在咸豐年間(1851-1861)的太平天國運動中,更是積極參與團練運動,成為地方事務的主持者,至民國年間鄔氏仍為南村首富。
第三篇則主要呈現市頭村作為龍舟活動“市頭景”所在地,其龍舟活動中神明崇拜、龍船會組織、探親交流背后的經濟、社會、歷史內涵,也關注到改革開放后傳統復興過程中,宗族組織、華僑和港澳同胞、政府、企業起到的作用及其對“傳統”本身的影響。龍舟活動中的村落、組織關系,背后是該區域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所依存的水運網絡,也涉及一些宗族關系等問題,與陸上鄉村誕會中的村落聯盟并不重合。[2]第四篇以羅邊村清末富商羅鏡泉對教育的重視以及取得的碩果為基點,挖掘了元代以后羅氏家族的家族建構與教育教化史。除經濟實力的壯大外,家族教育對宗族延續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在傳統社會,獲得功名的官紳群體往往是宗族整合、譜系建構的重要推手。而清末以后,羅鏡泉家族更是以其后代的教育成就,深刻影響了民國時期番禺地區的經濟發展和鄉村建設運動,這也是羅氏大族地位得以維系的重要原因。
上篇的寫作方法,四篇論文都以歷時的方式展開,其所關注的重點是村落的形成、宗族發展和文化建構、今存遺跡及儀式等環節。另外,四村的研究各聚焦一個側面,分別關注鄉村宗族的文化表征、誕會活動的物質基礎以及維系宗族延續的重要因素等內容。四篇文章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關懷,就是該地區鄉村社會的歷史變遷問題。作者試圖通過對每一個案不同側面的討論,達到“互文見義”的效果,以構成蓼涌地區村落、宗族、文化發展的全貌。
下篇以該區域歷史上的重要時期、關鍵問題為切入點,探討清末團練組織與地方社會、民間誕會與社會變遷、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三個問題。美國漢學家魏斐德早在20世紀60年代即曾揭示,清末廣州及附近地區的團練運動是影響廣東、中國近代史進程的重要因素,也由此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他在《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還熱情呼吁:“讓我們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3]本部分第一篇文章所關注的蓼涌乃至番禺沙茭地區的團練運動,其實也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是它的延續。在研究視角上,某種程度上也是其細化和深化。清咸豐年間(1851-1861)團練運動的興起,建立在地方宗族掌握巨大財力的基礎上,也是官府給予團練組織合法地位的結果。有組織的團練,在基層以社學、書院的形式發展,逐漸成為華南社會實際上的基層權力機構,這也是至今鄉村誕會活動中仍可見到的“五鄉會”“十鄉會”等村落聯盟的歷史基礎(參見本書第174-176頁《社廟與村落聯盟表》)。而第二篇緊接著討論這些村落聯盟在民間誕會中的作用,其實也是通過誕會中祭祀、巡游等儀式表征的變化,探討該地區社會變動、權力重組的過程。作者嘗試證明,“東山社”祭祀主神從南海神到北帝的變化,其實也是板橋黎氏在地方的影響力逐漸被南村鄔氏取代的過程。而更大范圍的北帝誕會巡游和聯誼,正是從清咸同年間至民國年間歷次地方動亂(包括宗族械斗、盜寇威脅及后來的日偽統治等)中,該地區各村落之間御寇聯防的結果。這一過程也可以從當地流傳的不同時期北帝顯靈的傳說得到驗證。第三篇主要關注20世紀30年代陳濟棠治粵時期設立的番禺“模范縣”及“蓼涌民眾教育試驗區”的問題,其中也可以看到四村借原有資源在這一運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
就目前研究而言,專論中所涉及的諸如地方團練運動等問題的研究不可謂不多,也已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但本書的特色在于,作者始終堅持地方視角,努力從地方社會具體的歷時變化入手,將地區、國家層面的重大事件與鄉村的社會、文化變動相結合研究。其目的就在于揭示鄉民們是如何從具體的利益、訴求出發,面對具體的問題,利用宗族組織、村落聯盟等手段,維護其所處的鄉村、地區秩序的。而今天仍然存續于民間誕會等活動中的儀式關系,正是這些特定階段歷史事件的遺留,其背后隱藏著地區、國家的歷史。如此展開研究,相當于賦予我們所習聞的框架式、粗線條的歷史敘述以筋骨血肉,使之更加充盈、具體,其實也正與劉志偉教授曾提倡的“人的歷史”的理念若合符節,即“我們的歷史分析以人作為邏輯出發點,那么在人的行為之上,有或強或弱的國家權力存在,有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形成不同的文化傳統,還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東西,都要進入我們的視野,從而得以由人的能動性去解釋歷史活動和歷史過程。”[4]
在史料上,除政府文書、地方史志外,本書也利用了大量族譜、碑刻文獻及田野訪談材料、地方耆老的回憶文字等,也吸收了學界關于各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在上篇、下篇七篇論文中均有體現。作者善于結合方志與各種地方文獻,梳理揭示地方歷史文化變遷的過程及其文化建構。如對板橋黎氏祖先譜系的建構、龍舟活動的社會歷史背景的討論等,多有精彩之處。
二、價值和問題
本書的價值與存在的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討論。
首先,本書作為一部“村史”。現階段的村志、村史編纂者,一般為本地耆老或外聘團隊,前者熟悉鄉村情況,但多未受過系統的史學訓練,編修質量難以保證;后者具備專業知識,但往往對鄉村并不熟悉,容易出現“隔靴搔癢”的問題。[5]而本書作者不僅史學科班出身,且長期從事珠三角歷史文化研究,還承擔著番禺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相較于一般的學院研究者有較大的資料和田野調查經驗優勢。書中除方志、族譜外,使用了大量碑刻、訪談材料,都是作者一次次普查、訪談的成果。在對地方的熟悉程度上,作者也不遜于鄉村耆老,在某些方面的資料掌握上甚至可以說超越了當地人。[6]但本書意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嘗試探索鄉村史志書寫的新模式。如作者曾在《名鄉坑頭》中所坦言的那樣:“我們嘗試借鑒長時段、總體史的史學理念,去重構坑頭村及周邊地區的區域鄉村社會文化史,書寫一部新型的鄉村志書……看到禺南地區區域社會歷史演變的縮影。”[7]也就是說,面對鄉村,我們看到的不應只是鄉民引以為豪的祖先故事、祠堂建筑和儀式場面,也不只是作為廣府城市地區發展史的附屬,而是至今仍然生生不息的宗族、人群生存繁衍、經濟開發、文化創造的歷程。在城市化高歌猛進的今天,這種研究的意義不可謂不重要。不然,將來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在城市高樓夾縫中的青磚祠堂、簡陋小廟,端午節鑼鼓喧天的龍船景,以及帶著“村氣”的地鐵站站名等這些彰顯的物質、文化符號背后所蘊含著何種意義。
但是,就“村史”而言,筆者認為仍有必要區分“村志”與“研究”兩種意義的村史。前者重在存史,同時蘊含著當地村民的鄉土情感和自豪感,以及行政指導下的“教化”意義,是一種歷史記錄;而后者旨在梳理村落形成、社會文化演變的過程,是對村落發展史的梳理和總結,是一種歷史認識。二者不相同,也并不沖突。本書顯然更偏向后者,主體部分上、下篇即屬后者,但同時也在努力兼顧前者,試圖使兩者互相補充證明,融為一體。那么,如果可以增加附錄內容,將與該地相關的史料,重要者、不經見者全文收錄,單行易得者著錄并撰解題,以便讀者“按圖索驥”,當會大大增強附錄的意義。
其次,“區域研究”與其說是針對某個特定區域的研究,不如說是以“區域”為視角的研究。無論研究對象是村落、流域、政區或者其他,都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將研究對象放在區域聯系中進行考察。如著中所言:“作為一個小流域或村落群的蓼涌區域,是一個既相對穩定,對(又)動態開放的空間……蓼涌的歷史可以是大谷圍、番禺縣、珠三角乃至嶺南社會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中國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乃至)全球史、世界史的一部分。”[8]這一點并不夸張。蓼涌先賢在維護番禺的地方穩定、經濟發展方面曾發揮重要作用,也曾參與近代以后的留學運動、國際貿易。在這一意義上,本書上編的“個案”也是區域研究,下編定名為“區域”就顯得多余。它實際上是以蓼涌流域或更大范圍的專題研究,定為“專題”或更恰當。
而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是一項歷史人類學研究。題目中“結構過程”一詞,即劉志偉教授對蕭鳳霞教授提出的“structuring”一詞的翻譯,意即個人在歷史或社會中不斷創造關系和意義的網絡(結構)又受其影響的永無止境的過程。[9]程美寶教授也曾指出,區域史研究“在于明白過去的人怎樣劃分,在于明白這段‘劃分’的歷史”,其實也是這一意思。[10]作者細致關注蓼涌宗族族譜編纂、祠堂營建、神明崇拜的變遷過程,其所關懷的,實際上就是在這些鄉村社會文化建構活動背后,蓼涌、番禺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社會變遷的歷史。通過作者對這四個村落及所在區域的細致研究,人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明清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歷史,了解今日所見社會、文化現象從何而來。而專題研究中清末盜亂中“盜匪”與地方宗族的關系、民國蓼涌民眾教育試驗區等問題的探討似仍有繼續深入的空間。
最后,本書每篇之后都配有圖片,使讀者在文字論述之外,可以直觀地了解該地區的聚落形態、建筑風貌、儀式場景等,是一大優點。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過于追求齊整,其中的地圖與其他圖片按同一規格排列,導致很多內容細節難以辨識。如導論中所附清末至20世紀40年代蓼涌流域地圖(第16頁),對理解前文所述蓼涌地區時空變遷非常重要,應適當加大排印尺寸。而一些呈現村落風貌、儀式現場的照片,則可在保證相當清晰度的前提下加以壓縮。另外,書中引文偶有標點錯訛,再版時可以加以改進。
總體上本書是一部“解剖麻雀”之作,為人們了解珠江三角洲地區歷史時期、特別是明清以后鄉村社會的變遷提供了一個“顯微鏡式”的窗口,也為珠三角乃至中國鄉村社會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供對話的樣本。朱光文先生從事番禺暨珠三角歷史文化研究近二十年,不僅情感所系,用力深勤,也在不斷地嘗試新的研究視角,從聚落、建筑、文化旅游、鄉村社會史,到歷史人類學、區域史,本書可謂其多年精耕細作的成果,期待朱先生未來有更多創獲。
注釋:
[1] 參見劉志偉:《祖先譜系的重構及其意義——珠江三角洲一個宗族的個案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18-30頁;劉志偉:《宗族與沙田開發——番禺何族的個案研究》,《中國農史》1992年第4期,第34-41頁。
[2] 作者也曾專文討論沙灣司龍舟習俗與當地磚瓦業生產所依存的市橋水道水運網絡之間的關系。參見朱光文:《水運社會的地方文化網絡——以宋以來廣州府番禺縣沙灣司磚瓦業和龍船習俗為中心的考察》,《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6卷第2期,2018年10月,第43-92頁。
[3] [美]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王小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6頁,1988。
[4] 劉志偉、孫歌:《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于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第21-28頁,2016。
[5] 張麗蓉:《改革開放以來村志編修的分析與思考——以廣州地區為中心》,《中國地方志》2016年第10期,第32-38頁。
[6] 朱光文先生曾編纂《南村人文讀本》(后改為《南山記憶——南村鎮歷史文化通識讀本》)、《禺山記憶——番禺非物質文化遺產通識讀本》等針對中小學的鄉土讀本,實際上也親身參與了當地鄉村記憶的保護與傳承。
[7] 朱光文、陳銘新:《名鄉坑頭:歷史、社會與文化》。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第230-232頁,2013。
[8] 朱光文:《區域社會的結構過程——番禺蓼涌四村歷史文化論集》(《番禺文史》第二十九期)。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第12頁,2020。
[9]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54頁。
[10]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31頁,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