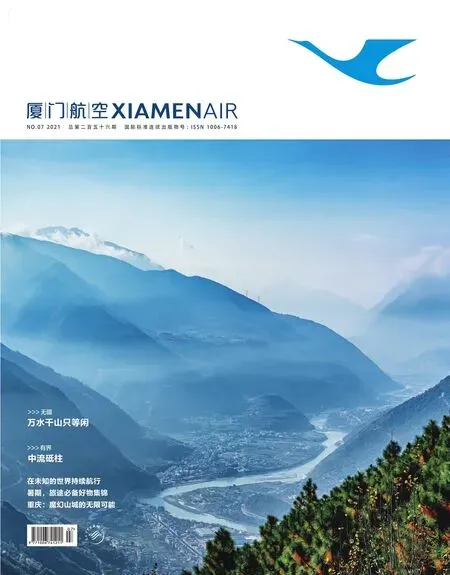自家智慧便通神
撰文_曹放
迎面千佛閣,一副對聯(lián)分外醒目。上聯(lián)是:“運(yùn)法眼看得分分明明,這個該如何,那個該如何,到頭來無可如何,絕世慈悲都入夢”;下聯(lián)是:“把靈心養(yǎng)的活活潑潑,動機(jī)亦在此,靜機(jī)亦在此,立腳處全然在此,自家智慧便通神”。好聯(lián),好聯(lián)!我心神一斂,不由暗自贊嘆。是呀,何必妄運(yùn)法眼,即使看得分明,你指手畫腳,到頭來又能如何。好一份莫向外求的通透!是呀,何妨養(yǎng)好靈心,要相信,只要良善而有悟性,你自己的智慧便可通達(dá)神靈。好一份全然在我的自信!
蘭州名勝地,共談五泉山。五泉山,《大明一統(tǒng)志》記載:“泉有五眼,相傳漢霍去病擊匈奴至此,以鞭卓地而泉出。”可惜,晚清戰(zhàn)亂,這座蘭州第一名山破敗荒蕪了。劉爾炘,光緒年間進(jìn)士,翰林院編修,目睹了甲午海戰(zhàn)之慘敗,“見清季事不可為”,在京供職三年后,遂于1895年辭官,“浩然歸里”。在返回家鄉(xiāng)蘭州之后的三十四年中,他事功赫赫,其中一大功業(yè)就是重振五泉山。千佛閣上的這副對聯(lián)就出自他的手筆。
記得是十多年前了,2010年8月,又一次暢游蘭州,我登臨了五泉山。曲折盤桓之后,但見千佛閣巍然聳立,林泉清流環(huán)繞而下,重檐亭榭相依陣列,那一份雄鎮(zhèn)萬里西北的高邁,讓人心生敬畏;而劉爾炘撰寫的聯(lián)語“自家智慧便通神”,更是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和長久的啟迪。
壯游大好河山,徐霞客可謂中國自然地理學(xué)的一代宗師,而如果就人文地理學(xué)而言,扛鼎大師則是與他同時代的王士性。王士性,明代萬歷年間進(jìn)士,為官二十余年,他無時不游,無地不游,一生足跡遍布兩京十三省;特別是,他傾盡畢生心血寫成了《廣游志》《廣志繹》《五岳游草》等皇皇巨著,在中國地理學(xué)和旅游學(xué)的史冊上,放射著奪目的光芒。
那是怎樣詩意浪漫的人生喲!王士性是浙江臨海望族之后,出生時家道中落已然清貧,但他自小就“小天下,狹九州”,他那“遙從馬首覓青山”的宦游人生,更是生動地詮釋了同輩思想家李贄發(fā)出的時代宣言:“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他初仕出任河南確山知縣,想到從此以身許國,不知何時才能重返故里,思量之下,他的腳步一走出臨海,不由得被杭州羈絆住了。“當(dāng)其暖風(fēng)徐來,澄波如玉,桃柳滿堤,丹青炫目……余時把酒臨風(fēng),其喜則洋洋然。”一篇《游武林湖山六記》,那字里行間的至情至性,可謂“驚起一灘鷗鷺”。河南確山任職期滿后,他趁著休整空隙,游歷了嵩山少林寺。“活人做死事,難向一切說。打破這片石,方許見如來。”他在少林寺題詩一首,不僅證明他靈通佛性,而且留下了一道人文勝跡。奉派四川參議,他一路逍遙,穿行燕趙韓魏古國舊地后,取道華陰,登臨西岳華山,過了關(guān)中是寶雞,不知不覺間進(jìn)入連云棧道了……“此地青山夾馳,綠水中貫,豐林前擁,疊嶂后隨,去來杳無其跡”。四川為官期間,他還跑去了峨眉山,機(jī)緣之下得遇燦爛佛光,“一大圓相光起平云之上,如白虹錦跨山足,已而中現(xiàn)作寶鏡空湛狀,紅黃紫綠五色暈其周”。哈哈,王士性,你是怎樣的“獨(dú)向江門枕濁流”呀!
王士性宦游的意義,不只是摹寫下田園山水之勝,更有旅游產(chǎn)業(yè)意識的萌發(fā),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觀念的覺醒。他在《廣志繹》卷四中提出:“西湖業(yè)已為游地,則細(xì)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yè),反不便于此輩。”他這樸素的表達(dá)中,最難得的是,蘊(yùn)含著民本思想和旅游產(chǎn)業(yè)意識。他還以敏銳的洞察力,闡明了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一種關(guān)系,其中,有一個論點(diǎn)特別值得玩味,這就是:“天下事不可懦而無為,尤不可好于有為。”當(dāng)工業(yè)革命帶來嚴(yán)重的生態(tài)災(zāi)難之后,品讀這“尤不可好于有為”之論,有如空谷足音。
又一輪官運(yùn)來了!歷任廣西參議、云南副憲、河南提學(xué)、山東參政之后,大明萬歷皇帝欽定王士性為河南巡撫,這樣的鴻運(yùn)當(dāng)頭,多少人夢寐以求啊!萬萬沒想到,王士性卻力辭不受。為什么呢?因?yàn)樗麉捑胧送玖恕K⒉幌『边@封疆大吏的實(shí)權(quán)與實(shí)惠,他知道,這還伴隨著機(jī)關(guān)算盡的鉤心斗角和應(yīng)接不暇的繁文縟節(jié)。他早已經(jīng)心在山水田園了!“余游行海內(nèi)遍矣,惟醉心于是,欲作菟裘,棄人間而居之。乃世網(wǎng)所攖,思之令人氣塞”。這是他在云南任職期間,悠游大理時寫下的文字。沖決“世網(wǎng)所攖”,洞開“令人氣塞”;過盡千帆皆不是,唯山水田園可寄平生。品讀王士性,我欣然一笑,這真是“自家智慧可通神”,官場上難得的清醒而曠達(dá)。
再回頭說到劉爾炘。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三千萬兵員和平民的傷亡引來舉世震驚。梁啟超趕赴歐洲考察后,但見滿目瘡痍,他對人類命運(yùn)與中華國運(yùn)的思考,也深深地觸動了遠(yuǎn)在西北一隅的劉爾炘。這個滿腦子“之乎者也”的儒學(xué)大家,四處搜尋,找來了西方哲人的學(xué)術(shù)著作,哥白尼、笛卡爾,牛頓、達(dá)爾文,他一一細(xì)心品讀,同時又深深思慮。結(jié)合對時事的研判,1921年,他在全隴希社國文講習(xí)班的一次訓(xùn)話中,提出了一個振聾發(fā)聵的問題:機(jī)器劫。他指出,百余年來為世界少數(shù)人造最大幸福的是機(jī)器,此次歐戰(zhàn)人類所受最大的劫難也是機(jī)器,因此對這一問題當(dāng)名之曰:機(jī)器劫。在眾口囂囂中,他保持著清醒的獨(dú)立思考,他并不是要阻礙科技進(jìn)步,而是擔(dān)憂如果沒有文明力量的引導(dǎo),科技就會失控,機(jī)器就會統(tǒng)治人類,甚至成為一種戰(zhàn)爭工具。在那次訓(xùn)話結(jié)束的時候,他還極其沉痛地預(yù)言:“全世界若不同心同德挽回這次劫運(yùn),這次歐戰(zhàn)還是小事,大禍還在后頭呢!”果不其然,不到二十年,1939年爆發(fā)二戰(zhàn),傷亡多達(dá)九千萬人。這是劉爾炘預(yù)言的一個殘忍驗(yàn)證。
如何應(yīng)對氣勢洶洶的“機(jī)器劫”,這一命題深深地困擾著晚年的劉爾炘。“向五大洲中靜觀,日后群倫那個能逃機(jī)器劫;在數(shù)千載上便憂,天下來世而今枉費(fèi)圣人心。"他精心撰寫的這副對聯(lián),題刻在五泉山萬源閣上。他殫精竭慮,寫下了平生最后一部著作:《拙修子太平書》。劉爾炘的答案是:實(shí)行“以理馭氣”,并輔之“以氣制氣”。他認(rèn)為,要以儒學(xué)之“理”,駕馭物質(zhì)科學(xué)之“氣”,使得理有主權(quán),氣能達(dá)用,形成社會運(yùn)行于正確軌道的有效機(jī)制;然而,單憑精神的力量是不夠的,他提出還要“以氣制氣”,就是依靠物質(zhì)的力量去解決物質(zhì)的問題。他滿懷信心地作出了一個展望,一個發(fā)乎儒學(xué)本源又著眼人類千年的展望:世界動亂1000年以后,人類幡然醒悟,儒學(xué)與科學(xué)合為一體,得“神悟”發(fā)明“中和素”,氤氳流布五洲四海,人類共得熏陶感化,蓬勃煥發(fā)出先天的善良秉性。從此,人類進(jìn)入太平盛世,那是一個“全球一家、景星慶云、和風(fēng)甘露”的太平盛世。他將這個太平盛世命名為“還醇世代”,并將其到來的具體時間作了標(biāo)定,是在公元3330年。哈哈!劉爾炘,“自家智慧便通神”,在儒學(xué)發(fā)展史上,他這樣的見解和表述方法,可是前無古人的吶!
古往今來,中華士人文化博大精深,細(xì)細(xì)探究起來,總會看見幾許靈性光芒的閃耀。那是怎樣一種會心之喜呀!王士性的豐盈情致,豈是一個巡撫的官位能夠籠罩住的呢?他沖決了世網(wǎng)之?dāng)t,那詩意的人生是何等的光華流麗……劉爾炘的悲天憫人,又是怎樣的闊大而深邃呀!他前瞻人類未來的胸襟和眼界,遠(yuǎn)遠(yuǎn)地超越了他困居的中國西北邊城,他對中國儒學(xué)的高度自信,也釋放出一種穿越時代的萬丈光芒……真的,只要心無塵垢,只要靈性加持,我們“自家智慧便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