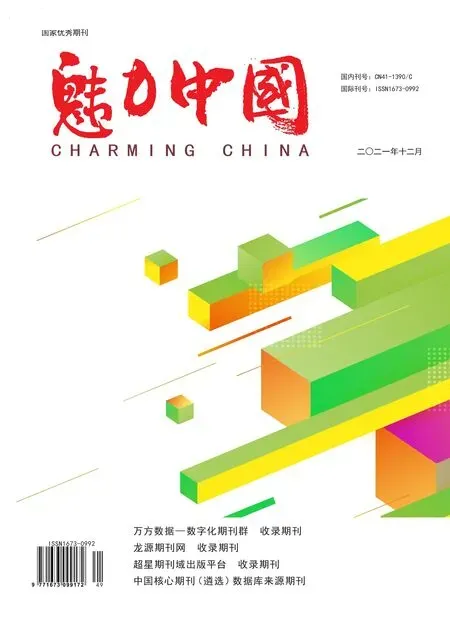淺談戲曲表演藝術(shù)特征
朱麗芳
(常州市武進(jìn)區(qū)戲劇團(tuán),江蘇 常州 213000)
程式的出現(xiàn)使中國戲曲形成了一種獨(dú)特的形式美感。“藝術(shù),意味著對象被轉(zhuǎn)變成形式。”戲曲是一門形式感很強(qiáng)的藝術(shù),用李澤厚先生的話說,“京劇的程式就更厲害了,程式是很能體現(xiàn)形式美的”。和其他藝術(shù)形式相比,戲曲的獨(dú)特之美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程式化。“京劇演員的地位、轉(zhuǎn)身、動作處處有板有眼,有一定規(guī)則。但這不但不呆板,反而非常自然,這是一種美術(shù)化的自然。”這是對程式化的推崇。沒有了程式,戲曲就會黯然失色,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增強(qiáng)了生活化卻丟失了程式化的影視戲曲不能十分吸引受眾的原因。對于戲曲來說,程式并不代表僵硬死板、一成不變。由于程式是藝人在創(chuàng)造具體角色的過程中產(chǎn)生的,所以角色行當(dāng)不同,表演同一個動作,在程式上就有了區(qū)別。
一、戲曲行當(dāng)?shù)牧髯?/h2>
在戲曲的發(fā)展史中,行當(dāng)?shù)淖兓且粋€由簡至繁的過程。從參軍戲中兩個角色“一主一仆相從為戲”到宋雜劇中的“末泥”“引戲”“副凈”“副末”“裝孤”(《都城紀(jì)勝瓦舍眾伎》),再到南宋戲文的生、旦、凈、末、丑、外、貼基本定型,其發(fā)展動力是已有行當(dāng)不能滿足戲曲表現(xiàn)社會生活的要求。各種生活內(nèi)容被不斷搬上舞臺,這必然要求進(jìn)一步豐富戲曲人物,正像王國維所說:“一表其人在劇中之地位,二表其品性之善惡,三表其氣質(zhì)之剛?cè)嵋病!币虼耍輪T必須不斷創(chuàng)造出新的表演技藝,以與新的人物和內(nèi)容相適應(yīng)。這一過程在戲曲發(fā)展的歷史進(jìn)程中被不斷重復(fù),所以今天的戲曲舞臺上才有如此豐富的行當(dāng)種類。而每一個新行當(dāng)?shù)拇_立,即標(biāo)志著一套與之相適應(yīng)的表演程式已經(jīng)發(fā)展完備。戲曲“演人物”,是通過表演技藝的不斷豐富和完善來實(shí)現(xiàn)的。屢屢有人出于“演人物”的需要,敢于突破行當(dāng)限制,從不同行當(dāng)中吸取不同的特征加以融合,從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人物。當(dāng)這種新人物的創(chuàng)造被不斷重復(fù),直至作為一個類型為觀眾所接受時,新行當(dāng)即宣告出現(xiàn)。王瑤卿、梅蘭芳當(dāng)年創(chuàng)造“花衫”這一行當(dāng),即不滿足于其時行當(dāng)對戲曲人物類型的限制,于是將青衣的沉靜端莊、花旦的活潑靈巧以及刀馬旦的武打工架等特點(diǎn)融于一體,進(jìn)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唱、念、做、打并重的旦角行當(dāng)。由此可見,行當(dāng)?shù)牟粩喟l(fā)展和豐富同樣也是出于“演人物”的實(shí)際需要。所謂“演人物”,其特征如張庚在《戲曲藝術(shù)論》中所說,演員“通過有意識的心理技術(shù)達(dá)到下意識的創(chuàng)作”,如此則要求演員“在舞臺上,在角色的生活環(huán)境中,和角色完全一樣正確地、合乎邏輯地、有順序地、像活生生的人那樣地去思想、希望、企求和動作”。戲曲是演員通過行當(dāng)?shù)谋硌菁妓嚕砸环N“有規(guī)律的自由”來表現(xiàn)人物,因此,任何舞臺形象的塑造都離不開對表演對象的體驗(yàn)。時下,部分戲曲演員對行當(dāng)及其程式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囿于已有行當(dāng)固步自封,無論演出傳統(tǒng)劇目,還是新編劇目,都只知機(jī)械的表演程式,這其實(shí)是與行當(dāng)?shù)谋举|(zhì)——“演人物”背道而馳的。總之,只有當(dāng)演員充分認(rèn)識到戲曲行當(dāng)與人物塑造之間的關(guān)系,不再被“演行當(dāng)”還是“演人物”所困擾時,才可能在幾近凝固的程式表演中破繭而出,不斷創(chuàng)造出新的舞臺形象,甚至創(chuàng)造出新的行當(dāng)。
二、戲曲藝術(shù)的綜合性
稱得上綜合性的藝術(shù)有很多,如話劇、歌劇、舞劇等。但與這些綜合性藝術(shù)相比,中國戲曲的綜合性程度更高。“綜合性”指戲曲不僅能把“唱、念、做、打”四種表演手段有機(jī)地融為一體,而且它將作為時間的藝術(shù)(如表演、音樂、舞蹈、歌唱、朗誦等)與空間造型的藝術(shù)(如繪畫、建筑、雕刻)等有機(jī)地融合起來。中國獨(dú)有現(xiàn)人物、抒發(fā)感情、深化主題服務(wù)。'在節(jié)奏的統(tǒng)領(lǐng)下,每一種表演語匯的獨(dú)特表現(xiàn)力都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例如,戲曲中人物的服飾、帽翅、翎子、甩發(fā)、水袖、髯口、鸞帶等,在演員表演的過程中均能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特點(diǎn)、內(nèi)心世界及所處境遇等等。在京劇《野豬林》中,林沖在受酷刑時,就運(yùn)用了甩發(fā)中的“打”“挑”“旋”等技巧動作,表現(xiàn)自己對高俅忍無可忍的沖天憤恨;當(dāng)高俅一再逼供之時,林沖義憤填膺地唱出“我寧愿一死也決不招認(rèn)”之后,又運(yùn)用了甩發(fā)中的“帶”的技巧,昂頭挺胸亮相來突出林沖寧死不屈的倔強(qiáng)性格。再如漢劇的神話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為了表現(xiàn)白骨精被孫悟空戰(zhàn)敗之后的狼狽之態(tài),運(yùn)用了甩發(fā)中“旋”的技巧動作,這一鼓巧的運(yùn)用,對于表現(xiàn)白骨精焦頭爛額、無路可走的狼狽相,起到很好的藝術(shù)渲染作用。同樣,髯口的多種表演方式如“摟”“撩”“挑”“推”“托”“抖”“甩”“吹”等,都可被表演者依據(jù)劇中人物情緒的需要而靈活地加以運(yùn)用。
三、虛擬的表演特性
任何一種藝術(shù)形式都要考慮到如何處理藝術(shù)真實(shí)和生活真實(shí)的關(guān)系的問題。在戲曲形成的過程中,由于物質(zhì)條件有限,舞美設(shè)計十分簡陋。在這種條件下,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現(xiàn)生活真實(shí)?其實(shí),不僅是戲曲,很多其他的藝術(shù)形式,如話劇、芭蕾舞、歌劇,也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所以,必須對生活進(jìn)行變形才能形成藝術(shù)真實(shí)。只是各種藝術(shù)形式對生活進(jìn)行變形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
戲劇是通過舞臺表演的形式來反映生活的。舞臺對于戲劇就是一種限制。話劇是這樣處理生活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的關(guān)系的:戲劇家要求反映的生活是無限的,而舞臺的空間總是有限的。戲劇情節(jié)時間跨度往往很大,但一臺戲?qū)嶋H演出的時間只能持續(xù)3 小時左右。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一種做法是:把舞臺當(dāng)作相對固定的空間,采取以景分場的辦法,截取生活的橫斷面,把戲劇矛盾放到這個特定場景中來表現(xiàn)。在同一場中,情節(jié)的延續(xù)時間要求使觀眾感到與實(shí)際演出時間大體一致,時間的跨越則在場與場的間歇中度過。這就是西方戲劇中自有“三一律·”以來所慣常采用的基本結(jié)構(gòu)形式。而中國的戲曲卻沒走上這條道路。相比之下,它對舞臺時空的處理更為靈活。它的虛擬、假定、夸張的手法使其有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魅力,這是.在中國獨(dú)有的追求神似、不追求形似的審美觀的影響下形成的。所以,戲曲表演的重要特點(diǎn)就如著名戲曲導(dǎo)演阿甲所說的:“略形傳神,以神制形”。
因此,戲曲的虛擬性就體現(xiàn)在對時空的處理更為靈活上。戲曲中的舞臺時空,是根據(jù)演員的表演需要而不斷流變的時空。時空的變化,周圍的環(huán)境、情景,都以通過演員的虛擬、假定的表演來體現(xiàn),不用實(shí)物,或只用部分的實(shí)物。在戲曲欣賞過程中,演員同觀眾達(dá)成了某種共識,觀眾通過演員虛擬性的動作、表情聯(lián)想到了演員想要表現(xiàn)的真實(shí)生活中的內(nèi)容,從而使演員達(dá)到了藝術(shù)表現(xiàn)的目的。這給演員提供了更大的表演空間,同時也是對他們表演功力的考驗(yàn)。
四、戲曲表演的虛擬手法
首先,對周邊環(huán)境的虛擬。戲曲舞臺總是能用最少的道具、裝置、實(shí)物來表現(xiàn)盡可能多的內(nèi)容,這個虛化了的環(huán)境是由演員的動作、表演來向觀眾暗示說明的。幽比如,在戲曲舞臺上沒有繁復(fù)的舞臺布景,沒有炫目的舞臺裝置,它上面只有簡單的桌椅,甚至空曠的舞臺。戲曲舞臺上的“桌椅”按照不同的用途區(qū)分為不同的含義:有時“桌椅”即為桌椅,如表現(xiàn)廳堂、書房、官府大堂、金殿等環(huán)境;有時“桌椅”則不是桌椅,桌子可以做床、做山,椅子可以做窯門、做井。“桌椅”具體指什么,起決定作用的是演員表演。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無所不指。
其次,對時間的虛擬。舞臺時間是對生活時間的模擬。戲曲有時故意將時間縮短,演員一個下場再上場,雖然是一瞬間,也可表示已經(jīng)過了十年八年。有時故意將時間拉長,如大將戰(zhàn)勝敵人后的耍槍花或刀花,是用拉長時間或時間暫時停止的辦法來表現(xiàn)人物戰(zhàn)勝敵人的高興心情。有的是將時間假定,如《三岔口》在燈火通明的舞臺上表現(xiàn)黑夜中兩人的打斗。
再次,對空間流變的虛擬。通常是通過演員在舞臺上走上半個、一個或多個“圓場』’來表現(xiàn)空間的變換。比如,演員在臺上轉(zhuǎn)一圈可以代表已經(jīng)走了十萬八千里。此外,還可在舞臺上同時出現(xiàn)同一時間發(fā)生在不同地點(diǎn)的事。如山東呂劇《姊妹易嫁》“迎親”一折,左前臺是張父擺酒款待前來迎親的女婿毛紀(jì),臺右的后側(cè)是樓上張素花、張素梅姐妹的臥室。妹妹正再三規(guī)勸姐姐快快梳妝,姐姐卻千方百計拖延時間拒不更衣。張父時而上樓催促女兒素花,時而下樓來安撫女婿毛紀(jì)耐心等待。這場戲極為精練地把發(fā)生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diǎn)的事件及各個人物的不同思想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舞臺氣氛緊張而又有風(fēng)趣。
最后,對動作對象的虛擬。戲曲還可以通過特定的程式化動作對動作對象進(jìn)行虛擬。有的是對對象全部虛擬,如開門、關(guān)門、上樓、下樓、跋山涉水、登高、下坡這些動作的對象并不存在;有的是對動作對象部分虛擬,如以槳代船,以鞭代馬、代驢等等。例如在《秋江》中,老艄公送少女過江,道具只有一支船槳,以一高一矮的站姿來表現(xiàn)兩人在船上一頭一尾的位置和船的起伏,以人的走動來表現(xiàn)船在游動,但無論快慢,兩人必須保持等距離以表現(xiàn)船的大小。為了表現(xiàn)船動而非人動,兩人的起伏動作不能影響兩人的對話。這就要求動作既要協(xié)調(diào)又要熟練,給人“下意識”的感覺。兩人談笑的內(nèi)容與節(jié)奏和劃船的動作與節(jié)奏要各行其是,互不干擾。要使觀眾感覺有情、有景,情景交融。
以上對戲曲具有的高度的綜合性、虛擬性、程式化的藝術(shù)特征分別做了簡單的介紹。但在戲曲表演過程中,這三者是互相交融、互相依賴、互相補(bǔ)充,被節(jié)奏有機(jī)地結(jié)合在一起的,共同為戲曲表演服務(wù)。三者不能相互脫離而獨(dú)立存在。中國戲曲的獨(dú)特的藝術(shù)特征是在傳統(tǒng)美學(xué)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的。它把藝術(shù)作為表現(xiàn)生活本質(zhì)的一種有效工具,顯然,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遠(yuǎn)比單純模仿生活或刻意制造真實(shí)的幻覺要復(fù)雜和深入。對戲曲這三方面特征的了解,更有利于我們提高對戲曲藝術(shù)的欣賞水平,領(lǐng)略戲曲藝術(shù)的美。也正是由于戲曲具有的幾方面的表演特性,造就了“有規(guī)則的自由行動”(布萊希特語)的特點(diǎn),使戲曲與“斯系”(斯坦尼拉夫斯基的“體驗(yàn)派”表演體系)、“布系”(布萊希特的“表現(xiàn)派”表演體系)一起構(gòu)成世界三大戲劇表演派系
綜上所述,戲曲表演程式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多個程式按照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的需要和人物性格的不同組合起來,才能完整地塑造形象和演進(jìn)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