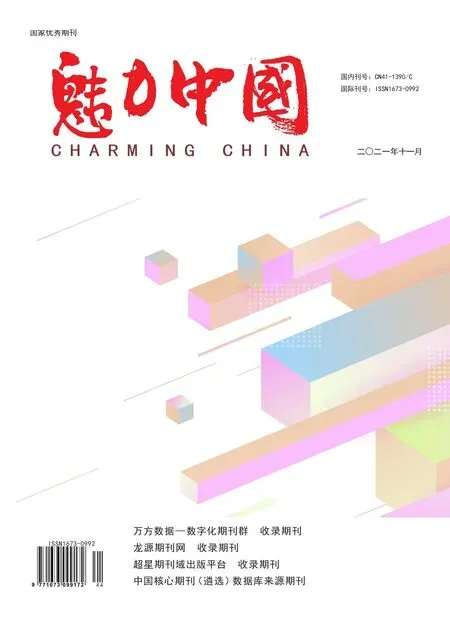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提升策略研究
周麗麗
(山東現代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社會發展也進入了一個劇烈變遷的轉型時期。在這個趨勢下,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城鎮人口遷移活躍度日趨提高,人口遷移的方式也由單打獨斗的個人遷移轉向了家庭式遷移。隨遷子女因為受流動的家庭生活方式的影響和父母職業特征的局限,在面臨完全陌生的生活環境時往往更加茫然無措,隨遷子女家庭在限制資源的前提下面臨著更大的壓力。為了能順利應對家庭遭遇的困境和危機挑戰,這意味著每個隨遷子女家庭成員都需要共同應對這一難題。家庭抗逆力是將家庭視做為整體,在面對困境和危機挑戰時家庭全體成員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和潛能,展現出良好的適應性、溝通力和復原力,使家庭度過危機和逆境。如何調節壓力,有效組織家庭資源,深度挖掘家庭自身的力量,以提升家庭凝聚力和引領力從而克服危機,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的發展現狀
家庭式的遷移方式改變了中國原有的家庭結構和家庭形態,由此出現的隨遷子女群體也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有研究顯示,隨遷子女在抗打擊能力、承受挫折能力和抗逆力等方面與一般兒童有較大差距,目前社會各界對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的關注度和提升也存在著不足和欠缺,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多關注問題視角,優勢視角關注度不足
調查發現,外界多以“問題視角”來關注家庭存在的現實困境,在指導中多是依靠單純的外在救助和服務,單純的為他們鏈接資源來解決問題,并未將重點放在發現和協助服務對象的潛能上,對其家庭內在資源和優勢的挖掘利用明顯不足,造成很多實踐干預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同時,問題取向的隨遷子女實踐干預具有更多的社會成本,也不利于發揮隨遷子女及其生態系統的主體性。隨著積極心理學的快速發展,在家庭抗逆力的實踐指導中,優勢視角日漸受到關注。
(二)多關注個體抗逆力的培養,系統性取向關注度不足
目前,抗逆力的指導多是針對隨遷子女個體而言,未能有效的關注個人所處的系統。比如如何提高隨遷子女的人際交往能力、交流融入能力,如何促進家庭團結和實施有效的親子互動等未能引起足夠重視。在深入開展活動的過程中,研究者雖然會有意識地將家庭、社區、學校等系統納入進來,但開展的關于相關活動也多是從隨遷子女自身出發,讓其學會理解父母、加強親子交流和認識社區等,其系統之間的雙向合作和相互作用的開展還有待于提高。實踐中更多的是將家庭看作個體抗逆力發揮的重要場所,忽略了家庭整體力量的發掘,并未將家庭作為一個整體的特殊優勢和資源來進行探討和加以運用。
(三)多關注現階段的干預,發展性實踐干預不足
目前抗逆力的實踐干預大多只局限于現階段隨遷子女的狀況,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可以解決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即時問題,但卻忽視了隨遷子女及家庭的發展特性,對其在后續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境缺乏預見性,所以一旦實踐服務停止,隨遷子女及家庭仍會陷入困境。所以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家庭和個體都是可持續發展的有機體,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會面臨著不同的心理和社會挑戰,社會實踐的干預指導不應該是靜態的而應該根據隨遷子女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開展具有發展性的、能培養家庭抗逆力的實踐活動。
二、阻礙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提升的影響因素
家庭抗逆力是指將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在面對困境和危機挑戰時挖掘家庭整體的潛力和優勢,充分借助優質資源和社會關系,獲得較好的支持,來解決困難和渡過難關,同時展示出家庭積極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和過程。家庭抗逆力對隨遷子女的影響是持續性的,這與父母的家庭教育觀念與能力息息相關,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教育觀念模糊,教育方式欠妥
隨著社會和科技的高速發展,隨遷子女的成長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家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也需要與時俱進,以滿足新時代的教育需求,但多數隨遷子女家長對于教育觀念的認識仍然較為模糊,往往在“棍棒教育”和“快樂教育”之間搖擺不定。傳統的“棍棒教育”已不能夠滿足教育新要求,而家長對于“快樂教育”的認識也大多僅僅停留在表面。很多家長在家庭教育的過程中未能找到合適的教育方式,存在溝通方式簡單粗暴極端、情緒管理缺失、親子關系緊張等現象。因為工作時間繁忙等客觀原因,家庭成員之間交流時間大幅度減少,相互之間缺少情感交流,對于家庭成員的抗逆力的培養近乎空白或僅流于表面。
(二)教育能力不足,問題視角突出
受學歷、文化水平和精力的限制,隨遷子女的家長在對子女的家庭教育方面多存在無力感,對子女的要求易出現較高和較低兩個極端。當家庭出現困境時家庭成員多是以家庭問題與劣勢的角度來抵御,對家庭成員的潛力和家庭資源優勢的挖掘尤為不足,對提升家庭抗逆力的重視程度較為欠缺。研究中發現,外界夸大了隨遷子女家庭的弱勢和自卑,忽略了他們的積極能動性和富有活力、堅強、正能量的一面。
(三)缺乏多元化的社會支持系統
目前,我國對于提高家庭抗逆力多方合作重要性的認識有待于加強。家庭教育指導的實施主體較為單一,社會力量參與較少,像社區、社會組織以及政府方面尚未參與進來。從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具體組織情況來看,實施主體多為“家園”或“家校”,主要是通過家長學校的媒介,利用家庭和學校的資源來為隨遷子女提供家庭教育指導和學業支持的服務,實施主體主要是家庭教育指導教師等。缺乏多主體參與的聯動機制和多元化的社會支持系統來更好的為隨遷子女家庭提供配套支持服務,同時家庭教育指導所需要的資金來源渠道也有待于拓寬。
三、提升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的實踐框架
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的提升,不僅需要重視家庭成員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相互支持,明確成員各自的責任、權利和義務,還要更加注重家庭抗逆力的整體提高,形成以隨遷子女健康成長為核心的家庭整體抗逆力的提升機制。
(一)轉變關注方向,建立以家庭為本的生態系統
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第一場所,是由若干家庭成員組成的集體,一個人的改變、系統之間的關系變動都可能引起家庭的變化,相應地也會影響家庭其他成員的行為和思想[1]。家庭抗逆力理論中將家庭視為整體,研究重點是關注家庭在困境中如何適應、調整并最終達成平衡和成長,這對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家庭整體適應環境的能力若是未能得到充分激發,那以個人為中心的實踐效果極有可能被大大消解。在提升家庭抗逆力的指導實踐中,本著以家庭為本的原則,將家庭成員做為抗逆力形成的重要因素,將干預系統從個體取向轉向系統取向,幫助各成員加強自我認知、心理健康和提升應對技能,針對其面對的逆境和壓力、問題解決等困難提供具體指導。加強家庭成員之間的有效溝通,提高父母和子女應對壓力的技能,增強家庭凝聚力,在家庭代際內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使之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協作,家庭內部和諧的良好氛圍。指導隨遷子女學會以積極的心態和正確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來應對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挑戰,進而提升家庭適應力和家庭抗逆力水平。
(二)挖掘家庭優勢和潛能資源,建立家庭多系統框架
“優勢視角”是積極心理學中的重要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而“抗逆力”是該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是一種關注人的內在力量和優勢資源的視角,它的最終目標是培養個體和群體的抗逆力。家庭抗逆力的理論體系主要是強調家庭優勢和資源,認為所有的家庭在困境中都可以通過挖掘、利用和調動家庭內部以及外在系統的優勢資源和潛能,成功擺脫危機局面,在逆境中得到成長和恢復,展現出良好的家庭風貌。家庭優勢資源是家庭抵御危機,進行自我修復并能從危機中獲得成長的動力,所以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的實踐干預視角,要從家庭問題轉向家庭資源。
家庭抗逆力的實務取向是重視建立家庭網絡的優勢和潛能,家庭抗逆力框架的應用應圍繞增強家庭的功能、增強家庭內部關系的鏈接、增強家庭與社區之間的重要連接、整合資源以滿足未來生活的挑戰等幾個方面展開。家庭抗逆力實踐的任務是既要識別隨遷子女家庭所存在的風險,幫助家庭成員直面危機并能獲得積極正面的思想活力,保持彈性而穩定的家庭組織模式,肯定、發掘和整合家庭本身的優勢和擁有的支持性資源,協助建立家庭信念系統、家庭組織系統以及家庭溝通系統來更好地抵御困境。
(三)轉變關注方向,重視家庭抗逆力的發展特性
家庭抗逆力雖然有其固有的家庭特征,但并非是靜態的、恒定不變的,而是在與環境的互動中不斷的發展變化。隨遷子女家庭在不同生活階段的環境下發生了改變,危險性因素也相應的發生改變,會遇到不同的困境和危機挑戰,所以不能一味的將家庭抗逆力視為一種個體的、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而應該意識到家庭隨著生命周期的不同,優劣勢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危機也可以成為積極的、正面的轉折點,將家庭抗逆力的過程視為一個發展的過程以應對和解決相應的問題,并且在實踐干預中家庭抗逆力的實踐框架也要緊隨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體現出其成長性和相對性。
針對隨遷子女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挑戰,家庭抗逆力實踐干預過程需要聚焦于家庭所面臨的即時問題,深度挖掘、利用家庭優勢資源以減少、改變或避免風險暴露的機率。協助隨遷子女家庭成員正確看待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境遇以及如何利用系統內外的資源有效抵御困境。針對隨遷子女家庭生命周期不斷發展變化的特點,開展具有預防性的、發展性的實踐干預措施,為家庭提供幫助,提升隨遷子女家庭應對未來持續性危機的能力,使其能更好地做好戰勝困境和危機挑戰的準備,以應對未來可能的難題。
(四)完善組織機構建設,搭建多元化的社會支持系統
家庭抗逆力干預過程應該聚焦于家庭,但是又不應該局限于家庭,需要將隨遷子女及其家庭放到更大的背景環境中去考慮,并且需要結合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來看待問題。完善的配套服務是提高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的關鍵,我國目前尚未建立系統化的、常態化的指導體系。鑒于隨遷子女家庭的類型有千差萬別的特征,不同的家庭在面對逆境時的適應過程差異也較大,在家庭抗逆力的干預實踐中需要不斷的擴充不同類型的家庭樣本,探索擴展多樣化的家庭抗逆力干預模式。同時激發家庭抗逆力系統內部和外部的協同合作,完善組織機構的建設。將鄰里、社區、政府機構、學校等納入家庭抗逆力實踐框架,有效地開展提升家庭抗逆力指導活動,尋求他們和其他社會服務組織的合作,搭建社區、學校、政府機構和社會組織相互合作的多元化社會支持系統,并且強化服務的整體性和資源的整合性。
四、結語
總之,隨遷子女家庭抗逆力實踐干預強調家庭整體優勢,可以有效地協助隨遷子女家庭解決面臨的現實困境,有助于家庭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圍,獲得具有良性的、發展性的動力,有助于家庭整體抗逆力的提升,能更好更快的融入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