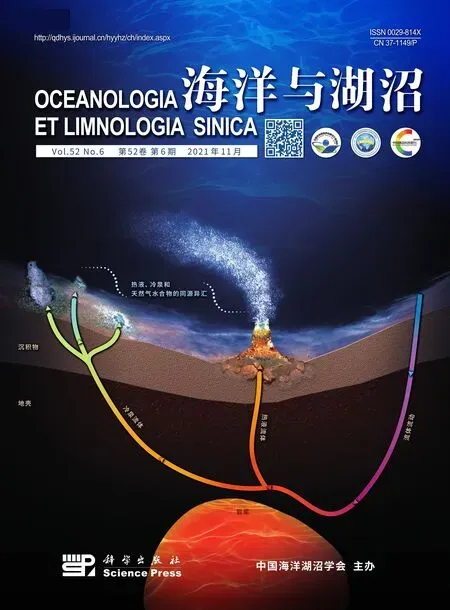基于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重構三維生物擾動構造——以長江口現代沉積為例*
米 智 范德江, 2 劉曉航 鄭世雯 程 鵬 張 鑫
基于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重構三維生物擾動構造——以長江口現代沉積為例*
米 智1范德江1, 2①劉曉航1鄭世雯2, 3程 鵬1張 鑫1
(1. 中國海洋大學海洋地球科學學院 青島 266100; 2. 中國海洋大學海底科學與探測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青島 266100; 3. 中國海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青島 266100)
生物擾動作用能夠加速水層與底質的物質交換, 對水層和底質的耦合作用有著重要的影響。受限于觀測手段和觀測方法, 當前對于生物擾動構造的研究多停留在定性—半定量化的階段。本文選取長江口現代沉積區的4個沉積物柱狀樣, 利用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對生物擾動構造進行三維重構, 運用數字圖像處理實現生物擾動強度的定量表征, 對研究區域生物擾動構造發育的影響因素進行初步分析。結果表明: CT (computed tomography)值與沉積物粒級構成和含水率具有一定關系, 能夠較好地指示沉積物密度變化; 該區出現挖掘構造、覓食蟲孔構造、逃逸蟲孔構造、生物遺跡構造等顯性擾動構造類型, 生物擾動強度介于0%—10%, 擾動強度極大值出現在長江水下三角洲前三角洲和陸架過渡區, 垂向上以及不同站位生物擾動構造差異顯著; 底質沉積物類型、上覆水團性質以及沉積速率是影響該區生物擾動構造發育的主要因素。
生物擾動構造; 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 三維重構; 生物擾動強度; 長江水下三角洲
生物擾動作用(bioturbation)是指底棲生物的攝食、爬行、排泄和駐穴等生命活動對沉積物初級結構發生的改變, 通常伴隨著沉積物的轉移、混合以及上覆水體涌入穴道的現象(Meysman, 2006; 覃雪波, 2010; Kristensen, 2012)。生物擾動構造是表征海底生態環境健康的重要指標, 生物擾動作用促進沉積物與介質之間的物質交換, 并可引起沉積物的擴散混合從而影響沉積物中記錄的古環境信號(Lyttle, 2013)。當前沉積記錄的研究分辨率可達百年尺度和年代際尺度, 由于生物擾動作用造成的測年偏移會使巖心的年代框架產生錯亂, 最終影響到整個研究結果(楊群慧等, 2008)。所以, 在進行高分辨率沉積記錄研究時, 應盡可能避免生物擾動作用對同位素測年的影響或者尋求其他手段消除這個影響(范德江等, 2008)。正因如此, 海洋研究者越來越重視生物擾動作用機制的研究(Mermillod-Blondin, 2011)。
受到觀測手段和研究方法的限制, 現代海洋沉積中生物擾動構造的研究一直處在定性-半定量化的階段, 這是由于生物擾動作用存在不確定性(龔一鳴等, 2009; 張翔宇, 2018), 以及擾動構造后期改造嚴重所致。21世紀之后數字圖像處理技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在地質學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優秀成果。計算機斷層成像技術是X射線技術的延伸, 通過螺旋掃射的方式, 可以獲得樣品三維立體的密度信息, 同時還繼承了X光負片無損性的特點(Hamblin, 1962)。故本文嘗試利用計算機斷層成像技術實現生物擾動構造的三維重構, 完成生物擾動強度的定量表征, 并對長江口現代海洋沉積物中的生物擾動構造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 初步分析生物擾動構造的發育特征和影響因素, 為生物擾動作用機制以及環境效應研究提供基礎。
1 樣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1.1 樣品采集
沉積物樣品于2020年10月由向陽紅18號科學考察船執行東海共享航次時獲得。通過箱式取樣器獲得底質沉積物, 然后進行插管取樣, 共計獲得4根沉積物柱狀樣。其中, SF-1站位處在長江水下三角洲前緣斜坡處, 受長江沖淡水作用明顯。S01-1和S01-2站位在前三角洲邊界地帶, S02-3站位進一步向海延伸, 處在過渡帶之上。柱狀樣品采用長60 cm、橫截面內徑直徑7.5 cm的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 PVC)管采集。站位信息見表1, 站位分布如圖1所示。
表1 站位信息表

Tab.1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ing sites and cores
1.2 分析方法
1.2.1 沉積物巖心CT圖像獲取 插管巖心樣品CT (computed tomography)數據是使用美國通用公司64排128層螺旋GE OPTIMA 660CT儀器通過平掃的方式獲取的。經多次嘗試使用120 kVp、50 mA的工作環境能夠使圖像質量達到最高水準。本次掃描分辨率是0.625 mm, 即每隔0.625 mm獲取一次切片的CT數據; 空間分辨率是512×512, 即最后成圖的水平像素點和垂直像素點個數均為512個(圖2)。最終將圖片以Dicom格式保存, 供后期進行數字圖像處理。4根巖心共獲得2 692張切片。

圖1 研究區及調查站位位置圖

圖2 原始CT (computed tomography)切片圖像
1.2.2 沉積物粒度和含水率測定 沉積物粒度測定: 選取SF-1、S02-3、S01-2沉積物巖心進行分樣, 取樣間隔0.25 cm, 共計獲得442個沉積物樣品。使用英國Malvern公司生產的Mastersizer3000型激光粒度儀進行粒度分析, 具體步驟如下: 取約1 g的樣品放入50 ml離心管當中, 加入5 ml濃度為30%的雙氧水用以去除沉積物中的有機質, 搖晃均勻, 此時會發現氣泡反應, 靜置24 h直至氣泡消失, 如若氣泡不消失則繼續靜置。然后加入3 ml的0.5 mol/L的六偏磷酸鈉, 使沉積物顆粒分散, 最后超聲30 min后進行上機測試。粒度分級采用Ф值標準, 粒度數據以0.25Ф的采集間隔導出, 粒度參數采用McManus矩法公式計算。
含水率測定: 選取各個巖心中分布沉積物樣品進行含水量測定, 將樣品放在電子恒溫干燥箱中于110 °C干燥至恒質量, 用公式(1)計算含水率。

其中,為含水率(%),1為干燥前濕樣質量,2為干燥后樣品質量。
2 計算機斷層掃描的三維重構技術
2.1 基于CT值的數字圖像處理技術
CT值(記為CT)的標準定義是具等厚的物質對X射線衰減的影響變化, 它是計算機斷層掃描中普遍使用的無量綱單位。計算公式如下(汪家旺等, 2004; 彭文獻等, 2010):

式中,為衰減系數,為標度因素, 當=1 000時,CT為Hounsfield單位。
前人研究指出物質衰減系數與物質密度成線性正相關(章程輝等, 2006), 因此推斷CT值受到物質密度的控制, 可以作為密度大小的反映。在沉積學的研究當中, 沉積物密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 受到含水率、孔隙度、組分含量等因素影響。同時CT成像技術相較于傳統X光技術可以獲得高分辨率的信息。對基于CT值的數字圖像處理技術包括圖像預處理、原始CT值提取等工作流程。
2.1.1 圖像預處理 利用ImageJ軟件打開沉積物巖心CT圖像的Tag信息列表, Tag通過數據集的形式保存了拍攝時間、工作環境、掃描分辨率、空間分辨率、窗寬數值、三維空間位置等信息, 這對后續處理工作非常重要。獲取Tag信息之后就需要將原始CT切片進行預處理工作, 選用Python編程語言作為工具開展預處理工作, 包含圖片排序和圖片裁剪兩個步驟。
(1) 圖片排序: 醫用級CT儀器對X光切片的排列順序非常混亂, 與我們常用的排列順序邏輯不一致, 不同的設備之間的排序方法也不一致, 有時會出現切片缺失的情況, 對于生物擾動構造的識別造成不便, 因此需要根據實際層厚(0018, 0050 Thinkness)和切片實際位置(0020,1041 Slice Location)進行重新排序。
(2) 圖片裁剪: 因沉積物柱狀樣CT圖像拍攝時為多根一組同時掃描, 故需要將CT切片進行批量裁剪, 并且在裁剪過程中需要保持坐標系統不變, 這里運用到Python的os、mumpy和matplotlib三個工具包, 在可視化頁面下將圖片裁剪為矩形。最后將矩陣數據保存成mat格式, 以便后期在Matlab環境下進行操作。
2.1.2 原始CT值的獲取 CT值會被計算機通過直線映射的方式轉換為灰度值, 故此我們需要通過逆映射的方式獲取CT值, 逆映射公式如下所示:
CT=××, (3)
式中,為像素pixel的取值;為斜率slope的取值;為截距intercept的取值。
每個點的像素可以在Python中通過get函數獲得, 斜率和截距均能在Tag信息中獲取。至此原灰度圖像已經轉換為CT值的矩陣, 將所獲得的矩陣保存為mat格式。
2.2 CT值與沉積物平均粒徑和含水率的關系
在CT切片圖像上取40×40像素點大小的矩陣, 獲取每一個像素點的CT值, 利用Matlab中的mean2函數求取二維矩陣的平均值, 這樣就獲得每一個切片的平均CT值, 利用沉積物平均粒徑和含水率的高分辨率記錄, 分析CT值與平均粒徑和含水量的關系。選用S02-3站位沉積物數據, 繪制CT平均值、含水率、平均粒徑變化趨勢圖(圖3), 提取相同深度的CT平均值與平均粒徑和含水率分別進行統計學分析(圖4)。
如圖3和圖4所示, CT值與含水率有較為顯著的線性負相關關系, 符合線性回歸方程=1.035 6-0.000 5, 系數在99.9%的置信區間上顯著, 擬合優度2=0.551, 2.5 cm處含水率較低而該處CT值顯著升高, 5 cm處含水率較高CT值則非常低, 整個沉積物巖心20 cm以上區域的含水率約在50%以上, 20 cm以下的區域含水率較低, 約為40%, CT值在20 cm也出現了變化, 底部區域CT值顯著高于頂部區域。
CT值與沉積物平均粒徑的波動趨勢也有著一定的對應關系。經過統計學分析, 發現平均粒徑與CT平均值符合二次項回歸方程=303.9–0.060 87+ 0.000 32, 所有系數均在99.5%的置信區間上顯著, 擬合優度2=0.15, 二次項回歸方程的對稱軸在CT平均值為1 015處, 即當CT平均值小于1 015時, CT平均值上升而平均粒徑變小; 當CT平均值大于1 015時, CT平均值升高則平均粒徑變大。選用數據縮尾法對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分別去除5%的極值數據后重新進行回歸分析, 發現平均粒徑與CT平均值仍然符合二次項關系, 所有系數在99.5%的置信區間上顯著, 擬合優度2=0.17, 擬合優度的上升說明回歸分析通過穩健性檢驗。從地質學角度來講, 淺表層區域的沉積物較為松散, 固結程度差, 平均粒徑大引起沉積物孔隙度變大, 導致密度降低。20 cm以下的深部區域, 沉積物固結程度相對較高, 孔隙度對于沉積物密度的影響減小, 此時CT值與平均粒徑呈現微弱的正相關關系, 這也揭示了該站位樣品由松散到緊密的壓實作用。

圖3 S02-3站位CT平均值、平均粒徑、含水量變化趨勢圖

圖4 S02-3站位CT平均值與含水率和平均粒徑的回歸方程
注:,,,1,2表示擬合系數;表示相關系數;2表示擬合優度
S02-3站位沉積物CT值具有顯著的分段性, 20 cm以上部分CT值較低且變化幅度較大, 20 cm以下深度CT值較高且變化幅度不大。結合平均粒徑和含水率的變化狀況不難看出, 沉積物CT值對于含水率和平均粒徑具有一定的指示意義, 可以很好地展現沉積物密度變化。
2.3 CT圖像三維重構的實現
三維重構技術是指將多組二維圖片按照一定順序輸入計算機, 得到幾何物體的各項參數信息后重構其幾何狀態(王宗彥等, 2002)。針對連續切片的CT圖像常采用體重構法(volume rendering), 即將CT獲得的連續切片按照比例放大, 再按照原層厚組合起來, 實現三維空間的重構。該技術已經廣泛應用于醫學、材料學等領域, 并且有多種軟件可以實現三維重構, 例如3D Slicer、3D Doctor等。本文利用了3D Slicer軟件用以沉積物CT圖像三維重建。
3D Slicer是一款開源的醫學圖像處理軟件, 基于VTK、Python、Qt的基礎上研發, 支持Windows系統, 提供了多模式數據處理的可視化操作功能(曾文曄, 2013)。基于3D Slicer的沉積物CT圖像三維重構工作流程如圖5所示。利用該方法對沉積物樣品的CT圖像進行三維重構, 獲得4個重構模型。

圖5 CT圖像三維重構工作流程圖
2.4 生物擾動強度的定量表征
生物擾動強度通常以擾動比例來表示(王英國等, 1999), 即生物擾動構造體積與沉積物體積的比值, 數學表達式如下:

式中,擾動表示生物擾動構造體積;沉積物表示沉積物體積。本文為實現生物擾動強度的定量化表達, 在高分辨率的條件下將擾動構造近似看做規則圓柱體, 生物擾動比例的計算公式可以得到如下變換:


前文已將沉積物CT圖像轉換為矩陣數據進行保存, 利用Matlab進行下一步分析處理, 處理之前結合生物擾動構造的三維重構圖像, 本文統計了生物擾動構造特征要素的CT值, 如表2所示。
表2 生物擾動構造特征要素CT值統計

Tab.2 CT statistics of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bioturbation structure and other materials
圖像增強是數字圖像處理的關鍵步驟, 其含義是根據矩陣數據進行數字變換使想要研究的區域特點放大, 改善圖像的視覺效果(解睿, 2019)。常采用閾值調節的手段, 本文曾嘗試多種算法調節閾值凸顯生物擾動構造特征, 同時減小沉積物、貝殼、含水率的影響, 但是結果并不如人意, 這是由生物擾動構造的隨機性和環境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故根據特征要素的CT值統計結果, 劃分CT值梯度用以強化生物擾動構造的展示效果。梯度選擇如下: (-1 000,-500, 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600, 650, 700, 900, 1 300, 1 500)。在Matlab中加載預處理完成后的數據矩陣, 根據CT值梯度畫橫剖面和縱剖面的等值線填充圖像, 如圖6和圖7所示。共計獲取橫剖面實驗用圖2 692張, 縱剖面實驗用圖678張。

圖6 S01-2沉積物巖心橫剖面實驗用圖
注: a為11 cm處橫剖面示意圖; b為11.062 5 cm處橫剖面示意圖

圖7 S01-2沉積物巖心縱剖面實驗用圖
通過圖6和圖7可以很清晰地觀察到生物擾動的蟲孔構造。結合蟲孔構造的生長性特征, 并用三維重構圖像和縱剖面圖像可以將生物擾動構造與沉積物區分開, 之后使用ImageJ軟件通過標定感興趣區域獲取生物擾動面積。根據計算公式即能實現生物擾動強度的定量化表達。
3 長江水下三角洲的生物擾動構造
3.1 長江水下三角洲概況
長江水下三角洲是由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緣、前三角洲組成, 呈從河口開始舌形向東南突出(陳吉余等, 1959, 1987; 陳中原等, 1986; 董永發, 1989)。該處近海環流發育, 水動力環境不穩定, 以長江沖淡水的影響最為劇烈, 它具有顯著的季節變化特征(王亮, 2014)。長江入海陸源碎屑物質大約有50%在此沉積, 以細砂粉砂為主, 底質沉積物類型復雜。長江口及其鄰近海域存在大型底棲生物約400余種, 主要分為四大類: 多毛類、軟體動物、甲殼類、棘皮動物(劉錄三, 2002)。多毛類和甲殼類整體分布廣, 遍布整個長江水下三角洲區域, 軟體動物主要分布在三角洲前緣斜坡和泥質沉積區當中, 棘皮動物種類較少, 多分布于浙閩沿岸和陸架斜坡處。多毛類是在生物量上占據絕對優勢, 自近岸至外海逐漸降低, 是該區最主要的造跡生物。
3.2 生物擾動構造的三維重構
利用三維重構技術對各站位生物擾動構造進行重構, 可以清晰地顯示各個站位沉積物中生物擾動構造發育和分布特征(圖8)。
(1) SF-1: 生物擾動構造數量較多, 各個層深均有分布, 整體擾動強烈。表層存在單側通水的逃逸蟲孔構造, 該構造長約5 cm, 垂切于沉積物表面, 其下部發育有一巨大的U型蟲孔構造, 斜插在PVC管中, 該構造屬于覓食蟲孔構造, 視野內直線長約18 cm, 蟲孔內徑最大處約為1.2 cm, 蟲孔周圍的沉積物擾動明顯, 影響到蟲孔壁的觀察, U型蟲孔構造近沉積物界面一側似與頂部的逃逸蟲孔構造連接在一起, 形成共生組合。中下部多發育各種形態的覓食蟲孔構造, 亦可見部分殘存的挖掘構造, 最長一處構造痕跡長約12 cm, 內徑不足0.1 cm。
(2) S01-1: 該站位生物擾動構造集中在淺表層5—10 cm處, 頂部生物擾動發育, 中下部生物擾動幾乎不發育。單個擾動構造呈現U型、Y型等多種形態, 多數為逃逸蟲孔構造, 垂向長度小于10 cm, 內徑細小, 纖維管狀的蟲孔構造相互交纏, 呈樹根狀錯綜復雜的組合形態。

圖8 各站位生物擾動構造三維重構圖
(3) S01-2: 該巖心生物擾動狀態與S01-1相似, 巖心上部(0—10 cm)逃逸蟲孔構造發育, 垂向長度約為7—8 cm, 相互交纏呈網狀; 中部區域可見較多地覓食蟲孔構造, 孔徑較頂部的逃逸蟲孔構造明顯增大, 約為0.5 cm, 構造周圍有不規則沉積物聚集, 推測為蟲孔通水后致使周圍沉積物密度發生改變所致, 頂部的逃逸蟲孔構造與中部覓食蟲孔應為共生組合; 下部生物擾動不發育。
(4) S02-3: 整體上來看該巖心生物擾動作用較為微弱, 且擾動構造主要集中發育在頂部, 以微小纖維管形式出現, 向下生物擾動構造零星出現; 底部出現一生物遺跡構造, 呈現月牙形, 由許多球形顆粒堆積而成, 推測為生物排泄物的堆積體。多數蟲孔構造都有重新充填的痕跡, 與周圍沉積物發生混合作用, 密度特征效應降低, 導致形態展示模糊。
3.3 生物擾動強度及其垂向分布
巖心SF-1、S01-1、S01-2、S02-3的平均生物擾動強度分別為1.325%、0.889%、1.680%、0.471%, 擾動強度的極大值點出現在S01-2巖心的表層0.3 cm處, 約為10%, 極小值為0, 表示無擾動狀態, 多出現在巖心中下部, 四個不同巖心的生物擾動強度差異顯著。同時擾動強度的垂向分布特征也不盡相同(圖9), S01-1和S01-2站位生物擾動強度垂向上呈現向下衰減的形式, 但是衰減速度不一致, S01-1站位擾動強度的衰減速度較慢, 呈現垂向遞減形式。S01-2站位擾動強度的衰減速度較快, 呈現指數衰減的形式。SF-1站位沉積物中部生物擾動強度較高而兩側較低, 呈現形式為中間隆起的橄欖形式。S02-3站位的生物擾動強度微弱, 垂向上呈現波動減少的特點。
3.4 生物擾動構造發育影響因素的初步分析
劉衛東等(2009)在進行生物擾動構造研究的過程中曾經指出溫度、光照、食物是影響底棲生物活動的重要因素, 而王慧中(1985)指出沉積速率較快的河口地區不適合生物擾動構造的發育。本文以底質沉積物的類型和上覆水的溫鹽數據為支撐, 對生物擾動構造發育的影響因素進行初步分析。
3.4.1 底質類型 底質類型會影響大型底棲生物的棲息環境, 并且朝利于生物活動的環境遷移。生物擾動構造在淺表層發育顯著, 故取頂部(10 cm以上)沉積物生物擾動強度與沉積物組分含量進行分析, 將生物擾動強度和沉積物組分含量匯總見表3。
結合圖9和表3可知, 生物擾動強度與底質中黏土含量密切相關, 黏土含量高的站位(如SF-1)生物擾動強度較低, 而黏土含量低的站位(如S01-2)生物擾動強度較高。黏土組分在生物擾動作用中代表的主要是顆粒細、孔隙度小、固結程度強的沉積物, 黏土組分含量低則砂質+粉砂質含量高, 含水率和含氧量均會隨砂質+粉砂質的含量上升而升高, 可能形成利于生物棲息、覓食的環境, 促進生物擾動作用。
從生物擾動構造類型的角度來將, 砂+粉砂質含量較高的沉積物中易發育網狀、根系狀蟲孔構造, 蟲孔交織纏繞, 對沉積物擾動強烈。而黏土組分含量高的沉積物中生物擾動構造發育程度較弱, 主要發育挖掘構造, 底棲生物向深部掘穴獲得生命所需營養物質、空氣和水。沉積物粒級組成與生物擾動強度具有顯著的相關性(覃雪波, 2010)。在加拿大芬迪灣的生物擾動作用研究中Dashtgard等(2008)建立粒度參數與總有機碳的關系以及野外實測調查解釋這一現象, 同時也指出相同環境下生物擾動易在砂質含量高處發生。本文實測結果對該結論加以印證。
3.4.2 水團和沉積速率的影響 長江水下三角洲上覆水團受河流和海洋的混合作用, 溫度、鹽度變化較大, 在河口汊道區以淡水為主, 水流湍急, 而前三角洲和陸架過渡區則以海水為主, 受環流、沖淡水的共同作用, 不同的水團環境所發育的生物擾動構造和擾動強度也不盡相同。相對而言, 在受長江沖淡水影響的海域, 因為接收了豐富的長江來源的營養鹽(董書航, 2015), 有利于生物的生存, 可以促進底棲生物的發育, 導致該區S01-1和S01-2的生物擾動強度值較高, 生物擾動類型以網狀蟲孔構造和根系狀蟲孔構造為主, 集中發育在頂部沉積物區域; 而S02-3站位于正常陸架, 受長江來源影響小, 生物擾動作用較前兩處站位微弱, 接近于不發育狀態。同樣受長江沖淡水強烈影響的SF-1站, 總體上生物擾動強度反而較低, 或是因為高速的沉積速率不利用大型底棲生物生活。

表3 頂部沉積物生物擾動強度與底質組分

Tab.3 Bioturbation intensity and sediment composition of the top sediment
統計前人在該研究區域210Pb、137Cs測年的研究結果,通過插值法獲得四個站位的沉積速率。SF-1站的沉積速率約為1.14 cm/a, S01-1站約為0.69 cm/a, S01-2站約為0.35 cm/a, S02-3站約為0.623 cm/a (王永紅, 2003; 莊克琳等, 2005; Liu, 2006; 王昕等, 2013; Qiao, 2017)。關于沉積速率對生物擾動作用的影響, 學者持有不同觀點, Rhoads (1982)認為生物擾動強度與沉積速率呈現負相關關系, Moore等(1957)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研究時也指出當沉積速率超過4 cm/a時生物擾動幾乎不發育, 覃雪波(2010)則認為高沉積速率可以帶來更加豐沛的營養物質從而促進生物擾動作用進行。結合本文生物擾動強度數據以及前人實測的沉積速率來看, 沉積速率制約生物擾動作用, 當沉積速率過快時生物擾動構造發育微弱, 在長江水下三角洲及其鄰近海域最適宜生物擾動構造發育的沉積速率約為0.3—0.6 cm/a。
6.牛流行熱。急性死亡多因窒息所致。剖檢可見氣管和支氣管黏膜充血和點狀出血,黏膜腫脹,氣管內充滿大量泡沫粘液。
4 結論
利用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實現生物擾動構造的三維重構, 并以此為基礎對長江水下三角洲生物擾動構造進行三維重構, 初步探討了生物擾動構造的影響因素, 取得以下認識。
(1) 形成基于CT數字圖像的重構沉積物巖心中三維生物擾動構造的方法和處理流程。
(2) 揭示了沉積物巖心CT值與含水率、沉積物粒級構成的關系。經過統計學分析, 發現CT值與沉積物含水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與沉積物平均粒徑的關系較為復雜, 與CT值存在二次項關系, 在淺表層與沉積物平均粒徑呈現負相關, 在深部區域與沉積物平均粒徑呈現正相關。
(3) 重構了長江水下三角洲4個站位的三維生物擾動構造, 揭示該區出現挖掘構造、覓食蟲孔構造、逃逸蟲孔構造、生物遺跡構造等顯性擾動構造類型和垂向發育特征, 定量計算生物擾動強度。
(4) 該區生物擾動構造的類型和強度與底質類型密切相關, 黏土含量高的泥質沉積物不適宜生物擾動構造的發育, 而在砂質和粉砂質含量高的沉積物中易發育網狀和根系狀蟲孔構造。沉積速率以及上覆水團性質也對生物擾動構造有著重要的影響, 沉積速率過快不利于生物擾動構造的發育, 正常溫鹽的海相環境中生物擾動構造較發育, 而在溫鹽梯度變化大的混合水團環境中生物擾動作用微弱。
王 昕, 石學法, 王國慶等, 2013. 長江口及鄰近海域現代沉積速率及其對長江入海泥沙去向的指示意義. 地球科學—中國地質大學學報, 38(4): 763—775
王 亮, 2014. 東海典型泥質區高分辨沉積記錄及其對氣候環境變化的響應. 青島: 中國海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18—20
王英國, 王珍如, 1999. 河口灣區生物擾動強度及擾動作用特征研究——以山海關大石河河口灣為例. 青島海洋大學學報, 29(4): 709—714
王永紅, 2003. 長江河口漲潮槽的形成機理與動力沉積特征.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
王宗彥, 梁遠蕾, 李奇敏等, 2002. 斷層數據三維重構技術的研究進展. 工程圖學學報, (1): 125—130
王慧中, 1985. 江浙一帶現代海灘的生物擾動構造及其指相意義. 地質科學, 20(1): 53—58
莊克琳, 畢世普, 劉振夏等,2005. 長江水下三角洲的動力沉積. 海洋地質與第四紀地質, (2):4—12
劉衛東, 陶 麟, 劉吉全, 2009. 生物擾動構造及其意義簡述. 內江科技, 30(5): 15, 40
劉錄三, 2002. 黃東海大型底棲動物生物多樣性現狀及變化研究. 青島: 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4—44
楊群慧, 周懷陽, 季福武等, 2008. 海底生物擾動作用及其對沉積過程和記錄的影響. 地球科學進展, 23(9): 932—941
汪家旺, 王德杭, 張廉良等, 2004. 骨組織CT值與骨結構成分間的關系研究. 中國醫學影像技術, 20(9): 1328—1330
張翔宇, 2018. 遺跡化石Zoophycos及生物擾動強度的分形拓撲研究. 焦作: 河南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3—63
陳中原, 周長振, 楊文達等, 1986. 長江口外現代水下地貌與沉積. 東海海洋, 4(2): 28—37
陳吉余, 張重樂, 1987. 長江河口及其鄰近海域的自然環境.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 86—94
陳吉余, 虞志英, 惲才興, 1959. 長江三角洲的地貌發育. 地理學報, 25(3): 201—220
范德江, 徐 琳, 齊紅艷, 2008. 長江水下三角洲淺表沉積層中的生物擾動構造. 海洋與湖沼, 39(6): 577—584
龔一鳴, 胡 斌, 盧宗盛等, 2009. 中國遺跡化石研究80年. 古生物學報, 48(3): 322—337
章程輝, 徐 志, 韓東海, 2006. 紅毛丹組織X射線衰減系數與其密度的相關性. 熱帶作物學報, 27(3): 94—96
彭文獻, 彭天舟, 葉小琴等, 2010. CT掃描參數對人體組織CT值影響的研究. 中華放射醫學與防護雜志, 30(1): 79—81
董書航, 2015. 東海營養鹽分布特征及跨陸架交換研究. 青島: 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4—47
董永發, 1989. 長江河口及其水下三角洲的沉積特征和沉積環境.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 78—85
覃雪波, 2010. 生物擾動對河口沉積物中多環芳烴環境行為的影響. 天津: 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16—26
曾文曄, 2013. 醫學圖像處理平臺3D Slicer結構剖析及國際化方法研究. 杭州: 浙江工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3—5
解 睿, 2019. 數字圖像處理技術的發展現狀問題研究. 數字通信世界, (6): 130
Dashtgard S E, Gingras M K, Pemberton S G, 2008. Grain-size controls on the occurrence of bioturbation.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57(1/2): 224—243
Hamblin W K, 1962. X-ray radiography in the study of structures in homogeneous sediments.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 32(2): 201—210
Kristensen E, Penha-Lopes G, Delefosse M, 2012. What is bioturbation? the need for a precise definition for fauna in aquatic sciences.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446: 285—302
Liu J P, Li A C, Xu K H, 2006. Sedimentary features of the Yangtze River-derived along-shelf clinoform deposit in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26(17/18): 2141—2156
Lyttle A M, 2013. Carbon-mineral interactions and bioturbation: an earthworm invasion chronosequence in a sugar maple forest in Northern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issertations & Theses-Gradworks, 70—73
Mermillod-Blondin F, 2011.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bioturbation and biodeposition on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at the water–sediment interface in freshwat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Journal of the North American Benthological Society, 30(3): 770—778
Meysman F J R, Middelburg J J, Heip C H R, 2006. Bioturbation: a fresh look at Darwin’s last idea.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1(12): 688—695
Moore D G, Scruton P C, 1957. Minor Internal Structures of Some Recent Unconsolidated Sediments. Aapg Bulletin, 41: 2723—2751
Qiao S Q, Shi X F, Wang G Q, 2017. Sediment accumulation and budget in the Bohai Sea,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Marine Geology, 390: 270—281
Rhoads D C, Boyer L F, 1982. The Effects of Marine Benthos on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ediments-A Success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USA: Springer Press, 19—40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BIOTURBATION STRUCTURE OF MODERN SEDIMENTS IN CHANGJIANG RIVER ESTUARY USING COMPUTER TOMOGRAPHY
MI Zhi1, FAN De-Jiang1, 2, LIU Xiao-Hang1, ZHENG Shi-Wen2, 3, CHENG Peng1, ZHANG Xin1
(1. College of Marine Geo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Key Lab of Submarine Geosciences and Prospecting Techniques, MOE China,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3.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Bioturbation at sea bottom accelerates the exchange of materials between bottom water and sediment. However, in-situ study of the bioturbation structure is limited by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is mostly qualitative and semi-quantitative. Four sediment cores were s collected from modern sedimentary area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stuary, to which computer tomography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reveal the bioturbation structure in three-dimension and the digital images were taken and processed. The bioturbation intensity was characterized quantitatively,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bioturbation structure were preliminarily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computed tomography (CT) value was related to sediment grain size and moisture content, and it could indicate changes in sediment density. Second, excavation structure, foraging wormhole structure, escaping wormhole structure, biological heritage structure, and other obvious bioturbation structures were observed. The bioturbation intensity was between 0—10%. The maximum bioturbation intensity was found in the front of the Subaqueous Changjiang River Delta and the transition zone of continental shelf, and the bioturbation structures varied significantly and vertically at different stations. Third, the types of sediments, the properties of the overlying water masses, and the deposition rate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ioturbation structure.
bioturbation structure; computer tomography technology;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bioturbation intensity; the Subaqueous Changjiang River Delta
*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課題, 16YFA0600904號; NSFC-山東省聯合基金, U160640號。米 智, 碩士研究生, E-mail:oucmizhi@qq.com
范德江, 博士生導師, 教授, E-mail: djfan@ouc.edu.cn
2021-04-19,
2021-06-22
P736.21
10.11693/hyhz2021040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