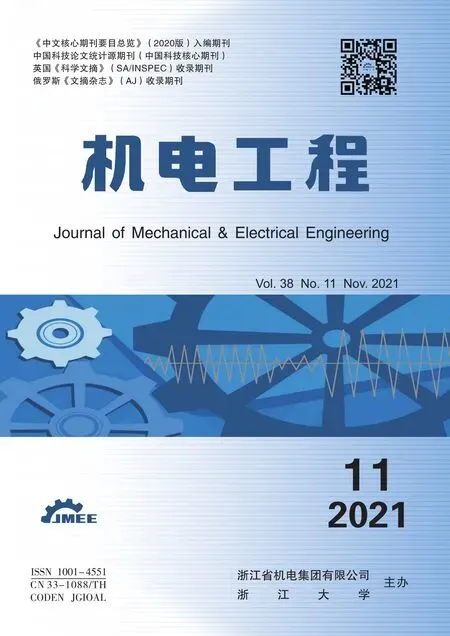裂紋故障下軸承浪型保持架的動態特性分析*
謝宏浩,牛藺楷,2*,肖 飛,祁宏偉,鄭一珍,熊曉燕,2
(1.太原理工大學 機械與運載工程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0;2.太原理工大學 新型傳感器與智能控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山西 太原 030000)
0 引 言
軸承保持架是指部分地包裹全部或部分滾動體,并隨之運動的軸承零件,其作用是隔離滾動體,引導滾動體并將其保持在軸承內。
作為滾動軸承的重要組成部分,軸承保持架的成本約占整個軸承的20%到30%,其穩定與否直接影響軸承的運轉狀態。保持架的輕微故障會引發其他部件也出現故障,且難以分析故障產生的原因,嚴重的保持架故障例如保持架卡死,會造成重大的事故。
裂紋是一種常見的保持架故障類型,且裂紋萌生初期往往難以發現,原因在于相比于球與故障套圈之間相互作用造成的沖擊,球與故障保持架之間相互作用造成的沖擊存在幅值較小,且周期性不強的特點,故無法直接在時域及頻域圖上得到清晰的保持架故障指標,更無法有效地判斷軸承保持架是否發生了故障。
作為深溝球軸承,浪型保持架是其常用的一種保持架。不同于其他類型的保持架,該類型保持架不由套圈引導而是直接由球引導,因此,其球與故障保持架之間的互相作用更加頻繁,更容易引發保持架出現疲勞裂紋的故障。
多年來,有眾多專家學者對軸承保持架故障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唐德堯[1]提出了一種聯合軸承保持架故障特征譜與外孤譜的保持架變形識別方法。李修文等人[2]提出了一種基于整周期時域回歸的方法,來提取出軸承滾子之間的間距變化信息,進而判斷軸承保持架是否出現了故障。但上述兩種方法對其有效使用的場合較為嚴苛。
鄭一珍等人[3]提出了一種基于EMD分解振動加速度信號的SDP特征融合的,卷積神經網絡軸承故障類型診斷法。韓清鵬等人[4]提出了一種基于ARMA模型使用時域指標參數,對滾動軸承故障進行診斷的方法。但這兩種方法對不同使用場合下的軸承自適應性不強。
針對不同類型的軸承保持架,研究其正常狀態與故障狀態下不同的動態特性,揭示其故障的動力學機理,對于軸承保持架的故障診斷具有重要意義[5]。因此,對于該類型故障,直接從故障保持架自身的動態特性入手,得到故障特征,對于更好地對保持架裂紋故障進行診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針對該類型軸承保持架,筆者采用將不同裂紋保持架離散為柔性體后,再進行動力學仿真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保持架的動態特性。
1 球軸承多體動力學模型
1.1 模型的建立
軸承內部保持架與球均具有6個自由度,且保持架引導方式為球引導,二者之間的互相作用頻繁,并且不具有很強的規律性,使得整個軸承系統內部的動力學求解過程復雜。因此,本文運用多體動力學軟件ADAMS建立球軸承的多體動力學模型[6],進而對保持架動態特性進行分析。
此處筆者分析所用的球軸承為深溝球軸承6205,其具體結構參數中,徑向游隙與保持架兜孔間隙取文獻[7]中振動加速度級最小時所對應的值。
對于軸承所設的約束為:
(1)外圈固定,0個自由度;
(2)內圈設置為平面副,保留繞軸線旋轉和徑向平面內的平動3個自由度;
(3)球與保持架均保持6個自由度[8-10];
(4)球與內圈、外圈、保持架之間設置為體對體接觸。
1.2 保持架裂紋建模及柔性化處理
保持架裂紋的具體建模工作由三維建模軟件來完成。此處設定裂紋寬度為1 mm,深度分別為0.35 mm、0.7 mm、1.05 mm、1.4 mm及1.75 mm(斷裂)。后續提到裂紋將只表示深度,不再體現寬度。
裂紋的設定位置為鉚釘與兜孔之間,筆者并在此處作如下假設:裂紋主要是由疲勞產生,因此不考慮因工藝裝配誤差、運轉過程中,異物入侵、鉚釘缺陷等等因素產生的其余形式的保持架裂紋。
此處將軸承保持架離散為柔性體,更能準確、真實地表達保持架的動態特性,也更接近于其真實的運行情況[11]。保持架柔性化采用模態綜合法,在ADAMS/FLEX中實現。離散保持架時選擇體單元,手動選擇單元大小為確保精度前提下的最優化仿真速度的值;模態選擇18階模態,其中,前6階模態為剛性模態,FLEX系統默認選擇其為無效模式。
對于柔體保持架而言,此處在ADAMS中選擇觀察其模態初始條件,可以得到其各階固有振動頻率。
各深度裂紋的保持架部分階數固有振動頻率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當保持架出現裂紋后,保持架的固有振動頻率下降,這意味著相比于正常保持架,出現裂紋的保持架產生共振現象的可能性增加。

表1 不同裂紋保持架固有振動頻率表
保持架出現裂紋后其整體剛度減小,會導致其固有振動頻率減小。其原因在于,保持架斷裂后其已經不再屬于圓環類零件,整體剛度下降明顯,故固有振動頻率遠遠小于未完全斷裂時;同時,與未斷裂保持架相比,斷裂的保持架也更易產生共振。
1.3 接觸參數的計算
在接觸分析中,軟件自帶懲罰函數法與Impact法。本文選擇Impact法的原因在于:(1)懲罰函數法適用于動力學中的間歇性接觸,用于持續性接觸則有可能造成顫振或者輕微的約束失效;(2)Impact法具有更強的魯棒性以及對求解器公差范圍的低敏感性,且它也是唯一可以用于柔性體接觸的方法[12]。
本文通過計算接觸剛度和油膜剛度的方法,來求解考慮彈流潤滑的保持架綜合剛度[13]。
1.3.1 球與滾道、保持架接觸剛度計算
套圈滾道的曲率半徑系數為:
(1)
式中:r—滾道曲率半徑;Dw—球的直徑。
套圈主曲率的計算公式表如表2所示。

表2 套圈主曲率計算公式表
ρ1I,ρ1II—滾球表面接觸點在軸向、徑向平面內的主曲率;ρ2I,ρ2II—滾道表面接觸點在軸向、徑向平面內的主曲率
筆者在求得內外套圈滾道的曲率半徑系數后,將其代入表2中,來分別計算內外套圈的主曲率。
設定1為滾球,2為滾道,I為軸向平面,II為徑向平面。
平面主曲率之和的計算式為:
∑ρ=ρ1I+ρ1II+ρ2I+ρ2II
(2)
由以上參數可計算滾球與內外滾道之間的接觸剛度系數,即:
Kj=2.15×105(∑ρ)-0.5(nδ)-1.5
(3)
而對于球和保持架兜孔之間接觸剛度,其表達式為:
(4)
其中:
k=1.033 9(Rη/Rε)0.636 0
(5)
R=RεRη/(Rε+Rη)
(6)
Rε=0.5DwDp/(Dp-Dw)
(7)
Rη=0.5Dw
(8)
ε=1.000 3+0.596 8Rε/Rη
(9)
Γ=1.527 7+0.602 3ln(Rη/Rε)
(10)
式中:Dp—保持架兜孔直徑。
1.3.2 球和滾道、保持架兜孔油膜剛度
接下來,筆者對球和滾道、保持架兜孔油膜的剛度進行具體計算。
對于內圈而言,有:
(11)
對于外圈而言,有:
(12)
其中:
(13)
(14)
(15)
(16)
式中:a—所用潤滑油黏度的壓力系數;η0—常壓下的動力黏度;n—內圈或外圈的轉速,r·min-1;rj—無量綱參數;dm—節圓直徑;E0—等效彈性模量;u—泊松比;E—彈性模量;e—自然對數的底;Qmax—受載最大的滾動體負荷;Fr—徑向載荷;Z—滾動體個數。
對于保持架兜孔[14,15]而言,有:
hmin=|Cp-Zc|
(17)
(18)
Rx=0.5Dw
(19)
式中:Cp—保持架兜孔的間隙;wc—保持架公轉的角速度;wok—第k個鋼球的公轉速度。
油膜的剛度公式為:
(20)
(21)
(22)
Vm=0.5Dwwb
(23)
Rx=0.5Dw(1-r)
(24)
Rx=0.5Dw(1+r)
(25)
G=aE0
(26)
式中:U—無量綱速度參數;Vm—球與滾道之間的相對平均速度;Rx—當量曲率半徑;G—無量綱材料參數。
在求出油膜厚度后,筆者將其代入以上各式,即可計算出油膜的剛度。
在以上各式中:式(22)適用于球和套圈滾道,式(23)適用于球和兜孔,式(24)適用于內圈,式(25)適用于外圈。
1.3.3 等效綜合剛度計算
接下來進行等效綜合剛度的計算。
等效綜合剛度的計算式為:
(27)
式中:Kj—球與其點接觸物體的接觸剛度;Ky—球與其點接觸物體之間的油膜剛度。
通過上式計算得到的綜合剛度,即為考慮彈流潤滑后的球與各部件之間的綜合接觸剛度。
2 仿真及結果分析
因為浪型保持架由球引導,不穩定因素較強,所以球與保持架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視為隨機激勵。對于該種隨機過程,一種較為普遍的處理方法是研究其某些“統計規律性”,故其仿真總體時間的設定也是研究裂紋故障的重要因素。時間較短,則會導致所分析的樣本函數仍具有一定的隨機性;時間過長,則會導致某些時刻因故障產生的激勵被較大的數據量所掩蓋。
故在3種轉速下的時間選取上,筆者都以保持架旋轉80圈左右為標準,且其截取的數據均為保持架進入“穩態”以后的數據。在保持架的加速過程中,其動態性能則不在本文考慮范圍之內。
2.1 質心軌跡的分析
由于各裂紋情況除斷裂外并無較大差別,此處只展示正常(裂紋深度0 mm)、裂紋(裂紋深度0.7 mm)以及斷裂(裂紋深度1.75 mm)3種情況下裂紋保持架的質心軌跡。
在徑向載荷200 N與重力場作用下,各裂紋深度與轉速對保持架質心軌跡的影響,如圖1所示。

圖1 不同裂紋保持架質心軌跡演化圖
由圖1可以看到:
(1)在軸承徑向力的作用下,保持架質心先向Z軸負方向偏移(Z軸負方向為重力方向與徑向載荷施加方向),并在較高轉速下,由于離心力的作用開始向一側偏移;
(2)該型號球軸承由球引導,因為徑向游隙與保持架兜孔間隙的存在,故而其保持架質心軌跡為在一定的橢圓范圍內不規則的渦動;
(3)在同一轉速下,由于裂紋的存在使得保持架質心的渦動范圍不斷增加,且這一特征隨著轉速的升高變得越來越明顯;
(4)隨著轉速的升高,裂紋保持架質心渦動軌跡相較于正常保持架的變化趨勢保持一致,斷裂的保持架則明顯不同于前正常和裂紋保持架。
2.2 保持架轉速的分析
對于各深度裂紋在各內圈轉速下的保持架轉速,通過觀察其概率密度函數(PDF)圖,可以更清晰地觀察到各種參數值的變化[16,17]。
不同裂紋深度下,保持架轉頻的概率密度函數如圖2所示。

圖2 不同裂紋保持架轉速PDFs
為便于觀察,保持架轉頻的跨度此處均設為5 Hz。對于正常保持架3個內圈轉速,與無故障保持架經驗公式求得的保持架理想轉速的誤差分別為2%、1.1%、1.3%。該結果說明了所搭建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由圖2可看出:
(1)在40 Hz和100 Hz的內圈轉頻下,保持架的各項參數指標及轉速分布情況均與正常狀況有所差異,但并不能清晰地表達保持架的故障,這一點的敏感性差于質心渦動軌跡;
(2)在200 Hz的內圈轉頻下,斷裂情況下的保持架轉速分布情況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此時若是把平均轉速這一參數作為識別軸承故障的依據,相對于裂紋保持架,斷裂保持架的轉速降低1.4%左右,敏感性較差,但在概率密度函數圖上仍可以清晰地捕捉到這一改變(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為:保持架斷裂后,對球的周向保持作用下降,同時因保持架斷裂自身產生不平衡力,使得球在滾道內產生竄動。球的不穩定也使得球對保持架的引導處于失衡狀態,導致保持架公轉速度降低)。
2.3 球與保持架的碰撞分析
保持架與球頻繁的碰撞是造成疲勞裂紋的主要因素,故而了解保持架與球碰撞的規律至關重要。
在正常、裂紋和斷裂情況下,在保持架公轉1周的過程中,相同的2顆球(故障保持架選取裂紋兩側的球)與保持架兜孔的接觸力,如圖3所示。

圖3 保持架兜孔與兩球接觸力圖
從圖3可以看出:在旋轉1周的過程中,斷裂保持架與球的總碰撞次數,明顯多于正常裂紋保持架和球的總碰撞次數,且在線條加粗的時間段內(對應圖4中0°~90°),其碰撞次數明顯比其他時間段更多;裂紋保持架與兩球的碰撞次數在圖示的所有時段均明顯要高于正常的保持架。
與受力圖中的線條加粗區域相對應,保持架與兩球頻繁碰撞的區域,如圖4所示。

圖4 保持架與球頻繁撞擊區示意圖
結合圖(3,4)可以看出:保持架與球頻繁接觸的區域不在承載區,而在沿旋轉方向從0°~90°的過程區域。其原因是:在承載區,套圈與球的作用力為主導;在脫離承載區以后,球沿90°~180°運轉過程中開始與重力方向(本文模型Z軸負方向)相反,導致球的速度變慢,從與保持架發生頻繁碰撞。
保持架與球發生碰撞會導致其速度改變,這一現象反映在圖上即為曲線斜率的改變。
在頻繁碰撞區,保持架的速度變化曲線如圖5所示。

圖5 保持架公轉速度圖
由圖5可知:在相同時間的步長內,斜率改變的次數隨著裂紋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分別為27次、34次、35次。這一改變說明,保持架在出現裂紋故障后,相同時間步長內的碰撞次數明顯增加;
同時,結合圖3也可知:兩球與斷裂保持架兜孔頻繁碰撞的時間比裂紋保持架的更長。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即在保持架疲勞裂紋萌生以后,會因為以上的原因而使裂紋快速擴展。同時,這也是在工程實際應用中,多數保持架故障被發現時已經是到了斷裂狀態(晚期)的原因。
3 結束語
筆者通過多體動力學仿真軟件ADAMS對不同裂紋深度下的柔體保持架進行了動力學仿真,得到了不同裂紋深度下保持架的質心渦動軌跡、轉動速度的概率密度函數、球與保持架的頻繁撞擊區域,以及球和不同裂紋深度的保持架的碰撞規律,得到了裂紋擴展過程中,保持架動態特性的改變以及不同維度的表現形式。
研究結果表明:
(1)浪型保持架質心渦動軌跡范圍隨著裂紋程度的加深而增大;
(2)在內圈高轉速且保持架斷裂時,從浪型保持架轉速的概率密度函數圖可清楚地觀測到其差異,在其余情況下則敏感性不強;
(3)浪型保持架與球碰撞最頻繁的區域不在承載區,而在沿旋轉方向的逆重力方向,且當出現裂紋時其碰撞次數要顯著多于正常情況時,這些因素也是造成保持架裂紋擴展的主要原因。
在后續的研究中,筆者將針對球軸承浪型保持架,應用電渦流傳感器以實現對球軸承保持架質心渦動軌跡及轉速等變量的測量,達到在線監測保持架裂紋故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