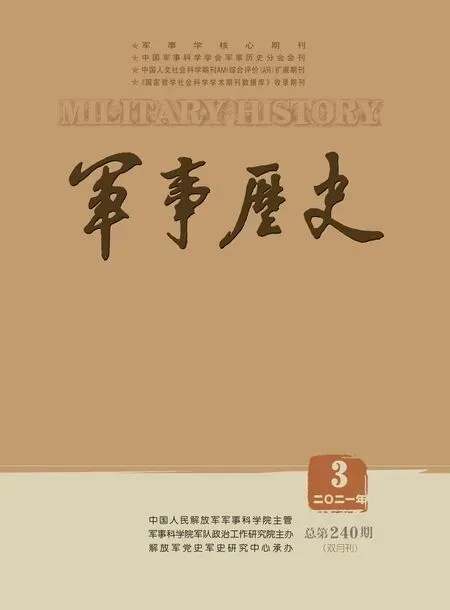試論陳毅在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中的歷史貢獻
★ 李 濤 孫 健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陳毅因傷留下,擔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與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項英等領導一部紅軍和地方武裝堅持斗爭。在遭受重大損失后,根據中央指示,于1935年3月分散突圍至贛粵邊地區的油山,同中共贛粵邊特委書記李樂天領導的部隊會合,開始了極端艱難的三年游擊戰爭歲月。這是陳毅一生中所經歷的最艱苦的斗爭。面對瞬息萬變的形勢、錯綜復雜的局面,他不僅完成了中央賦予的任務,而且為黨和人民保存了一支革命隊伍,在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加強黨組織建設,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
黨的堅強領導,是贛粵邊紅軍游擊隊能夠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確保正確的斗爭方向,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主力紅軍長征后,1934年12月,根據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共贛南省委在雩都(今于都)小溪成立信(豐)、(南)康、贛(縣)、(南)雄特別委員會(后改稱贛粵邊特委),李樂天任書記、楊尚奎任副書記,以加強和統一贛粵邊的領導,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3月,項英、陳毅及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贛南少共省委書記陳丕顯等,先后率部突圍轉移到油山,繼續領導贛粵邊紅軍游擊隊堅持斗爭。當時,贛粵邊黨內存在著有礙于長期堅持斗爭的嚴重現象,如“黨的發展完全選擇群眾中最老實(所謂要忠實)膽小不敢作壞事的吸引入黨”“把黨陷于麻木不仁的無能的地位”“黨的支部,無自己的工作,一切工作由區委同志包辦”“把游擊戰爭變為單純的打土豪籌款”“提拔干部完全離開政治立場”①《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86~87 頁。等等。項英、陳毅等認為“黨的領導決定斗爭的前途”②《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26 頁。,提出:堅決反對土匪主義和游擊主義;大力發展黨組織,吸收群眾斗爭中最積極分子大批入黨,反對專找老實人;健全支部生活和建立支部獨立工作,反對區委代替支部;轉變黨的領導方式,注意實際解決問題,反對空泛的論調,幫助下級干部,建立經常的巡視制度等。“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和斗爭,以至二年以來我們還毫無動搖的堅持這一路線。在基本上說,我們已把這些現象打擊下去,建立黨的正確路線。”①《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89 頁。4月上旬,陳毅參加了中央分局和贛粵邊特委在大庾(今大余)縣長嶺村召開的干部會議。會上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于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的指示精神,分析了斗爭形勢,批評了悲觀失望和盲動主義的錯誤傾向,統一了干部的思想認識,制定了“依靠群眾,堅持斗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②《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6 頁。的方針,研究部署了恢復和建立贛粵邊黨組織的問題,決定加強信康贛、南雄兩個縣委和信南工作團的領導,并由中央分局和特委領導人分頭去各地檢查指導工作。陳毅先后到油山游擊隊獨立大隊、中共南雄縣委,及時糾正了他們工作中存在的極左思想、吃喝成風、亂抓亂殺等問題,使長嶺會議精神得以貫徹執行,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為長期堅持游擊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割裂贛粵邊紅軍游擊隊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國民黨軍采取移民并村和驅趕群眾出山等“封坑”手段,進行更為殘酷的“清剿”。贛粵邊遭到空前浩劫,許多地方成了“鳥無棲息之所、人無藏身之處”的無人區,紅軍游擊隊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危急關頭,項英、陳毅在信豐潭塘坑組織召開特委、信康贛縣委和南雄縣委聯席會議,研究確定了“有計劃地分配黨團員隨群眾出山到大村居住,在那里重新組織黨支部或小組,繼續領導群眾斗爭”③《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9~10 頁。等7 條對抗“封坑”的辦法。會議還決定中央分局和特委領導分散到各縣直接領導、指揮斗爭,縣委則分散到區委,深入到山邊或山外開辟新區。根據這一方針,1936年1月,楊尚奎首先到大庾梅山地區開展工作,發展黨的組織,相繼成立了黃坑、洋坑、坳頭三個黨支部和以黃贊龍為書記的梅山區委,使離縣城僅十幾里的地方發展成為贛粵邊游擊隊活動的堅強堡壘。2月,陳丕顯也率工作團在大庾池江的彭坑、黃種、小汾、路箕坑一帶開展工作,先后組織了三個貧農團和游擊小組,并吸收了一批黨團員,建立了小汾、弓里、板棚三個黨支部,把游擊區從山里伸向山外④大余縣軍事志編纂委員會:《大余縣軍事志》,大余縣人民武裝部,2011年,第11 頁。,從而確保贛粵邊地區的反“清剿”斗爭始終處于黨的堅強領導下。自1935年3月初,中央分局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絡、陷于孤立斗爭的困境后,在項英、陳毅的正確領導下,贛粵邊各級黨組織仍能堅持“時時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以加強對于整個斗爭形勢的估計和分析的正確性,來保證黨的方針正確”,“在干部中進行政治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⑤《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26 頁。,充分發揮了黨的核心領導作用。陳毅親自組織干部學習他從中央蘇區帶出來的《列寧主義問題》,有時結合《左傳》《三國演義》等中國歷史讀物,用生動活潑的思想工作提高指戰員的政治水平。也正是緣于黨的堅強領導和及時有力的政治工作,贛粵邊紅軍游擊隊才能在極端困境中愈戰愈強、愈挫愈勇,不僅造就和培養了一批忠于革命、英勇善戰、富有經驗的軍政干部,而且保留下一支700 余人的革命隊伍,為后來新四軍馳騁大江南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從敵我斗爭實際出發,不斷調整斗爭策略
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是在革命受到嚴重挫折、敵我力量異常懸殊的情況下進行的,只有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才有可能取得勝利。當時留在中央蘇區的部隊為紅24 師以及地方武裝共1.6 萬余人,另有傷病員3 萬多人。由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中央最初劃定瑞金、會昌、雩都、寧都四縣之間的“三角地區”為基本游擊區和最后堅守的陣地,命令留下的部隊采取陣地防御作戰來保衛根據地。對此,陳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蔣介石不會因紅軍主力撤出而丟下中央蘇區不管,也不會讓蘇維埃政權繼續存在,“反革命大風暴很快要襲來,必須迅速作好打游擊的準備”。面對強敵環伺的不利形勢,陳毅提出在完成掩護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的任務后,“紅軍二十四師和獨立團,應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各個游擊區去,作為游擊戰爭的骨干,這樣可以保存一批相當可觀的革命力量”。①《陳毅傳》編寫組:《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133 頁。遺憾的是,項英并沒有接受這一正確主張,而是機械地執行了中央的既定方針,指揮留下的部隊仍然采用大兵團作戰方式與敵人硬拼,結果遭受很大損失,至1935年1月下旬被壓縮在貢水東北狹小地區,危在旦夕。2月5日,遵義會議后的中共中央致電中央分局明確指出,“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13日又發來關于堅持游擊戰爭的具體指示。中央分局遂決定分九路突圍,開始實行由蘇區方式向游擊區方式、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的戰略轉變。陳毅深刻領會了中共中央關于軍事斗爭戰略的調整,在敵強我弱、斗爭困難的情況下要徹底粉碎“圍剿”,必須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后去進攻敵人。“因為這樣的行動,將在離開堡壘的地區中得到許多消滅敵人的戰斗機會,解除敵人的武裝壯大紅軍,在廣大的新的區域中,散布蘇維埃影響,創立新的蘇區,將發動并依靠新的區域中更廣大的群眾斗爭的力量,更有力的進攻國民黨的統治。”②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 冊(1934-193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389 頁。為此,他在長嶺會議上提出必須接受中央蘇區丟掉的教訓,迅速轉變戰略思想和斗爭方式,應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反對與優勢敵人作戰,改變過去集中和正規化的作戰方式,采取小規模的、分散的、群眾性的活動方式,以打圈子和挺襲的游擊戰術,反擊敵人的“清剿”。③《陳毅傳》編寫組:《陳毅傳》,第147 頁。并結合贛粵邊實際提出了以后的任務:以油山、北山為主要根據地,依靠群眾堅持游擊戰爭,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反對死打硬拼和消極隱蔽的傾向,采取靈活機動的方式開展反“清剿”斗爭,使整個工作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這一斗爭策略的改變,分散和縮小了目標,加強了群眾工作,使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得以生存和發展。在反“清剿”斗爭中,陳毅和項英等摸索出了一整套游擊戰的基本原則,即: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擴大政治影響的仗,打能發動群眾的仗,打能得到物資補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賺錢就來,賠本不干”,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戰果。④《陳毅傳》,第155 頁。為了讓廣大指戰員熟悉游擊戰法,陳毅和項英還把這些游擊戰術編成歌訣:“團結群眾,配合行動;支配敵人,自己主動;硬打強攻,戰術最忌;優勢敵人,決戰要避……”,讓大家傳唱熟記,用于實踐。⑤《陳毅傳》,第156 頁。在這些基本原則指導下,贛粵邊紅軍游擊隊堅持公開斗爭與半公開斗爭相結合,武裝斗爭與地下黨的內線工作相結合,武裝斗爭與群眾斗爭相結合,時而集中,時而分散,時而活動,時而隱蔽,聲東擊西,神出鬼沒,使敵人捉摸不定,而游擊隊處于主動地位,利用地形地物打伏擊戰,打破了敵人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嚴密封鎖,挫敗了敵人的連續“清剿”,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為開辟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此外,陳毅還遠見卓識地認識到統戰工作的重要性。1936年9月,為粉碎國民黨軍第46 師的“清剿”,陳毅和項英召開干部會,作出的“九月決議”規定:游擊區放手搞“兩面政權”,赤、白交界區搞“黃色村莊”。除派出以游擊隊和地下黨員為骨干的宣傳工作隊秘密進入白區活動外,同時要求各地利用撤換保、甲長的機會,派一些沒有暴露身份的地下黨員、革命群眾和開明人士當保、甲長;采取打擊與爭取相結合的方針和區別對待、分化瓦解的策略,盡量爭取保、甲長,利用其合法身份掩護紅軍游擊隊,把保甲機構逐步變成白皮紅心的“兩面政權”,表面上為國民黨效勞,實際上按共產黨的意圖辦事。這是贛粵邊的一大創舉,“這樣既可以長期堅持,避免敵人進攻,又可以使老百姓不受損失”⑥《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65 頁。,對游擊根據地的建立、紅軍游擊隊的給養保證,粉碎敵人的軍事“清剿”和經濟絞殺,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對黨在抗日戰爭中開展敵占區工作提供了重要經驗和借鑒。在獲悉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的情況后,陳毅認為中國革命已發展到國共兩黨重新合作抗日的新階段,并提醒大家必須做好思想準備,迎接新的斗爭,從而統一了干部戰士的思想認識。盧溝橋事變后,陳毅堅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同項英決定以贛粵邊特委和紅軍游擊隊的名義,先后發表《贛粵邊共產黨游擊隊聯合宣言》《中共贛粵邊特委告贛南民眾書》,向人民群眾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并提出與國民黨地方當局和駐軍早日實現談判,達成合作抗日協議。1937年9月,陳毅親自前往贛州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最終達成停戰協議,勝利完成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戰略轉變。正是由于項英、陳毅等從斗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制定和總結了一整套群眾性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適時轉變斗爭策略,執行正確的統戰政策,贛粵邊紅軍游擊隊在極其復雜和艱難的條件下才得以生存和發展。
三、開展經常性思想政治教育,鑄牢革命必勝的理想信念
對黨對革命無限忠誠、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是贛粵邊紅軍游擊隊取得三年游擊戰爭勝利的重要精神保證。從1934年底起,國民黨集中粵軍第1 軍3 個師及贛南警備團、保安團共4 萬余人,對贛粵邊地區反復進行“清剿”。在控制要道“駐剿”的同時,采取“聽響聲,看煙火,跟腳印”等辦法進山“抄剿”、燒山封山,并派出便衣偵探偽裝成紅軍,伏擊游擊隊或騷擾群眾;實行經濟封鎖,限制群眾購買糧、鹽、油等,嚴控膠鞋、電池等物資運入山區,妄圖將紅軍游擊隊困死在深山密林里;強化保甲制度,實行聯保連坐法,即發現“一戶通匪,十戶株連;一保通匪,五保連坐”;進行政治欺騙,造謠惑眾,反動宣傳,制定《共產黨人自首法》,張貼招撫標語,企圖瓦解紅軍游擊隊的軍心。在“惡風暴雨住無家,日日野營轉戰車”的斗爭歲月里,要經受住血與火的洗禮,經得起生與死的考驗,就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堅定理想信念。陳毅始終把革命前途的教育放在首位,提出“保持干部,保持游擊隊,保持政治旗幟”①《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49 頁。,對英勇犧牲的烈士給予高度贊揚,號召大家學習和發揚這種崇高的革命精神;對思想動搖者,認為在當前的困難面前,可能出現一些講怪話、開小差的現象,這是不足為奇的,不要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應該正確對待。革命是自愿的,不能逼著人家革命,更不能綁著人家革命。②《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3 頁。他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沒有采取簡單粗暴的批判方式,而是對這些出現思想波動的同志進行耐心說服教育,增強他們的革命信念。1935年11月,國民黨軍實行移民并村的“封坑”政策后,“幾十里路、幾百里路大山區,一個人也沒有”③《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52 頁。,贛粵邊的游擊戰爭進入最為艱苦階段。紅軍游擊隊糧食斷絕,晝伏夜出,幾乎過著野人般的生活。“天將曉,隊員醒來早。露侵衣被夏猶寒,樹間唧唧鳴知了。滿身沾野草。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④胡興武:《陳毅詩詞鑒賞》,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1 頁。陳毅在油山寫下的《贛南游擊詞》,真實再現了當時的艱難困苦。少數革命意志薄弱者,如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贛粵邊特委后方主任何長林等先后叛變,給贛粵邊區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至1936年5月,贛粵邊紅軍游擊隊由1400 余人銳減至不足300 人,李樂天、蔡會文等領導人英勇犧牲。就連陳毅也于當年冬天被國民黨軍圍困在梅嶺長達20 天之久,藏身叢莽間苦慮不得脫險,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絕筆”——《梅嶺三章》。面對如此殘酷的斗爭環境,陳毅與項英認真分析部隊的思想狀況,在政治上堅決反對那種認為“革命前途渺茫”“等待主力回師”的悲觀主義傾向,采取在紅軍游擊隊內部開展形勢教育、階級教育和紅軍優良傳統教育,編寫《關于開展反叛徒斗爭討論大綱》等一系列積極措施,教育廣大指戰員“革命就要斗爭的決心,流血犧牲的精神”“流血犧牲是革命的光榮事業”“流血犧牲的精神是推動和爭取革命勝利的偉大力量”“背叛革命是可恥的行為”⑤《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29~31 頁。,提高了思想覺悟,堅定了革命信念。同時堅持官兵平等,實行經濟民主,以達到鞏固內部,防止叛變事件的發生。
在斗爭極為尖銳、復雜、艱苦、殘酷的時期,革命隊伍內部的問題層出不窮,但陳毅以深入人心的思想工作引導團結廣大指戰員,共同堅持黨的正確路線,為游擊戰爭的開展確立了正確方向。從中央蘇區突圍到贛粵邊地區后不久,他發現中央蘇區來的干部和當地干部在團結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互相瞧不起。中央蘇區干部認為當地干部沒有政策水平,當地干部則說中央蘇區干部不會打游擊,關系一度不是很融洽。陳毅首先向中央蘇區來的干部提出要求:虛心學習當地干部打游擊的經驗,學習當地語言、風俗人情。同時也要求當地干部向中央蘇區來的干部學習,互相取長補短。①《陳毅傳》編寫組:《陳毅傳》,第150 頁。正是堅持進行具體實際的思想教育和反叛徒斗爭的教育,認真執行區別對待的政策,使贛粵邊紅軍游擊隊指戰員的思想更加一致,組織更加純潔,革命勝利的信念更加堅定,經受住了考驗,英勇頑強地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有力支援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行動。
四、重視做好群眾工作,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開展對敵斗爭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②《毛澤東選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11 頁。革命戰爭是人民群眾的戰爭,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戰勝敵人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和力量,必須廣泛動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1935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中央分局,強調當前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用游擊戰爭堅忍地、頑強地反對敵人的堡壘主義與‘清剿’政策”,指出“游擊隊應緊密的聯系群眾,為群眾切身利益斗爭”③《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26~27 頁。。陳毅與項英、李樂天、楊尚奎等中央分局和贛粵邊特委領導人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把群眾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改變初期僅限于打土豪籌款的做法,積極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長嶺會議上制定的方針第一條就是“依靠群眾”。隨后在潭塘坑會議上提出的7 條對抗“封坑”辦法中,有5條與群眾工作相關。如“動員群眾離山之前把糧食埋藏趕來,留給游擊隊使用”“組織群眾性的游擊小組積極配合游擊隊的行動”“動員群眾以‘無房住,無柴燒’為理由,開展‘鬧回坑’的活動”“做好少數落后群眾的工作”④《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9 頁。等。“九月決議”明確指出:“群眾工作是我們反對敵人新的進攻的基礎。”⑤《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97 頁。陳毅帶頭執行和維護群眾紀律,以自己的模范行動影響大家。一次,交通員給游擊隊送來上百套單衣。陳毅問給錢了沒有。交通員不以為然地說資本家也不缺這點錢。陳毅嚴肅批評:“這可不光是錢的問題,是黨的工商業政策,我們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譽,是我們的命根子。”他親自派人將應付的200 塊銀洋給縫紉店老板送去。在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中,紅軍游擊隊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處處維護群眾利益;動員和組織群眾支援革命,開展反叛徒和反“清剿”斗爭;對遭受敵人打擊、摧殘的群眾,想方設法進行援救,發動群眾實行互救。各游擊隊分成多至十余人、少則三五人的武裝工作組,穿著農民裝束,以職業為掩護,深入群眾,宣傳“革命只是暫時失敗,暫時困難,將來一定能勝利”的道理;不會手藝的游擊隊員就跟群眾一塊下地蒔田割禾,和群眾交朋友、結同庚,組織群眾參加和支援游擊戰爭。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民黨實行“北和南剿”的方針,加緊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清剿”。1937年3月,贛粵邊特委根據項英、陳毅的意見,組織發動群眾開展鬧春荒斗爭,積極配合紅軍游擊隊打土豪、籌款項、開谷倉、分糧食,粉碎了敵人的“清剿”。
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是在極端殘酷惡劣的環境下進行的,紅軍游擊隊得以生存、堅持和發展,須臾也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陳毅常常教育大家:我們的全部地盤,就是這么幾個“島子”,但是我們有著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沒有人民的積極支持,沒有與人民群眾生死與共的團結,要想堅持下來是不可能的。①《陳毅傳》編寫組:《陳毅傳》,第156 頁。在反“清剿”斗爭中,贛粵邊人民群眾冒著生命危險給紅軍游擊隊運物資、送情報、當向導、作掩護;在國民黨軍實行移民并村、驅趕群眾出山之際,群眾就把自己的口糧、食鹽等物資埋起來,做上記號,留給游擊隊;當游擊隊被敵人圍困在山上處于斷糧的危急時刻,群眾就把糧食藏在竹杠里,趁上山砍柴之機留給游擊隊。在大庾、信豐、南雄等縣的游擊區,只要紅軍游擊隊一進坑活動,當地青壯年便自覺組織趕來,站崗放哨。如發現國民黨軍進山,即高喊“東邊牛吃禾了”“西邊豬吃菜了”,暗示紅軍游擊隊上山隱蔽或離開。“中央紅軍長征過金沙江到四川的情況,以及長征到西北的情況,都通過老百姓的幫助,不通過老百姓無法取得這些情報。”②《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64 頁。1936年6月,陳毅腿部傷口復發,住在彭坑周籃嫂家里養傷。她不但悉心照料,而且在危急關頭,英勇機智地掩護陳毅躲過了國民黨軍的搜剿。贛粵邊人民群眾舍生忘死,與共產黨和紅軍游擊隊共患難,“敵人打來時,不泄露秘密,不走漏消息,幫助游擊隊防御,幫助收容傷兵”③《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55 頁。。為了支援和掩護紅軍游擊隊,“老百姓被打掉牙、打斷手、打斷腿,房子燒了,東西搶得光光的”④《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贛粵邊游擊區》,第154 頁。,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對此,陳毅曾深情地感嘆:“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斗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⑤胡興武:《陳毅詩詞鑒賞》,第22 頁。
綜上,在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中,陳毅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從敵我斗爭實際出發,根據新情況創造性地采取新的斗爭策略,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開展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挫敗了敵人的多次大規模“清剿”,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有力支援了主力紅軍的長征,積極配合了南方其他游擊區的斗爭,為迎接抗日斗爭新高潮的到來創造了條件、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