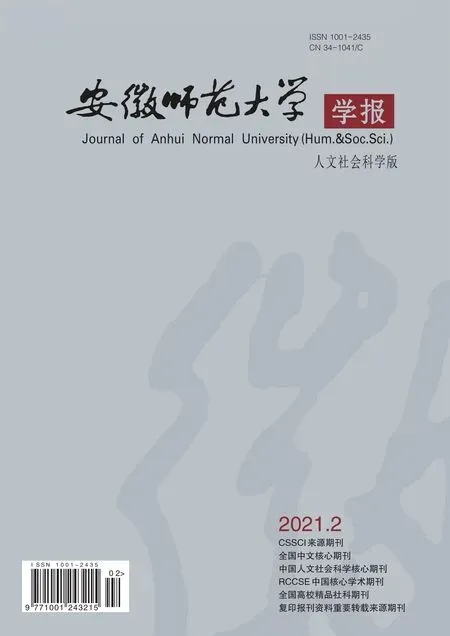自然美的轉向:從“祛魅”到“復魅”*
——以大自然文學創作為例
張 嫻
(1.安徽大學文學院,合肥230001;2.安徽工商職業學院,合肥231131)
自然美問題一直都是美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并始終圍繞“人與自然關系”這一核心要素展開。隨著人類歷史發展語境的變化,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以及人類對自然的審美態度也發生著不斷的轉變,從起初把自然作為客體性對象進行神化膜拜,到后來“人類中心主義”提出對自然的“祛魅”①“祛魅(Disenchantment)”一詞最早出現在馬克斯·韋伯提出的觀點“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里,其本意是指西方國家在從宗教社會向世俗化社會轉型過程中對世界宗教性統治的解體,后多為美學界引用。、將人的主體性及創造性凌駕于自然之上,再到“生態中心”論“自然全美”等觀點的提出,美學界以呼吁對“世界的復魅”[1]3實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審美模式的徹底反撥,有關自然美的生成范式及審美轉向在美學及文學創作領域也有了劃時代的體現。在20世紀全球性生態危機背景下崛起的、具有中國本土生態文學特色的大自然文學,就是以自然美及人與自然關系為主要書寫內容,并以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詩意家園為最高審美理想,具有鮮明的現代生態倫理意識的一種文學現象。從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生態存在論等角度探討在當今綠色發展語境下自然美的轉向及其新的審美核心,通過闡述工業時代以來“祛魅”所導致的人類生存困境及在現代文學創作領域中體現出的反思,提出以“人在自然中存在”來體認生命之“魅”的觀點,為自然的“復魅”之路構建新的哲學美學維度,最終指向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類“詩意地棲居”①出自海德格爾在其論著《荷爾德林詩的闡釋》中所引荷爾德林的詩歌名句“Full of merit,yet poetically,man dwells on this earth”(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在地球大地上),后被譯介為“詩意地棲居”。。
一、“祛魅”導致的困境
工業時代以來,現代科學以種種量化的指標對不同性質的事物進行抽象化比較與剝離,使得人與物、人類與世界之間最本真的價值聯系喪失。馬克斯·韋伯的“世界的祛魅”[2]168之說,認為由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人們不再相信世界上存在著“任何神秘、不可測知的力量”[2]168,一切事物都是可以通過技術性的方法計算并掌控的,世界在人們眼中不再具有神秘魅力。人類過分迷信并自信于科技知識對自然的駕馭、對世界的改造,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與神圣性被徹底祛除,更多的是作為人類科技進步作用下物質資源的占有與利用而存在。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認識論美學應運而生,它以主客二分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作為審美的哲學基礎及邏輯起點,把人與自然進行形而上的分離,將人的認知凌駕于自然之上,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忽略并抹煞自然的本體意義。認識論美學把審美過程直接等同于人的某種政治的、經濟的、功利的認知手段,自然美則等同于主體對客體征服過程中的價值確認,是價值選擇后的結果。人對自然的態度從精神化膜拜轉變為“理性化”主宰,并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作為自身價值的體現,而僅僅被視作審美客體的自然世界,只有在符合了人類的美感形式體驗時,才具有美的意義與價值。
這種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思想核心的世界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可知意識”過分膨脹,無限放大了人的主觀力量,并以此曲解了人對自然世界的貪欲就等同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祛魅”雖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人在對世界認知過程中所持有的一種具有主觀盲目性的“超驗崇拜”,但同時也將人與自然世界完全剝離,摒棄了自然的本原力量及與人類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在這種世界觀的主導下,“祛魅”所導致的人類生存困境日益凸顯,這一困境在社會發展中所帶來的必然后果就是生態危機爆發,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物種滅絕等問題頻頻發生,人與自然對立的狀態日益嚴重。同時,就人類自身發展而言,如果僅僅憑借工具理性在各種科技、知識領域以符號式、量化式的形態來實現自我的價值認同,否定自然的力量及自然的規律,那么人的本真價值也必將因過分迷信知識科技的“無所不能”而淪為工具的“奴隸”,人類也就失去了自身本源力量不斷上升的空間,走向一種價值歸屬與自身發展相悖的境地。
二、文學創作中的反思
在文學創作領域,西方作家最早開始以環境污染問題及生態危機作為文學創作新的題材,審視人類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生存困境、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以文化啟蒙主義姿態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對“世界的祛魅”的功利化態度,在反思人與自然的沖突及自然書寫的核心價值中形成獨特的美學追求,提出了“重返自然”理念及生態主義思想,并由此引發了環境文學、自然文學、荒野文學、生態文學等一系列有關生態書寫的文學創作風潮。通過對自然神圣的復歸及對自然書寫的獨特美學追求,來喚醒當代人類日漸消退的自然意識和融入自然的文化傳統。
在中國,以劉先平、葦岸、胡冬林、劉亮程、宋曉杰等為代表的大自然文學作家,將文學創作的人本主義立場轉向生態整體主義,以探索的姿態將人置身于自然整體之中。他們對自然的書寫強調人的在場感、親歷性、紀實性,自覺地把過去傳統文學作品里僅僅對人的生存境遇的關注,延伸到對自然及自然界其它生命物種生存境遇的關注,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蔑視與戕害,拷問如果失去對大自然、對地球生命物種應有的尊重與保護,人類將何去何從,并以此吹響呼吁人類回歸自然、敬畏自然的號角。“它們在人類獵殺、壓迫下的苦苦掙扎……它們生存的空間,正被人類蠶食、掠奪……自然養育了人類,可我們缺失了感恩,缺失了對其它生命的尊重”。[3]在劉先平《黑麋的愛情故事》中,黑麋所賴以生存的密林被人類濫伐、生存家園遭到破壞,致使黑麋無奈之中闖入居民區以尋求人類的保護,其通過對自然界生命物種生存境況的思考,反思人類自身生存境況的窘迫;在《魔鹿》中,一連串的感嘆:“是的,魔一般的鹿樹,魔一般的美!美是有距離的!我愿意保持這種距離,為了欣賞美。”[4]11則是完全站在審美論的角度,由人的本位延伸到自然的本位,自然不再是被剝奪了主體性價值的美感客體,而是一種主體性的獨立的美的價值與存在。
三、審美的轉向
當代生態美學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應是“我與你”式的對等的主體間性關系,把人與自然作為兩個主體進行平等對話,并把這種“審美主體之間的對話放到生存本體論的意義上來考察”。[5]50這種基于主體間性哲學審美世界觀的轉變,“把人的感性和理性統一于人的生存”[5]50,重新肯定了自然的本體意義,打破了“人類中心論”的價值體系,以對自然“復魅”的審美轉向來實現對過去“祛魅”時代所導致的人類困境的突破與超越。
如果說“復魅”的過程可以看作是對過去傳統的以認識論為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一種消解,那么消解之后勢必也需要再次對自然美問題進行新的學理重構與認識升華。我們應該認識到,從“祛魅”到“復魅”審美轉向的發生,既不是單純地對過去人類企圖主宰自然的全面否定,也不是提倡重新恢復對自然的盲目崇拜,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復魅”不是形而上的愚昧神化,也不僅僅是精神敬畏,更多的應是一種對自然的價值認同,并以此為前提重新確認人在生存發展進程中的自我價值與身份認同。
那么,在當代有關自然書寫的文學作品里,自然之于人類的本質意義何在?書寫自然的“魅麗”,是否就等同于恢復地球原始生命狀態、等同于人的“在場性”的缺失?首先,當代自然文學作品里有關自然的審美書寫,自然不再只是作為一種具有參照性的“景物”,而是直接作為藝術主體及審美本體、作為一種具備本源性美感呈現的審美存在,自然之“魅”從未消失,也不會因人的審美方式、價值標準的變化而轉移。其次,回到自然美與藝術美的關系這一美學命題上看,自然美為我們展現出無窮無盡的張力與審美體驗,自然美與藝術美并非對立而是統一、融合。我們的文學作品雖將自然直接作為藝術創作主體和審美本體,但并未回避“人”,作家對自然的書寫也未抹去人的情感體驗與人文關懷。在生態環境支離破碎、生命物種不斷瀕危的當下,把人置身于自然之中,直面人,直面人對自然該有的責任意識與道德關懷,既是一種對過去審美活動中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否定,也是對當今西方“荒野文化”忽略人的“在場性”的一種糾偏,更是一種徹底的自然主義與徹底的人道主義相統一的體現。
《云海探奇》里領略到大自然的瑰麗多姿及猿猴世界的精彩紛呈的主人公黑河與望春;《呦呦鹿鳴》里從打獵隊的槍口下救出梅花鹿的主人公藍泉和小叮當;《大熊貓傳奇》里為了尋找一對饑餓的大熊貓母子,在川西高原充滿野性的原始自然生態環境中走進自然、親近野生動物的兄妹倆果彬和曉青。他們勇敢地走向大自然,把自我置身于自然之中,與自然融為一體,在探索自然的神圣與瑰麗的同時也在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與生存意義。
四、“復魅”:新的美學核心
馬克思曾說:“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也就等于說自然界同人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96存在論哲學則直接指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護者”。[7]385自然孕育了人類,而人類本身就棲居在自然之中,也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宇宙自然則是容萬物于其中的存在場域。從這一哲學起點出發,我們可以說大自然之于人類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自然之物,它應是存在之物在不斷生長涌動著的同時又向自身返場的一種“存在的暈圈”[8],并在其生生不息自融自洽的動態平衡中,源源不斷地召回“人”這一存在之物,向內在的“暈圈”里去探求與發現未知世界。
“我對自然的觀察,就具有了另一種視角和另一種含義——實際上是和大自然相處,融入自然……通往沙漠深處的紅柳、滂沱大雨中撲入胸膛的小鳥、青藏高原的花甸、天鵝湖畔的麝鼠城堡、南海紅樹中的蛇鰻、從雨林中伸出的野象長鼻、進入箱式峽谷尋找黑葉猴王國……往往比結果更有意義。發現過程的艱辛,自有一種蘊藏在平常中的特殊的魅力。”[9]295-297這段文字充分體現了大自然文學創作者的自然哲學觀,自然之美是建立在“關系之美”的基礎上的,即人與自然在審美境域里是“此在與世界的關系”[10]43,是人在本己存在中對存在本源的融入與參悟。從這個角度去構建新的自然美,我們可以發現,對自然審美的轉向,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人自身“此在”存在的一種本源上的確認和旨歸,自然的魅力來自生命的魅力,而生命這一主題本身也意味著人與自然世界的同一性。
如果說“人在自然中存在”是自然“復魅”之路新的哲學起點,那么對自然萬物生命的體認則可以作為自然審美新的美學核心。從生命萬物交互通感的角度,將人的全部感官與感覺滲入自然之中,形成種種交合感應,把自然與人的感官體驗、精神意志相契合,突破形而上的審美形式,以自然的存在指向生命的本質,以生命的本質展開自然的存在。這也與伯林特提出的“參與美學”相契合,他提出重建美學理論的核心就是,應顛覆過去那種把自然作為一件事物或場景在遠處去“靜觀”,而應以人的各種感官作為審美感知和判斷的基礎,人應全部“參與”到自然世界中去,從而在“參與”活動中獲得感性體驗與哲理性思考相結合的審美愉悅。
《東海有飛蟹》里小兄弟倆對大海之生命力量持有一種本能的感知與應和;《美麗的西沙群島》里海疆的自然之美與守衛邊疆戰士的心靈之美交融一體;《大熊貓傳奇》里女騎士駕著黑駿馬馳騁川西山野的臉龐與心靈深處的喜悅完完全全融入山原之中;在《魔鹿》中,作家在感嘆帶給人們魔一般美麗享受的鹿樹卻因物種生存競爭,被所謂丑陋的高山榕樹的根包裹絞纏以致枯死腐朽的同時,為同樣是自然生命物種的高山榕樹的生存權利發問:人類不應賦予地球生命物種“美”與“丑”或“貴”與“賤”的定義,生命的權力都是一樣的,都應得到尊重。作家把自然與人的生命意志同一呈現,把對生命本身的美感體認作為審美對象,并以人的所有感官介入來實現這一審美過程,實現人與自然自在自由的審美對話。這就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靜觀之美”“形式之美”,而是一種“結合之美”“通感之美”。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認識到“自然文學作家的作品實際上是人類心靈與自然之魂的溝通與對話”[11]5。
海德格爾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一體的觀點,我國古代哲人提出“道法自然”,將道、天、地、人有機相連,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天人相和”“天人合一”思想。《周易》中論述的“中和之美”“生生之美”“復歸之美”,都是一種天地人道各在本位又渾然一體的生態整體主義思想的體現,這種本然狀態也是一種萬物復歸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才會構建出天人萬物生命同一的美的“家園”。在此,我們提出以“人在自然中存在”來體認生命之“魅”作為新的自然美的審美核心,既不同于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下的“人化”之美,也有別于生態中心論中完全拋棄人的立場的“自然全美”,它是一種從生態整體主義出發的“結合美”與“融入美”,是人回歸自然本真的、與其他審美形態同格的“棲居家園”之美。
五、終極追求
從“祛魅”到“復魅”,以“人在自然中存在”、體認生命之“魅”來重構自然美的核心,還是要回到人類如何生存這一終極命題上來,這也是與完全拋棄人的立場及生存發展的生態中心論的核心區別所在。海德格爾指出“此在總是從它的生存來領會自身,此在的‘本質’在于它的生存”[12]186;當代生態美學也認為,“恰恰是人與自然共生中的‘美好生存’將生態觀、人文觀與審美觀統一了起來,‘生存’成為理解生態美學視野中自然之美的關鍵”。[10]“生存”首先意味著棲居,“祛魅”將棲居工具化、人本化,丟棄了“家園意識”,更喪失了地球生態系統中自然與生存的本質內涵。從“祛魅”到“復魅”,更多的應體現由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整體主義而非生態中心主義的轉變,并以此明確人與自然、此在與世界的存在關系。不回避人,不排斥人的立場,而是以“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方式將人置身于世界本源之中。
對自然的“復魅”,重在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把自然界視為生生不息孕育生命萬物的有機整體,只有在這一有機整體之內,人的創造性才能協調于自然的源生力量,并融入這一力量不斷蓬勃向上生生涌動的過程之中。實現了自然之神圣性與人的創造性的雙重肯定,才能真正地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類文明才真正得以可持續發展,人類社會才能夠在磅礴浩瀚的宇宙家園中“詩意地”生存并前行。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提出對自然的“復魅”、確定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共同體價值,終極追求應是此在與世界生存關系中實現人類詩意精神的“返鄉”與“回家”。自然的魅力是無窮盡的,這正如人類對世界的認知也應是無止境的。對自然的“復魅”,不是退回前現代的神化膜拜,更不是抹去人的存在價值與創生力量,而是以“復魅”確認人的價值歸屬與生存內涵,以“復魅”帶領人走向地球“家園”,在“回家”的路上“詩意地棲居”。
綠色發展理念“著眼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經濟與生態協調共贏,為生態文明建設和推動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可行途徑”。[13]當代大自然文學創作的興起及這一文學現象的繁榮,正是文藝創作領域對地球家園意識與綠色發展意識的呼喚。從紅樹林、杜鵑花、野百合、奇山云海,到葉猴王國、梅花鹿、金絲燕、大熊貓、相思鳥、藏羚羊、麋鹿、雪豹……世界自然萬物,無不彰顯著生命的廣延與魅力、浸透著自然的通靈,而人在置身大自然探尋自然的魅力與價值的同時,也在體認自身存在于自然萬物之內的自我價值與身份歸屬。這是由“此在”走向“外在”進而又回歸“此在”的一種升華,是對過去工具理性下機械自然觀的一種指正,是正視人在自然世界中存在、直面人對地球自然不可缺失的責任的一種人文關懷。我們認為,這種人文關懷是新時期生態文明建設形勢下重構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突破,也體現了以實現人的“詩意地棲居”、實現生態平衡為核心指向的“復魅”精神的終極追求。
“我在大自然中跋涉了三十多年,寫了幾十部作品,其實只是在做一件事:呼喚生態道德——在面臨生態危機的世界,展現大自然和生命的壯美。”[9]297這是大自然文學創作群體在人類不斷面臨地球生態危機時的一種人文自覺,作家通過文學作品的創作為我們呈現大自然廣闊的“美”與“魅”,并在這一審美呈現的張力下呼吁對地球生命萬物的肯定與尊重,實現人類精神生態的返鄉與回歸。我們也只有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恢復對自然必要的敬畏與尊重,關注自然本身的詩意價值與審美意義,才能真正把握新時期人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蘊涵,實現地球自然萬物在整體合一的動態平衡中共生共榮、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