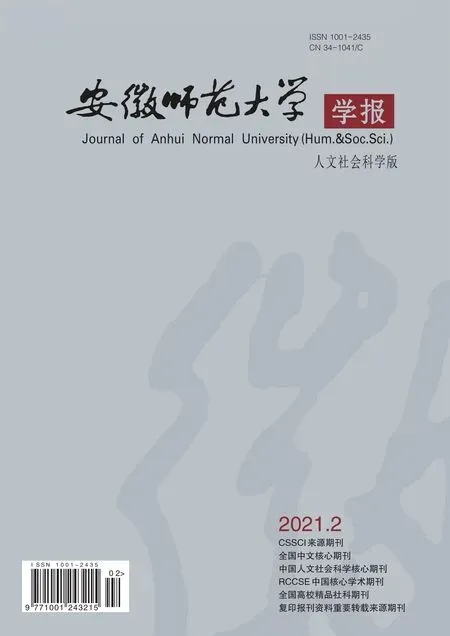“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流轉規則的法教義學分析*
吳 昭 軍
(中國農業大學1.土地科學與技術學院;2.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北京100193)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土地承包法》與《民法典》相繼肯認并表達了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政策,承包地上的權利結構獲得重塑,進入“兩權”(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與“三權”并存的階段。農地“三權分置”指向的標的物是家庭承包經營的土地(以下簡稱“承包地”①承包具有兩種方式: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在廣義上,通過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地”也可被稱為“承包地”。本文采狹義的“承包地”概念,指家庭承包的土地。),但是在政策入法過程中產生了體系效應:2018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將原法中的“四荒地”上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轉換并納入到了土地經營權概念之中。“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成為承包地“三權分置”的體系產物,但是《農村土地承包法》的這種體系化存在不徹底性。不論是“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即土地所有權直接派生的土地經營權)還是承包地土地經營權(即土地承包經營權派生的土地經營權),均是市場化的土地利用權利,本應在土地經營權體系化構建的同時,設置專章將二者一同規定,但是《農村土地承包法》最終沿采“第二章家庭承包”和“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二分的章節體例,在結構上割裂了兩類土地經營權。體系效應與結構割裂雙向反力造成“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流轉規則的解釋與適用困難,即其是否與承包地土地經營權適用相同規則。例如,《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5條規定的工商資本流轉取得土地經營權的規則,是否適用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條件、方式等是否與承包地相同;“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抵押是否適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7條等。雖然承包地和“四荒地”均為農村土地,但是基于二者具有不同的土地用途、不同的社會功能,兩類土地上設立的土地經營權是否能夠適用相同的流轉規則,需要進行具體分析。目前學界關于土地經營權的討論多著眼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派生的土地經營權,而忽略了“四荒地”上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導致理論研究與規范闡釋不足。本文擬立足于《民法典》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條文,以解釋論視角分析“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規則。
首先需要理清的是,土地經營權流轉應區分設立環節的流轉與二級市場中的再流轉兩種類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6條和《民法典》第339條所使用的“流轉土地經營權”表述,混淆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經營權能和土地經營權。在土地流轉之前尚未發生“三權分置”,土地經營權尚未產生,此時承包地仍處于“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兩權結構,承包方行使和處分的是土地承包經營權。[1]所以,這兩個條文實際要表達的含義是承包方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債權性處分,通過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轉承包地,從而設立土地經營權,而不是對土地經營權進行處分的規定。[2]“四荒地”上的土地經營權則是由《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9條規定的以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流轉“四荒地”而設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6條、第53條和《民法典》第342條規定的才是以土地經營權為客體的流轉(法律將其表達為土地經營權再流轉),即經營權人對土地經營權的處分。
環節不同必然導致流轉的法律效果的不同。以承包地上的土地經營權為例,在設立環節,承包農戶將土地入股,為受讓人創設土地經營權,自己不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3]在再流轉環節,經營權人將土地經營權入股,產生的效果是土地經營權的移轉,經營權人喪失土地經營權,獲得股權,受讓人繼受取得土地經營權。在設立環節,承包農戶將土地出租,為受讓人創設土地經營權,土地承包關系不發生變化;②2005年原農業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35條規定,出租是指“承包方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一定期限租賃給他人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出租后原土地承包關系不變,原承包方繼續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承租方按出租時約定的條件對承包方負責”。在再流轉環節,經營權人將土地經營權出租,實際上是對農地的轉租,其法律效果應依《合同法》第224條和《民法典》第716條進行判定,即承租人(經營權人)與承包方之間的出租合同繼續有效,第三人在轉租期限內享有對土地的經營權,成為次經營權人。[4]
既然《民法典》與《農村土地承包法》條文中的“流轉”既包含土地經營權設立環節的流轉也包括土地經營權設立后的再流轉,那么本文所闡釋的“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流轉規則便也囊括這兩個環節。
二、“四荒地”土地經營權設立環節的流轉規則
承包地上的土地經營權是經由流轉而設立取得,而在《農村土地承包法》條文中,“四荒地”土地經營權乃“通過其他方式的承包”取得,同一立法使用了兩種不同的表述方式,分別規定兩種土地經營權的設立,帶來理解和適用上的疑問:在“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設立上,“其他方式的承包”是否等同于流轉?若“四荒地”土地經營權亦由流轉而設立,那么流轉規則與承包地土地經營權是否相同,尤其是在工商資本下鄉流轉取得土地經營權的規則上?
(一)“四荒地”土地經營權設立的流轉方式
對于承包地上土地經營權設立的流轉方式,《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6條明確規定為“出租(轉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農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時,將原法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拆分為“依法互換、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和“依法流轉土地經營權”兩部分。此種拆分是基于“三權”分置改革項下的法律效果區分:前者是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性處分,發生物權變動的效果,但不派生土地經營權,不涉及“三權”分置;后者產生承包地的債權性移轉效果,派生土地經營權,導致“三權”分置。[5]207故“流轉的應當是土地經營權,而不是土地承包經營權”。[6]77所以,2018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將“流轉”限縮為“出租(轉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成為承包地上土地經營權的設立方式。但是對于“四荒地”上土地經營權的設立,《農村土地承包法》僅規定了“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這是程序意義上訂立承包合同的方式,而非處分土地的方式。那么法律解釋上的問題便是,“四荒地”上土地經營權的設立,是否與承包地相同,為“出租(轉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
筆者認為,“四荒地”上土地經營權亦是通過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轉設立,與土地承包經營權派生的土地經營權相同。土地的處分包括物權性處分和債權性處分兩種,《農村土地承包法》將“流轉”和轉讓、互換相互剝離,正是基于土地債權性處分和物權性處分的分野。“四荒地”屬集體所有,在發包承包過程中,不存在土地所有權的轉讓、互換、抵押等物權性處分。“四荒地”上土地經營權由集體土地所有權直接派生,是對土地所有權設定的負擔。出租和入股等流轉方式均為集體保留土地所有權,將土地的使用權移轉給他人,交由他人經營,為他人創設土地經營權。這與承包農戶保留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轉給他人從而設定土地經營權的邏輯路徑是一致的。所以,《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9條規定的以其他方式承包“四荒地”中的“承包”、訂立“承包合同”,在性質上均應屬于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等債權性處分方式;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其他方式”則是訂立這些合同的程序性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期限(承包期限)與承包地不同。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21條,家庭承包地的承包合同期限為30年至70年不等。對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農村土地承包法》未在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中規定承包期限。從章節體例上看,“四荒地”土地經營權不應直接適用第21條關于家庭承包期限的規定。從民法基礎理論來看,不論是出租還是入股,流轉為他人設定土地經營權的行為實質上反映的都是一種土地租賃關系,屬于特殊的不動產租賃合同。①若發包方將“四荒地”以入股的方式進行發包,其中土地所有權不得轉讓,入股的財產是土地經營權,即接受入股的合作社或公司等主體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對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試點實踐中多采取土地年租金乘以入股期限的方式對入股的土地經營權進行作價,這實質上屬于一種特殊的土地租賃關系。作為租賃權的土地經營權可以出資入股。參見劉云生、吳昭軍:《農村土地股份制改革中的行為特征》,《求實》2016年第9期;房紹坤、張旭昕:《“三權分置”下農地權利入股公司的路徑與規則》,《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在法律適用上,《民法典》合同編是不動產租賃合同的一般法,在其他法律規范未作出特別規定時,“四荒地”承包合同便應遵循《民法典》合同編關于租賃合同的一般規定。梳理相關法律政策發現,雖然《農村土地承包法》沒有對“四荒地”承包期限進行特別規定,但是部分法規和規范性文件規定“四荒地”的土地使用權最長不超過50年,例如2014年《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17條、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治理開發農村“四荒”資源工作的通知》等。對此,應認定其屬于法律的特別規定,不受《民法典》第705條關于不動產租賃合同不超過20年的約束。相較之下,《農村土地承包法》沒有對承包地上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期限作出特別規定,那么依照法理,由土地承包經營權派生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期限應遵循《民法典》第705條關于不動產租賃合同的一般規定,最長期限不超過20年。
(二)社會資本流轉取得土地經營權的規則是否適用于“四荒地”
對承包地上的土地經營權,2018年《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5條增設了工商企業等社會資本流轉取得土地經營權的準入、監管制度,并對集體經濟組織收取管理費作出規定。對于“四荒地”上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新法未作此規定,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第45條是否適用或者類推適用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意即,工商企業等社會資本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四荒地”上的土地經營權,是否應依照第45條的規定,遵循準入、監管制度和向集體繳納管理費?
在章節設置上,第45條位于第二章,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則置于第三章,在形式邏輯上無法直接適用第45條。至于能否類推適用第45條,應區分不同款項。
首先,第1款不宜作類推適用。其一,該款實際上創設了一項新的行政許可,由政府審核批準社會資本的準入。我國《行政許可法》規定了行政許可法定原則,要求行政許可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范圍、條件和程序進行。[7]226立法未明確規定此項行政許可適用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根據行政許可法定原則,不宜通過解釋擴張其適用范圍。其二,對于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政策和立法須考量如何平衡多方主體利益,保護農戶利益不受損,防止土地過于集中,維持農地農用,故對社會資本準入設置行政許可。[8]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2條第2款,在“四荒地”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流轉時,亦須對受讓人的資信情況和經營能力等予以審查,此處受讓人便包括社會資本,只不過審查的主體是發包方。其目的是保障土地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開發和利用,這與第45條規定的資格審查的目的相同。[6]194可見,因為“四荒地”不具有社會保障功能,國家鼓勵多元主體參與這類土地的治理開發,立法對社會資本流轉取得“四荒地”的土地經營權的規定較為寬松,由發包方和集體成員決定流轉事宜未上升至行政許可。
其次,第45條第2款可以類推適用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該款認可集體經濟組織在一定情形下收取管理費的行為,有其合理性。在實踐中,集體經濟組織可以發揮自身優勢,為土地流轉、利用提供服務,有助于農戶、社會資本等多元主體的溝通、協調等。社會資本流轉取得“四荒地”的土地經營權同樣存在此種情形,故可以類推適用該款。2021年農業農村部《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便規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參照適用該辦法。
三、“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條件
再流轉是土地經營權已經創設之后的“二級市場”,基于“四荒地”與承包地的功能不同,立法對兩者的再流轉設置了不同的限制條件。在土地經營權體系化塑造的視角下,尚需對立法中關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條件作進一步的規范解釋。
(一)再流轉是否須“登記取得權屬證書”
《民法典》第342條相較于《物權法》第133條,增加了“經依法登記取得權屬證書的”作為再流轉條件,這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條保持一致。這便引發條文理解和司法適用上的困惑:“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是否以登記取得權屬證書作為必要條件?若未登記取得證書,再流轉行為的效力如何?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1條第1款規定,“四荒地”承包方若未辦理登記取得證書等,那么流轉行為將歸于無效。最高人民法院的理由包括三項:對原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9條的反向解釋;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物權,應自登記時設立;在登記之前該權利屬于債權,不能進入市場進行流轉。[9]223-224筆者認為,這三項理由不能成立,該條司法解釋更不能繼續適用于修法之后的“四荒地”土地經營權。
首先,2018年《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條(原法第49條)規定經依法登記取得證書的“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可以流轉,該條文在性質上屬于賦權性規范,不是強制性規定,更未明確禁止未登記取得證書的“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流轉,所以不能從反向解釋得出未登記取得證書的土地經營權流轉行為無效的結論。
其次,登記是“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對抗要件,而非設立要件。原農村土地承包法僅在第二章明確規定了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自承包合同生效時設立,登記僅為對抗要件,成為我國物權體系中采債權意思主義的特殊用益物權;第三章卻未明確規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何時設立。對此,有學者認為,既然立法對其未作特別規定,那么便應適用不動產物權變動的一般規則,即登記設立。[10]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2005年司法解釋中明顯采此觀點。筆者認為該結論在解釋論上不能成立。作為原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后法與上位法,《物權法》第127條明確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自承包合同生效時設立,沒有區分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是對兩種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一體化規定。[11]那么,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自應適用《物權法》第127條,登記不是其設立要件。2018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將該權利修改為土地經營權后,在解釋上便不能再適用《物權法》第127條和《民法典》第333條了。此時,“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登記規則應直接適用《民法典》第341條,采登記對抗規則,或者類推適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1條關于承包地土地經營權登記對抗的規則。一方面,《民法典》第341條規定的是土地經營權的登記對抗規則,沒有區分不同取得方式的土地經營權,那么“四荒地”土地經營權自然可以適用該規定。另一方面,《農村土地承包法》僅在第二章規定了承包地土地經營權的登記對抗規則,在第三章對“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卻沒作規定。基于兩類土地經營權均為市場化的土地利用權利,在法技術上,“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可以類推適用第41條。[12]
最后,登記不是“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必要前提條件。學界關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存在很大爭議。有觀點認為應延續原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將其定位為物權;也有觀點認為,在土地經營權體系化塑造下,“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已轉化為債權;還有觀點認為,期限五年以上或進行登記的為物權,否則為債權。[13]實際上,不論“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屬于債權還是物權,都可以進行流轉。若界定為物權,“四荒地”土地經營權采登記對抗規則,即便未辦理登記取得權利證書,亦不影響土地經營權的設立與變動。若界定為債權,“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屬于依法可以轉讓的債權,亦不需要以登記取得權利證書作為處分的前提條件。而且,對于承包地上土地經營權的再流轉,立法并未設置須辦理權利登記的限制條件,同一權利體系下的“四荒地”土地經營權亦無理由多此限制。那么《農村土地承包法》為何在“四荒地”權利流轉中規定登記呢?全國人大法工委的解釋是,“四荒地”的承包期限一般較長,“雙方需要建立一種物權關系”,[14]118“以便更好地得到保護”。[6]220由此可見,登記是為了強化“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穩定性和對抗性,保護權利人的利益,這與登記對抗規則相協調,而不是為了限制權利的流轉。所以,登記取得權屬證書不是對“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流轉行為的效力不因是否登記取得權屬證書而受影響。2020年12月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便刪去了原司法解釋的第21條,殊值贊同。
(二)再流轉是否須集體成員民主決議同意
發包方將“四荒地”向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進行發包時,需要“事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意即非本集體成員的民事主體若通過流轉取得“四荒地”土地經營權,須經集體成員的民主決議程序。在規范理解與法律適用上存在的問題是,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權利人,將該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給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是否仍須經集體成員民主決議同意?
這一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有法院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95條認為,“四荒地”的承包方可以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但是須經發包方同意。①參見西鄉縣人民法院(2017)陜0724民初763號民事判決書、葫蘆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遼14民終1534號民事判決書等。有法院根據原《土地管理法》第15條第2款認為,承包方向本集體外部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需要經過村民民主決議程序。②參見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黑01民終1242號民事判決書。也有法院認為,發包方將土地向本集體外部發包時需要通過民主決議程序,是為了保護本集體成員利益,已經承包土地的承包人對外流轉無需經過民主決議程序。①參見涼城縣人民法院(2018)內0925民初482號民事判決書。《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沒有規定“四荒地”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需要經過發包方同意,可以自由地進行市場流轉。②參見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陜07民終191號民事判決書。
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時刪去了原法第15條第2款關于本集體外部的個人或組織承包經營集體土地須經民主決議通過的規定,《民法典》第342條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條亦未規定“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向本集體外部再流轉時須經民主決議通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民主決議程序不適用于此種情形。筆者認為,“四荒地”的承包方將土地經營權向本集體以外的組織或個人再流轉時,應類推適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2條。
在“四荒地”發包環節(土地經營權流轉設立環節),《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2條之所以規定向本集體外部發包須經民主決議程序,主要原因有兩方面:其一,保障集體成員的權利,防止個別人員侵害集體土地所有權;其二,對集體外部的承包方的資信情況和經營能力進行審查,確保集體土地能夠得到合理開發利用,合同得到全面履行。[6]219這兩個問題在再流轉環節同樣存在。第一,若僅在發包環節對向本集體外部流轉“四荒地”設置民主決議程序而在再流轉環節不設置的話,可能會誘發道德風險,例如本集體成員和本集體外部的主體串通,先由本集體成員承包“四荒地”,然后再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本集體外部的主體,便可以規避民主決議程序,損害集體成員的利益。第二,在再流轉環節,“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流轉給本集體外部的主體,亦會存在受讓方是否具有足夠的資信狀況和經營能力的問題,這直接關系到集體土地能否得到有效合理地利用開發,集體收益能否得到切實履行和保障。在工商資本下鄉、經營主體良莠不齊的現實背景下,為防止“四荒地”承包方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不具有經營能力或資信狀況不好的主體,保護集體財產權益,有必要對向本集體外部再流轉土地經營權的行為進行民主決議和審查。
此外,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6條,承包地上的土地經營權再流轉須經承包方同意。其中的原因是,承包農戶不是再流轉合同的當事人,對再流轉的次受讓人的資信狀況、經營能力等不了解,也無法把握次受讓人對土地的真實利用情況、是否對土地造成損害等,最終可能損害承包農戶的權益。[6]197那么,為防止集體所有權受到損害,“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再流轉同樣也應有一定的限制。若再流轉的受讓方為本集體內部成員,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封閉性和農村的“熟人”社會狀態,集體成員之間較為熟悉,可以不經發包方同意或民主決議通過。但是若向本集體外部再流轉,則需要滿足一定的程序要求。此情形下的成員民主決議程序具有發包方同意的效果。
概言之,不論是“四荒地”發包環節,還是“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環節,只要向本集體之外的組織或個人流轉或轉讓,均應適用或類推適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2條,經集體成員民主決議通過。
四、“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方式
圍繞“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再流轉方式,最具焦點性的兩個問題便是,在《農村土地承包法》關于承包地“三權分置”的體系效應下,“四荒地”土地經營權能否轉讓以及如何抵押。這關系到“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和承包地土地經營權規則的體系沖突與協調問題。
(一)轉讓是否屬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方式
《民法典》第342條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條相較于《物權法》第133條,在“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處分方式中刪除了“轉讓”,增加了“出租”,由此便產生理解和適用上的問題:“四荒地”土地經營權能否進行轉讓?
梳理相關規范可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6條規定了承包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沒有列舉再流轉的具體方式,第53條規定“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列舉數項再流轉方式;《民法典》第342條則照搬了《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條。在解釋上,《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6條沒有對再流轉方式作出限制,自然應包括所有流轉方式。問題在于如何理解此處的“流轉”。有學者認為,此處應包括轉讓、出租、入股、抵押等所有處分方式。[15]相較之下,第53條所列舉的流轉方式中則沒有包含轉讓。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解釋是,本次《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家庭承包和以其他方式的承包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將流轉對象由土地承包經營權調整為土地經營權,同時將“流轉”概念進行了限縮,主要是指“出租、入股或其他方式”,不再包括轉讓、互換,所以“本條中不再規定轉讓為流轉的方式之一”。[6]221對此,有學者認為,土地經營權作為市場化的權利,理應可以再進行轉讓或繼承,新《農村土地承包法》之所以沒有明確規定土地經營權的轉讓和繼承,可能緣于立法將土地經營權再流轉和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設立進行合一調整,后者不包含轉讓和繼承,也就未對前者的轉讓和繼承進行列舉規定。[16]這一觀點頗值贊同,立法在本條將土地經營權流轉設立和土地經營權再流轉兩個環節中的“流轉”概念進行了統一,但仍應區分兩個環節中權利處分方式的不同。
基于體系的協調性和概念的一貫性,立法關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規則中的“流轉”概念應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6條規定的“流轉”含義保持一致,即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不包括轉讓、互換。那么土地經營權是否具有轉讓權能?筆者認為,雖然《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條和《民法典》第342條沒有明確列出轉讓,但是在解釋上,“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可以轉讓。其一,法律雖然沒有明確規定轉讓權能,但是也未明確禁止,民事立法以“法無禁止皆可為”作為基本理念,所以在解釋上不宜簡單認為土地經營權不能轉讓。例如,《物權法》第153條列舉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或者抵押,沒有規定出租權能,這并不意味著在法律上不能出租,根據《合同法》第212條和《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4條,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進行出租。[17]其二,“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尚存在爭議,但不論定位為物權還是債權,其均應具有轉讓的權能。若“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屬于物權,則根據《民法典》物權一般規則,在法無明文限制時可以進行轉讓。若“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是基于合同產生的債權,在作為特別法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沒有進行例外規定時,應適用《民法典》第545條關于債權轉讓的規定,權利人可以將其轉讓給他人。其三,土地經營權是市場化的土地利用權,放活土地經營權是承包地“三權分置”和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政策目的,“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更是自始便具有市場流通性,允許轉讓契合其權利性質和立法政策。其四,土地經營權的入股具有移轉土地經營權的效果,土地經營權抵押權實現時也將導致土地經營權移轉,與轉讓的法律效果相似。法律既然規定了“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入股、抵押的再流轉方式,就沒有理由否定土地經營權的轉讓。
綜上所述,《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條和《民法典》第342條中規定的“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不包括轉讓,但是轉讓仍屬于“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處分方式之一。
(二)“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抵押的規則適用
土地經營權融資擔保是本次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改的重要內容,在立法體例結構上,《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47條和第三章第53條均規定了土地經營權的融資擔保。在本次修法之前,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便具有抵押權能,可以直接適用《擔保法》《物權法》抵押規則,其在本次修法中被重構為土地經營權,由此便產生法律解釋上的問題:“四荒地”土地經營權融資擔保是否適用第47條,抑或適用《民法典》物權編抵押規則?這關系到“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的抵押權設立是采債權意思主義還是債權形式主義,擔保設立條件是否不同等問題。
第一,“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抵押是否以辦理土地經營權登記為前提?第53條規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抵押應首先辦理登記取得權屬證書,而第47條對承包地土地經營權抵押則未作此種限制。那么兩類土地經營權在以登記取得權屬證書作為抵押前提條件上是否存在差異,流轉期限五年以上和不滿五年的土地經營權登記能力不同,在擔保能力上又是否存在差異,便須作解釋。
有論者認為,應將辦理登記取得權屬證書設定為兩類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共同條件,將《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7條中的土地經營權限縮為已登記取得權屬證書的土地經營權。[18]此種觀點有待商榷。其一,在金融實踐中,金融機構為確保交易安全,對抵押物的公示性、流通性等會有一定的要求,通常會要求辦理土地經營權抵押登記。而土地經營權抵押登記的前提是已辦理土地經營權登記,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1條,期限不足五年的土地經營權不具有登記能力,那么也就意味著,未辦理登記或者不能辦理登記的土地經營權將是信貸市場中不受歡迎的擔保工具。有觀點進而認為此類土地經營權價值不高,不宜設立抵押。[1]但是在法解釋上,第47條第2款采取的是抵押權登記對抗主義,登記并非土地經營權抵押權設立的必備條件,那么土地經營權登記便也不必要。故而,不論是期限不滿五年而不能辦理登記的土地經營權,還是期限五年以上尚未辦理登記的土地經營權,只要當事人愿意就此進行擔保,達成抵押合意,那么便可以設立土地經營權抵押權。[15]其二,如前文所述,第53條將權屬登記作為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抵押前提的規定,是基于保護當事人利益的考量所作的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在承包農戶流轉產生的土地經營權和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均為市場化權利,并進行一體化塑造的立法意旨下,不宜在抵押權設立行為效力上將二者割裂,意即,雖然《農村土地承包法》在管理上對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抵押設有登記取得權屬證書的前提,體現公法對不同取得方式下的土地權利施加不同的管制措施,但這一前提要件不影響法律行為效力。若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未辦理登記取得權屬證書,抵押合同不因此而無效,抵押權亦不因此而無法設立。
第二,在抵押權設立模式、設立條件、實現方式等方面,“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是否適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7條?從條文內容來看,第47條對承包地土地經營權抵押設置了諸多特別規定,例如第1款規定的向發包方備案、經承包方同意、抵押權人限于金融機構等條件,第2款規定的抵押權登記對抗模式,第4款規定的授權性條款和轉介條款等。與之相比,第53條對上述內容均未作規定,“四荒地”是否適用或準用第47條不無疑問。
第47條第1款第一句適用情形為“承包方”以其“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擔保,在文義上,第53條所規定的其他方式承包“四荒地”中的土地經營權人也屬于“承包方”,也是以其“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抵押,似乎符合第47條第1款第一句的適用情形。但是在章節結構上,第53條位于第三章,第47條則位于第二章“家庭承包”之中,難以直接相互適用。第53條所規定的此類土地經營權來自原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本次修改之前便具有抵押權能,適用《擔保法》《物權法》。本次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改時,第47條的制定是以承包地“三權分置”為主要適用情形,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派生出的土地經營權擔保為主要適用對象,在立法意旨上沒有將“四荒地”土地經營權納入一同考慮、一同調整之意。[6]200
如此一來,《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條所規定的“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抵押自應適用《民法典》第209條和抵押權的一般規則,這便導致兩種土地經營權在抵押時的體系矛盾:由土地承包經營權派生的土地經營權設立抵押權,依《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7條第2款采登記對抗主義,而由集體土地所有權派生的土地經營權設立抵押權,則依《民法典》第209條和第402條采登記設立主義。《民法典》第395條關于可以抵押的財產范圍,刪去了“四荒地”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成為該條第七款“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財產”,第402條未明文規定其采登記對抗主義。但是,根據《民法典》第209條不動產物權變動采債權形式主義的原則,在法律未另有規定的情況下,“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抵押權應適用登記設立原則。在兩種土地經營權均為市場化權利,均為可登記的債權,均旨在放活、加快土地流轉的制度定位下,抵押權設立模式不應有異,應然的制度設計是統一兩種土地經營權抵押權生效規則。目前這一體系矛盾只能在立法論層面尋求解決,有待未來修法或由其他法律進行規定。
在設立條件方面,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派生的土地經營權進行抵押,須經承包方同意并向發包方備案,因“四荒地”不具有生活保障功能,立法者在制度設計時給予更寬松的空間,無需經發包人同意或備案。[6]220在抵押權人主體范圍上,前者限于金融機構,后者則沒有法律限制,這也是基于承包地和“四荒地”功能不同所作的政策考量。所以在此方面,“四荒地”土地經營權既不適用也不能類推適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7條第1款。至于第47條第4款規定的土地經營權融資擔保辦法可否將“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容納在內,尚有待根據未來該辦法的內容來具體判定。較佳的立法方案是在該辦法中對兩類土地經營權進行一體化調整,對登記對抗規則、抵押合同內容、抵押權實現方式等共通的規則作相同規定,對設立條件、程序等可以基于兩者之間的差異性作相異規定。
五、結 語
隨著承包地“三權分置”入法,原農村土地承包法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二元結構不復存在,衍生出土地經營權的二元結構:承包地流轉所派生的土地經營權與“四荒地”上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2018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在土地經營權體系化塑造上尚有不足,以致兩類土地經營權在規則適用上存在齟齬。從《農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法過程和理論研究來看,“四荒地”土地經營權尚未受到足夠的關注,條文的內容擬定仍存在一定的立法技術問題,規范的理解與適用也需進一步地探討。土地權利義務的具體設計是由土地所承載的不同用途與功能決定的。承包地不僅擔負農民生活保障功能,而且在用途管制制度下還承擔著農地農用、保障糧食安全的重任。故而,承包地上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受到法律的一定限制。“四荒地”不承擔這些社會功能,也不受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的剛性制約,所以在經營用途、權利流轉上較為寬松。未來在進行法規范解釋時,須尊重“四荒地”和承包地的不同資源屬性和社會功能,二者在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規則上可以存在一定差異。[19]在此基礎上,基于土地經營權的體系化塑造,“四荒地”和承包地上的土地經營權應在規則設計上盡可能趨于統一、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