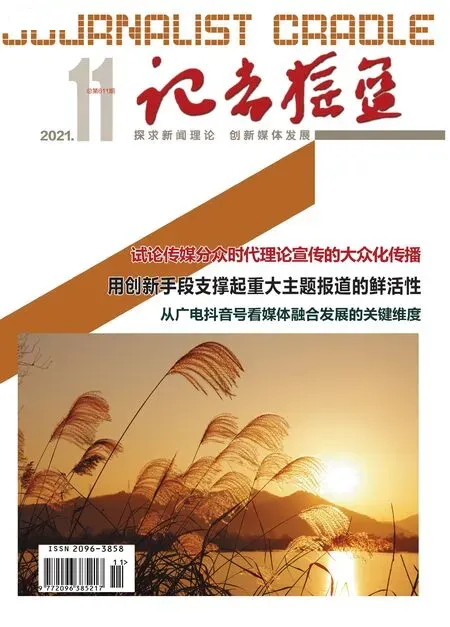互文性與差異性:新聞事件改編電影研究
□宋亞歐
2020年春節檔,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前五位分別是《戰狼2》《紅海行動》《哪吒之魔童降世》《美人魚》和《我不是藥神》,其中新聞事件改編電影占據三席,分別是《戰狼2》《紅海行動》和《我不是藥神》,它們分別改編自利比亞撤僑(部分改編)、也門撤僑以及極具影響力的“陸勇案”。影片的上映使新聞事件時隔多日又重新回到受眾和媒體視野中,經由現代傳播技術與手段的助推,更多人在接受電影作品的同時,重新接觸并參與到新聞事件的二次傳播中來。
“在我國電影事業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新聞與電影之間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下新聞與電影在新的社會時期相互融合產生了具有時代意義的電影類型,即新聞事件改編電影。”在新聞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社會作為大文本與電影文本的生產相互交織,形成一個經過改編之后的新文本。電影將社會新聞納入自身,通過相互引用、對照、模仿、改編、戲擬、重寫等互文方式,重新建立一個不同于此前文本又有此前文本痕跡的新文本。但為了迎合觀眾,創造戲劇沖突,有時新文本會刻意強調故事性和情節的夸張性,于是便偏離了原有的社會文本。新聞的核心是真實,電影的核心是創造戲劇沖突,所以新舊文本差異性的產生是必然的,那我們就要在社會文本的真實性和電影文本的故事性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一、真實性的建構
新聞事件改編電影之所以在上映后能夠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討論,與其脫胎而來的真實性是密不可分的,觀眾可以通過電影了解新聞事件,從而為新聞事件創造更高的話題討論度,滿足了環境真實性和人物真實性的改編作品可以“從多方面向社會闡釋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用鏡頭的生動講述,拉長新聞的時效,引導受眾對新聞事件的二次傳播,喚起觀眾對新聞背后意義的再思考,推動社會發展”。
1.環境真實
環境真實指的是改編作品選擇的新聞事件必須能夠針對當下社會熱點,反映社會矛盾,能與大眾產生共鳴,只有如此才能在公映后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實現改編電影的社會價值。
電影《親愛的》根據2008年彭高峰尋子事件改編。彭高峰的兒子彭文樂走失,三年里他四處尋找兒子,終于在2011年找到了兒子,并且意外發現,養父母家還有一個妹妹,似乎是棄嬰,后被送到了福利院。“打拐”本來就是當今社會的熱點話題,是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再加上央視報道了“彭高峰事件”,這在當時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其社會關注度自然就更高,觀眾會沖著對新聞事件的關注而去觀影并在觀影時代入社會真實背景,從而使得大眾對拐賣兒童和尋子父母這一社會群體產生強烈的關注和思考。
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一部電影要想給觀眾以震撼,就必須先還原真實環境,讓觀眾進入場景,繼而去感受人物,理解劇情的走向,引發情感共鳴。在構建環境真實中,真實性不僅僅是環境的基石,也是整個改編電影的基石,在此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影片才能引發觀眾思考的同時激發其內心情感,獲得超越商業價值的社會認可:《紅海行動》與《戰狼2》等電影的熱映,打破了傳統主旋律電影枯燥、老套的刻板印象,主角直面危險與死亡,在困境中創造奇跡。這既體現了民眾對國家“強起來”的高度認同感和自豪感,也是對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的突顯。
2.人物真實
將環境構建成功后,下一個要素就是人物。人物形象的構建,是改編電影體現故事性的關鍵。改編給予劇本創作者一定權利,對新聞人物原型進行戲劇創作,但是新聞事件本身的真實性又要求創作者不能過分夸大或者異化,適當的改編則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戰狼2》中的主角冷鋒是一個虛構人物,是導演吳京為了用自己的方式講述海外撤僑的艱辛而塑造的一個代表性人物。影片中高舉紅旗的冷鋒,其原型人物是中建利比亞分公司的實驗室主任王守合。為了保障中國工人的安全,上級要求他帶著269名同胞撤往埃及。在撤離途中,王守合帶頭唱起了國歌,并高舉國旗,以此來尋找遺失的伙伴。最終王守合率領的269名中建員工平安回國。王守合只是一名普通人,他并不像冷鋒那樣有強大的體魄以及意志力,但是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賜予了這位普通人“特種兵”的力量,讓他創造出了生命奇跡。
同樣,以“中國民航英雄機組”真實故事為原型改編的電影《中國機長》在保留了人物真實狀態和行為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細節創造表現,比如機長的冷靜睿智和臨危不亂。人無完人,或許故事原型中的人物沒有影片所呈現的那么完美,但是,這一改編符合影片的主題,也契合人物的職業特征。還原新聞事件人物形象的真實性也是改編電影在故事性和真實性處理中的重要一環。
二、故事化的表達
一個新聞事件是有限的,如果把這個新聞事件拍成一部電影的話,就必須對原事件進行延伸,這需要創作者全方面了解整個新聞事件的過程,挖掘背后的故事,在尊重新聞事件真實性的基礎上運用電影創作技巧對其進行故事化的改編,增加戲劇沖突,提高影片的藝術性和可看性,這就是所謂的“延伸”。
在《戰狼2》里,冷鋒孤身前往交戰區救人的過程就是影片的主體情節,但其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起初冷鋒只是去營救干兒子的媽媽,但編劇在此之前確立了冷鋒的軍人情懷,曾經是軍人的責任感與使命感,讓他毅然決定放棄平安撤離,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去交戰區帶回中國員工和陳博士。這是一項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解救陳博士的過程中,他就陷入了雇傭兵和紅巾軍的重圍,陳博士被殺,他自己也在突圍過程中感染了病毒,險些喪命。后在瑞秋和帕莎的幫助下治好了傷,他們三人逐漸形成了營救團隊,開始向工廠進發。但又遇到囂張跋扈的公子哥卓亦凡,冷鋒又被孤立于他的團隊之外,最終冷鋒用自己過硬的軍事實力證明了自己,與何建國配合擊退了雇傭兵的進攻,融入了卓亦凡的團隊。就在冷鋒準備帶領大家撤離時,轉折又一次到來,林志雄揭發了冷鋒感染病毒的事,讓冷鋒被迫離開了工廠。而女孩帕莎,則成了整個電影情節轉折點,她是治療拉曼拉病毒的關鍵,也是陳博士研究的心血,這使冷鋒受到極大觸動,他再次回到工廠,工廠激戰也推動情節向著高潮發展。最終冷鋒手持國旗,在交戰區扔下武器,帶領眾人平安抵達安全區,使得整部影片的情緒在此刻達到了高潮。在真實事件中并沒有人能用國旗讓雙方停火,而電影中的冷鋒高舉國旗在交戰區通行無阻,這也印證了影片改編不能局限于真實情況,還應該充分考慮其是否符合戲劇創作規律,是否具有可看性。
三、結語
電影產業發展的迅猛程度和影視作品的創意靈感是成反比的,在缺乏好故事、好素材的創作大環境下,真實新聞事件無疑是改編電影的一大素材庫,其天然的真實屬性和自帶的社會討論度與虛擬劇情相比能夠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因此,由真人真事改編的影視作品更需要謹慎創作。
在改編電影籌備初期事先獲得改編授權和豁免的處理方式要優于事后補救的處理方式。同時,編劇在改編真實人物和事件時,最重要的是選取兼具賣點和時代共鳴的改編主題,之后再以此為基礎選取和塑造主角,這就要求我們觀察時代、理解觀眾,明白觀眾關心什么;在改編電影創作中,涉及敏感情節的,制片方應當與原型人物或利害關系方進行充分溝通,從而對劇本進行更加嚴謹的二度創作,這當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改編的度,遵循忠于傳媒、忠于人性原則,符合故事發展的情節可以夸張,但人物形象必須遵從原型。成功改編的作品在產生社會后續效益的同時還帶來經濟效益,傳達積極的價值導向;而只重注故事性的改編則會對新聞當事人產生二次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