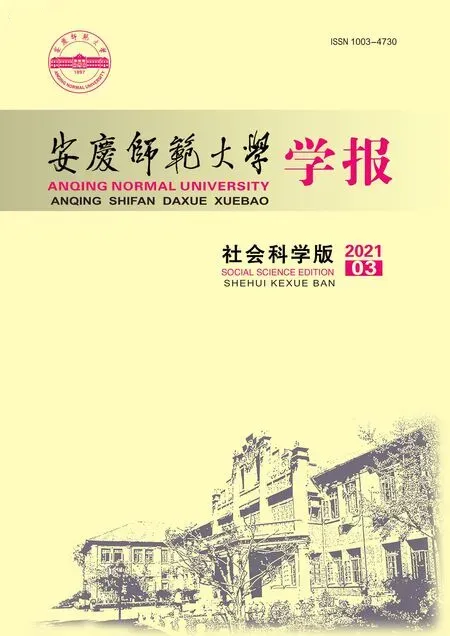政治民主 經濟自給 文娛高尚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外國記者視野中抗日根據地的特質
李軍全
(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揚州225009)
特質就是人或事物表現出來的與眾不同的整體面貌和精神狀態。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起來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展現出一種特質,不僅使其擁有了抗擊侵略者的生存空間和戰略依托,還使其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支持。那么,這種特質是什么呢?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學術界已有非常豐富的成果,不過,在尋覓“他者”視野的方面仍有討論空間,其中曾游歷過抗日根據地的外國記者的觀察值得再度重視。
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批親歷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外國記者根據親身體驗,著書立說,記錄了他們的所看、所感和所悟,從中提出了許多有啟發意義的真知灼見。比如,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杰克·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白修德、賈安娜的《中國的驚雷》,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詹姆斯·貝特蘭的《華北前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國人征服中國》,等等。整體來看,他們的認知趨向于從群眾方面尋找中共力量之源,集中在群眾為何支持中共的問題上,這深深地影響了該領域的研究。
近年來,學術界注意省思該領域的研究,有學者指出以中共及其革命為中心的“我者”論述傾向明顯,相對忽視了政治黨派、民主人士、日占區和國統區、海外國家和人士等與中共相對或有聯系的“他者”論述[1]。在這種省思中,學術界整理和出版了《第三只眼看延安》(任文主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外國觀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戰”(呂彤鄰等主編,上海遠東出版社2019年版)等系列資料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外國記者的觀察也再次受到重視,涌現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李金錚的《以民為本:外國記者的革命敘事與中共形象》(《河北學刊》2015年第3期),耿磊的《忙而有序:另一視野下的陜甘寧邊區鄉村社會——以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為中心》(《歷史教學》2015年第16期)等。有論者認為,他們的觀察“基本上是反映中共革命歷程的第一手資料,對此作必要梳理和科學、理性的分析,可為還原歷史面貌提供一些客觀依據”[2]。鑒于此,本文擬以這批外國記者的觀察為中心,宏觀審視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整體面貌和精神狀態,從中總結和提煉其特質,這或對于理解抗日根據地如何立足于敵后的問題有所裨益。
一、民主的政治
民主的政治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渴望,也是中國政治走向現代化的必然。中華民國成立后,效法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體制取代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宣告了中國民主政治邁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可是,這并非意味著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完全實現,那些服務于個人或集團的專制理念根本沒有遠離中國政治的權力舞臺,或謀求帝制復辟,或塑造領袖專權,或建立集團獨裁。在這樣的權力更迭中,無論如何美好的民主政治體制設計都只得流于形式,變成徒有其表的政治口號,甚至異化為強權打壓群眾意愿的工具。因而,相較于一種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真正地落實民主政治更為艱難。在抗日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始終強調民主政治,建立代表群眾意愿的權力結構,實行廣泛的民主選舉,展現出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落實民主政治的決心。
民主的政治就是大多數人的政治,但并非什么事情都要由群眾解決,它的實現必須得建立有組織體系的權力結構,在一種高度秩序化的權力結構中,達到約束政治權力、體現群眾意愿的政治目的。在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的大背景下,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不再沿襲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專政體制,而是按照中華民國的政治框架建立權力結構。一般來看,這個權力結構是由參議會、政府、法院三個部分組成的,三個部分之間既聯系又制約。這種受西方“三權分立”學說影響建立起來的權力結構并不新奇,新奇的是抗日根據地通過它真正地落實民主政治,克服了其徒有其表的缺陷。比如,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權,完全拋棄了個人或政黨專制的政治理念,由多方力量構成的權力機構不僅保障了權力實施的民主性,還會促進人員團結,增強行政力量。1942年5月,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工作報告中說:“在我們邊區政府中,在多數縣鄉政府中,共產黨員和其他黨派的人士,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都很親密的合作,像一家人一樣,并不感到有主客之分,非共產黨員都同樣有職就有權,使工作得到更大的發展。”[3]3對此,美國記者G.斯坦因有同樣的感受:“這些領袖們,并不都是共產黨人,在民主的人民參議會中,隨處我都遇見一種對中國完全新型的,有才能而忠誠的非共產黨人:地主們,舊式的士大夫階級的社會改良者們,從前的軍隊與地方政府中的國民黨員們。”[4]
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只是體現在對政治權力的約束和分享上,關鍵的是把民主精神融入鄉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而并非圈限于政治集團和社會精英。不同于歷史上任何政治力量,抗日根據地將以選舉為核心的民主政治延伸到了村莊,彌補了鄉村民主權力的不足,顛覆了地主、豪紳、權貴控制村莊的權力格局,喚醒了長期遠離權力中心的鄉村群眾的政治意識和熱情,讓民主政治真正地落地生根。在村莊選舉過程中,有的群眾說:“今天圈的,等于咱們種地的種子,收成好不好,就看種子好不好,以后咱鄉下公平不公平,就看咱今年選舉的人公正不公正!”[5]對此情形,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寫道:“在整個中國歷史上,農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村和縣的議會出現了,而且都賦有解決農民基本生活問題的種種權力,這些問題實際上是他們自幼即已面臨的問題。農民第一次走進了政府機構,卻發現了他們自己也賦有未被發覺的智慧和毋庸置疑的能力。”[6]基于同樣的認識,美國記者愛潑斯坦說:“村選是直到邊區參議會為止的整個制度的基礎,由邊區參議會選舉政府,這真正代表了中國的一種革命。”[7]
村選不只是改變了村莊權力的代言人,還讓吃苦受窮的鄉村群眾有了生活底氣,在村政權的領導下,群眾組織發展迅速。正是群眾組織的大量存在,鄉村群眾找到了心理和組織的雙重依靠,行動上有了主心骨,投入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事業中。對此情形,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有所描述:“青年和老人,婦女和兒童,都為了當前的斗爭組織了,訓練了,武裝了起來。男子和婦女組成了‘抗日自衛團’。青年們有‘少年先鋒隊’,甚至兒童也有‘兒童團’的組織。”[8]曾進入過晉察冀邊區的英國大使館新聞專員林邁可也寫道:“到處都在開群眾大會,演抗日戲劇,墻上出現新寫的標語口號,新組成的軍隊在操練著。對于群眾團體、村莊動員大會和民眾教育的開展,人人都非常感到興趣。”[9]82
政治的民主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干部作風,拉近了干部與群眾的距離。在抗日根據地,群眾路線是干部工作的基本原則,廣大干部被要求深入鄉村生活,與群眾打成一片,有學者指出抗日根據地的縣長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封建官員的圓滑世故,他們“毫無‘官本位’的精神世界,積淀的正是其艱苦奮斗的生活軌跡和與民眾同甘共苦的生活作風”[10]。這種生活作風的形成,逐漸驅走了群眾內心中“怕官老爺”的心理意識,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變得親密起來。對此,美國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寫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在邊區一個縣看到的一位老農,這位老農捶拍著原來是他村里一個苦孩子的年輕縣長的背說,‘你看這家伙背了多少筐糞到我們地里?有誰以前看見過這樣的官?從前,當官的聞的是他們姨太太的香水味,怎能聞這鮮大糞呢?’年輕縣長希望不要用這樣赤裸裸的語言同一位外國‘貴賓’談話,但老人對于什么是值得稱道的有他自己的想法,因此不聽勸告繼續講下去。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以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官員,也沒有人見過這樣的情景。”[11]
抗日根據地努力推行民主政治,在一定意義上消除了自民國以來民主政治限于社會上層及流于形式的弊病,讓民主政治真正地延伸至社會底層,展現出從未有過的強勁生命力,這深刻地改變了群眾對政治、政府和干部的認識,逐漸生成了公眾信任心。對此,美國記者斯諾說:“他們(群眾)可以不必擔憂會受貪污官吏的中飽私囊,或作買賣外匯的投機,或購買婢妾。那里跟別的各處地方不同,沒有從軍火買賣舞弊的百萬富翁,也沒有剝削難民和傷兵勞動力的豪紳。這些有組織的農民知道,他們付給地方政府多少錢,他們的代表可以向參議會核對賬目。”[12]顯然,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治的實踐,不僅凝聚了抗日力量,還給予了群眾一種政治希望。
二、自給的經濟
經濟供給是抗日根據地生存的根本保障,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的經濟能力,抗日根據地根本無法在敵后立足。全面抗戰初期,抗日根據地的經濟收入主要來自國民政府發放的薪餉、進步人士和海外僑胞的捐獻、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等外部援助。據周祖文的研究,1937—1940年陜甘寧邊區經濟收入中,外部援助占當年財政收入的51.69%~85.79%之間,基本上占到了七至八成[13]。而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也不容忽視,黃道炫認為中共基本上每年都會從共產國際得到援助[14]。不過,在復雜多變的政治局勢和戰爭狀態中,外部援助的穩定性難以保證,一旦縮減或斷絕,抗日根據地便會遭受致命威脅。自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在國民黨頑固勢力不斷掀起反共高潮和日軍瘋狂包圍進攻的大背景下,抗日根據地陷入物質極端匱乏狀態。抗日根據地倘要在敵后生存和發展,只有依賴于內部征收,不斷提升自我供給的能力。
不同于其他政治力量,抗日根據的內部征收是從休養民力開始的,主要表現為采取“合理負擔”的征收原則,及動員性的號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抗日根據地,農業是最大產業,糧食是內部征收的重心所在。起初,糧食征收主要表現為“合理負擔”指導下的救國公糧。救國公糧實際上是在傳統田賦征稅無法適應根據地糧食征收情況下的臨時措施。另外,抗日根據地還實行減租減息政策,調低土地的租額和借貸的利息,既便利于民主政治建設,又減輕了貧苦家庭的經濟負擔。只是隨著抗日根據地的發展,非生產人口急劇增加,經濟開支越來越大,抗日根據地只得提高救國公糧的征收量,加之救國公糧征收中形成了“少數富有家庭多負擔而大多數普通家庭少負擔”的不合理現象。在這種情形下,作為直接稅的統一累進稅成為抗日根據地內部征收的基本標準。
對于農民而言,統一累進稅的最大不同就是把負擔固定在土地上,他們能夠保留超出稅額的產量,可是達不到土地應產量,仍然按照應產量征收,這意味著勤于勞動就可能獲得更多產量,而懶于勞動則一定不能,消除了此前“生產少、負擔少”的社會心理,也讓各階層負擔趨于合理。況且,累進率和核算表簡單明了,他們能夠輕易地計算出自己應繳納的稅額。權衡利弊后,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提高,連那些懶漢、二流子也不得不參加生產。對此情形,曾游歷晉察冀根據地的林邁可說:“‘統一累進稅’的實施,是組織工作中一個很大的成就,和我談論過這個稅制的所有的老百姓,都認為這是一種很合理公平和管理得很好的稅制。”[9]85
統一累進稅的實施,不僅規范了內部征收的標準,還實現了“開源”,提升了自我供給能力。不過,倘要保證“源頭”富足,就必須要加強勞動生產。于是,大生產運動成為一項關鍵舉措。可是,在現實的勞動生產情形中,有的家庭存在缺乏生產工具、生產資料、勞動力等諸多困難。于是,以互助合作為生產模式的變工隊應勢而生。變工隊的意義遠非解決家庭生產困難那么簡單,它還在生產過程中將分散的個體生產組織起來而生成的集體勞動,實現了在生產資料私有基礎上局部的集體化,如果從未來中國的發展形勢來看,這實際上孕育了未來中國經濟的希望。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注意到了這個希望:“合作事業以私人財產為基礎,自愿同意為原則,用著許多方式用來組織散漫的,個別的,落后的農村經濟。有十萬以上的農民(約占農村勞動力四分之一)已經組成變工隊和扎工隊。有二十萬人已經加入消費、運輸、生產和信用合作社。有婦女十三萬七千人以上已經組成紡織合作社。”[15]63
大生產運動還改變了傳統的勞動觀念,代之而起的是“勞動光榮”。鄉村社會長期流行著“食人者治于人,食于人者治人”“以勞動為恥”等勞動觀念,從事勞動的人不被社會尊重,勞動成為低級的社會地位的身份標識。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崇尚勞動,倡導“勞動光榮”,不單發動鄉村群眾勞動,還組織黨政軍等各種人員參加勞動生產,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勞動景象。面對這樣的情形,高崗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代表大會與生產展覽會開幕典禮上自豪地說:“在我們這里,革命以前勞動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現在他們也受到了無上的尊重。但是就我們全中國來說,除了我們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外,別的地方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16]對此,美國記者M.武道寫道:“每一個人——士兵、黨的負責人、學生、工廠工人,都參加生產運動。在他們正規的職務之外,他們同時種榖物和蔬菜,做木工,紡紗,捻毛線,織毛衣毛襪,釀蜜糖或者制造醬油。”[17]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也說:“給人的感覺是每個人都有工作干。使每個人都成為生產者的計劃具有實際意義。不種田的人,就干如紡線之類的活計。”[18]因而,大生產運動不僅“教育與鍛煉了許多干部”,還使群眾“獲得實際的經濟利益,提高了生產的熱忱,認識了中共的領導究竟是不同的”[19]。
自給的經濟能力的提升不僅要開源,還要節流,而精兵簡政就是抗日根據地厲行節流的一項重大舉措。簡而言之,“精兵”主要是對正規部隊進行整編,將老弱人員轉移到生產中,加強士兵的政治軍事訓練,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同時增強非正規部隊的武裝力量,而“簡政”主要是縮編政府人員,精簡機關,提高行政效率[3]2。精兵簡政的全部意義在于“統一,少而精,提高效率”[20]。比如,陜甘寧邊區的內部機構裁并了1/4,35個直屬機關減至22個,95個稅局、稅所減至65個,撤銷了全部銀行辦事處,各系統緝私機關與保安處檢查機關合并在一起,專署及縣府的內部機構也從8—9個減至4—5個。各級政府的人員精簡也按照方案落實,有的機關還缺人[21]。與此同時,正規部隊和非正規部隊也實施了精兵政策,提高了戰斗力。
至此,繼游泳之后,輪滑成為我院體育教學的又一大特色,2014年輪滑、游泳等選項課建設成為我院優質課程。除此之外,輪滑運動開設初期成立的輪滑社團的發展壯大也是輪滑教學成果體現,輪滑社會員長期保持在100人左右,每周活動不少于兩次,活躍于校園角角落落的輪滑愛好者已然成為學校體育文化代表符號。
在困苦的環境中抗日根據地不斷地提升自我供給的經濟能力,既保障了軍用民食,又積蓄了戰斗力量。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并不是過度消耗民力,依賴民力,而是與民同甘共苦,始終以減輕群眾負擔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展現了一心為民的政黨本質,誠如岳謙厚所言:“在抗戰最困難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利益為先的信念堅如磐石。”[22]源于此,中國共產黨收獲的政治認同越來越多,展現出與眾不同的政黨自信。
三、高尚的文娛
一個堅韌又有活力的社會秩序往往建立在一種主流價值觀念上。在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治和自給經濟搭建了一種嶄新的社會秩序,可是要保持這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就必須得建立起與之相匹配的主流價值觀念。較于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的推行,主流價值觀念的塑造絕非易事。因為傳統價值觀念仍在鄉村社會根深蒂固,抗拒著任何外來的價值觀念,在這種狀況下,抗日根據地的前途取決于中國共產黨能否重新塑造鄉村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而這一切的首要在于找尋能夠與鄉村群眾進行價值觀念交流的有效渠道。
由于生活窘迫,大多數鄉村群眾是遠離正規的國民教育的,他們的價值觀念取向更多的來自與他們生活密切相關的秧歌、戲劇等民間文娛。民間文娛就成為重塑鄉村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一條理想渠道。對此渠道,中國共產黨一向重視。美國記者海倫·斯諾說:“中國人最喜愛戲曲,現在仍然如此。演戲從一開始就對共產黨革命起了重要作用,這不僅是為了宣傳,也是通過娛樂贏得民眾。”[23]但是傳統的民間娛樂集中表達的是舊統治秩序下的價值觀念,與抗日根據地的要求相差甚遠。比如,傳統戲劇“敘事主題多是宣傳封建禮教或忠義觀念,政治語境多是‘帝王將相’或‘才子佳人’,完全服務于舊統治政權,歌頌的是一種帝王秩序下的倫理文化,頌揚的是一種符合舊政權的歷史觀。”[24]傳統秧歌“純粹是一種民間娛樂,內容大致有兩種:一種是諷刺的,諷刺官僚士紳,以發泄民間的苦悶;一種是娛樂的,多半為男女的調情”[25]。可見,抗日根據地倘要借助民間文娛構建主流價值觀念,就必須得進行改造,使其實現從“落后”到“高尚”形態的轉變。
現在來看,民間文娛“高尚”形態的形成,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造重心在于采用舊有娛樂形式表現符合根據地現實的新內容,即“舊瓶新酒”,這種改造既改變了原有的娛樂內容,又抓住了民間娛樂的形態核心和娛樂本質,展現出新姿態。對于這種新姿態,英國記者斯坦因描述道:在每一個新秧歌里,主角發生變化,“工農兵”是舞臺主角,惡徒“是日本兵、漢奸、巫師、二流子,或者是妨害作戰努力、妨害增加生產、妨害政治經濟進步的其他反社會分子”,英雄“是八路軍、民兵,或者是階級協調互助的先驅,反迷信、反文盲、反疾病的戰士,或者是鄉村、工廠、合作社、政府機關的模范工作者”[26]。第二個階段,改造重心在于完全采用群眾的日常言行表達抗日根據地的現實生活,即“新瓶新酒”,這種改造突出抗日根據地中鄉村群眾的地位和作用,倡導“自編自演”式的集體娛樂,不再限于表演者和圍觀者之間的互動,而是突破時空限制,模糊表演者和圍觀者之間的界限,讓文娛演出化為集體狂歡,從而產生更大的教育意義。
經過改造的民間文娛體現了符合抗日根據地要求的價值觀念,傳遞的是“應當怎樣”和“不應當怎樣”的言行規范。當看到熟悉的語言、人物、事例和生活被搬上舞臺時,鄉村群眾很容易把劇中情節與自身現實生活聯系起來,產生思想情感上的共鳴,實現個人價值觀念的轉換。比如,興縣楊家坡群眾表演了《劉成龍誣告》的秧歌劇,大致劇情是劉成龍利用一個二流子誣告村主任,最后在村主任、民兵、群眾的共同說服下,二流子轉變立場,開始揭露、批判劉成龍。在觀看表演時,大多數群眾被陣線分明的場面、二流子改悔、村主任檢討、群眾覺醒等情節感染[27]。對此,美國記者福爾曼也深有感受:“它們永不使我不被迷惑。它們與在中國各地所能看到的東西完全不同。他們大多數采取戰爭的題材:一個鄉村奸細的故事,一個兵士妻子的英雄行為,日本人在俘虜營中殘忍行為。這很需要一番努力使我能夠慣于傾聽詩句,但是戲劇的表演技巧一剎那就可以把我抓住。”[15]92
抗日根據地借助民間文娛構筑了培養主流價值觀念的輿論網絡,其最大意義在于為抗日根據地提供了精神支撐。20世紀上半葉各種政治力量都試圖向鄉村社會滲透,只有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持久的控制力,究其緣由,其關鍵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走進群眾心靈的思想教育渠道,進而在鄉村社會塑造起來符合自身需求的價值觀念。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塑造主流價值觀念的時候,并不是采用暴力手段鏟除舊觀念,強力推行新觀念,或者另起爐灶,而是在舊有價值觀念之上順勢介入新觀念,根據斗爭形勢適時地改造、調整和替換,始終注意將鄉村群眾由被動的接受者轉化為主動的宣教者,使其在現實生活中感知、接觸和理解新觀念,最終樹立起為新社會奮斗的信心,這又是抗日根據地一項獨特的“政治優勢”。
四、結 語
在敵后,抗日根據地時刻面臨著難以想象的困境。以解決困境為核心,抗日根據地逐漸表現出特有的氣質:民主的政治不僅在于團結了各階層的抗日力量,更在于喚醒了鄉村群眾的政治意識,激發了他們支持或參與政治的熱情;自給的經濟不僅在于提供了黨政軍民的日常生活消耗,更在于激發了鄉村社會的生產能量,儲備了開展游擊戰以及進行戰略反攻的物質基礎;高尚的文娛不僅在于活躍了鄉村社會的生活氣氛,更在于傳遞了抗日救國的政治信念,塑造了擁護共產黨八路軍和保衛抗日根據地的價值觀念。重要的是,這些特質并非孤立存在,民主政治提供了權利保障,自給經濟提供了物質基礎,文化娛樂提供了價值觀念,它們共同構建起來一個嶄新的社會新秩序。借助這些特質,抗日根據地緩解或解決了生存和發展的難題,支撐了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抗日前線的軍事行動,展現了不同于其他區域的整體面貌和精神狀態。確實如此,在慘烈的戰爭環境中,殘暴和失敗帶來的沮喪情緒無所不在,抗日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的最大意義就是給予了中國民眾一種定會徹底驅趕走外來侵略者的希望,這是其他政治力量無法與之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