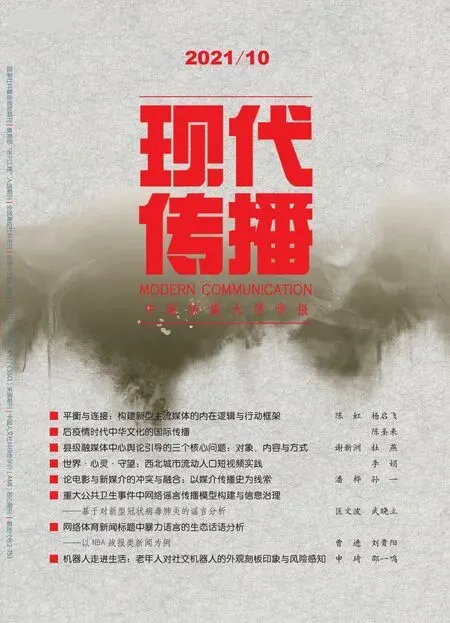賦權·賦能·賦意:平臺化社會時代國際傳播的三重進路
■ 李 鯉
一、研究緣起:以平臺為中樞的國際傳播
當前,以大型互聯網平臺如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等為主導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通過數據搜集、算法驅動、智能運轉等數字化方式,正在全面重構國際傳播的整體格局。國際傳播進入依賴平臺運行的平臺化時代。①按照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的界定,平臺化社會(platform society)是指“社會、經濟和個人之間的溝通很大程度上依靠線上的平臺生態進行規劃”②。在此,平臺不僅指向了“物質性的技術實踐”,還包括“與之相關聯的制度安排、知識形構、意義生產、利益競爭以及價值維系”③等各個方面。這一充斥著互聯網公司、政府機構、技術組織、新聞媒體等多元主體制衡,以及技術、資本和政治等多樣話語博弈的平臺生態,為全球化的信息交往方式、傳播秩序建設與文化身份想象設定了全新的語境。
中國國際傳播的轉型升級戰略有待對接全球數字平臺的內在邏輯,以“平臺”作為全新的戰略意識,在整體觀的視域下思考數字化國際傳播的實踐進路。一方面,平臺本身的屬性決定了國際傳播的主體關系、權力結構與話語方式。平臺推動的全球信息流動的底層邏輯可以大體概括為技術賦權的“可見性”(visibility)邏輯和算法驅動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邏輯。其發展由大數據技術支撐、為所有主體賦權,擴大了信息在世界范圍內的可見程度。同時平臺又受到全球資本規制和政治行動者的影響,信息的傳播過程處于新的不可見“算法黑箱”之中。另一方面,平臺作為一種新的全球社會結構,如何避免技術權威、市場理性和信息地緣政治成為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新手段④,中國國際傳播的數字化轉型需要借助人類社會建構與文明發展的價值邏輯,參與全球數字平臺建設和治理話語建構,以“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打造新的全球共識。
全球數字平臺為系統考察國際傳播的技術動因、信息流動、制度安排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視角。這一視角既體現了國際傳播研究的主體性,也為國際傳播研究與其他領域的研究對話拓展了新的邊界。本文透過平臺賦權、賦能、賦意的內在機制,探討平臺化社會中國國際傳播的主體特征、價值空間和敘事轉型,歸結中國國際傳播的現實進路,回應如何借助數字平臺“講好中國故事,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這一時代命題。
二、賦權個體:基于社交融入的全民外交
賦權一般指個體通過對話、傳播而獲得的自我效能感或彼此的認同感。⑤平臺為多元主體的言說提供“支持性傳播”的外部推動力量,為搭建人人參與的交流、傳播和對話賦予了可能。由此推動國際傳播走向“普遍交往”的社會化語境,構造出基于“社交融入”的全民外交(total diplomacy)新特征。
(一)從“多元主體”到“人人參與”
平臺生態可以概括為一種建立在通信技術和連接規則基礎上的網絡通用服務,包括三個基本的傳播層次⑥:一是提供傳播的技術基礎架構,如信息傳輸系統和傳輸規制;二是提供傳播的基礎功能架構,諸如Google、百度、Facebook、阿里巴巴等資訊、社交、服務平臺;三是提供傳播的價值變現架構,如對接生產貿易、經濟發展、新聞媒體等行業的具體應用服務。在此,任何符合底線邏輯的個體都可以免費入場,并依照個體意愿與他者進行交往、交換,普通個體的角色在整個國際傳播鏈條中得以凸顯。
首先,平臺為個體賦權。以往,機構媒體作為國際傳播的主角,以信息(information)作為主要內容進行生產與傳播。平臺化社會,搭建平臺的數字公司,將來自個人、企業、媒體、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海量數據(data) 作為基本原料,通過后臺算法生成信息并整合分發,活躍在平臺上的多元傳播者成為國際傳播的主角。在平臺強大的賦權作用下,那些在大眾傳播時代被邊緣化的非國家行為體尤其是普通個體,主動尋求信息并自由表達思想,成為擁有傳播權利(right to communication)的主體。截至2021年6月,TikTok 全球月活躍用戶達8億之多,有研究通過觀測一個月內 TikTok 用戶的行為,發現 68%的TikTok 用戶觀看了別人的視頻,而55%的人上傳了自己的視頻。⑦
其次,人人參與的節點式傳播。一般而言,國際傳播的主體先在平臺上發布一次信息,然后平臺將聚合而來的信息通過算法推薦給感興趣的用戶,用戶作為重要“節點”參與平臺二次傳播的把關過程。⑧雖然不同平臺的算法推薦規則有所差異,但用戶普遍認為,“基于歷史消費行為的算法是比人工編輯更好的新聞推薦方式”⑨。可以說,平臺賦權于個體,包括信息傳播者的顯性參與和接受者的隱性參與這兩個維度,從而將國際傳播中人、信息、物的關系拓展深化為人與人的關系,傳受雙方形成一種“互為主客體的、對話性的主體間性人際關系”⑩,形成了以個人為中心的節點式傳播。
最后,以個體化、個性化為主導的傳播結構。在平臺的作用下,以個人為基礎的表達和參與顯著上升,國際傳播成為多元傳播主客體建構關系、獲取資源和象征資本的重要渠道。在2019—2020年度全球網絡平臺有關中國主題的國際傳播力評估中,多位“網紅”如李子柒、小馬在紐約、Jabiertzo、滇西小哥等位列前茅。這些傳播者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但不論是對中國民俗生態的個性化展演,還是對“我拍故我在”的中國“全域旅游”展示,都在形構一種基于個性化傳受需求的連接關系網絡,即一種更加微觀的跨國人際傳播生態。
(二)從“圈層傳播”到“社交融入”
廣義來講,圈層指“基于多種緣由的社會成員通過互聯網媒介平臺集聚與互動,所建立并維系的一個社會關系網絡”。在去中心化的規則下,全球數字平臺中個人對組織機構的依賴減弱,基于人際傳播形成的圈層網絡成為國際公眾獲取資源與匯聚價值的中介場域。
一方面,平臺通過同類聚集的方式分發信息,構筑用戶標簽明確的“信息圈層”。雖然目前全球大型數字平臺公司尚未按照國別差異設計算法推薦規則,但“信息找人”的流量邏輯使平臺孕育的每一個信息群落,都深受其國家背景和文化習慣的影響。在國際傳播的實際過程中,世界不同國家(地區)或同一國家(地區)的不同群體,對中國信息的認知、理解與需求都有所差異。因此,要基于平臺用戶的標簽屬性,精準把握不同國家、地區用戶的信息依賴路徑,打造具有垂直屬性和社區特性的賬號資源;同時推動我國媒體平臺和企業平臺出海落地,加強與海外用戶的信息互通、商品聯動和生活互動。以此嵌入國際平臺用戶的信息圈、生活圈和社交圈,觸及用戶的生活需求、文化訴求甚至情感渴求,提升中國信息傳播的觸達率。
另一方面,民間創作者通過打造個人品牌、建立社交化信息群集,形構更深層次的“社交圈層”。社交圈層具有“傳播內容接入過程簡化,價值和觀念涵化,情緒感染加快和行動模仿”等特點,有助于國際傳播打破固有的文化區隔,實現“個體認同聯結”轉化為“共識認同交往”。有研究顯示,當前國際信息流動出現的重要轉向之一是“平臺用戶對于機構媒體的辨識度和信任度走低,精英和名流的話語權被來自基層草根階層的 KOL(關鍵意見領袖)瓜分和蠶食”。這提示我們,構建國際傳播平臺生態的重要路徑之一,是培育具有個性特征和人格魅力的文化領袖、意見領袖,建立和維系以“關鍵領袖”為核心的互動圈層傳播,并借助優質內容和交往分享機制增強傳播節點間的關系黏度,形成基于圈層的情感共識和意見共識,在新型“平臺公共領域”參與國際對話與交流。
德國學者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正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往才構成了現實的社會”。在全球數字平臺這一巨大的虛擬現實社會中,通過具有普遍交往性的圈層關系,實現了人與人在世界范圍內的連接,它超越了傳統媒體時代國際傳播中等級森嚴的“中心—邊緣格局”,將人的行為與生活引入國際交往與關系構建之中。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際傳播被視作一種融入日常生活的交往實踐,其“創構的傳播圖景已經成為個體跨文化融入過程中不能忽視的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羅伯特·福特納(Robert S.Fortner)所提出的“人是國際傳播中除國家外的另一個中心”,即以“人”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為中心的人本主義國際傳播方法論變革。
三、賦能數據:邁向數字治理的行動集合
平臺化時代,數據成為國際傳播乃至全球社會運行最重要的驅動力量。從國家行動的基礎語境來講,我國國際傳播既要搭建平臺、賦能數據,又要規制平臺、善用數據,在邁向全球數字治理的整體語境中,形構政府和民間多元行動者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能力。
(一)從“數字之物”到“數據之爭”
在國際傳播進入數字物理空間的當下,作為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平臺本身具有物質性的特征,同時又在普通用戶中保持著最大程度的“透明性”(transparency)。何謂透明性?即數字平臺構成了國際公眾的棲居環境,人們不再感受到它的存在。在平臺傳播日趨智能化的當下,平臺上的國際傳播活動幾乎等同于數據的流動。作為按一定規則排列組合的物理符號,“跨境數據的交換與融合以網絡化、動態和實時的方式發生,在發送方或接收方渾然不覺的情況下跨越許多邊界”。諸如谷歌、蘋果、微軟等具有壟斷性的科技巨頭公司掌握著大量關于用戶行為的數據,通過搭建具有高度整合和分發能力的數字平臺,將全球范圍內的個體溝通行為、信息路徑和日常生活全部納入國際傳播的網絡之中。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國際傳播如何賦能數據?簡言之,即通過平臺建設提升數據跨國流動的速度、廣度、深度,提升國際信息傳播的可見性。一般而言,平臺建設大體涵蓋提供設備和網絡支持的物理層、負責硬件運行的代碼層以及包括圖文、視頻等可見信息的內容層。物理層如我國主導的“一帶一路信息高速路”等互聯網互通工程,致力于消弭不同文明之間的數字鴻溝,以此促進國際社會結構的整體聯結。代碼層則是由數據、算法和協議共構的交互界面,它通過算法機制控制著用戶唯一可見的內容層。算法傳播范式“賦予了主權國家以更大的權力實施信息傳播,算法技術強國在國際傳播中能夠置身于由中心觀察四周的全景敞視空間,從而繼續主導信息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國際傳播接下來的著力點將在于一方面繼續推進海外互聯網互聯互通市場的整體布局,另一方面重點孵化一批基于大數據和算法、更具內容吸引力和粘附力的軟件平臺,以主動策展的方式參與國際數據話語權的競爭。比如先后在泰國、印尼、越南等地落地的騰訊視頻海外版 WeTV的國劇節目就受到了較大關注。
(二)從“地緣政治”到“技術政治”
有關全球數字平臺的地緣政治博弈,范·迪克認為目前主要表現為世界上兩大平臺系統,即以美國商業模式主導的“五大互聯網巨頭”(臉書、蘋果、亞馬遜、微軟、谷歌)和中國國家模式主導的“五大互聯網公司”(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網易)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潛在矛盾。美國政府和企業憑借其強大的技術優勢和商業實力,占據全球數字平臺的主導地位,獲得針對其他國家的數據威懾優勢。與以往的跨國媒體和互聯網全球治理不同的是,這些占據壟斷地位的巨型平臺“已經成為跨境的政治行為參與者,政治與技術之間的距離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諸如新冠疫情以來Facebook和YouTube屢次將中國官方媒體的視頻內容貼上“虛假信息”的標簽,Twitter則將中國和俄羅斯的官方媒體標注為“國家附屬媒體”,置相關信息于算法推薦規則之外。有研究分析了美國、俄羅斯、烏克蘭等數十個國家社交媒體中的政治信息,指出了后臺數據和智能推送無所不在的操控行為。可以說,新技術在塑造新權力的同時也在顛覆原有權力的平衡,“大國圍繞技術權力的戰略競爭日益超越傳統地緣政治體系”,將國際傳播從“地緣政治時代”推向“技術政治時代”。
技術政治(techno-politics)一般涉及政治與技術兩個層面,就國際傳播而言,“一方面是通過主要大國之間的斗爭,另一方面則是治理與技術應用之間的沖突”。2020年8月,特朗普政府就曾以國家數據安全為由對TikTok 提出質疑,要求擁有1億多美國本土用戶的 TikTok出售或剝離在美業務。拜登政府進一步制定了以“數字現實政治”為基礎的國家戰略,在“技術多邊主義”框架下布局構建技術聯盟,對中國科技發展和應用進行輿論攻擊。面對美國主導的全球技術政治新格局,作為國家行為體的中國需要從被動反應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一是持續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全球公共服務性的數字平臺,分區域、分主體支持平臺企業通過市場化機制出海,對抗數據霸權;二是伸張基于全球互聯互通的網絡正義觀,協同國家政府、國際組織、平臺企業以及個人行動者,把握“共享發展”的主線,堅持以多利益攸關方為基礎的數字技術治理,推動全球平臺傳播規范的對接和跨境數據流動規制的建立。需要指出的是,參與全球數字平臺治理是一個漸進式的博弈過程,既需要關注美國系統的全球性進路,還要統籌歐、亞、非洲等國家市場的力量,避免陷入數字威權主義的“威脅論”話語陷阱。
四、賦意話語:講述全球故事的集成敘事
全球數字平臺為中國故事提供了智能化敘事的基礎語境,“個體作為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的具身,與平臺、算法、機器等非人類主體共同構筑了跨文化敘事的故事景觀”。“中國故事”在多元主體的協同敘事中全面打開,發展成為一種智能集成、多媒共生的“全球故事”。
(一)從“人機協同”到“智能集成”
如前所述,平臺化社會激活了個體敘事者,極大地釋放了中國故事的創作動能。與此同時,技術推動智能機器不斷突破工具屬性,與多樣化的個體具身彼此互嵌,重構故事的敘事方式。首先,機器通過模仿人類創作者的思維方式、審美取向和創作技巧,借助數據接入、語料分析、語圖識別等方法,實現故事的主題編創、情節構造和內容創作。目前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文案已通過圖靈測試,機器敘事產品Quik能夠“解釋、放大和闡述重大事件及其內在的價值”,微軟“小冰”則在詩集中發出了諸如“人生之苦”的情緒化感嘆。從算法、認知到感知,機器介入故事創作的程度不斷加深。其次,機器與用戶協同進行故事再生產,如騰訊游戲推出的“王者榮耀”海外版,通過傳感器實時捕捉用戶數據,動態調整游戲場景、角色設計和情節鋪設,面向全球用戶的iQIYI App透過更加細微的用戶行為分析進行定制化的內容生產與分發。這一建立在“規模數據+多模態算法”上的人機協同敘事,不僅包括了平臺數據運行、智能算法等技術架構,也包括了指令呈現者的表達意圖、用戶使用情境等人的理性與感性因素,共同推動著中國故事走向人機協同、智能共創的創作語境。
在這一語境中,智能機器(物)不斷與用戶(人)進行故事意義的交互,來自不同文化基模的主體共同參與敘事,中國故事表現出開放式、集成化的敘事特征。首先平臺數據驅動多元化和智能化的故事內容創作,接著這些故事又以算法推薦、評論點贊等數據流的形式在平臺節點之間流轉,不斷產生的數據流為新的故事創作提供了可供循環利用的資源。每一個關系節點都在與更大的媒介環境、文化語境和社會情境進行交流,故事被視為一種沒有邊界和終點的意義流動。易言之,走向全球的中國故事有待于在與全球媒介平臺、各國政府組織、跨國公司行為體以及更為廣泛的平臺用戶、算法、機器交互集成的過程中,共同生產一個不斷生成的、關于全球—中國的連貫性敘事。中國故事釋放的議題與文本也應愈發表現為一種與全球文化、社會以及政治經濟關系之間的呼應關系,其中“不僅包含了如何反映中國文化本身的‘走出去’姿態,而且在于重新看待中國與全球化流動、與全球治理體系相互耦合的進程”。
(二)從“萬物互聯”到“多媒共生”
從中國故事到全球故事,通過“連接”組成的關系網絡進一步凸顯了平臺賦意的話語效用。在這一萬物互聯、無限延伸的行動者網絡之中,現實權力關系與資本邏輯不可避免地滲透其間,中國故事的講述始終伴隨不同層級敘事者的話語博弈過程,那些具有更多意義觸點的故事將受到更多關注。如何在故事的流動中捕捉共通的意義?故事“共通性”的構建,在于“構建共同的場景、尋求情感共鳴、分享共同的意義”。
其一,借由數字媒介形構多樣化在場的故事,構筑與千里之外的他者和諧共處的場景。5G網絡、AI機器人、虛擬現實技術等突破了實體地理空間與虛擬網絡空間的屏障,智能語音和聊天機器人的伴隨性敘事,使中國故事在海外用戶的生活空間落地,打造融入日常的“信任場景”。此外,借由可穿戴設備和擬像化的全息場景建構虛擬的“共在空間”,中國故事“不再只被視為視覺化的象征物體和表征系統,而是習慣下展演和實踐的體現”。如在全球知名游戲發行平臺Steam上線的社交游戲VRChat,就打造了一個全球用戶共同參與敘事的虛擬場景。虛擬化身置身其間的房屋設計、空間裝置和服飾展演,都成為凸顯本民族文化故事的在場表達,故事的意義也在人與場景的互動之中重新生成。
其二,依托感官媒介生產,打造全息化的體驗故事。技術推動平臺媒體進一步朝向視頻化、影像化的方向發展,人類正面臨一場感性認知的革命。有研究者通過分析傳感器用戶的身體經驗、情境氛圍等不同維度,探索技術化身如何拓展體驗式認知的邊界,發現那些“發生在身體邊界斷裂或融合狀態的瞬間感知……如使用鼠標的酸痛感、模擬射擊游戲手柄的后坐力,往往會帶來在體驗中的思考行為”。這提示我們,媒介語法和技術邏輯顛覆了傳統的故事生產思維,也推動著平臺社會故事敘事要素的重構,中國故事的跨文化敘事有待營造出更加細致入微的感官互動體驗,并在此過程中與參與者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發生關聯。
平臺算法、智能機器、虛擬現實等對中國故事敘事的滲透,從表層來看,是平臺化社會內容生產與分發的技術革命,就深層而言,是人與物、人與信息、人與人之間話語關系的重構。這提示中國故事的意義創作需要平衡各方力量的博弈,一是借技術之勢,將中國價值融入全球共享的意義空間;二是防技術之險,警惕陷入技術烏托邦的美好幻想;三是共人文之情,以“人”的價值為本位促進交流共享。
五、結語
全球數字平臺重構國際傳播的信息格局,其內在生成機制是通過平臺賦權,形構人人參與、以“人”為中心的全民外交;賦權背后的實際作用力量是數據的爭奪與治理,通過賦能數據重塑全球信息流動中的國際話語權;話語同時又與敘事流通過程中的傳播效果息息相關,中國故事有待發展成為一種智能化、集成化的賦意實踐,走向全球—中國的整體語境。平臺賦權、賦能、賦意這三個層次之間形成了彼此關聯、相互支撐的邏輯關系,牽引著平臺化社會國際傳播主體特征、價值空間和敘事方式的變革。但也正如有學者所言,任何技術革命都會導致我們必須預料的新的不平衡,包括媒介技術的可得性、平臺背后的科技巨頭公司和政府力量的滲透,以及不可忽視的語言和跨文化交往的障礙。如何從國家行動者整體性統籌、社會行動者差異化應對以及個體行動者多維度參與等層面主動布局,在邁向全球數字互聯的整體語境中,以“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話語打造全球共識?平臺化時代的國際傳播研究尚需更多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支撐。
注釋:
① David B.Nieborg,Thomas Poell.ThePlatformizationofCulturalProduction:TheorizingtheContingentCulturalCommodity.New Media & Society,vol.20,no.11,2018.pp.4275-4292.
② José van Dijck,Thomas Poell,Martijn de Waal.ThePlatformSocietyasaContestedConcept.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https://www.oxfordscholarship.com/view/10.1093/oso/9780190889760.001.0001/oso-9780190889760-chapter-2 retrieved on January 2,2020.
③ Parks L.Water,Energy,AccessMaterializingtheInternetinRuralZambia.In Parks L.& Starosielski N.(eds).SignalTraffic:CriticalStudiesofMediaInfrastructures.Illinoi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5.pp.5-13.
④ Nick Srnicek.PlatformCapitalism.Hoboken:John Wiley &Sons.2017.pp.8-13.
⑤ Rogers E.M,Singhal A.EmpowermentandCommunication:LessonsLearnedfromOrganizingforSocialChange.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vol.27,no.1,2003.pp.67-85.
⑥ 喻國明:《新型主流媒體:不做平臺型媒體做什么?——關于媒體融合實踐中一個頂級問題的探討》,《編輯之友》,2021年第5期,第6頁。
⑦ 《您可能需要了解的10個TikTok信息》,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 /411943559_115514,2020年8月7日。
⑧ 沈國麟:《全球平臺傳播:分發、把關和規制》,《現代傳播》,2021年第1期,第9頁。
⑨ N.Thurman,J.Moeller,N.Helberger,D.Trilling.MyFriends,Editors,Algorithms,andI:ExaminingAudienceAttitudestoNewsSelection.Digital Journalism,vol.7,no.4,2019.pp.447-469.
⑩ 李智、劉萌雪:《新媒體時代國際傳播的社會化轉型》,《對外傳播》,2019年第12期,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