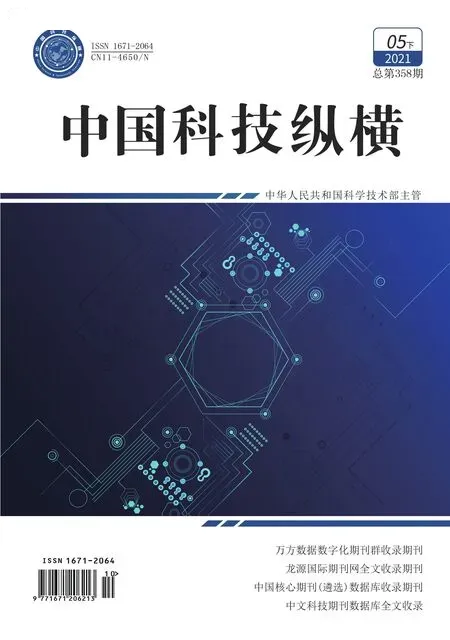盤活創新要素資源,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郭曉莉
(中國專利信息中心,北京 102200)
高校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科技成果的重要供給側。2020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教育部、科技部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等部委也密集出臺了多項政策以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從《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20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來看,2019年3450家高校院所以轉讓、許可等方式轉讓科技成果的合同項數有所增長[1]。雖然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取得了一些積極進展,但和發達國家相比,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仍較低,需要從體制機制和要素資源方面進行調整和盤活,以加快供給側改革,促進科技創新發展。
1.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現狀與分析
1.1 高校專利質量不高
近年來,高校專利申請量穩步增長,但存在“重數量、輕質量”“重申請、輕實施”的問題,維持在6年以上的發明專利不到30%,實用新型專利普遍維持時間只有2到3年[2]。高校專利數量多、質量差的問題應與職稱評定和專利資助政策關系較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知識產權工作正在從追求數量向提高質量轉變。”為提升高校專利質量,加強專利運用效益,2020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部關于提升高等院校專利質量促進轉化運用的若干意見》,明確了四項重點任務和組織實施的機制建設,《意見》集中體現了回歸專利政策制定初心,提高專利源頭質量,完善高校科研成果運用和管理的政策意圖。
1.2 產權和分配體制有待改進
高校科研成果多數是使用國家財政性資金完成的項目成果。高校作為事業單位,其科研成果一直作為無形財產管理,對應監管政策較為嚴格,因為科研資金來源于財政性資金,高校一直面臨著審計和巡視等監管要求,而科技成果轉移本身就帶有較強的不確定性。國有資產流失風險的責任讓高校對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有所顧慮。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出臺的各項政策都明顯傾斜獎勵發明人,對發明人的獎勵力度普遍在50%以上甚至達到70%,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涉及發明人、高校、企業等多個環節,需要統籌平衡轉化鏈上各主體的動力、權力、責任和義務關系,高校和院系在目前的分配體系下在科技成果轉化的責權利方面存在一些不平衡現象。
1.3 缺乏科研成果轉化資金支持
科研成果轉化存在復雜性,具有技術不成熟、市場需求不確定的風險。企業不愿承擔新技術開發所需的高額資金和風險,傾向于追求快速變現、低成本高收益的項目。基礎研究與市場所需要的產品開發之間存在的鴻溝被比喻為“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這個“死亡之谷”造成了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斷裂帶”,成為制約大學技術成果應用于市場的一個攔路虎。在對美國技術轉移成功經驗的研究中發現,許多大學都有種子資金、孵化資金等。此外,許多大學成立了“價值證明中心”(University Proof of Concept Centers,以下簡稱POCC),它是促進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一種創新組織。大學價值證明中心的成立,加速了大學技術商業化進程。在價值證明中心里專門設有價值證明基金,為處在“胚胎期”的技術的早期科技成果轉化提供資金支持,填補了實驗室初期技術到市場成熟應用技術之間的空白[4]。我國目前也正在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開展科技成果轉化貸款風險補償試點。
1.4 缺乏專業性較強的服務中介
科技成果轉化是專業性較強的復雜性工程,對比美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在拜杜法案頒布后,相繼成立的高校專業技術轉移機構OTT與技術經理人聯盟AUTM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而我國高校在專業技術轉移機構與人才方面較為匱乏,嚴重制約了科技成果轉化。據2019年科技成果轉化年報顯示,全國高校設立技術轉移機構的只有30.1%,已經建立的機構不同程度存在職能定位分散,服務水平低、人才儲備少等問題[3]。2016年中國高校技術轉移聯盟成立,但組織機制、服務功能建設還不完善,短時間內無法取得與 AUTM 相同的推動成效。2020年,科技部和教育部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高等院校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建設發展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其中明確了要建立技術轉移機構、明確成果轉化職能,建立專業化人員隊伍、完善機構運行機制等6方面任務[3]。
1.5 科技成果轉化流程不成熟
從國外大學的實踐經驗來看,很多大學早期就會介入項目選題和立項。美國大學OTT模式的運行流程為在科研人員有了新的科研技術后,科技成果轉化的第一步就是科研人員將其科研技術的有關信息披露給OTT,收到發明的信息披露后,OTT將會有專門的技術專員來負責跟進發明的一系列情況;在多方考慮之后對技術進行技術價值評估,評估技術的市場應用價值及潛在價值,然后決定是否申請專利,專利申請通過后便是技術的許可,最后是分配通過就技術許可所得到的現金收入[4]。在我國,目前還沒有一套較為成熟的高校科技成果轉移流程。
2.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創新要素和主要制約因素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涉及到技術要素、人才要素、資金要素、信息要素、服務因素等創新要素,制約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體制機制因素等。為促進創新要素市場化配置,加快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需要明晰科技成果產權、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合理安排激勵約束制度,補齊專業轉移機構和人才短板,充分保障對應資金支持,建設科技成果信息流通平臺,多項舉措并舉,才能盤活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的要素資源,提升科技全要素生產率。
3.思考及建議
2020年以來,科技部、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等相關部門密集出臺了多項政策,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可見對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重視。其中,多項舉措涉及提升高校專利質量、職務發明下放長期使用權、建設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實行專利許可發布等信息溝通機制來促進創新要素流動,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可見相關部門對科技成果轉化中存在的問題認識較為全面深刻,任務措施安排系統周全。通過文獻調研和政策追蹤,筆者認為還有以下幾點需要在后續政策安排中加以注意。
3.1 對高校和技術轉移機構要適當放權
我國高校屬于事業單位,對科技成果的管理和人事制度、考核評價、國有資產的管理方面行政化色彩濃厚,但沒有轉化落地的科技成果就是浪費,面對轉化鏈條復雜、價值評估困難、國有資產監管又嚴格的高校應針對性地采取靈活的政策,參看美國和日本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經驗來看,美國的高校對技術轉移機構的管理上充分授權,其財政和人事安排上完全自主,日本高校則在高校法人所有權制度改革后,高校科技成果才活躍起來。當然,在放權的同時,也應兼顧國家和公共利益,可采取對應的職務科技成果披露和國家介入權安排,從最近出臺的文件能看出,對此也有相應考慮。
3.2 合理安排創新主體激勵分配制度和對應約束機制
《拜杜法案》要求大學必須與發明人分享轉化收益,但沒有具體規定比例或者數額。按照美國相關數據統計,在總收益去除學校機構運行成本過后,大學、院系和發明人大概各占1/3。而我國中央及地方出臺的獎勵政策都非常傾斜發明人,對發明人的獎勵達到50%以上,高校是關鍵的創新主體,其推動力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中異常關鍵。Goldfarb和Henrekson的研究發現,即便給予發明人科技成果的100%權屬,其成果利用的實際作用依然遠不及《拜杜法案》的制度安排,原因在于大學積極性沒有得到調動[5],建議參考美國對高校科技成果的激勵分配政策,統籌考慮科技成果轉化鏈條上各關鍵主體的權責利對應問題,激發全鏈條各關鍵主體活力。
3.3 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促進創新要素流動
我國高校作為承接財政性資金承接科研項目的管理,對科技成果國有資產流失責任一直是選在管理者頭上的一把利劍;對科研人員的獎勵也一直有事業單位工資總額管理的約束,這些制度安排也是科技成果轉化的約束因素。建議財政部和人社部要從政策出臺激勵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角度考慮,統籌考慮相關制度安排。
3.4 加強立法水平,統籌協調出臺的法律法規
在美國以《拜杜法案》為支撐的技術轉移法律體系與中國以《科學技術進步法》牽頭的科技成果轉化法律體系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從科研機構區分、非營利機構區分、項目承擔人范圍劃分、技術成果界定、技術成果是否屬于公共科研的界定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別。美國的法律體系在主要方向、基本宗旨、指導思想的整體把握都比較明確,且會根據法律實施環境的變化不斷作出調整。而中國的法律體系發展程度遠不及美國,因此許多內容的范圍劃分并不具體,在部分重要條款中存在多種理解或解釋[6],各地方也出臺各自的地方法規,法律層面較為復雜。
3.5 加強理工人才培養,產學研結合應從大學生培養抓起
國外大學理工人才培養方案和國內差異巨大,寬進嚴出,更為偏重實踐與應用。發展科技創新產業,高校科研成果轉化需要大量熟悉政策、技術、產業、基礎知識扎實的理工背景人才,高校除了要重視科技成果轉化,也應從源頭抓起,優化理工人才培養方案,為科技事業發展提供大量的后備人才。
4.結語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國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和高校科研成果轉化工作,雖然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存在一些問題,但各部委近期也在密集出臺多項政策促進創新要素流動。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本就是復雜性較高的系統性工程,高校作為國家創新重要供給側,又有著作為事業單位的監管要求,在盤活創新資源要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放權,激發創新主體活力。相信隨著各項政策的出臺,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會邁上一個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