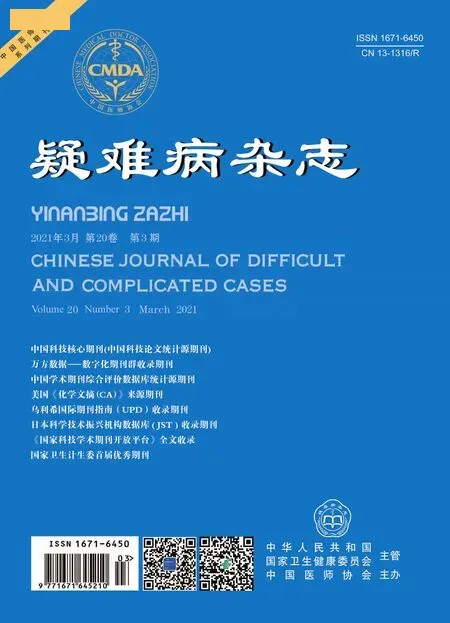氣道上皮細胞損傷修復在哮喘中的研究進展
金明珠,陳曉秋綜述 李鈺,曹志偉審校
哮喘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炎性反應性氣道疾病,全世界有超過3億人患有哮喘,發病率逐年上升[1]。哮喘的經典發病機制建立在氣道炎性反應的基礎上,過度的氣道炎性反應被認為是推動哮喘發生發展的主要病理生理過程。感染、變應原刺激是哮喘發作常見的誘因,哮喘病因非常復雜,是一種多因素疾病[2]。其中一種為“缺陷上皮”假說,即氣道上皮細胞損傷修復的缺陷是哮喘的病因之一。事實上,許多損傷因素亦是哮喘發作的誘因,而且哮喘患者氣道上皮已被證明有損傷存在,屏障完整性受損[3]。以上皮損傷和修復受損為特征的氣道重塑、網狀基底膜增厚、氣道平滑肌和杯狀細胞肥大、增生及血管生成可與氣道炎性反應并行發生。有研究認為氣道高反應性繼發于上皮損傷[4],這也進一步支持哮喘的缺陷上皮假說。盡管對哮喘的認識有所進展,目前尚無治療方法能改變疾病的自然病史和進展,關于氣道上皮細胞損傷修復的研究或許能對哮喘的治療開拓新的方向。
1 氣道上皮細胞的屏障作用及其損傷修復
氣道上皮細胞處于肺內環境與外界環境的交界,是呼吸道抵御外界刺激,如微生物、過敏原等的第一道防線,它維持著肺內各種生物學功能的動態平衡[5]。了解上皮細胞在內環境穩態和疾病病理學中的作用一直是醫學研究的熱點。
人類氣道有多種上皮細胞,根據細胞結構、生化和功能特性,主要分為3種,包括基底立方上皮細胞、柱狀纖毛上皮細胞和分泌型氣道上皮細胞,它們共同組成假復層黏膜上皮。基底細胞被認為是上皮細胞中的祖細胞,由其分化成分泌細胞和纖毛上皮細胞[6];傳導性氣道的大部分上皮細胞是假復層纖毛柱狀上皮細胞,來源于基底細胞或分泌上皮細胞,是它們的終末分化階段[7]。纖毛細胞的特征是其頂端表面多達300個的纖毛結構,細胞內大量的線粒體為纖毛擺動提供能量,這些纖毛以定向的方式,從肺部到喉部清除黏膜上的分泌物及異物;非纖毛上皮細胞,也稱為分泌細胞,包括杯狀細胞、漿液細胞、棒狀細胞及神經內分泌細胞。杯狀細胞主要存在于較大的傳導性氣道中,其特征是分泌黏蛋白顆粒,以捕獲氣道中的異物。漿液細胞雖與杯狀細胞形態相似,但缺乏黏蛋白糖。棒狀細胞主要產生表面活性劑和其他蛋白質成分。越來越多的新近證據表明,這些細胞發揮著重要的干細胞作用,即是纖毛細胞和黏液分泌細胞的祖細胞[7]。氣道上皮細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在損傷后以有效和協調的方式驅動上皮修復和恢復屏障的完整性。
作為對損傷的響應,氣道上皮必須迅速修復和再生,以恢復其完整性和功能,提供對外部環境的保護屏障及有效的氣體交換。細胞損傷修復過程的適當激活是恢復和維持上皮屏障功能的關鍵,這個過程包括初始炎性反應、細胞的遷移、增殖和分化、炎性反應的分解。這個復雜過程中的任何缺陷都會導致上皮細胞屏障功能的障礙和肺內組織的持續性損傷。傷口邊緣的分泌上皮細胞具有去分化能力,而纖毛細胞可以轉分化為鱗狀細胞以暫時覆蓋被剝落的區域。相鄰的基底細胞,稱為前緣細胞,能夠迅速擴散和遷移,使傷口再次上皮化,然后增殖和分化[8-9]。在動物模型中,受損基底膜的再上皮化初始過程主要是細胞遷移。盡管修復的初始階段同時涉及遷移和增殖,但傷口的大小似乎決定了哪個過程占主導地位。遷移可閉合小的損傷,而并不需要細胞增殖。較大的損傷則需要遷移和增殖共同修復[10]。作為修復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的細胞遷移由高度協調的活動組成,它們包括前緣突出、基底黏附、細胞體移位、與基底脫離和后緣收縮。這些修復過程一直持續到氣道上皮完全恢復完整屏障功能的假復層黏液纖毛上皮。
2 哮喘與氣道上皮細胞的關系
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的異常一直為人們所熟知,對于支氣管上皮的損傷如何導致哮喘患者的支氣管高反應性,已有各種理論。人們在哮喘患者的痰液標本中發現存在Creola小體、大量的脫落氣道上皮細胞,在支氣管活檢中也觀察到氣道上皮細胞的脫落。Creola小體是上皮細胞的碎片,上皮的脫落與碎裂被認為在哮喘發病中起重要作用。還有研究顯示,氣道的高反應性繼發于上皮損傷。上皮細胞功能缺陷是哮喘發生發展的重要因素。
2.1 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細胞修復功能變化 對于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細胞的損傷愈合能力,多數研究認為哮喘患者上皮細胞愈合能力明顯低于正常人[11]。研究證明,哮喘氣道上皮細胞具有較強的增殖能力,增殖細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PCNA)mRNA水平升高,但其修復功能失調[12]。另外,哮喘上皮細胞分泌更多的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PAI)-1、IL-1β、IL-10及IL-13,這些細胞因子在氣道上皮的增殖、分化和修復中起著關鍵作用[13]。哮喘上皮細胞顯示出更為低分化的表型,而且分化出更多的基底細胞和杯狀細胞,并有p63表達改變。哮喘患者細胞具有較低的跨上皮電阻(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TEER),細胞間緊密連接減少[14]。表明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細胞的屏障功能本身就低于正常人。
有學者認為氣道上皮是氣道炎性反應和重塑的整體調節因子[15],支氣管上皮的損傷可能在哮喘中產生重要的結構和功能影響,導致上皮表型改變,其特點是屏障功能不全、損傷修復不良、感染后缺乏先天免疫應答。有研究顯示,反復暴露于屋塵螨過敏原,會使氣道發生損傷和重塑[16]。氣道的重塑包括基底膜增厚、上皮下纖維化、血管生成增加和平滑肌細胞增生。其特征是上皮細胞增生,黏液分泌細胞數量增加,平滑肌肥大,血管生成增加,輔助型T淋巴細胞(T helper cell type 2, Th2)表型改變。這些特征都類似于人類持續性哮喘的情況。而氣道重塑的發生可能繼發于上皮損傷,是上皮修復障礙的結果。
2.2 哮喘炎性反應與氣道上皮細胞損傷的關系 哮喘患者的氣道上皮在損傷發生后,有多種細胞因子釋放,其中包括IL-13、IL-25、IL-33、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TSLP)等。它們可以激活2型天然淋巴細胞,促進Th2炎性反應[17-18]。但上皮細胞在損傷發生后的細胞因子分泌尚有爭議。
有研究發現,不同表型和基因型的哮喘患者對吸入或口服皮質類固醇等抗炎治療反應各異,其中一些患者不伴有氣道嗜酸性粒細胞炎性反應,而以嗜中性粒細胞炎性反應為主[19]。針對此類患者,用抗IL-5單克隆抗體(美波利珠單抗)或T細胞導向療法(可改善嗜酸性粒細胞炎性反應)治療后,癥狀控制不佳[20]。值得注意的是,在沒有特應性炎性反應或嚴重氣道炎性反應的情況下,結構改變本身也與哮喘患者呼吸道癥狀和氣道生理功能異常有關[21]。以上皮損傷和修復受損為特征的氣道重塑、網狀基底膜增厚、氣道平滑肌和杯狀細胞肥大、增生和血管生成不一定是繼發于氣道炎性反應,而可能與氣道炎性反應并行發生。因此,哮喘患者潛在的上皮功能缺陷可能使其氣道易于發生損傷、炎性反應、氣道重塑及哮喘癥狀的持續。
2.3 哮喘Th2型炎性反應與氣道上皮細胞損傷修復 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細胞較正常人損傷修復能力差,目前已有多項關于Th2型炎性反應的研究[22],但對于Th2型炎性反應中各種重要的細胞因子對上皮細胞損傷修復的作用,尚有爭議[23]。人們通過小鼠模型描述了Th1、Th2型炎性反應在免疫應答中的作用。結果顯示,在過敏性哮喘模型中,炎性反應以Th2型反應為主[17]。用皮質類固醇及靶向Th2通路組分的分子,如抗IgE、IL-4和IL-13治療,證實了Th2型炎性反應與過敏性哮喘之間的關系[18]。
在Th2型炎性反應與上皮細胞損傷修復關系的實驗中,IL-13頗受關注。已知IL-13能上調與氣道上皮重塑相關蛋白的表達,其中包括periostin和表面蛋白D[24]。雖然IL-13會參與一系列與哮喘相關的炎性反應,但對上皮細胞屏障功能的作用尚存在矛盾。有學者認為IL-13對損傷修復起促進作用,也有實驗顯示IL-13會破壞上皮細胞的屏障功能,并降低細胞損傷修復能力[23,25]。還有研究認為,IL-13似乎具有雙重作用:低水平的IL-13將有利于BEC遷移和傷口愈合,而高水平IL-13可能降低細胞損傷修復[26]。
3 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細胞損傷修復的模型研究
許多體外和體內模型已被開發用于研究慢性氣道疾病,拓寬對生理和病理狀態的理解,以及發現新的治療藥物。然而,體內動物模型往往由于缺乏人體疾病如哮喘的解剖學或遺傳學基礎,并有顯著的種間差異,而難以與人類生物學聯系起來。例如動物模型缺乏人肺呼吸細支氣管中基底細胞的單純立方體上皮[27]。在小鼠中,含有基底祖細胞的假復層上皮主要局限于小鼠氣管,而在主支氣管中沒有基底細胞向柱狀上皮的過渡[27]。在人類哮喘的情況下,由于疾病的異質性和對疾病發病機制的有限知識,研究氣道疾病中主要細胞類型的復雜相互作用十分困難,確定它們在發病和疾病發展中的作用頗具挑戰,而目前尚沒有完整的人類患者替代模型。鑒于實驗過程中無法在人體支氣管內行任何形式的損傷,為了克服種間差異,明確細胞對損傷的特異性反應,上皮細胞培養模型已被廣泛使用。這些培養方式下的損傷修復模型對損傷修復過程的理解具有重要影響。
3.1 氣道上皮單層細胞培養損傷修復模型 目前主要的細胞培養方式是單層細胞培養,即常規培養皿培養[28]。使用細胞培養單層損傷試驗有諸多優點,如這種培養方式相對簡單易行;細胞選擇多樣,既可以選擇細胞系,亦可選擇原代上皮細胞;連續動態觀察細胞在損傷修復不同時段的表現。人們利用這種培養方式獲得了許多氣道上皮損傷修復的信息。
通過上皮細胞的單層培養損傷修復模型,人們發現哮喘上皮細胞存在損傷修復缺陷,即上皮缺陷假說,上皮的這種缺陷會在哮喘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29]。多項實驗證實,損傷后的上皮細胞中,多種炎性細胞因子、尤其是Th2相關細胞因子表達異常,說明上皮細胞的損傷會引起一系列哮喘相關炎性反應,而這些炎性反應也被認為是哮喘的重要驅動因素。在這個模型中,人們還發現,Th2相關細胞因子會對細胞損傷修復產生影響。關于這種影響,學界還存在許多爭議,用Th2相關細胞因子在不同濃度和不同時段刺激上皮細胞,會對損傷修復產生促進、抑制、甚至是濃度依賴的雙重作用。Th1相關細胞因子對損傷修復的影響則與Th2相關細胞因子相反[4]。單層培養損傷修復模型為研究上皮細胞損傷修復與哮喘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可能,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哮喘的發生發展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一問題仍是現今的研究熱點。
另外,通過單層細胞培養,人們發現上皮細胞的擴散和遷移依賴于纖維連接蛋白及整合素介導的細胞間相互作用。還有研究使用支氣管上皮細胞系(1HAEo-)體外模型發現,在正常損傷修復過程中,mRNA的表達在不同時間點受到不同調節[23]。但這些研究也顯示,細胞系和原代細胞培養在損傷修復時間上的差異,1HAEo-細胞系在24 h內愈合,而相同條件下,原代細胞培養至少需要48 h才能愈合[30]。
3.2 氣道上皮細胞氣液平面培養損傷修復模型 單層細胞培養解決了許多關于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細胞損傷修復的問題,但人體內的支氣管上皮細胞時刻暴露在空氣中,與空氣只相隔細胞表面的黏液毯。而單層細胞培養過程中,上皮細胞浸泡于培養基中,與空氣沒有接觸,細胞沒有明顯極性,與體內細胞有很大區別。常規的培養皿無法做到既提供細胞所需的養分,又保證細胞接觸外界空氣。如果要研究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的真實狀態,就需要開發更接近人體內狀態的損傷修復模型。借助腫瘤侵襲研究中常用的transwell小室培養板,人們研發出了氣液平面(air-liquid interface, ALI) 培養方式[31]。在transwell培養板的下層放置培養基,細胞培養于上層transwell小室的半透膜上,培養基可以通過transwell小室的半透膜達到細胞下部,這樣既保證細胞所需養分,又能使細胞上表面暴露于空氣,細胞自身分泌的黏液分布于細胞與空氣之間,形成類似于人體內支氣管上皮細胞上的黏液毯。
通過此模型,人們發現哮喘患者分化良好的上皮細胞與單層細胞不同。ALI細胞培養模式會在很大程度上模擬人體內情況,培養的細胞會處于極化狀態,多數實驗通常選擇培養4周左右的時間,細胞的上層會分化出纖毛[10-11,32]。Wenzel實驗室發現,支氣管上皮細胞培養至第7天即呈現極化狀態,細胞表面出現纖毛,細胞呈現復層生長,這也大大縮短了觀察時間,提高了實驗效率[33]。而且研究也發現,ALI培養狀態下細胞間連接形成[32],以此研究細胞間相互作用對損傷修復的影響。
但ALI培養也有其局限性,在ALI培養狀態下,除去培養皿底,光線還需穿過小室半透膜、底層培養基才能達到物鏡,即倒置顯微鏡很難觀察到細胞。小室的上部框架使得正置顯微鏡的物鏡也無法貼近細胞。如何更好地利用ALI培養方式觀察細胞損傷修復過程有待進一步研究。
3.3 氣道上皮損傷修復研究的其他模型 技術的進步和跨學科研究帶來了更多創新的模型開發。鼻息肉組織原代上皮二維培養被用于氣道創傷修復的細胞力學研究,人們還開發出原位支氣管黏膜組織的機械損傷模型和三維體外/硅創傷修復模型[34-35]。其中肺泡上皮創傷修復的硅膠模型可以模擬細胞培養的損傷修復模式[36]。另外,體外上皮損傷修復的數學模型也為創傷修復和細胞生物學領域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工具。
4 小 結
綜上,有效的氣道上皮損傷修復對維持氣道環境穩態至關重要。細胞損傷修復過程的不同是在健康氣道上皮和哮喘氣道上皮的重要差別。各種創新的模型正在更加深入地研究氣道上皮損傷修復與哮喘發生發展的關系,為哮喘的治療尋找新的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