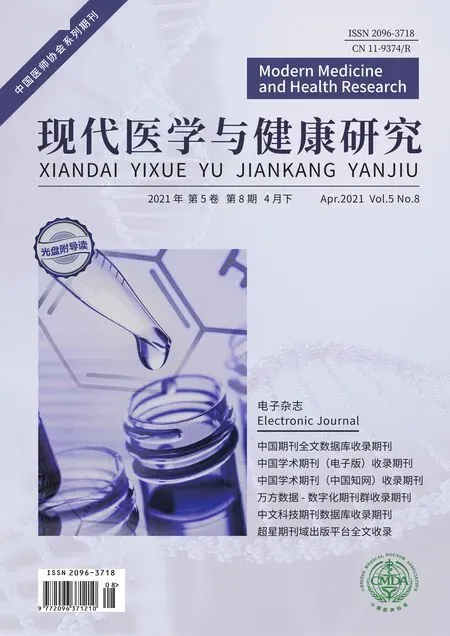藥物性膽汁淤積型肝損傷的研究進展
馮 紅
(遵義市播州區人民醫院藥劑科,貴州 遵義 563100)
膽汁淤積型肝損傷是藥物性肝損傷的主要表現形式,膽汁淤積型肝損傷病理可見淤膽、膽管增生、肝細胞壞死、炎癥浸潤、羽毛樣變性及脂肪變性等,嚴重者可發展為纖維化、肝硬化、肝腫瘤甚至肝衰竭[1]。膽汁酸是膽汁的重要成分之一,參與人體膽固醇、脂質、糖類代謝,肝臟是膽汁酸合成和轉運的主要場合,其平衡紊亂會導致肝內膽汁淤積,并且膽汁酸毒性與其親水性及疏水性等特點有關[2]。藥物性膽汁淤積型肝損傷機制復雜,膽汁酸組分研究已成為膽汁淤積型肝損傷機制研究的熱點。本研究對膽汁酸組分變化與藥物性膽汁淤積的關系進行綜述,以期為藥物性肝損傷的診斷與處理提供參考,現綜述如下。
1 膽汁酸合成、轉運
膽汁由膽固醇在肝臟轉化而來,不僅可以促進脂類物質的消化和吸收,還可以促進體內毒素和代謝物的排出。膽汁酸按類型可分為游離膽汁酸和結合型膽汁酸,按來源可分成初級膽汁酸和次級膽汁酸。常見游離型膽汁酸有膽酸(CA)、去氧膽酸(DCA)、鵝去氧膽酸(CDCA)等;常見結合型膽汁酸有甘氨膽酸(GCA)、牛磺膽酸(TCA)、甘氨鵝去氧膽酸(GCDCA)等。在膽汁酸核受體法尼酯X受體(FXR)的參與下,在經典途徑膽固醇7-羥化酶(CYP7A1)、甾醇12α羥化酶(CYP8B1)及替代途徑甾醇-27-羥化酶(CYP27A1)、氧固醇7α-羥化酶(CYP7B1)的催化下,膽汁會形成初級膽汁酸,在膽汁酸結合酶(BAAT、BACS)的作用下與牛磺酸或甘氨酸結合形成結合型膽汁酸[3]。
已形成的膽汁酸主要經以下過程轉運:①通過位于毛細膽管膜側膽酸轉運體(Bsep、Mdr2、Mrp2)將膽汁酸轉運至毛細膽管腔中;②進食后,膽汁酸排入至腸道,在腸道菌群的作用下轉化成次級膽汁酸;③在基底外側膜上轉運體作用下,次級膽汁酸和部分初級膽汁酸重新進入肝細胞,使有限的膽汁酸得以充分利用,滿足機體需求[4]。上述任何環節障礙均可能導致膽汁酸在體內的蓄積,最終導致膽汁淤積型肝損傷,嚴重者可發展為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甚至腫瘤。
2 膽汁酸組分特征
2.1 膽汁酸組分與膽汁酸核受體FXR關系膽汁酸穩態調節主要有FXR、孕烷X受體(PXR)、組成型雄甾烷受體(CAR)、維生素D受體(VDR)及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α(PPAR-α),其中FXR為關注熱點,激活FXR可通過蛋白酪氨酸磷酸酶(SHP)依賴或非依賴方式抑制合成酶CYP 7 A1、CYP 27 A1等的表達,從而減少膽汁酸的合成,此外,激活的FXR可促進膽汁酸解毒酶(CYP 3 A11、CYP 2 B10、UGTs、SULTs)和 BACS、BAAT的表達,從而減輕膽汁酸的蓄積并降低游離膽汁酸的濃度,改變膽汁酸構成比[5]。抑制FXR會導致靶基因膽鹽輸出泵(BSEP)、膽汁酸輔酶A合酶(BACS)等下調,造成膽汁酸合成紊亂,減少結合型膽汁酸合成,增加牛黃-β-鼠膽酸/牛黃膽酸(T-βMCA/TCA)比例等,導致膽汁淤積性肝損傷。FXR變化可導致膽汁酸組分改變,反之,膽汁酸也可引起FXR變化[6]。膽汁酸為FXR的天然配體,但不同膽汁酸對FXR激活水平存在差異,激活力依次為:CDCA>DCA>石膽酸(LCA)>CA,且相應甘氨酸和牛磺酸結合物也顯示出FXR激動作用,而熊去氧膽酸(UDCA)和α/βMCA對FXR影響較小或沒有影響。
2.2 膽汁酸組分毒性膽汁淤積是指膽汁分泌或排泄障礙,導致膽汁在肝內和體循環內過度堆積,通常由最初的炎癥表現逐漸發展為纖維化、肝壞死、肝硬化等病變。疏水性膽汁酸通過介導炎性因子的表達,激活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途徑誘導蛋白激酶,擾亂膽汁酸平衡[7]。膽汁酸組分存在物種間差異,人類主要以CA、CDCA及甘氨酸結合膽汁酸為主。目前膽汁酸毒性大小報道為:游離膽汁酸>甘氨酸結合型膽汁酸>牛磺酸結合型膽汁酸;游離型膽汁酸毒性大小為:LCA>DCA>CDCA>CA>UDCA;牛磺酸結合型膽汁酸毒性大小為:TDCA>牛磺鵝去氧膽酸(TCDCA)>TCA>牛磺熊去氧膽酸(TUDCA)>T-βMCA;甘氨酸結合型膽汁酸毒性大小尚無報道。膽汁酸毒性不僅與其結構、種類有關,還與膽汁酸濃度有關。低毒性的牛磺酸結合型膽汁酸在肝臟中主要由膽鹽轉運因子BSEP轉運,抑制BSEP功能會減少牛磺酸結合型膽汁酸外排并導致其在肝細胞內蓄積,從而產生肝毒性,但BSEP對膽汁酸的親和力也存在差異[8]。牛磺酸結合型膽汁酸再攝取主要經攝入轉運體牛黃膽酸鈉轉運蛋白(NTCP)調節,受損的NTCP會阻礙結合型膽汁酸的再攝取,破壞膽汁酸循環和肝細胞中膽汁酸的平衡,從而導致肝毒性[9]。
2.3 膽汁酸誘導肝損傷的主要途徑膽汁酸誘導肝細胞損傷不僅與膽汁酸結構有關,還和膽汁酸濃度有關[10]。疏水性膽汁酸在低濃度(≤?100 μmol/L)時會引起肝細胞凋亡,在高濃度(≥?250 μmol/L)時會直接損傷肝細胞膜,最終造成肝細胞損傷。LCA是目前已報道的毒性最強的膽汁酸,體內實驗表明LCA導致直接肝毒性,表現為肝細胞大面積壞死,基本不受中性粒細胞的影響,常用于藥物性膽汁淤積模型造模[11]。疏水性膽汁酸為炎癥刺激劑,經過促進炎性因子的表達,導致肝細胞炎癥,并可改變線粒體膜的通透性損傷肝細胞。DCA可誘導氧自由基的生成,耗竭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TP),改變線粒體通透性,促進人源誘導型肝樣細胞的凋亡和壞死。
3 藥物性膽汁淤積特點
藥物性膽汁淤積分為急性和慢性膽汁淤積,發生率較高,危害較為嚴重,并且以中藥所致膽汁淤積型肝損傷居多。目前尚無特異性診斷指標,部分患者表現為厭油、納差、黃疸、乏力、皮膚瘙癢等,亦有部分患者無明顯癥狀,在臨床上易被忽視。目前臨床主要參考《2019年歐洲肝病學會臨床實踐指南:藥物性肝損傷》[12]中的相關標準來診斷膽汁淤積型肝損傷,同時還結合血清生化指標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天冬氨酸轉移酶(AST)、總膽紅素(Tbil)及總膽汁酸(TBA)的改變進行判斷。
藥物所致膽汁淤積型肝損傷中可見膽汁酸組分增加,但并不一定是毒性較大的膽汁酸變化所致,且該類型肝損傷存在代償現象,膽汁酸組分呈動態變化,機體受損后血清生化指標會逐漸恢復。如在α-萘異硫氰酸酯(ANIT)膽汁淤積模型中,給藥后第1周肝損傷指標水平達到最高,第4周開始逐漸下降,同期病理由細胞腫脹、壞死、炎性細胞浸潤、膽管上皮細胞增生等轉變為肝細胞結構基本恢復,偶有炎性細胞滲出,纖維化逐漸加重現象,但第4周可檢測到的膽汁酸種類較第1周增加,此外,藥物性膽汁淤積中,常伴隨膽汁酸核受體FXR、外排轉運體以及膽汁酸解毒酶等的減少,膽汁酸合成酶的表達增加[13]。膽汁酸譜可見膽汁酸如CA、TCA、TCDCA及T-βMCA等升高。
藥物性膽汁淤積以對癥治療為主,膽汁酸轉運體和信號傳導在膽汁淤積治療中具有重要意義。次級膽汁酸UDCA及其衍生物norUDCA通過激活膽汁酸轉運蛋白表達促進膽汁酸的排泄,緩解肝內膽汁淤積。UDCA是目前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用于治療膽汁淤積型肝損傷的唯一藥物。研究報道膽汁酸螯合劑對藥物膽汁淤積型肝損傷具有治療作用,其主要通過抑制腸道膽汁酸轉運體依賴性膽汁酸轉運體(ASBT),抑制膽汁酸腸道重新收,加快膽汁酸隨糞便排出,從而減輕膽汁酸在肝內蓄積[14]。FXR激動劑上調FXR及其靶標基因的表達,可加快膽汁流出,減輕肝臟膽汁負荷,抑制炎癥反應的發生,減少有毒膽汁酸含量,緩解肝損傷。
雖然引起膽汁淤積的藥物以中草藥居多,但部分中草藥具有治療或緩解藥物膽汁淤積型肝損傷的作用。赤芍單用可降低膽汁淤積患者血清ALT、AST等指標水平,并緩解皮膚瘙癢和肝臟腫大等癥狀;苦參和UDCA聯用可增強膽汁淤積治療效果;積雪草酸通過抑制肝細胞凋亡,可降低膽汁淤積炎性因子表達水平和血清生化指標,減少肝組織膠原纖維等[15]。
4 膽汁酸組分變化在藥物膽汁淤積性肝損傷診斷中的應用
4.1 藥物膽汁淤積性肝損傷診斷現狀肝損傷診斷“金標準”ALT缺乏特異性,其在肝實質細胞損傷后才釋放入血,無法滿足臨床早期診斷的需求[16]。尋找肝損傷新型診斷標志物已成為等待解決的問題,近年來,新型生物標志物如TBA、乳酸脫氫酶(LDH)、谷胱甘肽-S-轉移酶A(GSTA)在臨床上已得到廣泛應用。研究發現血紅素加氧酶1(HMOX1)、膽汁酸轉運體Oatp、早期生長反應蛋白-1(Egr-1)、白介素-17(IL-17)等可作為肝損傷早期診斷的標志物,但臨床應用價值尚需廣泛驗證[17]。
4.2 膽汁酸組分變化與藥物膽汁淤積性肝損傷診斷膽汁酸譜的改變可能早于血清生化改變,可作為評價藥物性肝損傷的指標。體液中膽汁酸譜,即結合型膽汁酸含量和游離型膽汁酸含量變化或兩者相對比例的變化與肝損傷的發生有密切聯系。膽汁酸種類繁多,且存在種屬差異,動物和人類膽汁酸構成比存在差異,加之可致膽汁淤積型肝損傷的藥物較多,目前尚無具體某種或幾種膽汁酸變化作為藥物膽汁淤積性肝損傷診斷的標準,實驗研究中主要與空白組或健康組進行對照作為判斷依據[18]。可作為診斷標志物的膽汁酸不全是目前報道中毒性大的膽汁酸如LCA等,也可能是毒性較小的牛磺酸結合型膽汁酸。
ANIT所致膽汁淤積型肝損傷模型中,血漿膽汁酸譜的變化早于生化指標的變化,其變化主要表現為結合型膽汁酸含量增加,并且以三羧酸循環(TCA)增加最為明顯。膽汁酸譜的變化與給藥時間密切相關,呈動態水平,有學者報道給藥8周時試驗組患者肝臟中T-αMCA、T-βMCA含量較正常組顯著增加,而血清膽汁酸無明顯變化,但12周時血清膽汁酸出現顯著變化的膽汁酸種類增加,如GCA、GCDCA等,同時血清中初級和次級膽汁酸如CA、CDCA、TCA等較正常組顯著增加[19]。
膽汁酸譜的變化對人類肝臟疾病和肝損傷診斷也具有重要意義,賀曉立等[20]通過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UPLC-MS)檢測不同年齡、不同性別肝病患者和健康患者血清膽汁酸組分,結果顯示GCA、GCDCA、CDCA及TCDCA在肝病患者中較健康檢查者中顯著增加,具有作為診斷肝損傷的潛力。陳陽等[21]對肝硬化患者和健康檢查者血清膽汁酸譜分析顯示,肝硬化患者血清中TCA、GCA增幅變化最大,LCA、GCDCA、TDCA與健康檢查者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5 小結與展望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們對健康的重視程度逐漸增加,中草藥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但中草藥在預防和治療疾病的同時具有較高的肝損傷發生率,并且因肝損傷缺乏臨床特異性診斷指標,往往會使患者錯過最佳治療時間,導致預后較差。藥物性肝損傷的診斷已成為藥物安全應用的一大難題,探索其診斷標志物也已成為研究熱點。蛋白組學、基因組學等顯示新的標志物可作為藥物性肝損傷的診斷指標,但缺乏臨床診斷證據,尚不能得到廣泛應用。隨著超UPLC-MS技術的發展,利用該技術研究藥物肝損傷模型中膽汁酸組分的改變以尋找新的診斷標志物的研究不斷增加。藥物肝損傷動物模型中顯示膽汁酸組分變化與傳統的診斷標志物一致,可作為診斷標志物。
臨床肝病患者中膽汁酸組分與健康檢查者相比有明顯差異,但動物模型可能無法完全復制人類膽汁淤積,因此,藥物性膽汁淤積模型中膽汁酸組分改變作為診斷的生物標志物可能還需要加大樣本量進行實驗研究,同時還需臨床實驗的證實。